- +1
德里达:文学是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可以是保守秘密的权利 | 纯粹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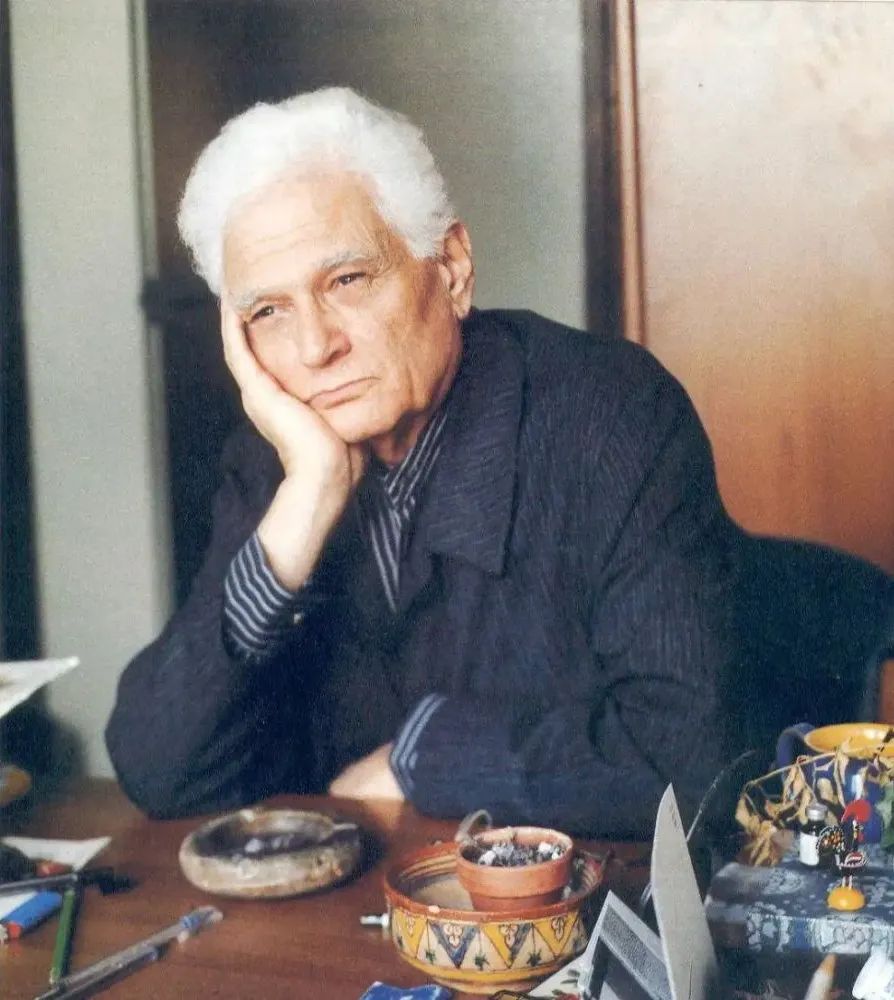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德里达与解构策略
文/陈永国
在《德里达的遗产》一文中,J.希利斯·米勒提出的问题是:德里达去世了,我们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这里的“遗产”当然指的是文化遗产,是他的全部著作,他的所想和所写,也就是可以用“德里达”这个名字称呼的单一个体的“全集”。所谓“处理”当然不是变卖,而是关乎其能否得到继承,能否得到正确的理解或“正确地占用”的问题。这是德里达在生前就曾经担心并在若干重要场合和后期几部著作中详尽讨论过的问题(其实也是米勒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他自己说从不在乎死亡和死之后别人会如何对待他的“遗产”)。现在,德里达已经去世近三年了,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产”呢?实际上,“处理”还为时过早,我们所面对的应该是如何整理他的遗产问题。本文试图简要梳理德里达的文学理论遗产,即他的文学批评解构策略。
一、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
在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解构”这个问题。德里达认为,应该首先把“解构”看作一种“分析”,分析的客体是“积淀起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话语因素,即我们用以思考事物的哲学话语性”。在继续描述这个分析客体时,德里达说这个“哲学话语性”就是“思想的话语性”,是“我们”实际上进行操作的结构,它是通过语言发生的,因此与哲学史相关,也与整个西方文化相关。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德里达的批评理论中,语言并不就是一切。
对德里达来说,语言是理性的,是他解构的对象,但当质疑西方哲学传统的时候,当挑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候,当把柏拉图、海德格尔和马拉美拿来作为分析客体而证明某种不可能性的时候,他也必须使用同一种理性的语言。没有人能够摆脱语言的牢笼,没有人能够在语言之外达到解构语言本身的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在摆脱理性语言的情况下去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这也是他生前就力图澄清的一个误解。在德里达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解构”不过是他使用的一系列关键词中的一个。早在1982年“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不愿意使用“解构”这个标签或不喜欢人们给予“解构”以种种特权,其实他所暗示的或许是“解构”这两个字不可能概括他的全部思想,不可能总结或“再现”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解构“是对不可能的事物的一次经验”,“承认解构是不可能的并不失去解构的任何意义”。
实际上,德里达的“解构”所要破解、分析和对抗的恰恰是“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结构主义语言观⑤。解构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对抗”,“对抗语言学的权威,对抗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权威”。本杰明认为这种对抗的立场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一种批评形式,对抗就是拒绝接受,而拒绝接受的对象是一种占主导的语言观,传统上语言与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第二个是拒绝接受传统在对抗的客体与对抗的立场之间拉开的距离,从而打开了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其意义在于它含蓄地承认没有外部,所以,构成所对抗传统的一部分的语言和术语就成了参与和发明的场所”。这意味着所对抗的传统并没有被消除,而成了一个新的发明的空间、行动的空间,或者说是介入的空间。
最后,场所的这种不可消除性就是解构的部分定义。解构始终是一种介入形式,一个参与的策略,“解构不是用来发现抵制系统的方法的;相反,它包括对文本的重讲、阅读和阐释,使哲学家能够建立系统的东西不过是某种功能失调或‘失调’,无能封闭系统的表现。无论在哪里,当我采用这个研究方法时,都是要展示某系统不发生作用,而这种功能失调不仅颠覆了系统,而且本身激起了对系统的欲望,是从这种脱臼或失调中汲取生命”。如此说来,“解构”就是通过重读、重讲和重新阐释发现某一系统内的功能失调,功能失调的场所恰恰是这个系统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生机的地方,可以从事新的发明的空间,也是产生新的可能性的希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也是一种重构、重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只不过它所重构、重写和肯定的系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具有单一性、特殊性。因为不同系统的“功能失调”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同一系统在不同时间的“功能失调”也是不同的,因此重构和重写的结果也不同。于是又可以说,“解构”不是方法,不是工具,不是简单地把分析客体从属于某种机械的操作。“解构”是一种策略。
最后的言者:为了保罗·策兰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法]莫里斯·布朗肖 等 著
张博 潘博 丁苗 等 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6
作为策略,“解构”具有使用的灵活性、定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多元性。正因如此,德里达才说“‘解构是X’或‘解构不是X’所有这类句子都先验地误解了解构的要义”。“解构”的要义在于解构的过程所展示的生存困境,一种双重束缚,即在可能性中看到的不可能性,或相反,在不可能性中看到的可能性的希望。“解构”打开了无限重复的一个空间,使作为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质疑的空间,在对抗的过程中予以肯定的并在封闭时马上开放的一个空间。“它是行动的场所,因此也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场所”。
二、作为语言之重要特征的重复
米勒帮助澄清了过去对德里达的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他的“解构”不是关于语言的思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关系,与“语言学转向”没有关系,因此不提倡“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绝对语言观和文本观。在语言与文本之间,德里达看重的是文本,而文本指的不是语言,不是语言结构,而是文字和文字的结构。最终,语言是通过文字结构而被理解和发生作用的,这是形而上学时代的一个历史必然。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说,“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问题,但它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侵入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的全球景观中来”。“(语言)仿佛不顾自身地表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的时代最终将把语言确定为它的总体问题的视野……语言本身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它已不再是自信的,平静的,不再受到似乎超越它的无限所指的担保”。语言何以受到威胁?是什么威胁了语言?文字的出现颠覆了言语的君主地位,打破了语言的逻各斯即语音中心主义,摧毁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认定的那个纯知性的秩序,即语言符号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能指与一个可理解的所指之间的统一。然而,德里达证明,这样一个纯知性的秩序根本不存在,理想的、一看就懂的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文字本身的重复性宣告了符号的神学时代的结束,由于这种重复性,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成了地位平等的交流形式:书面语言(文字)不再是派生的了,口头语言也不再由于其直接性而凌驾于文字之上了,二者都可以在接受者或说话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言语和文字一样也是可重复的记号。对如此理解的语言交流的一个必然发现是:凡是有语言交流的地方,就必然有误解(误读);没有误解,就不可能有交流,因为记号(语言符号)的重复决定了意义的不确定性。
然而,这种重复性却也决定了文字的可读性,决定了口头语言的可理解性(这在电话、录音机、视频聊天的时代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语言的生产者的缺场:作者和说话者的缺场。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可以在其生产者缺场的情况下发生作用,这正是语言的主要特征,又由于这是文字或语音的重复性造成的,所以重复性就成了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它的基本条件是:文字要想成为文字,即成为一种可重复的记号,就必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消失的情况下正常发挥作用,即被阅读,或在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不在场时仍被阅读。换言之,当信息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作为信息的语言(书面的和口头的)都应该具有在逻辑上仍然能被阅读的可能性,而当经验上可确定的发送者或接受者不在场时,结构上不可重读的、不可重复的信息就不是语言交流的记号。
这种重复性也是“事件”得以交流的惟一条件。就结构而言,“事件”就像一个词,或一个文本,是可重复的。因为可以对“事件”单独加以阐释、讨论、讲述或重讲,而每一次重讲或重复都是一次增补。在述行的意义上都是与原事件相关的另一次“事件”,都在差异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事件的属性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的“书写”或“文字”就不纯粹是人们所误解的“纯文本”,而成了具有历史内涵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其重复性而言,作为事件的书写必须脱离原作者才能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才能成为它应该成为的语言的记号,就是说,话一出口就具有了被重复的特征,就脱离了说话者而面临着多次的增补和重复,也就是对所说的话的“绝对的重新占用”。由此可知,任何符号系统都不能只被一次使用,任何话语或书写事件都不能不被重复,而在理论上,只被一个人说过的话而不被重复就不能算作语言的记号。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著者:[德]保罗·策兰 王家新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1-06
这种重复或被重新占用就是“踪迹”作用的方式。“踪迹”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相区别从而使符号具有意义的一个因素。要理解一个符号的意义,首先必须承认或认出与这个符号相左的东西,然后将其抹去。这个被抹去的因素就是踪迹,没有它,语言作为差异系统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踪迹是意义得以产生的绝对源泉,但这样的源泉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踪迹都必然是另一个踪迹的踪迹,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要想在正常的语境中发挥符号的作用,就必须转换或被重复而改变其语义的或述行的价值,成为另一个语境。实际上,语言符号的踪迹是决定文学作品之“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作品边界的位移;绘画的“艺术性”取决于“画框”的位移;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经验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内部,而主要取决于作品的外部。外部渗透进来,决定了内部,而这个外部就是规定作品之单一性的习俗。
三、作为哲学研究之客体的文学
文学的存在就是要证明一种单一性,一种在哲学思想发生之前就存在的东西。这不是说文学先于哲学而存在,也不是说哲学研究必以文学为无条件的客体或惟一的客体,而是说文学是德里达哲学研究的最重要客体之一:“我最长久的兴趣,应该说甚至先于我的哲学兴趣,如果这可能的话,始终是趋向于文学的,趋向于那种称作文学的写作。”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才有一个被误读的德里达。罗蒂认为德里达是文学的哲学家,因此不是规范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哲学看作一种写作,而不遵守哲学的规则。哈贝马斯也认为德里达“出于文学的、美学的或毫无根基的决定而放弃了真理的标准和判断”,即为了刻意的“书写”而放弃了“活的语境”,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没有认识到交往的理性。米勒则认为,无论怎么看待德里达,都必须首先把他看作“20世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行为”见于他的全部著述,贯穿他的整个哲学和理论的写作生涯。米勒进一步分析说,德里达对文学始终如一的兴趣并不是为了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而是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坚持语言的“重复性”,从而解构文学与哲学由来已久的对立关系。“对德里达来说,文学能够在无数的语境中重复任何话语、文字或标志,而且能够在缺少明确的说话者、语境、指涉或听者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实际上,这种重复也正是文学所要证实的那种单一性。
一般认为,这种单一性就是哲学和文学相互区别的地方,而实则不然。不妨说,文学是用语言构成的东西,是以各种样式或体裁虚构的东西,正因如此,文学才似乎与哲学划清了界限——哲学探讨的是真理,它研究的客体是真实的世界,是实际存在,对立于虚构和虚假的东西,因此也对立于作为虚构之结果的文学。然而,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但不等于不存在,虚构是存在的,不然就不能对立于真实。哲学探讨的是原始的真理,文学探讨的是“超越真理的真理”,即超越哲学真理的真理。文学的确是虚构的,这种虚构含有真实或至少是源于真实的成分,也有纯粹虚假的成分,但决不缺少真理。对德里达来说,文学不是可以拿在手里阅读的一本书,也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某种再现。文学创造自己的语境,发明自己的环境、事件或赖以存在的条件。它不去挖掘潜藏在某一文本内部的本质,而是用文字、词语、声音、踪迹、言语行为等建构一种单一性、偶然性、意外事件,从而使思想成为可能。它不再现外部存在或超验现实,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声音呼唤人们去思考书写、文本性和互文性,去思考引语、重复、界限、隔膜、存在与非存在,去思考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法律、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揭示的东西必然成为哲学思考的条件,文学所描写的东西必然是已经留下了踪迹的经验,文学所陈述的东西也必然是抵制我们阅读的东西。在德里达看来,完全可读的东西不具有文学的单一性。不可读性、不可译性或完全他性才是文学的根本。
声音与现象
作者: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杜小真 译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10-10
正是在这里,德里达看到了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共同点,同时也消解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文学之所以具有文学性,是因为它具备语言的最典型特征——重复,而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延宕造成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之成为异质的、不透明的、不断延异的缕缕踪迹。所以,文学的文学性存在于文本之中,存在于书写文本的人的精神之中,也存在于书写的行为之中。这样的文本反映的不是人的原始感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所用的言语也不是作者或其文本所特有的,而具有历史性,受制于制度和习俗,也因此而拥有了说一切话的权利。在德里达看来,哲学是通过对文学的“模仿”才确立了哲学思辨的优越地位。用来讨论文学的一切话语,都可以用来讨论哲学,因为和文学一样,哲学也是一种书写,它本质上具备文学的全部结构。文学的书写反映真理,哲学的书写陈述真理。然而,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哲学中,总有无法接近的真理,总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总有意义的无限延宕或生成。如果说文学中的重复是创造场景、环境和事件,那么,哲学中的重复就是创造概念,能够重复的、可证实的、超越其具体现实而揭示真理的概念。
所以,文学和哲学一样,也不是模仿的艺术。德里达讨论的柏拉图的“药”和马拉美的“模仿”就力图从哲学和文学两方面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模仿论。“模仿既是艺术的生,也是艺术的死”。在自然与艺术的等级制中,柏拉图的模仿论把艺术的模仿排在第三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把艺术的模仿排在了第二等,但无论如何,二者都设定了一个先于符号而存在的理式,一个有待模仿的自然。这个理式、这个自然也就是艺术家如实描写、如实反映的真理。然而,德里达认为这种先于符号的“世界”并不存在,纯粹的感知并不存在,所揭示的“现实”也不存在。我们所知的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符号污染了现象的原生态,符号创造了自己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创作)的主体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系统”,由精神、社会、世界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马拉美的“模仿”从文学的角度证明了模仿的客体的模糊性,呈现了文本镜像的生成游戏,展示了“模仿”本身在书写过程中的空间生产。它所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是:模仿者最终没有模仿的对象,能指最终没有所指,符号最终也没有指涉。模仿、能指和符号最终都是用来理解真理的工具。
《柏拉图的药》讨论的是希腊术语pharmakon(药)的翻译问题,分析了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即从翻译问题入手进入哲学的探讨,指出该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良药和毒药),从而反驳了苏格拉底高扬言语(对话)而对书写(文字)的攻击。在德里达看来,翻译起源于翻译或任何可译的命题。一方面,翻译的可行性取决于意义的确定性,而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真理和意义,所以,在翻译无法进行的地方,哲学也必然陷入死胡同;另一方面,哲学有自己具体的语境。西方哲学有史以来始终以希腊哲学为基础,使用的大部分是希腊哲学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希腊哲学这个语境,pharmakon的意义不确定性问题就出现了,给异质性或他性留下了缝隙。因此,与文学一样,哲学的语境不可能是封闭的,而必然是向另一种语境敞开从而创造出新的语境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哲学的阅读和理解就如同文学的阅读和理解一样是以播撒为形式的。播撒不是意义的丢失,而是无穷的替代、增补和肯定,是片断的、多元的、分散的,一句话,是文本意义的生产。
四、作为言语行为的文学
德里达在学术生涯的中期就开始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问题。米勒认为要了解德里达如何定义文学,捷径是理解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ABC有限公司》等著述中最早提出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是针对J.L.奥斯丁对戏剧独白等文学言语的排斥而提出来的。如上所述,在德里达这里,重复性是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因此也是文学语言的最重要特征。一方面,重复是语言借以使自身脱离现实的语境而进入虚构空间的手段;另一方面,重复又是文学借以使自身脱离虚构空间而进入民主的空间、自由的空间以及话语、符号和书写得以不断重复的一个空间的有效途径。这个从现实到虚构、再从虚构到现实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重复,而重复的结果既是述愿的又是述行的,既是阐述真理的又是可以促成具体行动的。这是德里达所说的真正的文学性:特定作家在特定社会中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用语言虚构的东西发生了特定的社会作用。正因如此,他才说文学的文学性不在文本之内,而在文本之外,也是他所说的文学文本的大门“向完全的他者敞开”的意思。这种文学性也以其他方式见诸政治、伦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文本,《文学的行为》一书通篇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书写与差异(上下)
作者: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张宁 译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1-09
按此理解,文学中的言语行为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独立的宣言或他者的发明”。这种言语行为是用词语和符号建构起来的形象、场景和环境,是内在印象和经验的具体化,因此是异质的、矛盾的,包含着言语与行为、逻辑与修辞、已知与未知、可见与不可见等二元对立的因素。作为美国的解构主义大师,米勒发展了德里达的文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阅读理论,不仅强调文学的述愿方面,而且强调文学的述行作用。这意味着,读者在建构文学文本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聚焦于文本的“言语”本身,理解其真正的意思,而是它的潜在意义,试图把它重构成新的东西,结果必然是言语向行为的转化,虚构空间向现实空间的转化,也即文学向社会的转化。通过伦理的和政治的阅读过程,这种转化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新事物的出现。这种文学批评不再把语言看作能指的聚合,不再聚焦于文本的结构和形式的分析,而着重于文学语言如何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进而创造新的社会生活范式的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里达发表了许多论纲式的小册子,讨论言语的述行概念,述行话语的实践,以及言语行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并将其与决策、行动、秘密、证据、好客、谅解、义务和责任等政治和伦理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德里达晚年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或文学研究在政治和伦理责任中的作用,言语行为在文学中的作用,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人文学科以及大学的未来。
在《无条件的大学》中,他说“文学是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可以是保守秘密的权利,哪怕是以虚构的形式”。他认为今天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人文学科,正面临着种种威胁,因此“要求无条件地说一切话的权利……也包括文学……”,“这种假定的在公共空间里说一切话的自由,是所谓人文学科所特有或独占的地方——对这样一个概念的定义还要加以精炼、解构和调整,使之超越一个也需要锤炼的传统。然而,这个无条件的原则原本而且最突出地在人文学科中呈现出来。它占据一个本源的、特殊的位置,即在人文学科中表现、显示和保存的位置。它也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重新叙述的空间。所有这些都通过文学和语言(即被称为人的科学和文化的科学的学科)表现出来”。这或许是德里达终其一生研究文学进而研究哲学的宗旨,也是他利用“解构”进行的一次“策略性赌博”。如米勒所预测的:“如果他赢了这次策略性赌博,那么,这将意味着他的著作将改变所有世界规模的不同语境,这样,他的著作,虽说独特和个异,但却能在未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广泛的不同语境中取得述行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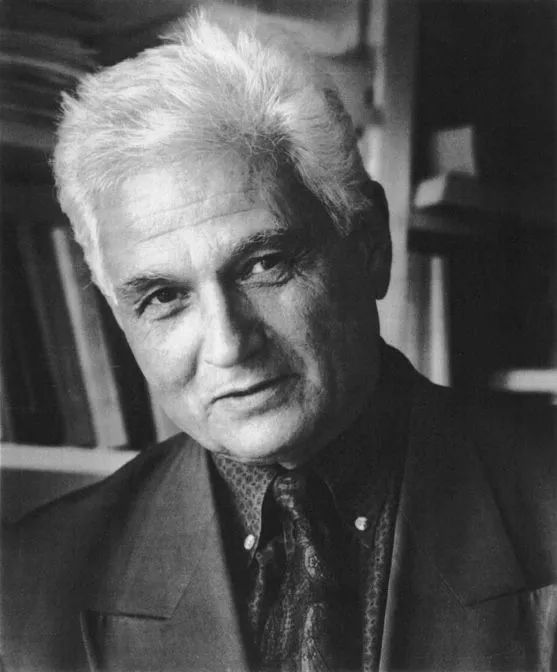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9岁时回法国就学,1956年至195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60年代成为《泰凯尔》杂志的核心人物。60年代末与该杂志分裂。后一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1983年起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研究主任,还是国际哲学学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法兰西公学院名誉教授。
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论文字学》(1967年)、《声音与现象》(1967年)、《书写与差异》(1967年)、《散播》(1972年)、《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年)、《丧钟》(1974)、《人的目的》(1980年)、《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1990),《马克思的幽灵》(1993)、《与勒维纳斯永别》(1997)、《文学行动》等。
原标题:《德里达:文学是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可以是保守秘密的权利 | 纯粹哲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