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楼巍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楼巍(章静绘)
维特根斯坦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每一个哲学研究者都绕不开的人物。而普通读者也往往听过一些来自他的著作的金句,或是了解一些他作为天才的怪癖。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楼巍长期从事维特根斯坦研究,著有《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注解》,译有《哲学研究》《论文化与价值》《蓝皮书和棕皮书》。他最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十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版),用十堂课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他谈到了语言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意义,以及维特根斯坦式的思考方法对我们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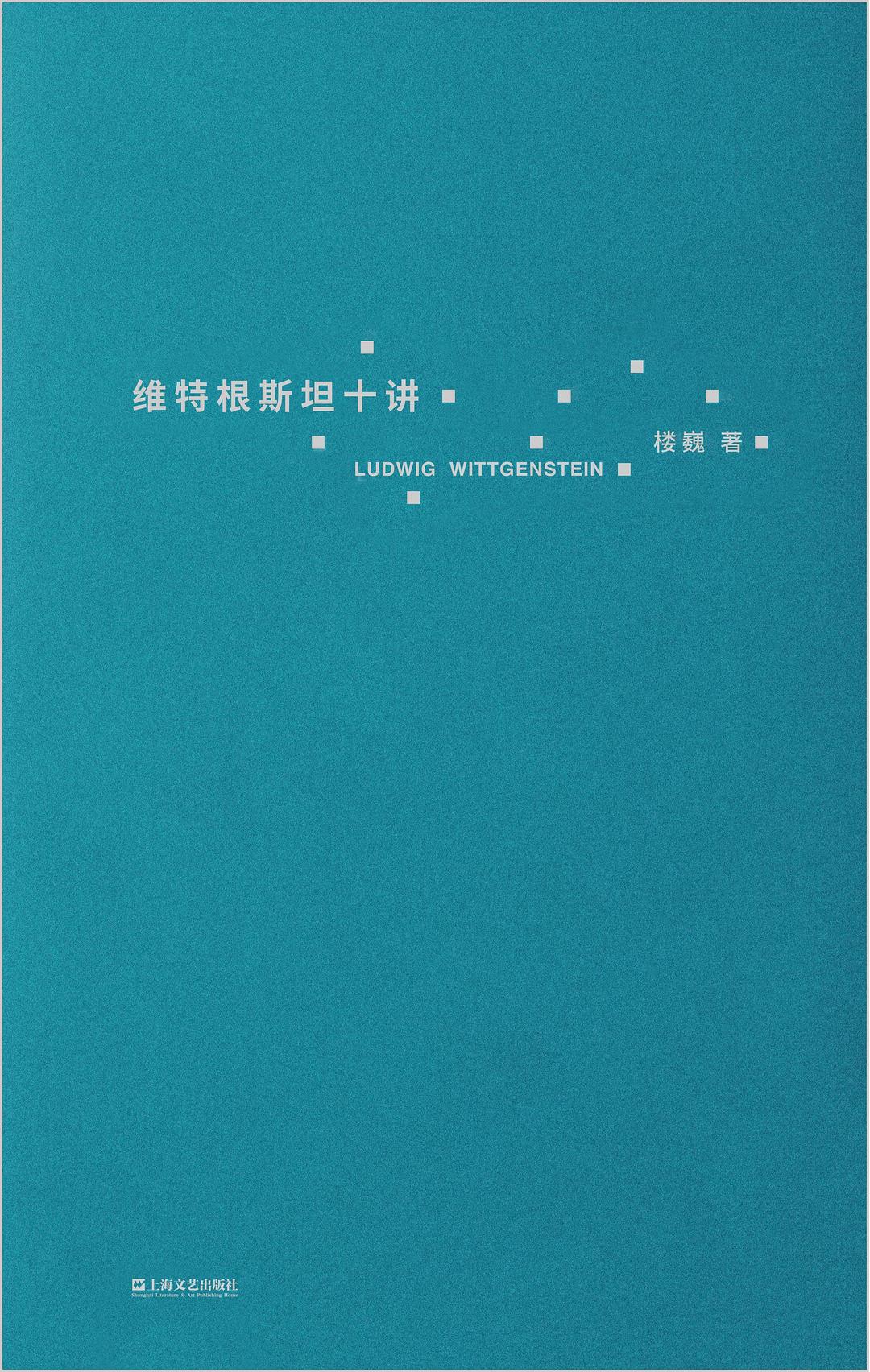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十讲》,楼巍著,光尘/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32页,68.00元

维特根斯坦
能否请您谈谈写这本书的缘起,以及维特根斯坦的现存著作是一个什么状况?
楼巍:我做维特根斯坦,平常都是跟研究者打交道,交换观点,相互商榷,时间久了,就想跳出研究者的小圈子,给大众写一本简明通俗、框架性地介绍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点的书。2013年,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书,给研究生讲维特根斯坦,每年大概十六次课,我挑了其中一部分,重写一遍,就有了这本《维特根斯坦十讲》。
说到维特根斯坦的现存著作,其实在他生前只出了一本《逻辑哲学论》,英文版出版于1922年,此外就是一篇名为《一些关于逻辑形式的评论》的文章。1951年,他去世之前,任命里斯为遗嘱执行人,安斯康姆和冯·赖特为其作品保管者,这三人都是与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冯·赖特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将维特根斯坦的作品存于何处,写于何时,内容为何,讲得很清楚。维特根斯坦除《逻辑哲学论》外的其他著作,都是在他去世之后,陆续由这些学生代为编辑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不喜欢写结构完整的长文章,总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段评论,这些评论构成了他的所有手稿。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他曾让打字员制作过一些打字稿,在此过程中又不停地对原内容加以修改和编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213号打字稿,即所谓的《大打字稿》。
编辑、整理维特根斯坦著作的过程是漫长的。首先出版的是最为成熟的《哲学研究》(1953),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维特根斯坦亲自编辑过,已经形成打字稿,明确想要出版的。之后,编者对剩下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编辑和整理。英国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十四本英德对照的维特根斯坦著作集,从最初的《哲学研究》,到最后的《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第二卷)》,中间间隔了四十年。除此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文集,一个是德国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八卷本德文版维特根斯坦《著作集》(Werkausgabe),另一个是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共同编辑推出的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著集》(Wittgenstein’s Nachlass: The 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包含了他全部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笔记,都转成了可以机读的电子格式,全部在网上公开。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卑尔根大学哲学系教授、维特根斯坦档案馆馆长皮奇勒(Alois Pichler)。这套电子文集对研究者而言虽然很有用,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过于专业了。
自从雷·蒙克那本传记《天才之为责任》中译本出版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维特根斯坦热”,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维特根斯坦作为天才的人生经历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的人生态度?
楼巍:我总结了维特根斯坦的四个精神特质。一、他对音乐和机械——也就是所谓的“钢琴与钢铁”——一生都很喜欢。二、他厌弃矫揉造作的人与事,例如不少哲学著作的文风。三、他对精神生活保有一种纯粹的热爱,愿意投身其中。四、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抱持一种批判和疏离的态度。理解了这四个精神特质,差不多就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全部人生。我在《维特根斯坦十讲》的第一讲“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中有详细讨论,可以参考。
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对不少哲学经典是不屑的,对哲学史也很漠然,他爱读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还喜欢侦探小说和侦探电影。他本人的阅读兴趣是怎样的?这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楼巍:像弗雷格、罗素这些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感兴趣的,读得也多。弗雷泽的《金枝》,很厚的大部头,他读得很仔细。你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作家,奥古斯丁、帕斯卡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他都爱读,他也读柏拉图。而黑格尔他从来就不喜欢——黑格尔让他抓狂。当然,像我们国内所提倡的,研究哲学先系统研究一遍哲学史,这个习惯维特根斯坦肯定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他喜欢从哲学根基处去把握问题。我们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观点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去的很多哲学其实是一种误解,例如,形而上学的命题其实就误解了语言的逻辑。笼统说来,他对很多的早期哲学都持这种否定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很多哲学是一种“哲学病”,正因如此,他对系统性地研究哲学史是不感兴趣的。
维特根斯坦曾经非常强烈地想要移民去苏联,这该怎么理解?
楼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时候曾经跟别人说,他自己内心深处是个左派。不过,他不是那种清谈式的沙龙左派,而是身体力行。他捐赠了所有的遗产,因为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偶然——因为偶然,他才成为一位大富翁的儿子。他追求的是一种必然性的人生,这种必然性在于,你只有对社会或者对某个共同体有贡献,你才能有一口饭吃。他去清苦的奥地利山区做小学老师、去修道院当园丁助理,就是想要通过劳动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资料。在他看来,当时的苏联就代表这种他认为符合必然性的生活,与他所厌恶的欧洲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不同的。
提倡逻辑实证主义、进行分析哲学研究的维也纳学派或维也纳学圈,受到《逻辑哲学论》很大的影响,不过维特根斯坦对他们的看法似乎比较微妙。我们该怎么理解?
楼巍:维也纳学派或维也纳学圈的成员中,像石里克和魏斯曼,维特根斯坦和他们的关系都是不错的,会定期一起讨论,魏斯曼也曾经写过一本与《逻辑哲学论》很像的书,试图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解释清楚,只是篇幅要厚很多。你想要去了解《逻辑哲学论》,看魏斯曼的书也挺有帮助的,相当于对维特根斯坦做了详细的展开,然后补充了很多论述,又改写了一部分内容。维也纳学派虽然有个宣言,其实更多像是一个松散的小圈子,很难说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学派,像纽拉特、卡尔纳普这些成员,思想都不太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提倡科学精神,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在他们看来说不清楚的东西——是嗤之以鼻的。相当程度上,他们是通过哲学来回应二十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的进展,像卡尔纳普就很明显,他的哲学是完全科学化、分析性的。
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是不太感冒的。就以石里克和魏斯曼为例,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两个人对《逻辑哲学论》只理解了一半。维特根斯坦确实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有意义的语言只能去言说世界中“可能的事实”。然而,在石里克和魏斯曼看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宗教、伦理和美这些不可言说的领域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这些领域不存在事实,所以没法言说——语言的功能就到此为止。按石里克和魏斯曼的想法,美、道德这些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就一下子给去掉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不喜欢维也纳学派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不可被经验验证的美和道德都是不重要的,而维特根斯坦恰好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语言的作用是有边界的,语言比较humble,它只能做它能做的事情,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恰恰是语言不可说的。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存在“早期维特根斯坦”与“晚期维特根斯坦”之分,现在又有人提出,还存在一个“转型中的维特根斯坦”,一下子制造出了三个维特根斯坦。对此,您怎么看?
楼巍:现在还有一个“最后阶段的维特根斯坦”,真要细究的话,维特根斯坦大概有五个。虽然很多人肯定不会同意,但是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只有一个——早期、中期、后期都是一样的。他自己跟学生说过,他的思想成型得很早,二十岁之后就没有再变过。对我而言,虽然维特根斯坦后来处理的问题与早期不一样,他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没有变化。读《逻辑哲学论》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很多层面上维特根斯坦那种很微妙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哲学研究》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逻辑哲学论》?它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之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楼巍:《逻辑哲学论》触及了很多弗雷格、罗素曾经研究过,但是没有解决,或者说在解决的时候遇到困难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逻辑哲学论》实际上很多内容是在回应罗素和弗雷格,但是,把这些哲学史的东西去掉,它自己的框架是:“语言是世界的图画。”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中可能的事态都包藏在语言之中。同样的道理,语言就被封闭在了一种跟世界的描画关系之中。既然被封闭在了这种描画关系中,很多东西都不可说了,它只能去言说世界中可能的事实。在这样一个语言系统之中,它有基本命题,有逻辑常项(比方说,“如果、那么”),然后借助这些逻辑的钩子,构造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语言系统。世界中可能的,语言中也是有意义的;世界中不可能的,语言中也是无意义的。理解了这个描画系统,你就会发现,伦理、审美和宗教领域不存在这种所谓的事实,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事实都是偶然如此的,其反面都是可能的,比如我是一个男的,这是个事实,但我也可以是个女的,这在逻辑上完全没问题,所以它是偶然的,而美学、宗教和伦理领域并没有什么事实(事实都可以有反面),比如“人不该作恶”的反面即“人应该作恶”,无论怎么说,都是不成立的。
以这样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宣布他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因为以前所有的哲学著作都在使用这样一种语言,按照他的想法,这种语言肯定是误解了语言的逻辑,或者说其实是无意义的语言。他认为,以前的哲学试图用语言去说宗教、伦理和美,而这些东西其实是无法言说的。
维特根斯坦说过,逻辑是思想的本质,然后您也提到,对早期维特根斯坦而言,逻辑是使思想、语言和世界处于完善的秩序之中的东西。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楼巍: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我试着简单表述一下。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说过,思想把它的法则同时颁布给了世界和语言——一股浓浓的德国哲学的味道。对他来说,语言就是思想的表达,思想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东西,语言是外在的、公然的东西。世界中可能的情况都是可以被思考的,所以,思想同时把它的法则颁布给了语言和世界,这样一来,就使得它们处在一种完善的秩序之中。这里“完善的秩序”其实是说,在语言中可能的东西,在世界中就可能,在世界中可能的东西,在语言中也就可能。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况都对应着一个有意义的语言,而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语言都对应着一种可能的情况。我们可以举开车为例,你在路上行车,左转是打一种转向灯,右转是打另一种转向灯,直行就不开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可能的情况了——你又不可能飞起来,对不对?这三种情况,在汽车转向灯这种表达系统中可以完善地得到表达,接下来不可能出现它不能表达的情况,因为交通规则早已规定好了,汽车转向灯的表达系统中只有左转灯、右转灯和不开灯这三种符号,然后这三种符号也只对应左转、右转与直行这三种情况,所以,它是一个完善的表达系统,不存在某种可能的情况,这个表达系统无法表达,或者表达系统表达了出来,汽车无法执行。实际上,语言和世界就处在这样一个关系之中,只是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
哲学史上存在一个从关注本体论到关注认识论再到关注语言的演变过程,维特根斯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楼巍:我书里引用了哈克(Peter Hacker),他是牛津大学教授、最有影响力的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诠释者之一。哈克评价说,维特根斯坦给了哲学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语言学方向。对符号和语言的重视,可能从罗素和弗雷格就开始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他甚至将整个世界都收纳在了语言之中——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这样说过:这个世界所有可能情况收纳在一套有意义的语言(基本命题的总和)以及它的相互组合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是哲学的语言转向最为关键的决定性人物 。
您提到,罗素想要理解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简直是绞尽脑汁。为什么对罗素这种大哲学家而言,理解维特根斯坦会那么困难?
楼巍:我始终觉得,罗素(以及弗雷格)无法理解《逻辑哲学论》,恰恰在于他们认为语言是没有界限的,语言应该是全能的(almighty),我难道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任何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吗?维特根斯坦恰好相反,他认为语言是有界限的。我隐约觉得这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最大区别,罗素对语言所抱持的想法是极为乐观的,而维特根斯坦则非常悲观——他们之间存在这种精神特性上的根本不同。很多人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恩怨很感兴趣,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恩怨,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很尊重,他对罗素的哲学观点批评很多,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我在第九讲中,总结了他们的哲学路线存在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说到这儿,让我想到您在《维特根斯坦十讲》的第九讲提到休谟的农场主问题,其中也涉及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批评,能请您展开讲讲吗?
楼巍:这涉及归纳的问题。比方说,你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如果有个人问你,你凭什么这么相信?其实你能给出唯一的回答是:因为以前太阳每天都升起。如果一个强烈的怀疑主义者问你:就算太阳以前每天都会升起,凭什么明天就会继续升起?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从今天到明天,你是没有一个跨越的通道的。这就是归纳的问题:你凭什么用一件事情以前经常发生来作为它接下来还会发生的根据呢?我们很容易设想它接下来不发生,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罗素对此的想法是,一件事情以前经常发生可以作为接下来发生的根据,他认为我们的语言游戏有一个理性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他的归纳原则(principle of induction)。维特根斯坦恰好相反,在我看来,罗素提出的归纳原则,简直被维特根斯坦驳斥得体无完肤。他认为,不需要为我们玩的语言游戏辩护,试图给它提供根据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我们为什么这么玩这个游戏?这些都不需要解释。我们之所以会说,一件事情过去一直发生,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发生,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是这样玩这个游戏而已。
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认为,语言游戏或者说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基础的,或者说不需要辩护和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解释语言也需要使用语言,那么,你怎么解释你用来解释的语言呢?他认为,用语言解释语言这种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条不归路,就相当于一条小狗自己追自己的尾巴一样,这是追不到的。
这就来到了一开始您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都提错了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对语言的误解。
楼巍: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你如果实在想这么玩哲学,那也可以,你就这么玩吧,只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严肃的哲学。所以他说过,哲学可以完全由笑话组成。你也可以把哲学当作一种脱口秀来玩玩。
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您吐槽说,大家不断地引用这句话,但是又不断地误会。对这句话的准确理解是什么?
楼巍:“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指向的是宗教、伦理和审美这些更高的领域,换而言之,它是有一个具体指向的,不是可以随便引用的。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无非就是,这些更高的领域,我们是无法言说的,语言能够处理的仅仅是语言范畴之内的东西,而《逻辑哲学论》就是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语言范畴之内。我觉得,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就好像一根结束了所有讨论的手指,它指向的是划定的语言范畴之外,那些不可说的、更高的领域。
前面聊了很多《逻辑哲学论》,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以及《蓝皮书和棕皮书》,您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以及《蓝皮书和棕皮书》,就好像从“光滑的冰面”回到了“粗糙的地面”,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
楼巍:大家不是都说,《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是对立的吗?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说,不要把他的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放置在一起出版,这好像就体现出了一种对立。那么,我索性就直接把这种对立总结为“光滑的冰面”和“粗糙的地面”。
后来还有一个比喻,可能更好。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认为语言是“可能的事实”的图画,把语言当作一种无差别的、单一化的、抽象的东西,这就像是通过地图去看城市,无论重庆还是上海,从地图上看,其实都是一样的,都被缩略成了点和线。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我认为是一种在城市中散步的感觉,这样一来,你会看到更丰富的细节和更粗糙的颗粒,在上海行走和在重庆行走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于是,你就会发现,语言的各个领域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形容词和名词就很不一样。
说到比方和举例,您在书中谈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而且有些例子本身就是维特根斯坦自己用过的。比如,他向学生总结他的教学目标,就引用了《李尔王》中的句子:“我将教你看到差异。”维特根斯坦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学生看到差异?
楼巍:一般人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观点的根据或基础,其实往往是一些语言使用的例子。对这一类观点,维特根斯坦就会给出更多的语言使用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让你知道,其实你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或者只是一部分性质。所谓“看到差异”,可以简单理解为让你看到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看不到差异,就会觉得语言是一样的。你看到差异,就会觉得每个词都是一个工具,不同工具的用法是很不一样的。比方说,像“罗素”“苏格拉底”这样的词都对应着一个人,在此基础上,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所有的词都应该对应一个人或一个东西。这就是看不到差异。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开头就提出,很多词没有这个对应的东西,比方说数词,“3”这个词对应什么呢,我们无法找到某个跟它对应起来的东西,然而,它似乎又可以对应任何三个东西,三头牛、三杯水,等等。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没有对应的罗素这个人,“罗素”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而“3”这个数词和“罗素”就不一样。再如形容词,“红色”对应什么呢,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跟它对应起来的东西,但是,所有红色的东西都可以被它言说。又如“今天”这个词也没有什么与它对应的东西,难道它就没有意义吗?显然也是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就是以这种方式让我们去看清楚,词语在我们的语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前面提到,每个词都是一个工具。维特根斯坦就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词语好比操纵杆,每根操纵杆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拉动这根操纵杆是打开离合器,拉动那根操纵杆就变成踩下刹车了,基本用法是很不一样的。
有人提到,维特根斯坦虽然致力于反对形而上学,可是他的著作后来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巍:因为维特根斯坦自己说过,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是徒劳的,试图通过这种哲学寻求答案的人,就像是被困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的一只苍蝇,试图通过撞击瓶子的侧面来逃脱,而他的哲学就是要给玻璃瓶子里的苍蝇一条出路。于是,就有人评论说,维特根斯坦号称要把苍蝇从玻璃瓶子里面放出去,可是他不也是陷在自己那个体系里吗?他自己不也是一只瓶子里的苍蝇吗?这肯定是不对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特点是什么?他的哲学的特点是,永远以语言实际上如何被使用为前提。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语言的用法也会变,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建立起一套一劳永逸的理论体系。所以,他的哲学是开放的。在我看来,他其实是提供了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或者说思考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可以真正被实践和应用的。
维斯根斯坦这种开放的哲学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能否请您谈一谈?
楼巍:记得以前有一则新闻引发了轰动,一位笔名叫陈直的农民工(其实“农民工”这个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时他是厦门一家工厂的工人)翻译了一本《海德格尔导论》,想要出版。很多人质疑说:一个农民工,懂什么海德格尔?这个时候,用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反问:说陈直不懂海德格尔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懂不懂呢?他们凭什么说陈直不懂海德格尔呢?假设那个质疑的人是一名大学教授,一般人会觉得,大学教授肯定要比农民工更懂海德格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问:为什么一个大学教授就一定更懂海德格尔呢?因为这个教授是被专家评出来的吗?被专家评出来的人就一定更懂海德格尔吗?你用维特根斯坦的方式追问下去,什么叫“懂”海德格尔,什么叫“更懂”海德格尔?谁来评判”懂“不”懂“海德格尔?这些问题一旦提了出来,其实很多东西就被解构掉了,就好像一个绳结松解开了一样。本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种质疑,好像也就接受了,确实,一个农民工,怎么会比大学教授更懂海德格尔呢?往往在最浅表的层面上,我们就停止了追问,可是,如果你继续追问下去,可能这个节结就被解开了,然后情况也就发生变化了。
我觉得,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商人的孩子,商人做生意,总是要把事情搞定,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get things done,他的哲学也是一样——要把事情搞定。这其实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做哲学的方式,日常所理解的那种做哲学的方式,其实就是,你提出一个观点,我又提出一个观点,大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互相商榷,把它搞成一个红红火火的圈子游戏,大家都来玩。而维特根斯坦不一样,他喜欢把事情搞定,就到他那里为止,把事情彻底聊清楚,聊完你就得到了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治疗哲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