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境逼而神境出——试论曾晓浒的山水画
真境逼而神境出
——试论曾晓浒的山水画
文丨王鲁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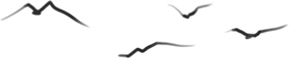
曾晓浒(1938~2015),四川成都人,父亲曾还九与張大千交厚,曾晓浒年幼时常亲观大千先生作画,培养了对国画的兴趣。1957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得到了关山月、黎雄才的指导。1961年毕业分配到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直至去世。在湘生活、教学、创作凡54年,笔耕不辍,教学相长,成就了自己融贯南北画风、吸收西画光色、表现湖南地域风貌的山水画风格,是二十世纪湖南美术界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卓越的山水画大家;同时也是湖南最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教师和画家。
曾晓浒的情况同千年前的岳麓书院山長张栻一样,是典型的蜀才湘用,一生事业成就于湖南岳麓山下,足迹遍三湘,画图尽三湘,弟子满三湘。
值得指出的是,曾晓浒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山水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花鸟画家、人物画家,还精于书法和篆刻,古诗文修养极高,是一位难得的修养全面而深厚的艺术家。夫人陆露音女士是一位油画教授,公子曾进也是山水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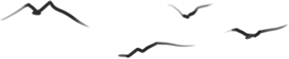
观察和研究曾晓浒,离不开四川、广东、湖南三省的空间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山水画革新运动这一时代背景。把他锁定在这个时空座标上,大体就能给出一个定位。
曾晓浒是川人,身上秉赋川人的灵秀和才情。四川的山水环境和巴蜀文化传统,似乎天生是孕育道教和神仙信仰的地方。川地文人和艺术家,自古迄今,各个身上都带着“仙气”:司马相如、李白、吴道子、苏轼、张大千、陈子庄、石鲁、常玉……仔细一琢磨,这些川蜀文人和艺术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生活态度的飘然不群,他们艺术神思的逸兴湍飞,他们艺术表达的奇诡瑰丽。他们的为人和为艺,似乎就是为了抵抗平庸。他们随意地挥洒着上帝赋予他们的才情,点亮尘世灰暗的生活。他们传诵千古的杰作,似乎都出自于漫不经心的随意。他们的才情如山洪泛滥,任意东西,俯拾即是,着手成春。
曾晓浒就是这样一位川人,观其山水,赏其人物,品其花鸟,味其书法,抚其篆刻,读其诗文,都有“美曰载归”的感觉,或“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或“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或“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或“露余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种种好景佳境,“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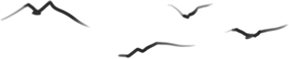
曾晓浒的国画,吃的第一口奶是张大千的。大千先生的山水对曾晓浒的影响,论者很少言及,其实这种影响痕迹是无处不在的,是在基因层面的。
曾晓浒的山水画讲究墨与色相得益彰,追求画面华丽甚至是纤秾的视觉效果,这与张大千的趣味是一致的。张大千晚年山水既泼墨又泼彩,以泼彩为主;曾晓浒晚年山水也是泼绘淋漓,既泼墨又泼彩,但泼彩谨慎,泼墨大胆,泼彩比张大千薄透,泼墨比张大千丰富而有变化。张大千泼彩泼墨更主观更抽象,曾晓浒泼彩泼墨还是谨守他心目中的“真境”;张大千泼彩泼墨“胸中只有全牛”,要的是“返虚入浑”“超以象外”的大效果,曾晓浒泼彩泼墨“载要其端,载同其符”,墨与彩还是为山石云烟的造型服务,看似豪放、疏野,实则沉着、缜密。这种对墨与彩的大泼绘的共同爱好与擅长,是因为他们同为川人,身上都有御气餐霞的仙人气质;而二人表现出的个性差异,又可能同各自所受的教育背景不同相关。

曾晓浒同张大千的联系还表现在二人的用笔上。张曾二人都喜欢用小笔勾山石树木和点景人物,也都擅长在画中留出大块的白石,以醒豁画面。张大千喜欢横构图,曾晓浒也喜欢横构图,两人都擅长在经营位置时,以阔远之法代深远、高远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构图上以阔远来统摄深远和高远。但张大千有点“偷懒”,往往一大块色墨占据画面五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权当主山山体,然后在边边角角添补些具象的树木房屋或水口;而曾晓浒很“老实”,他的闊远构图里总是藏着高远和深远,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层层翻高,层层递深,最后构成宏阔的壮伟景象,比如《百丈峡》《幽谷奇观》《晴空横翠》《山色朝晴翠染衣》等等大作皆如是也。
神仙都爱漂亮,神仙本人都很漂亮,乘云车,着霞衣,光鲜旖丽,手把芙蓉。张大千、曾晓浒的画也很漂亮,很光鲜,用笔爽利,用墨干净,用色鲜丽。不同的是,这两个蜀仙,一个生活在蓬莱仙岛,不食人间烟火;一个生活在山野,耳目所接,都是商旅樵牧。张大千是天仙,曾晓浒是地仙,两个人都是“一生好入名山游”,都是烟云供养一辈子。这种有仙气的山水画,本来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一大文化特质,是用来“澄怀观道”,卧游畅神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山水画里的仙气越来越少了。曾晓浒的山水画还多少保留着一些仙气,他画中的那些着现代衣冠的点景人物,其实和上古的葛天氏之民没有多大差别,仍然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羲皇上人”。他在大湘西的莽山野谷中感受到了这种永恒的存在,并烟霞云雾、溪流芳树一同画出,就有了现代山水画里难得一见的仙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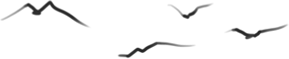
曾晓浒在绘画上吃的第二口奶是岭南画派。从1957年到1961年,曾晓浒在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受到系统美术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四年,正好是中国美术界发生观念大变革的关键年代。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兴起使美术界尤其是高等美术教育恢复了对中国画的文化自信,美院重启了中国画专业的招生和教学;另一方面,中国画必须通过变革求新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中,山水画要通过画家去到大自然和生产建设现场的写生来反映真山真水真生活的新观念业已成为新老画家的共识,北京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位央美教授率先于1954年到江南,直接用毛笔宣纸在大自然中对景写生创作。随后,西安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南京的傅抱石、钱松岩、宋文治、魏紫熙、亚明,广州的关山月、黎雄才,还有上海、杭州的老画家们纷纷走出画室,走向名山大川,走向建设工地,一股写生山水的大潮涌起,一批写生基础上创作的杰作诞生,“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新岭南画派”等等基于中国山水画革新观念和写生实践之上的地域性画派相继出现,中国山水画迎来一个发展大机遇。
曾晓浒的山水画观念就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提出的“真山真水真笔墨”的山水画美学的崇“真”精神和写生创作方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熏陶下成长和形成的。
曾晓浒就读的广州美院,是“岭南画派”的大本营。他的老师有关山月和黎雄才两位“新岭南画派”的山水画领军人物,他的观念和技法便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响。事实上,曾晓浒的山水画从广义风格上说,可以归入“岭南画派”。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热带,阳光强烈,色彩丰富,民间艺术崇尚颜色饱和热烈,加之最早受到港澳地区欧洲艺术的影响,追求写实风格,所以,岭南艺术热烈饱和的色彩倾向和求真写实的艺术追求,就成了曾晓浒山水画的艺术特色之一。
同样是好用色彩,张大千及其弟子何海霞的用色是源于东方传统的主观用色、装饰用色、类型用色;而岭南画派画家的用色,则更多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影响,其用色的观念,偏于客观性、感受性,而且自觉运用色彩学的科学知识,在色彩使用中加入了光与影、明与暗、冷与暖等等属于西画的表现手法。
很显然,曾晓浒山水画中用色的明丽,尤其是在山崖与树木表现上运用强烈光影的手法,同岭南画派是相通的。不仅相通,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看曾晓浒的大幅山水画,往往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这种感觉除了来自于其层峦叠嶂的“闊远涵深远”构图所带来的震撼气势,还与其光影明灭的色彩效果密切相关。有了这种色彩表达上的强烈的对比,王维说的“阴晴众壑殊”,杜甫说的“阴阳割昏晓”,才有了画面上直观的视象表达。《百丈峡》和《幽谷奇观》,就是这样惊心动魄的作品。
可能是长期在湘西涧深谷幽峰耸林密的环境中观察自然所得,曾晓浒对幽谷中的光影明灭特别有会心,他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艺术语言来表现他的观察。他往往会在峰头用淡墨泼绘勾皴出有阴阳向背的体面,好似强烈的阳光刚刚照射到上面,蒸腾起云气,弥漫出光雾,山头既虚且亮。而在山头下的深涧里,林木森森,阔叶林和针叶林用浓墨重色写出,自然形成与山头阳光灿烂的对比,显得阴凉湿润。曾晓浒会在这样的深涧里,以色当墨,或用青绿、或用朱砂、或用铬黄,总之,会用明度很高的纯色点画一株或两株明亮的乔木,照亮幽暗的涧底。这也是他对色彩的创造性使用。
用覆盖性强的石色(如石青、石绿、赭石、朱砂)在浓墨泼绘的墨团上点勾树木,是张大千从古代青绿山水的画法中创造性发展出来的新技法,这一技法又被何海霞发扬光大,形成何氏金碧山水的独门语言。曾晓浒又大胆地将之借用到水墨大写意山水画中,与泼墨相表里,极大地丰富了水墨山水画的语言表现力,也形成了曾氏山水画的个性魅力。
总结曾晓浒对中国山水画作出的贡献时,必须首先注意他对色彩的创造性运用,他对张大千、何海霞、岭南画派和西画的吸收各有会心,既有古典“随类赋彩”,也有写实光色表达;既有主观情绪用色,也有装饰美观着彩,而且能够巧妙融合并形成自家面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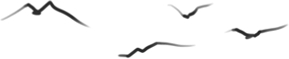
曾晓浒对色彩的偏好,不仅是因为色彩表现了一个色相丰富的大千世界,还在于色彩可以表现意境,为营造画面的诗意氛围服务。曾晓浒并不是一个客观使用色彩的画家,他其实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偏好。在众多色彩中,他偏好翠绿色系和赭黄色系。他有许多题跋直接写上“翠”与“绿”字,如《幽谷流翠图》《梦到山乡绿雨时》《浓翠参差净无尘》《山色朝晴翠染衣》《绿涨山原》《碧溪浼翠》《翠谷清风》《沐后秋山浮翠光》《晴空横翠》《入山销夏访翠微》《林麓散翠烟》《春云积翠波光静》《家居翠微一径幽》《云溪拥翠》等等,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山水画家,曾晓浒一定是青山绿水的迷恋者,绿代表生命,象征和平,而湖南雨水充沛,山深林密,其色相绿而至于翠,必定对曾晓浒的视觉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冲击。“翠微”本身就是湖南山水给中原人留下的视觉印象,曾晓浒用色阶丰富复杂的翠绿色系来作为他描绘其第二故乡湖南的主调,内心一定充满了对生命与安宁的衷心祝福。
翠绿色系是对盎然春意的美好祝福,赭黄色系则是对金秋的生命礼赞。曾晓浒对秋景情有独钟。他画过很多秋景名作,如《斜阳明芳树》《萧萧木叶秋正浓》《幻化云峰起遐思》《峨嵋山景》《苍然暮韻忆旧游》《溪云烟树醉看秋》《烟光藏落景》《石涧簇秋彩》《春山不媚是清秋》《巫峡清秋》《溪山秋深》《溪上人家岸下舟》《遍踏蜀山秋》《江岸秋艳》《龙泉秋光里》《明霞映秋树》《清秋走马出卧龙》《江濆秋雾》等等。中国文化人对秋天特别敏感,诗词歌赋及绘画作品描写秋景的特别多。我曾经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季节题材作过粗略统计,发现描写秋天的篇什远多于其他季节,而在描写秋天的诗歌和文赋中,又以悲秋和伤秋的主题居多。显然,秋天的成熟,秋天的灿烂,秋天的热烈和秋天的萧瑟,能够激发文人墨客太多的生命感悟。但在曾晓浒笔下,秋景则有着完全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情调。他会用大泼墨和大块面的山石留白的强烈的黑白对比来表现秋景的明净,运用西画的色调概念,将赭黄色作为基调,与淡墨浑融,渲染草坡和山石,再用朱磦、朱砂点染秋树霜叶,并衬之以浓墨,以使红色更为醒目。为了避免秋景的萧瑟,他还会用花青甚至带紫色的群青来大片渲染远峰青影和山谷岚气,暖色调的热烈和冷色调的清凉,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秋天的两面情调。
当然,这种对比色的大胆使用,可能会带来火燥之气,显得艳俗。曾晓浒往往会在最后借用水彩罩染法把红黄色作降调处理,消退火气。
自从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上”的主张,文人绘画离丹青愈来愈远,以至于提出了“水墨胜处色无功”的口号。岭南画派诸子大胆使用浓艳热烈的色彩并以色彩作渲染气氛的重要手段,尽管在格调和品味上还有待提升,但确实是对文人水墨画的清冷孤傲的基调作出的一个大的调整,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和地域的合理性。曾晓浒从岭南到湖南,一岭之隔,南北山川风物大异。按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点。曾晓浒必然要调整自我,以与湖南水土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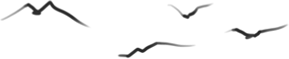
从四川到广东再到湖南,曾晓浒经历的不仅仅是地域山川面貌与气候的变化,也是巴蜀、南粤和南楚历史文化与风土民情的不同。
虽然湖南山川之胜早已见之于楚辞,自五代起就有董源《潇湘图》开山水画一代新风,又有“潇湘八景”作为诗画主题被历代文人反复吟咏与图绘,更有米氏云山作为湖南山水的水墨图式闻名天下,但湖南本土却一直没有出过大的山水画家,美术史上也少见有画家亲历三湘大地,画出洞庭、南岳、九嶷、苍梧、武陵的真景实境。那些以潇湘为题的画作,都是以古人诗句为想象的虚构之作。虽然民国出了个大画家齐白石,但他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亦多是异乡风景,《借山图》四十多景,也只有洞庭君山算是湖湘山水。
所以,曾晓浒1961年从广美毕业来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时,他所面临的湖南本土山水画资源,基本上是空白。
可以这么说,曾晓浒是美术史上第一个寄寓湖南五十多年,以一生的全部努力,开拓、发掘、创造湖南山水画资源并创作海量作品,形成潇湘山水画派的画家,其艺术成就堪称一代宗师。如果要论对湖南山水画的贡献谁最多?要比湖南画家在全国山水画界的影响谁最大?要问谁在湖南培养了最多山水画家,要说全国山水画家中谁的画最得潇湘山水之神韵,试问除了蜀人曾晓浒还有谁?

曾晓浒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山水画大家。
半个多世纪,一个四川人,走遍三湘四水,真的是“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雨余斜阳槕舨轻》这幅画上,曾晓浒题到:“昔泛舟沅水上,漂泊近十日,所过山村野浦多有苍茫浑朴之景。秋阳夕照,雨余青山,更见清旷,城市中人(不)可想见也。”这完全是一篇沈从文式的沅水游记。又如《南山秋晴》题跋:“浮云带雨蔽太虚,倏然迷蒙失前峰。山中自有超群客,佇立溪头听天风。甲戌之秋迁新居于麓山北首,日观山色变化,大有脱尘出世之快。”这种“此心安处即吾乡”的归宿感,表明了曾晓浒完全把自己融入了湖南。湖南的山水也幸亏有了他这么一位“超群客”,那些“倏然迷失”在云雨中的“前峰”,才豁然出现在他的笔下,山色变化,脱尘出俗。
曾晓浒画出了湖南山水的野和莽,也画出了湖南山水的清和幽。在他笔下,湖南山水显现出不同于江南山水、关陇山水、巴蜀山水、皖赣山水、云贵山水的地域性格,这一性格就是“野、莽、清、幽”。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曾晓浒对湖南山水并不做简单的符号化解读与表达。比如说,许多湘籍画家热衷于描绘的“洞庭秋月”、“岳阳楼”、“爱晚亭”、“橘子洲”、“祝融峰”、“韶山”就很少出现在他的山水画中。但是,他画出了大湘西的苍茫野性,画出了湘东山中小镇的烟开晓日,画出了湘南溪上人家的溪扉乡语,画出了那些在崎岖山路上匆匆行走的商旅,画出了那些从溪云烟树中走来的樵夫和牧童,画出了那些在湘资沅澧的支流小溪上放筏泊舟的忙碌身影。将曾晓浒的题画诗句予以集句,或许可以看出他对湖南山水意境的领会与表达:“朝行溪路沐清晖”,“路转幽微景更奇”;“苍山浴日梦初醒”, “山色朝晴翠染衣”;“穿云击石道又通”,“乱泉洩玉秋光里”;“幻化云峰起遐思”,“行尽崎岖见熹微”。从这些优美的题画诗句,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行尽湖南山水的画家的身影。他朝行暮归,在梦幻般的幽微奇景中,穿云击石,行尽崎岖,遐思湖南山水画熹光微现的晨曦。
相信在长沙火车站看过那幅高九米、宽十八米的“中国最大的山水画”的人,一定会为这幅名为《醴蘭沅芷·岳色湘声》的钜制所震撼。这是曾晓浒带着六位门生,走遍三湘四水,集湖南山水名胜之最于一图,奉献给南来北往途径长沙的过客的一份见面礼。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是举省公认的湖湘山水的代言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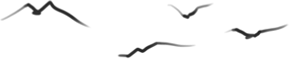
有论者指出,曾晓浒的山水画风,走的是一条“漫漫求真路”:“在当代山水画家中,曾晓浒先生的作品体现着真山真水真笔墨一路风格的较高水平。”
有“真山真水真笔墨”,就一定有“假山假水假笔墨”。那么,何谓“真”?何谓“假”呢?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有不同的定义和解读。
如果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山水画革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冲着自明清以来山水画的“假山假水假笔墨”而去的。从顾恺之、宗炳、王微到荆浩、董源、巨然,中国早期山水画无画史积累,故无成法可依,山水画家们都是崇尚自然的高士,用画笔图绘山川,是为了卧游,为了观道,为了畅神,为了养气,所以他们所画的山水画,都是自己饱游饫看的,是无数次游历山川后在大脑中形成的综合意象。他们的山水画,也许语言尚不纯熟,但一定是得自于个人的真经验,表达的是个人的真性情。这样的山水画就是“真”的。北宋文人的山水画是要寄托他们出仕后怀念家山的乡愁,也是为了随时准备致仕后觅一安居之所,满足其内心的“林泉高致”。他们对山水环境的要求,已经从寻仙、观道的超越性的精神层面,降维到了安顿身体和家族的世俗社会的层面,所以北宋人喜欢全景山水,因为它能满足欣赏者“可观可游可居”的身体要求。这样的山水画也是“真”的,其景得自于对自然山川的观察,其境来自于内心真实的理想,其笔墨皴法有真实的山石树木的形质依据。再后来,士大夫致仕后或归田园卜居问舍,或在城市和近郊买地建园,与此风相应,文人画家开始创作一种“丘园养素”的山水画,比如明代著名的“吴门画派”,其首领沈周所画丘园,就亲切可爱,在小丘小池小园里,叠石理水,一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河万里,可耕可读,可游可憩。这样的丘园山水画也是“真”的。
什么时候出现了“假山水画”呢?明清两代。出现“假山水画”的原因,一是有过剩的文人,能画几笔,但对真山真水无感,或者穷得既不能像荆浩、王维那样,在太行山和秦岭建别业,也不能像宗炳、米芾那样去名山大川旅行,他们只能搬弄一点前人作品的丘壑,熟记某些前人山石树木的画法,拼拼凑凑而成一幅山水图画。还有一个原因是艺术市场的出现,如盐商,他们附庸风雅,并不懂艺术,他们的需求催生了许多江湖气和市井气的“假山水画”。当然,还有一个艺术史逻辑的内在规律,即山水画如果从东晋萌生算起,经过隋唐五代两宋元,到明末的时候,已历千年,其间大师辈出,高峰迭起,创造了许多的经典图式,积累了深厚的语言程式,确实到了从图式到笔墨进行语言修辞学总结的时候,以董其昌、莫是龙、赵左为代表的画家,以其富赡的字画收藏为学术资源,开启了所谓的山水画创作的“形式主义”路子,以至于在江南地区延续到清代形成一股风气和潮流。清初“四王”的出现和皇帝趣味的加持,更是把这股风气和潮流推到极致,画家们按着既定的“风水”观,以美术史上的“某家样”为粉本,简单地摹仿几个图式和固定的皴法,就开始在纸上“叠山理水”。他们沉浸于这般笔墨游戏不亦乐乎而且相互标榜,全然忘记真山真水的存在。用李可染1950年谈山水画革新势在必行的说法,这股形式主义的潮流,已经堵塞了山水画的活水源头六百年。他号召中国当代的山水画家重新回到大自然中去,面对真山真水写生创作,并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实践中提炼自己的艺术语言。应该说,曾晓浒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山水画家,他必然走上一条求取山水“真境”的创作道路。

问题是,怎么理解“真”?如何理解山水画的“真”?
从常识的层次,“真”就是我们的感知觉感受到并确证存在的事物。对山水画而言,画我的眼睛确实看到过的山、水、树、石、房、人,以及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景象,尤其是,那些具有时代当下标志意义的事物,这些就是“真”,真山、真水、真人。而那些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出来表现这些真山真水真树真房子真人的笔墨,就是“真笔墨”,这样的“真笔墨”当中,还包括了“真色彩”。
可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山水画革新的求真理念,就是如此朴素和单纯。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当山水画家们描绘眼前某一具体的小景时,满足视觉真实的景致可以画得很生动很逼真,但如果想把大山大川表现出来,画出层峦叠嶂甚至咫尺千里的景象时,满足视觉真实要求的种种经验就不够用了。山水画家们发现,原来古代画家游历山川,除了“目所绸缪”,还有“身所盘桓”,他身体的移动行走带来了所谓“散点透视”,形成了“移动空间”,这就是宋人总结出来的“三远”:高远、深远、平远。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视觉经验里,空间不是割裂的,而是连续的,甚至时间与空间也是连续的。当出现了这种时空连续的意象时,古人就会说出现了“神思”:“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晨昏阴晴四时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里。正是这样的“移动空间”与“四维存在”,构成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美学魅力,也给艺术的“真”提出了问题:实境是不是真境?山水画是以画实境为目标,满足人们日常的视觉感受,还是以画超越一时一处的更大的时空连续体为目标,以满足人们“应目会心”、“感神畅神”、“澄怀味象”的更深刻更高级的精神需求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代画论提出了“实境”和“真境”这对范畴进行讨论。“实境”就是人们感官感受到的存在;“真境”除了这一层意思,还必须是一种理性思维认知的存在。比如对于道家哲学来说,“真境”是一种有“道”的存在,可以让人们“观道”“玄览”的存在;对于张载、王充这样的哲学家来说,“真境”必须是一种有“元气”的存在,可以感受到“元气氤氲,万物化醇”的存在;对于程朱理学来说,“真境”是一种有“理”的存在,可以理会到世界万物无所不在的“神圣秩序”的存在;对于佛教禅宗和阳明心学来说,“真境”就是“心境”,“心外无境”,“境由心转”,“境由心造”。各种哲学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就相应的有各自的“真境”观。落实到绘画,则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谢赫的“气韵生动”,宗炳的“澄怀观道”,荆浩的“搜妙创真”和“真者气质俱盛”等等,都是涉及到何谓“真境”的言论,都在努力回答,绘画创作中,画家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山水画,画家描绘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曾晓浒要描绘的是湖南这个地域的山水,他可以用他从美院学到的专业技能较轻松地把湖南山水的地域特色描绘出来,比如湖南山区特有的吊脚楼、苗寨、峰林等等,但这还只是属于“状物精微”的“取象不惑”的层面;这种微观真实要“隐迹立形”,融入到“思经天地”的宏观气象的“搜妙创真”之中。比如说,湖南属于暖温带,林相是针叶林阔叶林灌木混杂,而且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而绿色深翠,湘西、湘东、湘南山高林密,涧深溪流多,曾晓浒长期跋涉写生于这样的山区,形成了对其“真景”“真境”的深刻感知,并“删拨大要,凝想形物”,“制度时因,搜妙创真”,创造出晴峰与幽涧二元对位的大图式。在这个大图式里,又排比若干对二元对位的小图式,如白岩对黑石,针叶对阔叶,草坡对山径,溪水对木桥,行人对山居。色彩上是以翠绿或者赭黄为主调,但也在局部以二元对位法将明度和纯度极高的石绿、石青、朱砂、铬黄诸色点染于浓墨之上,大胆用墨,大胆用色,大胆用水,形成其用笔“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用墨“高低晕淡,品物浅深”、用色“文采自然,气韵高清”、用水“荡迹不测,品物流笔”的个人风格,湖南山水在他笔下“任运成象,气象幽妙”。
清代画家笪重光在其所著《画筌》中说过一句话:“神无可绘 ,真境逼而神境生。”由追求“真境”的表现,曾晓浒逐步地通过艺术思维的辩证法实现了由“真境”向“神境”的转化和升华,完成了其气韵阴阳、开合贯通、动静结合的图式构建:登高俯瞰,阴晴众壑;峰峦云动,雾海翻腾;山外青嶂,霞光山影——此其高远大势也。怪木森然,一径逶迤;小桥流水,寒亭古道;深谷跫音,牧樵行旅;吊脚野屋,时见幽人;风日水滨,隔溪渔舟——此其深远细观也。曲径通幽,穿云破石,是为了抵达雄冈巨阜,行尽崎岖见熹微;幻化云峰,大壑流云,是为了聆听天地清籁,苍山浴日梦初醒。
“动观行云流水,静听幽壑松声”。曾晓浒用他创作的湖湘山水真境,把我们带进了“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山水艺术神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于京华襟道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