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她的小说,那么轻,又那么重

燕妮·埃彭贝克
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视她为“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语小说家”,小说家米歇尔·法柏称其是“在世的最优秀、最激动人心的作家之一”,《爱尔兰时报》的记者艾琳·贝特斯比,则将她的作品视作“令人生畏的天才之作”。
她的小说并不厚重,薄薄一册,超然轻灵的文字,像圆舞曲或清晨湖边氤氲的雾气,写就的却是宏大的历史命题。她的作品“通过那些在历史转折中失落的人与物的故事,含蓄地展现历史磅礴的进程”(劳伦·奥伊勒,《纽约客》),文风有一种“古典的节制”(詹姆斯·伍德),“像梦境一样轻盈,又如现实生活一般沉重。”(艾琳·贝特斯比)
理想国已推出燕妮·埃彭贝克的两部作品《客乡》《白日尽头》。《客乡》以冰山一般的超然语调,讲述了柏林郊外一栋湖边别墅,几十年间不断变迁的居住在此的人们的故事。别墅居住者的故事折射出德国从魏玛共和国到统一后的百年岁月,十二块人生碎片构成一幅镶嵌画,过去与未来坍缩其中,故事真正的讲述者是时间,“永恒的生命,已存在于人类个体的一生中”。
《白日尽头》则通过一个女人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充满黑暗秘密的国家的寓言。经历了三个帝国、两场世界大战、五次死亡、四次重启人生,在人生的尽头她意识到:活着不过是让两股势力在她这里相互较量,并且让恶劣的最终落败。“当生命所有的库存都用完,那坚不可摧的储备显现出来。”
或许还有读者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借新书出版,我们将这篇《The Enduring Impermanence of Jenny Erpenbeck(燕妮·埃彭贝克的永恒无常)》分享出来,期待有更多中文读者能与这位小说家“相遇”。
所有事物最终会消散,即便是那些对我们来说似乎最永恒、最持久的东西。
以下内容来自《The Enduring Impermanence of Jenny Erpenbeck(燕妮·埃彭贝克的永恒无常)》,原载于《今日世界文学》2018 年 7 月刊,有删节、修改。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在燕妮·埃彭贝克的作品中,事物消失,人物消失,知识也会消失。即便传统习俗和仪式,这些旨在通过将我们与过去捆绑在一起来防止文化崩解的做法,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逝。埃彭贝克的作品主题很复杂,专注于历史,素材丰富,然而关于“无常”(一切终将消亡)的念头,贯穿了她的全部作品。
所有事物最终会消散,即便是那些对我们来说似乎最永恒持久的东西——还有谁比燕妮·埃彭贝克这样的作家更适合书写它呢?1990年德国统一时,她刚刚成年,目睹了东德被并入西德,她的国家迅速崩塌,属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文化被抹除。对于埃彭贝克而言,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家不是,国家不是,甚至记忆也不是。
21世纪的许多德国作家都将历史的目光投向了上一个世纪,并通过个人或家族史的叙事来聚焦这种目光。在这方面,无人比埃彭贝克做得更好。
她的小说处女作是中篇《老孩子的故事》(1999),一出版便获得批评界诸多好评,小说中的集体宿舍正是东德的象征。《老孩子的故事》是一个寓言,故事中的女孩被发现独自站在街角,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手里拿着的一个空桶,身无一物。她是社会意义上的一张白纸,不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她只知道自己十四岁了。当局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于是把她带到了儿童之家。在那里,由于举止笨拙、缺乏社交技巧,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她渴望融入儿童之家的社会秩序,并急切地接受了自己在底层的地位,这是任何社会秩序中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你无须捍卫它。她知道学校的围墙之外都有什么,她满足于学校本身的可预测性和秩序,尽管其他人都渴望自由。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女孩身上有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她似乎既缺乏自我意识,也无法控制自己笨拙的肢体。直到小说结尾突然的转折,我们才知道她隐藏着一个秘密:她实际上不是14岁,而是30岁。她是一个成年女人,选择退回到一个安全有序的儿童机构。
《老孩子的故事》中有许多德国文化和文学史的影射,尤其是19世纪有名的弃儿卡斯帕·豪泽尔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拒绝长大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就像在格拉斯的小说中一样,评论家们也留意到了埃彭贝克故事中的政治隐喻。东、西德统一之后,许多前东德人发现自己失业了,他们的专业证书被吊销,导致很多人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失去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他们免于贫困的社会机制。德国推进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令他们失望,对于很多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来说,自由的承诺就像一个残酷的骗局。
到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人希望回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评论家们将埃彭贝克的“老孩子”视为这种愿望的表达。也有评论家将这个女孩本身看作东方的象征,她突然出现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却不了解新的社会秩序。就像那个老孩子一样,东德在新体制下显得笨拙无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发育迟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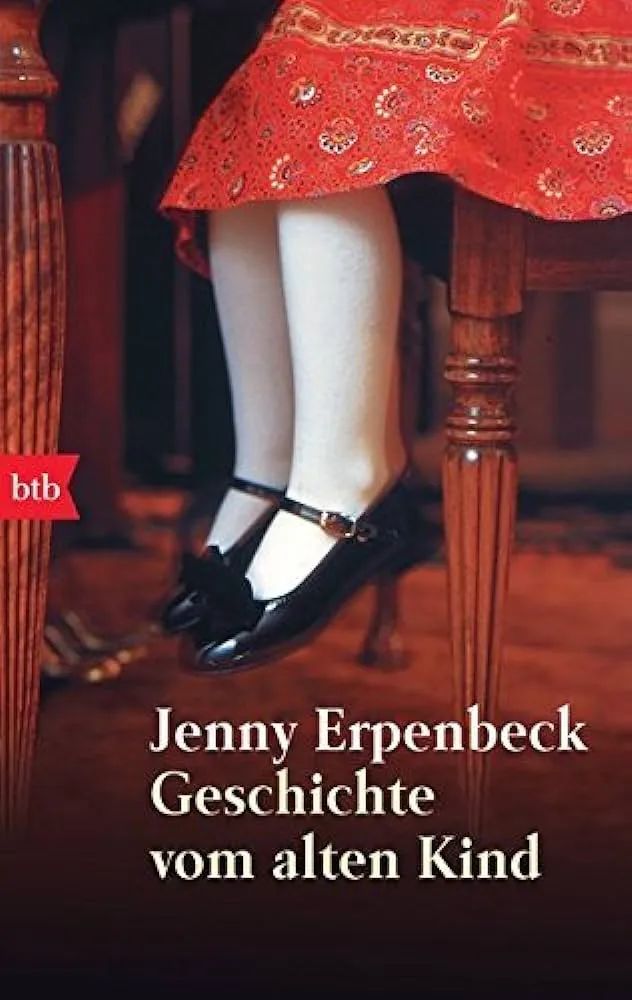
燕妮·埃彭贝克《老孩子的故事》(Geschichte vom alten Kind)德语版
20世纪是一片雷区
埃彭贝克此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客乡》和《白日尽头》将更长久的凝视投向了20世纪。《客乡》讲述了一座房子和一块土地的故事,在一个世纪之间,它的所有权发生了三次变更。当我们跟随与之相关的四个家庭的命运时,宏大的历史事件在房子的微观史中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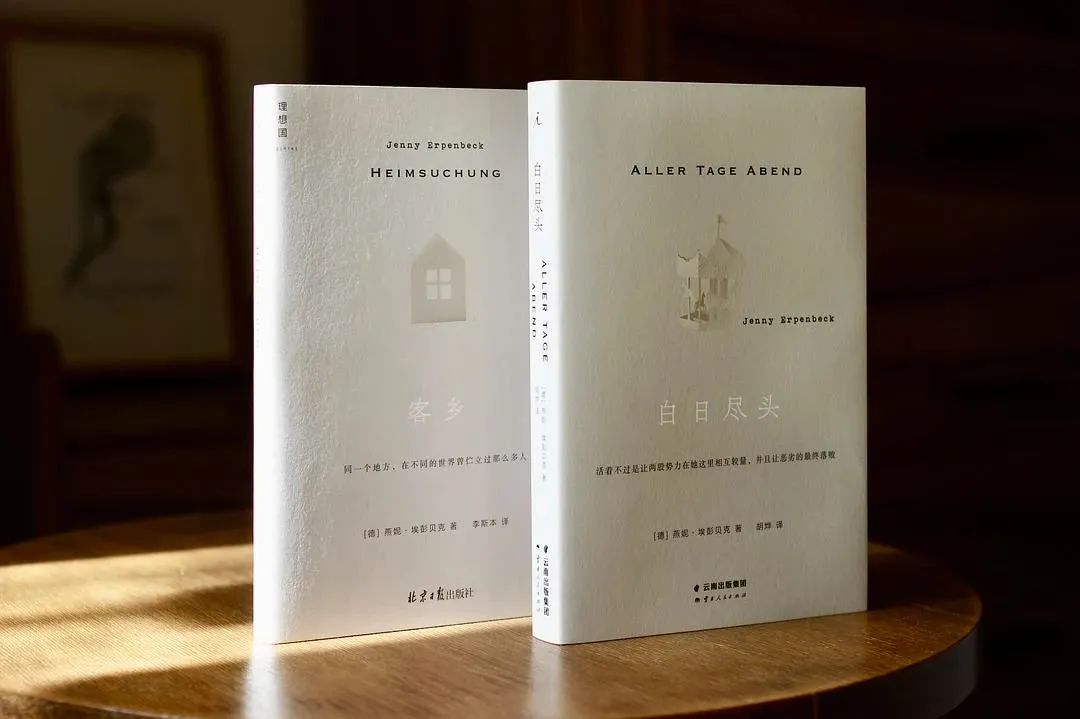
燕妮·埃彭贝克《客乡》《白日尽头》
在小说的开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位于勃兰登堡湖畔的那块土地是一个女人的嫁妆,意在通过联姻来巩固周边地主之间的财富。然而,当土地所有者的女儿克拉拉疯了,不能结婚时,她的父亲把土地卖给了一位建筑师。这笔交易导致了克拉拉的自杀,她的死象征着旧的社会秩序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而消亡。
20世纪30年代,这位建筑师在那片土地上建造了一栋房子,并以近乎掠夺的价格从试图筹资逃离德国的犹太业主手中买下了邻近的地块,包括一座船屋和通向湖边的栈桥,扩大了自己的地产。我们看到犹太邻居的女儿多丽丝在华沙隔都一个黑暗的壁橱里躲避纳粹,但最终被逮捕,继而悲惨地死去。对于德国那片湖上的风光的记忆,是她临终时唯一的慰藉。
我们看到建筑师的妻子在战争结束时被一名俄国军官侵犯。后来,建筑师在20世纪50年代逃往西方之前,把家里的贵重物品埋在了院子里。我们跟随一个女人的视角和思绪,她的祖母在纳粹时期流亡苏联,归来后被东德政府授予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在德国统一后,这位孙女必须为保留它而战,在建筑师的后代对它提出赔偿要求之后,她最终输掉了这场战斗。
最后一个故事的情节改编自埃彭贝克自己的家族史,包含着她对失去祖母位于勃兰登堡的湖畔别墅的哀悼,那是一个保存了快乐童年回忆的地方。小说的德语书名Heimsuchung,在英文版中由杰出的翻译家苏珊·伯诺夫斯基译为Visitation,意思是“拜访”,也有“幽灵”的意思,但你也可以把这个德语复合名词分解成“Heim”(家)和“suchen”(搜寻)。事实上,这座房子代表了这两者:对一个不再存在的家的渴望,以及被20世纪的残酷历史所侵扰的德国。
作为读者,我们站在自己幽灵般的位置,从一个无声的遥远距离和一个远远超出人类范围的时间线见证这些事件。“序章”讲述了形成丘陵和湖泊的冰山缓慢推移的数万年历史,“尾声”中房屋被拆除,从而恢复了原始的自然景观(尽管只是短暂地)。20世纪的人类活动只是地球历史长河与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时间对人类活动的冷漠,“此时此刻”对人类个体存在的紧迫性,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埃彭贝克通过视角的全景转换,以及对距离和变焦的运用来实现的。

燕妮·埃彭贝克《白日尽头》中文版
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白日尽头》中,20世纪从一个与《客乡》截然不同的角度被呈现了出来。《白日尽头》没有聚焦在某个地方,它的焦点是一个被迫在一个世纪里反复迁徙的中心人物。主人公是一名犹太血统的东欧女性,小说通过犹太女性遭遇的特殊困境和挑战来描绘了20世纪的事件。在不同的社会中(世纪之交波兰的加利西亚,法西斯兴起的维也纳,肃反时的苏联,战后的东德,最后是统一后的柏林),她面临着各种特殊的境遇,而她在这些社会中被接纳的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不同——这不断突显了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不稳定的处境。在《客乡》中,读者对小说中的事件隔着一种幽灵般的距离,而《白日尽头》则让读者靠近,通过与小说人物的密切接触来呈现20世纪的创伤。
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地点,时间也具有独特的含义。《白日尽头》呈现了主人公五个不同版本的生与死,这个女孩/女人没有名字,直到小说的尾声才揭示她的姓氏。第一卷围绕一个家庭的伤逝展开,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婴在睡梦中死去了,接下来的每一卷之前都有一个“间奏”,提出一个“假如”可能发生的场景,扭转死亡,延长女孩的生命。在第二卷中,这个婴儿成长为少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凋敝的维也纳经历了饥寒交迫、各种困顿,这一切促使她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但最后自杀身亡。在第三卷中,她成长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迁居莫斯科,为一家德语杂志撰稿。然而,被怀疑是托派分子后,她被逮捕并死于劳改营。在第四卷中,她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作家,移民到东德,帮助塑造这个新兴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化意识,但却死于纯粹的意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在第五卷中,她已经很老了,在养老院与她那一代的其他人一起活到了统一后的时代,由于失智和死亡,由于年轻一代的遗忘和不再问询,他们关于德国20世纪的那些故事最终湮没无闻。
在埃彭贝克的作品中,20世纪是一片雷区,只有靠运气和巧合才能幸存,而这个雷区也在代际记忆中制造了断层线。在章节间的间奏设想的每一个“假如”之后,叙事转向,某些信息、仪式和家庭故事被传递到后续的章节,而另一些则消失了。延续性似乎在物品和传家之物中保存得最好。然而,当后代无法识别这些物品时,它们的意义就丢失了。
时间,在她笔下变得难以预测
埃彭贝克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结构的尝试,也在于她将时间概念化的方式。它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线性的,在速度和方向上都难以预测。在《客乡》中,唯一一个始终与房子在一起的人是园丁,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角色。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年复一年,他种植、除草、移树、扎篱笆,为住在房子里的人做季节性的修剪大自然的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章节之间的间奏曲中,用他循环往复的劳作打破小说中向前发展的时间线。而在《白日尽头》中,时间并不仅仅是线性的(因为它记录了二十世纪的事件),周期性的(因为生命周期在几代人之间重复);它也是可逆的,因为主角被反复复活。对于埃彭贝克来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家不是,将我们与先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习俗不是,连死亡也不是。甚至连她的写作风格都在颂扬这种无常。它有音乐的质感。它是有节奏的,循环轮转;她的主题不仅在一部作品复现,而且贯穿她的全部作品。它们产生回声和余响:在她小说的开篇强势出现的元素会不断重复,但每次都略有减弱,直到最终完全消失。而沉默,即语言之间的空白,对于埃彭贝克来说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与那些被说出的话同样重要。我们会注意到什么不在那里,什么消失了。
埃彭贝克目睹过急遽的社会变革和她自己的国家的崩解,她明白任何制度都是多么的无常,将任何根深蒂固的东西视作永恒是多么的错误。由于她的家族史,她也十分清楚所谓稳定包含了多少不确定。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法律、人身安全,甚至边界(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都不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东西。如果我们睁开双眼,在身边的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许我们也可以成为一股力量,对抗曾在20世纪无处不在的失落与流离失所。
原标题:《她的小说,那么轻,又那么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