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刘永华: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合流,形成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着重讨论历史人类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取向,最后附带思考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除了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成果之外,更在于从本土学术传统中,探索出自身发展的路子。
一、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从近代学科的发展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本来十分密切。在进化论流行的年代,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不仅是历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学的关键课题。直至20世纪初,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因为研究文化的比较方法,不但包含了人类进化的大叙事,而且注重收集古典的、圣经的和民族学的资料。按现代的标准,它们对历史资料的引用,缺乏细致的考证,存在着断章取义的毛病。这点以传播论者尤为严重。
功能论的出现,应该说是对这种“揣测史”的反动。在拉德克拉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及其追随者那里,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考察社会文化的演进,而是探讨一套约定俗成的制度,是如何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均衡的。由于两方面的理由,他们对社会制度的历史不复有兴趣。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无助于解释这些制度对实践者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起了何种作用,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对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在拉德克拉夫-布朗看来,只能是“揣测”。这种对“揣测史”的排斥,最终导致对历史的完全摈弃。在同期的美国人类学家中,虽说对文化的亲缘关系和迁移始终相当关注,可在对文化和象征进行的共时性研究中,对历史的兴趣日见冷淡。对长时段历时性过程的研究,变成考古学家的专职任务。
功能论之后的几个理论流派,对历史的重视都很不够。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致力于构建“文化的语法”。他们注重考察二元对立的文化单位,是经由何种法则而转换成神话、婚姻规则、图腾制的。文化变成了分类系统和认知体系。文化语法是超越时空的。来自北美印第安人与澳洲土人的资料,和引自中国先秦时代的资料一道,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论著中,都被引以说明文化的语法。同样,象征人类学对历史在理解文化和象征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声称,象征是社会成员借由交流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精神(ethos)的媒介。他关注的问题是,象征是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观察、感觉和思考世界的。而对于文化的政治、象征体系的形成和存续等问题,格尔兹并没有多少兴趣,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极有益于重新评估历史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的。必须指出,格尔兹本人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曾撰写两部颇有见地的爪洼史论著,但它们在象征人类学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从60年代初开始,一些人类学者对人类学界漠视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批评。1961年,伊凡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指出历史和历史学对人类学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当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许多历史学家仍满足于撰写叙述史、战争史、事件史,尤其是政治史。另一些历史学家实质上是历史哲学家,当时尤以汤因比最为出名。伊氏心仪并认为人类学应予以重视的,是包括梅特兰(Maitland)、皮朗(Henri Pirenne)、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内的,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群众运动与大规模文化变迁的“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sociologues)。伊氏进而指出,忽视历史学给人类学研究带来各种困难。人类学家在使用文献时缺乏考证,他们也很少认真根据历史记载重构研究对象的过去。因此,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觉得在欧洲统治之前,原始民或多或少都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对历史缺乏兴趣,人类学家对历史、神话、传说、逸事和民俗没有明确区分,人类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也无法得到证实。

伊氏认为,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以往的历史是今天人们思想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再者,和人类学一样,历史学也将处理社会事实视为本学科的任务,假如人类学家想要进行理论综合,历史上的社会事实也必须加以利用。最后,历史编撰学本身,便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重要领域。梅特兰曾经说过,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伊氏也号召历史学与人类学合作,他仿照梅特兰的口吻说:“历史学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成为人类学,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伊氏的影响下,英国学者刘易斯(Ioan Lewis)曾组织一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探索两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可惜这一合作并未引起广泛的反响。60年代末开始,美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变动,美国人民对自由福利国家模式信任感的瓦解,以及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政治化,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所谓的“表述危机”。人们转而关注文化和象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过程。忽视历史,认为非西方人民“没有历史”,成为“政治上不正确”的做法。人类学家传统上使用来描述文化的“民族志的现在”(ethnographic present),亦即用现在时描述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社会文化事实,因为包含了研究对象没有变迁的意涵,受到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
在方法论方面,世界体系理论和实践理论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很有益于重新思考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实践理论从微观社会学的层面考察人类的行动,强调实践中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一理论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共时性分析转移到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转而强调微观的发展过程:交易、计划、策略、发展周期等。而世界体系理论及其他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注意结合大规模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欧洲的海外殖民和资本主义扩张,来把握人类学家研究的典型的小规模社会的变迁。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历史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关键象征”(Ortner语),对时间观、过程、再生产、变迁、发展、进化和转型的研究,虽说是否成为人类学的主流目前尚难定论,但至少成了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在历史学这边,重新思考和人类学合作,首先是与年鉴派的兴起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历史学年鉴派得名于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两位史学大师创办这一刊物的目的,在于同当时流行的事件史作斗争,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他们认为,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存在于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和心理诸因素之中。这无疑为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定下了基调,也为加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年鉴派的两位开创者都十分重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布洛赫在自己的论著中,即经常引述人类学家的见解。不过,此时的研究重点仍是社会经济史。
二战结束后,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领导下,年鉴派发展成一个历史学的运动,这一学派所提倡的方法,演变成“新史学”的纲领。1946年,《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意味着,对信仰和心态层面的研究,在继经济和社会之后,成为年鉴派的又一个研究重点。从6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年鉴派的地位逐渐下降,心态史一跃成了新的研究热点。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和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年鉴派第三代的史学家,都先后出版了心态史的奠基作,这就是所谓的“从地窖到顶楼的运动”。心态史的研究主题十分广泛,举凡从工作、家庭、寿命到教育、性、死亡,从体质变化、食品结构到健康状况、疾病、瘟疫、犯罪行为乃至人际关系,都成为它的研究对象。要处理这些主题,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勒高夫将人类学视为历史学对话的首选对象。在1975年前后,他倡导建立“历史人类学”这门学科,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之后,历史人类学成为年鉴派的标志性主题之一。1978年出版的由勒高夫等人主编的《新历史》一书,即着重介绍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和年鉴学派相似,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欧美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也是对传统史学过分强调事件史、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反动。他们倡导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人民群众的文化。由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束手无策,他们十分注意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汤普森(E. P. Thompson)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不仅广泛收集民俗学资料,而且借鉴人类学对仪式、交换等问题的相关理论。托马斯(Keith Thomas)对近代早期宗教和巫术的研究,也大量吸收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70年代以后,在格尔兹和特纳(Victor Turner)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关注历史上的文化、戏剧和仪式等问题。“历史人类学”开始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论著中频频出现。在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一书中,主编琳恩·汉特(Lynn Hunt)指出,卡尔(E. H. Carr)在20世纪中叶作出的对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论述已经过时,现在,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已取代社会学,成为对历史学最有影响的学科。
二、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三种理论取向
从其兴起历程看来,历史人类学主要是由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者,相互借用对方的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学科。由于来自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向对方学科借用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来自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术流派,对于历史人类学也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因此,与其笼统地界定“历史人类学”的内涵,不如厘清各个不同学科,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术传统,在理解这门学科上有什么不同。这里着重介绍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英美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与中北欧的欧洲民族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一)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
从历史学的本位看,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结盟的契机,在于从事件史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变。广义上的事件史,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其主要形式是叙述史。处理这种主题,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可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题,如社会结构、象征、仪式,就远非传统方法所足以处理了。所以,一般论者都强调有必要借鉴人类学处理这些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汤普森曾指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不在于建立模式,而在于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重视仪式,注意各种暴动和骚乱所体现的功能,强调权力、控制和文化霸权的象征性表述。戴维斯(Natalie Z. Davis)的看法比较相似,不过,她还特定提到田野调查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令人类学家可以观察到历史学家无法洞察到的问题。她认为人类学可供借鉴之处有四点:对社会互动的活生生的过程进行了细致观察;从饶有趣味的角度诠释象征性行为;讨论了社会系统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取材于与历史学家通常的研究对象截然不同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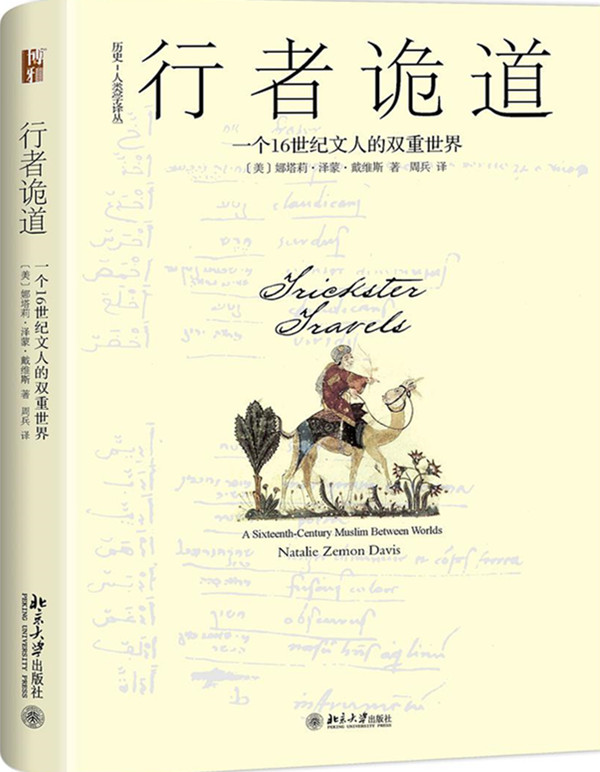
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人类学主要是“道德习俗史”,是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了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和心态习惯,而这些习惯都可以统称为心态,因此,至少从年鉴派史学家的理解看,历史人类学的领域和心态史的领域是十分接近的。年鉴派史学家比尔吉埃尔(Andre Burguiere)建议,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生活中或可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习惯,它应该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等介于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课题。在研究诸如饮食行为的演进等问题时,“我们既可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研究文化系统史。历史人类学的明确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学科的交叉点。”
彼德·伯克(Peter Burke)和古列威奇(Aron I. Gurevich)的民间文化研究,虽然使用的主要不是心态史而是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其研究主题仍可归入广义的心态史范畴。伯克对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引述了大量不为以往史学家所注意的资料,试图考察隐含在这些资料里面的、非常难以捕捉的日常感性和文化内涵。这种研究方法和利奇对文化与交流的讨论是息息相通的。伯克对路易十四的研究,不再因袭以往光给这位法国国王树碑立传的做法,而是广泛收集各种文本和石刻、铜版、绘画乃至蜡塑资料,透过同时代人的眼光,考察“太阳王”的公众印象。伯克称撰写该书的目的不在于立传,而是写“交流史,象征形式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历史”。不难看出,格尔兹对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的研究,对伯克的研究是有深刻影响的。古列维奇对欧洲中世纪民间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更重视发掘中北欧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教区层次的天主教”,强调社会各阶层文化和信仰的差异。他认为其历史人类学研究考察的仍是文化和心态的历史。
必须指出,传统的事件史处理的是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既已过去”。相比之下,新社会史和文化史涉及的是变动较少的历史,是“长时段囚牢”(布罗代尔语)和“静止不动的历史”(勒华拉杜里语)。可以说,战后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的最初动机,在于学习人类学家处理共时性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力图在看似变幻无常的历史现象背后,找寻常态的深层结构。一句话,他们所寻找的是不变。

(二)英美人类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
和历史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尤其是英美等国的人类学家,向历史学家学习的动机,是如何将文化历史化(to historicize culture),换句话说,是如何赋予“没有历史的人民”以历史。综合来说,他们是从三个方面把握历史的。历史首先意味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尤其是欧洲的海外殖民和资本主义扩张。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夏威夷群岛早期历史的研究和康玛若夫(Jean Comaroff)对19世纪初以来南非一个部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历史的第二层意思是历史意识。不少学者认为,不同的文化不仅有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有不同的历史意识。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对菲律宾山地易隆格人猎头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历史的最后一层意思,是历史编撰学,也是历史书写的问题,罗萨尔多对此也有多有论述,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对美国马西皮地区印第安人认同的研究,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是人类学家撰写的最为杰出的历史人类学论著之一。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萨林斯考虑的是如何将历史引进结构。他的出发点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重视语言而尽量排除对言语的考虑,反映在文化研究上,就是重结构而轻实践。在一般情形下,结构提供的一套范畴,是足以应付实践带来的各种意外情境的。可是,当两个迥然不同的结构相互接触时,其结果就常常不是结构所能包容的了。因此,结构将变形乃至解体,结构的再生产变成结构的转型。萨林斯认为,18世纪后期夏威夷群岛的历史便是如此。当英国殖民者库克船长来到夏威夷之时,当地的波利尼西亚人根据本土的文化范畴,将其奉为神明。可是,在随后的接触中,土人的文化范畴不再能有效解释和包容文化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实际问题。当地男人和女子、头人与平民、头人与神明的关系发生变化,禁忌制度土崩瓦解,阶级关系应运而生,最后,连夏威夷土著文化本身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1980年出版的《易隆格人的猎头活动,1883-1974》一书中,罗萨尔多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书中不乏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扩张如何影响菲律宾土著社会的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罗氏讨论的重点。罗氏力图传达的,主要是易隆格人的历史意识。在和易隆格人交往的过程中,罗氏发现,他们拥有和我们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其一,他们是以风景而不是日历,也就是以空间的形式来认识和描述时间的。在易隆格人讲述的故事中,故事的主要线索是地点的转移:从某岩石到某山丘,再从某山丘到某小溪。其二,历史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让易隆格人可以比较有弹性地组织社会关系,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其三,象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每一代的易隆格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代的历史都很不相同,但可以观察到一个周期,即猎头的频率在相对频繁和相对罕见之间交替。因此,易隆格人并非没有历史,只是他们体验和描述历史的方式和我们迥然不同而已。在传达易隆格人历史意识方面,罗氏是下了苦功的。他不仅曲意提供个人生活史来展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而且通过同类组群分析法(cohort analysis)来把握各代易隆格人历史体验的差异。在这种意义上说,本书为如何在“写文化”的同时兼顾历史表述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
(三)中北欧欧洲民族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
过去,英国和法国都拥有众多殖民地,人类学家可以到非西方的“原始”部落进行田野调查。美国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殖民地比较少,不过,由于国内印第安人分布很广,人类学家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但是,德国、瑞典等国过去没有或仅有很少的殖民地,导致研究本土的民俗学和欧洲民族学格外发达。从19世纪开始,当地民俗学家便对正在消逝中的乡民社会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调查,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民俗学资料,形成了也许可以称之为“内向发展”的学术风格。目前,当地不少大学都设有欧洲民族学系,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根据传统的理解,这门学科研究的是乡民文化和乡村史。在一些国家,民族学还包括了民俗学和社会史。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和历史学的对话自然比较没有学科的制约。尤其在年鉴派的影响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为当地欧洲民族学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由两位瑞典欧洲民族学家合作撰写的《文化的建设者》一书就是一个例子。
《文化的建设者》(中译本译作《美好生活》)所要挑战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现代人的时间观、自然观、家庭观和对灵与肉的看法,是属于人类的亘古不变的东西。弗里克曼(Jonas Frykman)和洛夫根(Orvar Lofgren)致力于解构这一观念。他们指出,这个观念实际上是19世纪市民阶级的文化构建。通过分析1880到1910年的瑞典社会,他们发现当时的市民阶级对于何为美好而适宜的生活自有一套标准。它们体现在日常的琐碎生活中:守时,自律,讲究卫生,热爱大自然,举办生日晚会等。市民阶级将之视为社会进化链上最高阶段的文化标准,并将之转化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向全社会灌输,后经长期渗透,演变成社会上绝大多数分子共同的信条。他们认为,市民阶级构建这套文化规范的动机,一方面是将自身与没落中的贵族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是与他们视为不守规范、桀骜不驯的工人阶级划清界线。通过他们的精彩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甚至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

三、几点思考
通过考察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源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要发展中国的历史人类学,除了不要忘记向西方取经之外,更要注重本土的学术资源,注意从本土的学术传统出发,探索自身发展的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学术传统和中北欧的情形比较相似。从30年代开始,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类学家就十分重视并积极从事本土社会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子,与英美主流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做法大相径庭(Leach即指出此点),而与中北欧的欧洲民族学“内向发展”的路子十分相似。同时,中国也有相当深厚的民俗学传统。司马迁注重实地考察的事迹不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顾颉刚、周作人、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即已倡导“走向民间”,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学者走进老百姓中间,发掘民俗学资料,收集了大量材料,不少对今天仍很有启发意义(如顾颉刚对泉州土地神的调查)。还必须提到的是,以傅衣凌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已自觉到民间发掘各种私文献、碑铭乃至口述史资料,并将之引用到具体研究之中,他们可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开山祖”,而这些学术传统应可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一批历史学者,与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史学者一道,在中国各地合作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田野调查,规模较大的有大陆和香港学者合作主持的“华南社会研究计划”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所谓“三方两国”的学者合作进行的“闽台文化比较研究”。在这些调查中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不仅反映在不少出色论著的出版,而且在制度的建设上也得到了证明。作为一门学科,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已初见端倪。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怀疑。他们觉得,田野调查的方法,充其量只能了解晚近的史实,我们如何能够应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明清史乃至隋唐史、秦汉史呢?笔者认为美国学者提出的“文献的田野调查”这一概念,也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文献的田野调查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文献的田野调查可以理解为文献研究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相印证的研究方法(field work of the archives)。我们知道,历史文献有多方面的局限性。它们反映的不仅是识字阶层的观点,而且仅反映了社会和文化某些方面的事实。为获致对历史的全面理解,我们就不能不到田野中收集资料。在田野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索人们如何生产、传播和解读各种官私文献,而且还可能收集到文献无法提供的社会文化事实。更进一步说,在田野中,我们不仅能够收集到各种文献和口述资料,而且对社会也可以获得相当感性的认识,获得陈春声教授所说的历史的“现场感”。这点光靠阅读文献是根本无法获得的。
另一方面,文献的田野调查也可理解为在文献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 in the archives)。不难理解,在这里“田野调查”是个隐喻,意思是透过历史上的“人类学家”的眼光,来探索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化。在欧洲史研究中,宗教审判曾为现代史学家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对蒙塔尤的研究和金兹堡(Carlo Ginzburg)对16世纪意大利一个磨坊主的宇宙观的研究,都得益于这些资料。金兹堡曾撰文称宗教法庭的法官为“人类学家”(Ginzburg 1990 [1986])。他们的研究都可说是在文献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典。中国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可堪媲美的资料,可是,我们也有丰富的文献和档案,一些海外学者已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优秀的论著,我们应该也可以拿出同样出色的东西的。
从这两方面看,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基本上无法应用到中国史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文献的田野调查的上述两重意思,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特别是在进行第二种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时,要通过直接访问了解久远的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研究者仍可走进历史发生和发展的现场,感悟历史文献所无法传达的信息。在研究1294-1324年的蒙塔尤村时,勒华拉杜里曾亲自前往该村实地考察,而戴维斯也曾造访马丁·盖尔生活过的村落,与村中老妇人聊天,其原因应该即在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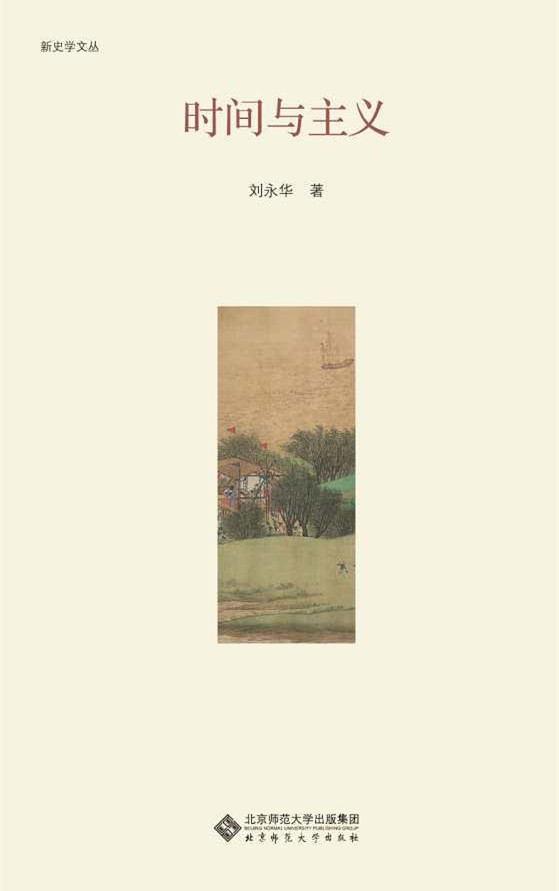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