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川端康成用文字打下密密实实的结,解开时犹如银河坠入身体

提起日本文学,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浪漫”或者“哀愁”。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今晚的月色真美”,被打上了浪漫表白金句的标签;“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信心,对人类满是怀疑”被编入一篇篇“太宰治丧系语录”,成为丧系青年的口头禅。
在碎片化语句的侵袭下,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印象逐渐单一刻板化。
实际上,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化体力”的普遍衰退,虔诚而完整地阅读一本书越来越难。

作家、评论家杨照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阅读。不仅自己爱读,也爱为他人解读经典。他迄今为止出书上百本,其中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讲给大家的中国史》《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
近期,杨照老师解读日本文学经典的新书——《日本文学名家十讲:我与世界挣扎久》(上辑5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5册书介绍了5位大名鼎鼎的日本文学大家: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
在《银河坠入身体: 杨照谈川端康成》中,杨照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别样的川端康成。幼时于亲人葬礼成长起来的川端康成,在国家战败与挚友去世的双重打击下,早早有了生命的“徒劳”之感:苟活余生,何以为继?

纤细敏锐的川端康成在小说中找到方法:小说可以凝结时间——那既是瞬间,又是被凝结固定住的恒常,两者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张力,迸发一种难以言喻的美。而在战后崇尚西方的风气下,川端康成作品中多层次的人心流转、人情美善,强烈的时间感知以及社会关怀视角,不仅为日本焕活了其本身的文明价值,更使其重新被世界看见、重视。
在对川端康成原著的解读中,杨照提供了自己的切入方式,以及对“物之哀”美学理念的深入诠释。
川端康成与“孤儿感”
在我了解川端康成、形成阅读川端康成的方式过程中,最有帮助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由三岛由纪夫所编的《川端康成论》,收录了那个时代日本文坛对于川端康成其人其作的方方面面意见,那是我在京都古书店里找到的一本精装旧书。另外一份是1949年,川端康成五十岁时,由新潮社出版的全集,一共有十六册,每一册都收录了川端康成自己特别撰写的“后记”,交代自己写卷中作品时的生活背景。这十六篇文章合在一起,等于是川端康成的早年自传,但可惜的是从来没有另行结集出版。我是早年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读这套书时,将所有的“后记”影印装订保留下来。
塑造川端康成生命最特殊的因素,据他自己所说,是“孤儿感”。从小如此孤单,亲人一一离去,以至于有一段时期他完全不说话,不知道要对谁说、说什么。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没有交过什么亲近的朋友,一度曾有过未婚妻,却没有结果,未婚妻离他而去,给了他更大的打击。
他在安静得近乎病态的环境中长大,这使得他的感官格外纤细敏锐。吉行淳之介的评论中说,川端康成和语言间有着奇异的关系。一般人运用语言时会受到社会习惯强烈影响,内化成一个“大声音”,听从那个“大声音”来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依照大家都认同的比例在语言中分配、表现重要性不同的事物。
然而在川端康成长期不说话的那段人格形成过程中,却给了他一种不受“大声音”影响的经验,以至于他会用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凸显描述、形容我们早早就认定了不重要,以至于不会去用心体会的琐碎、细密情感。

最好的例子是小说《雪国》的开场。《雪国》是极具川端康成前期文学语言风格的作品,读过的人一定记得第一句:“过了国境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同时也一定不会忘掉接下来两三页中的描述。
主角岛村坐在火车里,冰天雪地中火车停下来了,旁边的女孩将窗子打开,向月台上的站长讲述她弟弟的事。然后窗子又关上了,岛村开始回忆大约三小时前的事情。那就是用很细腻的方式呈现了我们一般不会那么认真去追索的脑中快速变动的联想。
岛村看着自己的手指,唤起了想用手指去触摸搭火车要去会面的女人(驹子)的感觉,想象延伸到气味,于是忍不住像是要嗅闻到留在手指上的女人气味般将手指凑近到自己的鼻子前,立即又意识到这样的行为看来很奇怪吧,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不自主地将手指移开,为了掩饰,就装作像是要用手指去擦拭因内外温差而满布在窗子上的水汽似的。他真的用手指在窗上画了一条线,没想到竟然画出了一双眼睛,让他吓了一大跳。定神之后,才发现那是火车上旁边女孩(叶子)的眼睛被反射映照在玻璃上。
读过了会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样的描写违反了我们感官与记忆的比例原则。这一段内容写了近千字,从三小时后的现实联想回溯三小时前的记忆,而三小时前的经验却又是开始于一段手指的想象,换句话说,在现实中没有发生任何事,岛村就是一直坐在火车上,但川端康成竟然能给我们如此丰富紧实的描述。
这段文字中,时态不断流动,三小时前岛村心中在向前想着即将要去和驹子会面,因为有未来的提示,才会让他想象这手指就快要触摸到那个女人了吧!三个小时后叶子对着窗外向站长诉说弟弟的事,同样是混杂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而明明和岛村不过是在火车上偶然坐在同一车厢的陌生人,神奇地,这个女孩竟然已经在他心中有了穿梭过去时间的记忆。
时间不会停留,真实的时间甚至不会一直向前流淌,而是如此不可控制、不可预期地在我们的生活、意识中晃荡,这是“物之哀”的根源,在时间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固态的,没有什么可以被人扎扎实实掌握。
他用绵延浓密的语言去写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遑论去记录的感受,反过来唤醒了读者如何去理解自己在生活中被社会“大声音”给消灭、排除了的细节观察与体会能力。
《伊豆的舞娘》开场的三种翻译
这种特殊的写法来得很早。川端康成二十八岁出版的《伊豆的舞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部小说的开头,是描述中学生川岛走在路上,很怕跟丢了前面舞踊队的焦急心情。
第一个句子:
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山林,从山路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
还有另一种译法:
山路愈来愈崎岖,已经快到天城山的山顶了,雨却在这个时候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袭来,浓密的杉树林顿时被笼罩成白茫茫的一片。
再看另一个译本:
当道路转入羊肠小道,心想就快到天城岭了,雨水把浓密的山林染成一片灰白。从山路以惊人的速度追上了我。
川端康成写的日文原文意思是,道路在前面弯折,表示本来是比较直的却开始变弯了,在那变化中,让他觉得(想象)也许天城岭快要到了。一直走一直走,遇到了道路弯折变化,于是想:或许天城岭接近了,反映了他焦急却又不知道究竟还离天城岭多远的心情。
原文中他将眼中所见的情景用汉字写成“雨足”,雨像是有脚一般,从底下一路将山林染白了,以快得令人惊讶的速度追上来。这又是非常形象化的写法。
或许如此你们能够稍微体会,少年的我为什么如此自不量力、热切地追求要有能力阅读川端康成小说的原文。他的日文有很多几乎无法翻译的细腻之处,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川端康成的响亮名号,他的作品在中文世界里有很多译本,大部分译者的日文和中文能力,不足以传达,有时甚至不足以理解川端康成文字中的特殊感性。
让我们不要忘了,很长一段时间,川端康成在日本文坛属于“新感觉派”。川端康成写出的文字,都来自主观的感觉。一个称职的中文译者必须先自行理解什么是“新感觉派”,掌握了“新感觉派”的美学信念,尽可能在中文中以各种方式,包括灵活运用语气助词,让读者能够明白什么是主观的感受,和客观描述区分开来。
“新感觉派”的主观描绘
《雪国》中著名的第一句话,意思是:穿过国境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表面上看起来是全称的叙述,但实际的效果是介于客观与主观间的暧昧。有中文译本将《雪国》书名译成《雪乡》,就错失了川端康成运用“雪国”汉字制造的效果。并没有一个客观的“雪国”存在于隧道的另一端,而是长长的隧道,加上冬天通过隧道后突然映入眼中的一片白色雪景,造成了如此强烈的感觉——仿佛离开了原来的国度,进入了另一个如梦似幻的国度。尤其是在夜间这种感受更强烈,隧道里是黑暗的,本来出了隧道的夜也是黑的,但地上的雪色,似乎将夜的背景都染白了——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人的主观感觉被带离了日常环境,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因而都有了幽微的传奇色彩,包括听见一个少女打开车窗对着月台说话的声音……
我们是这样随着岛村(即使那时我们还不认识他)进入“雪国”,跟着他产生了一种恍惚不实之感,所以他会想起几个小时前同样恍惚如梦地出现在车窗玻璃上的一双眼睛……

《雪国》同名电影剧照
如果将“新感觉派”的文字理解为客观的,就体会不到《雪国》开头这段的力量,也体会不到《伊豆的舞娘》开头的情境。那段话不是要客观描述在上到天成岭的隘口前,会有一段弯弯曲曲的路程,而是反映少年高中生赶路的心情,这时候路上任何的变化,都会刺激从而产生鼓舞作用:啊,我把直路走完了。不过立刻又有相反的心情袭来,他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任何可能迟滞他赶路行程的因素,这时候那个可怕的潜在因素就正从山底升起。
雨来了。山里的雨确实会随云雾水汽上升,不过在这里雨被主观地拟人化,像是长了脚快速地追来,而且追得特别急,因为主观感受者万万不希望自己被雨给耽搁了向前赶上舞踊队的路程。
“新感觉派”的崛起,是对应、逆反当时日本文坛主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而来的。写实主义重视客观性,到了自然主义甚至进一步援引科学信念,要将小说变成人与社会互动的实验场,以“遗传”与“环境”为两大变量,在小说中有意识地探索、铺陈“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样的信念更是注重客观而轻忽、摈弃主观。
“新感觉派”反对过度的客观,要将主观放回文学中,恢复主观感受在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谷崎润一郎早期的作品,也同样出于对自然主义的不满而凸显主观感受,不过他的小说情节充满夸张奇情,和强烈的主观感受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疯狂的性质,是在转述、传达了疯狂的人眼中所见到的世界,从疯狂的极端情绪中领受的周遭环境。
相对地,在川端康成笔下,他开创了新的文字,描述一个“正常”的高中生在特殊情境中的特殊感受,使得世界变得不一样。客观的世界,大家都同样感受的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尤其没有那么值得书写,正因为对大家都一样,也就不是任何人平常真正会感受的。对我们有意义的事物,一定是通过特定的主观,染上了特定的感情色彩,才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体验,成为记忆。
舞娘的对话
《伊豆的舞娘》的叙述者是一个二十岁的高中生,以现在的学制来说,比较接近是刚上大学的年纪,他在路上遇到、爱上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这样的故事在日本长期以来就被当作是最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内容。
然而中学生能从这部小说中读到什么?尤其是现今的中学生,让他们看一段甚至没有明确戏剧性的故事,男学生一直追着舞踊队,最后走到大田就结束了,没有明白的结局,他们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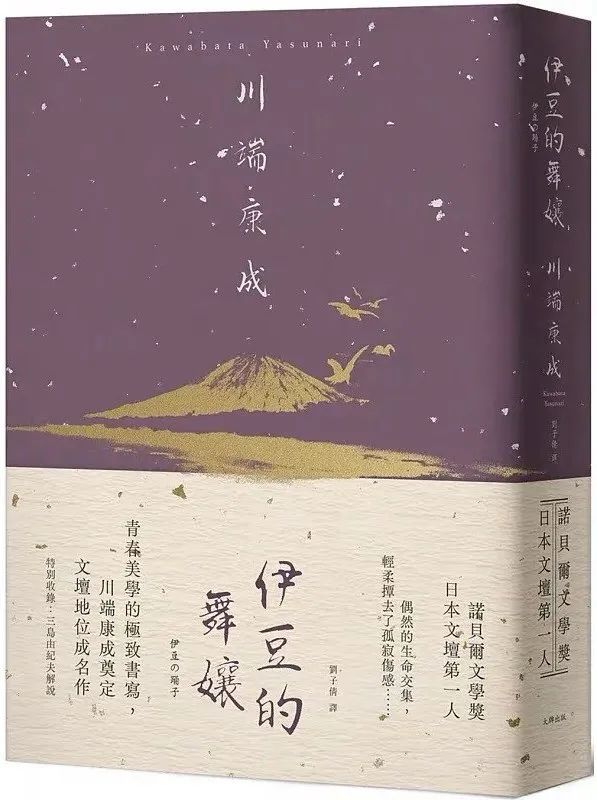
日本知名评论家,也是小说家吉本芭娜娜的父亲,吉本隆明就曾经说:《伊豆的舞娘》一定是日本文学史上最常被重读的一部作品。因为很多日本人在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通常都不喜欢,但会留有印象,然后等到累积了足够的人生经验与理解后,会在一个阶段产生冲动,想要重读《伊豆的舞娘》。这时候它不再是学校的指定作业,也没有老师来引导你,纯粹为了自己而阅读,突然之间,就得到了深度的感动与丰富的领会。
长大了之后才会被一些段落感动。例如叙事者“我”偷听到舞踊队里两个女生,千代子和熏的对话。两个女生在谈论他,来回总共说了三句话,一开始是熏,她称赞这个男学生:“是好人啊。”然后千代子响应:“是啊,是这样没错,应该是好人。”然后熏又说:“真的是好人啊,好人很好。”
三句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几乎没有具体内容。都是空话,只反复表达:是好人,真是好人,用词也再单调不过,连声音都是单调的,“好”就重复了五次,“好人”重复了四次,还有“是啊”这种重复的方式。
但这么简单的话中却带有真情。千代子说的“是啊”在日语中带有随口认同敷衍的意味,加上后半句用了“应该是吧”,语气上又是有保留的,于是熏才又特别重复强调:真的,他真的是好人,有这样的好人真好。那样的说法中显现出一份焦急,一定要说服千代子:这个男孩是好人。
中学生无法领会的,往往是我们透过不够精确的中文翻译也无法领会的,是这段对话来自两个如此素朴的人,素朴到近乎无能的人,但她们如此努力要表达对这个男孩的肯定与喜爱。她们没有足够的语言可以使用,但简单到这种程度的话,却带有一种无可取代的天真,不可能掺杂任何一点点虚假。
“我”不经意听到了这样的对话,被深深感动了。活在“孤儿感”之中,和世界有距离,在世界上得不到归属,如此单调的对话,带来最深切的安慰。两个女孩,尤其是熏,如此天真地信任他,如此深挚地强调他的好。这是中学生领受不到的关键,具体、清楚地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对舞踊队产生如此的迷恋,那不是一般的少年对女生一见钟情,而有着更深厚的执着依恋。
(《银河坠入身体:川端康成》杨照/著,春潮Nov+·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版)
文章编辑:张滢莹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资料图

原标题:《川端康成用文字打下密密实实的结,解开时犹如银河坠入身体|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