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文学的变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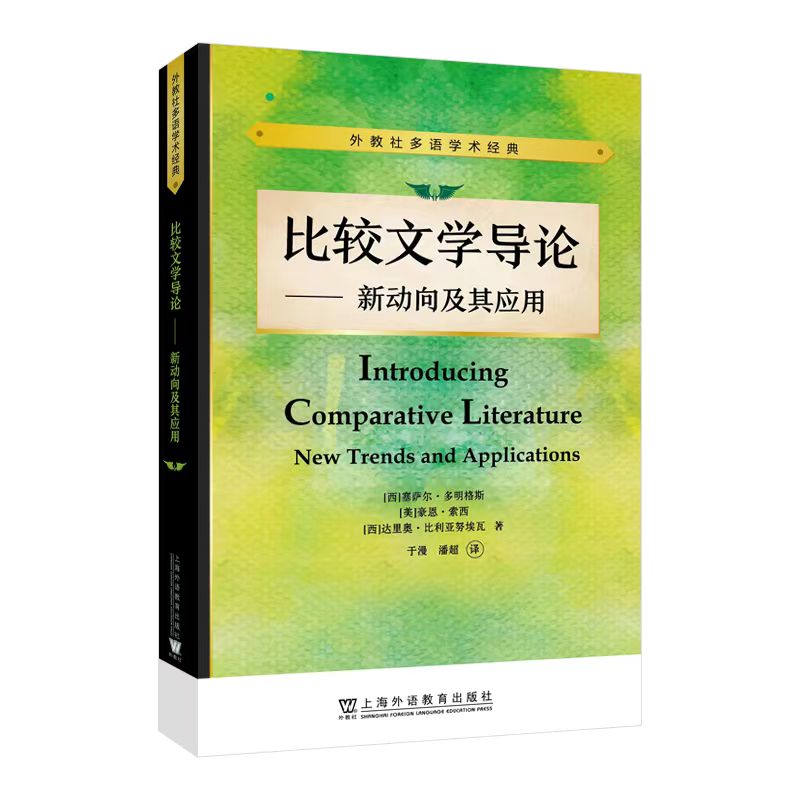
《比较文学导论——新动向及其应用》,【西】塞萨尔·多明格斯 等 著,于漫、潘超 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
近185年以来,“世界文学”一直被当作思考比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比较文学则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探索、文学评价视野、阅读和教学目标准则、教学项目和研究领域的形成。各种各样的原因促进推动了这一主题下不同变奏曲的发展变化,因此,将所有这些变奏集体性地归结为相同的指称或含义似乎有些夸大;而且,正如在比较文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世界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宣扬的远大抱负与我们实际达到的目标终究还是两码事。“世界文学”总是(正如歌德在1827年所言)即将来临;它是一个期望中的目标,一个未来的巅峰时刻,一个没有能够愿望成真的标准。无论在某个特定时期“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表达背后所蕴藏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断地在形式和逻辑意义上定义文学研究与文学领域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必须要认识“世界文学”,其作用在于“审视我们以前的文学思想观念中被忽略的种种,现在让我们去努力超越这些限制”。
世界文学隐含着对世界的定义。歌德曾用这个表述作为与“民族”文学相对立的概念,尤其是对19世纪早期德国视为从(主要是法国改编古希腊古罗马的)新古典主义模式中获得文化独立的“民族”文学的一种回应。于是乎,在一套共认的普遍性体裁、风格和标准已经被“民族”特殊性所取代的前提背景下,在歌德热切期盼的想象中,“民族”文学很快将会让位给“世界”文学,而且那个“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充满了同质性的空间,而是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歌德这种关于“交流”的论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脑海中打下了烙印,他们在1848年写道:
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各个民族的知识创造成为共有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土崩瓦解,于是在众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诞生了一种世界文学。(Marx and Engels 1948 :12—13)
审视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尽管使用了相同的名称,但他们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却不尽相同。一部中国小说促使歌德认识到写作创造的“人类共同财富”以及由它们记录下来的思想和感受;因此他敦促读者群里和作家同仁们走上更加广阔的舞台,共同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建设中来。而《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则把“世界文学”兴起的条件认定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让世界各地趋于大一统。歌德认为他发现了普遍存在的人性这一事实,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是由资产阶级促成的;歌德预见从差异走向融合,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有“民族和地方的”差异都将成为过去。
双方的论述全部成立,但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很好地辨别模棱两可的含义。毋庸置疑,用语言创作艺术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能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展现这种能力,也并非每个人类社会都能平等地培养这种能力。在我们能够认同另一个人类群体的“文学”之前,必须有人进行翻译、充当媒介或展开类比,将一个单纯的行为转换成文学。
易洛魁人的作品,即使充满荒谬,也是无价之宝;当我们置身于从未经历过的环境中,并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宗教观点的影响时,它能给我们提供人类心灵运作的独特样本。我们有时应该对由此产生的反向思维感到惊奇并受到启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应该学会拥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且应该学会感受这些观念的力量。(爱德华 · 吉本,《一篇关于文学研究的文章》[1761],引自Reiss 2004:136—137)
童话故事在世界各地流传了数千年,但只在近几百年它们才被归属为与史诗、抒情诗、戏剧比肩的文学类型。当一个古代文明被发掘出来,覆盖在这个文明之上的泥板得以被破解之时,学者们必须确认其留存的内容中哪些是历史、法律、统计、祈祷,哪些是文学。当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人类群体接触到另一种文明时,他们的一些歌曲和故事可能会借助翻译、选集和鉴赏而成为“文学”。自20世纪早期的达达运动以来,无意义的音节、彩票和传单只要以文本形式呈现并被接受为艺术表现,都能被解释为文学。在所有这些归类和分类行为中,作为中间人的翻译者、批评家或文选编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负责在言语艺术领域做分配,执行文本挑选的任务。
歌德认可并欢迎外国(中国)小说家成为世界文学的同道者,却忽视了翻译者、出版商和其他许多为了作品能顺利地从北京到达魏玛而努力扫清障碍的经济、哲学、政治和技术中间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同质化活动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认为交流对象只是交流网格建立过程中的附带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注定会失败的“民族片面性和狭隘性”的历史遗留,却被歌德认定是作家和民族应该给世界文学盛宴带来的瑰宝。
如果对歌德来说,文学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好处是增加了文学多样性的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此后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消除贸易障碍是迈向统一的必经之路,能够在最大范围的市场上成为最易于估值并交换物品的贸易者,就可以从规模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对于这一区别,可以说,歌德间接地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为,让歌德感知到中国人微妙情感的那部作品是一本白话体小说,一种比传统文言文作品更便于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文学类型;白话小说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与欧洲人熟悉的浪漫传奇小说交相辉映。相对于东亚地区的许多其他文学类型来说,中国小说在被歌德以及其他读者接受的道路上已经先行了一大步。(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和日本的诗歌才得以翻译成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表达形式。)对于世界文学来说,一个没有得到读者回应的风格或作品无异于失传—尽管对于(像爱德华·吉本这样想象力丰富的)异域读者来说,这样的风格或作品的文学价值无与伦比。因此,在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中,仅仅凭借着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等先驱的叙述,我们就能意识到,非常有必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详细的鉴别和语境化的理解:
● 全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与接受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各不相同的感知模式及特有盲区相比较;
● 跨时代和跨文化共情能力,与译者及译入国文学史的媒介作用相互比较;
● 作品和文化的个体特征,与文化交流市场相互比较。
任何情况下,当一部作品提升到了“世界文学”的地位,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认定这仅仅是其中的某种特殊因素的结果,不能因而就排除其他对应的相关因素。
(本文节选自《比较文学导论——新动向及其应用》,【西】塞萨尔·多明格斯 等 著,于漫、潘超 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