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周立红:年鉴学派的时代背影——追念勒华拉杜里教授

勒华拉杜里
他走了,一个时代落幕了。
勒华拉杜里教授,这位《年鉴》杂志的同龄人,这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转向中仍坚持“物质基础”的“布罗代尔主义者”,这位驾驶着年鉴学派这艘装满沉甸甸遗产的大船驶入21世纪的老人,我们可能要承认,随着他的离去,由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创,由布罗代尔赋予国际标签的那个原汁原味的年鉴学派已经寿终正寝。
转益多师、海纳百川
勒华拉杜里教授1929年出生在下诺曼底卡尔瓦多斯省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业资产阶级家庭,父亲雅克·勒华拉杜里致力于农业开发和工会活动。小勒华拉杜里在博卡日特色的田园风光里长大,听惯了父亲对天气的念叨,这是他日后研究乡村史和气候史的原始冲动。1940年法国的溃败在幼年的勒华拉杜里心里留下了创伤,随后他就读的中学被德国人占领,只能转到天主教开办的学校读书。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由于战斗过于激烈,卡昂这座美丽的省会城市在战火中几乎被摧毁,勒华拉杜里多位亲人遇难,战争就这样让他产生了“一种顿感过去破裂的悲怆之感”。
1945年,这位诺曼底的青年来到巴黎,先后在亨利四世中学和拉卡纳勒中学的精英学校预科班就读,1949年考入巴黎高师。在这期间,勒华拉杜里的政治意识觉醒了,受到战后兴盛的左翼思潮的影响,他加入当时法国的第一大党——法共,参加学生共产主义者联盟,后来又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勒华拉杜里这段激情的青春岁月恰恰赶上了二战后法国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1945年国家人口研究所成立,次年《人口》杂志创刊,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建立,国家科研中心还建立了社会学研究中心。1947年,法国的大学开始教授心理学。历史学踌躇满志,承担起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思考人类命运”的重任,在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中开疆拓土,并力求将人文科学汇聚起来建立“通用的语言”。勒华拉杜里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历史研究萌生了兴趣,受教于多位史学大家。
勒华拉杜里在巴黎高师读书时,曾上过让·默武莱的课。默武莱是一位能把研讨班从课堂上开到大街上、咖啡馆里的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这位当“20世纪只有1岁时出生”(默武莱出生于1901年,这是他调侃自己的话)的历史学家,是一位在亨利·豪瑟的指导下撰写了一篇从来没有答辩过的博士论文的传奇人物,一个“喜欢在学术丛林中缓行的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研究路易十四时期生计问题的大家。默武莱在巴黎和外省的档案馆收集了大量有关谷物价格、货币流通、气象信息的史料,不厌其烦地给学生们讲授计量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们使用工具书。他在课堂上多次讲到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的经济危机,几年后当勒华拉杜里在朗格多克的档案馆里发现了丰富的气候史料后,就想到要考察气候变化与17世纪危机的关系。
1955年,勒华拉杜里开始跟随巴黎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拉布鲁斯攻读博士学位,后者与布罗代尔齐名,曾共同主编多卷本《法国经济社会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布鲁斯门下还先后汇聚了皮埃尔·古贝尔、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佩罗、让·尼古拉、弗朗索瓦·孚雷、雅克·奥祖夫等五六十名青年才俊,他授意每个学生选择法国一个地区,研究该地在近代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勒华拉杜里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朗格多克的乡村社会”,后来以《朗格多克的农民》成书出版。勒华拉杜里从拉布鲁斯那里学到了著名的“抽屉理论”,即社会依次由五个层次构成:经济的、人口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心态的。同时他还受到拉布鲁斯的感染,终生对数字感兴趣,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计量方法。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出版不久就引起了勒华拉杜里的注意。布罗代尔在书中预测气候自16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可以遵照弗朗索瓦·西米昂的A阶段和B阶段,梳理气候变化的周期,这成为勒华拉杜里进行气候史研究的灵感来源。1953年,勒华拉杜里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时,布罗代尔正是考试委员会主席,这大概是他们首次正式见面。勒华拉杜里通过考试后去蒙彼利埃中学任教,1960年又到蒙彼利埃文学院担任助教。在这期间,勒华拉杜里几次去巴黎拜访布罗代尔,结识了他周围那个正在革新法国史学风貌的群体。
1963年,勒华拉杜里受到布罗代尔的征召北上巴黎,加入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即后来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他帮助布罗代尔管理第六部的科研工作,还与勒高夫共同主编《年鉴》杂志,成了布罗代尔寄予厚望的学术传人。
拉布鲁斯的学生古贝尔,比勒华拉杜里年长十几岁,也成为他学术创新之路上的关键人物。古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中指出,17世纪的经济状况反映了“一种不规则的食物供给和人口增多之间的阶段性不平衡”,而天气是影响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可能存在一个30年气候变化周期。这一发现启发勒华拉杜里在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中提出了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即主宰社会史的主要力量是天气和性, 前者决定农业成败,后者决定要供养的人数。
因此,培育勒华拉杜里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开放浓郁的经济社会史氛围,成就勒华拉杜里的是他海纳百川般的知识吸纳和综合能力。《蒙塔尤》的成功得益于他受到美国乡村人类学的启发,从一个村庄的角度解读《雅克·富尼埃宗教审判记录簿》。《圣西蒙或宫廷体系》则把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的心智类别分析应用到路易十四的宫廷集团。为了破解气候一成不变说,他广泛阅读气象学家的著作,学习借用树木年轮、葡萄采摘日期、冰川考察气候变化的方法,并多次到阿尔卑斯山冰川实地考察。他的三卷本《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果,既借鉴了德国天文学家施珀雷尔、英国天文学家蒙德和德国气象学家卢特尔巴赫尔对蒙德极小期的论述,又参考了法国历史学家格勒尼耶、勒布伦、贝尔纳、贝尔塞、拉希韦等人对法国旧制度时期饥荒和生计危机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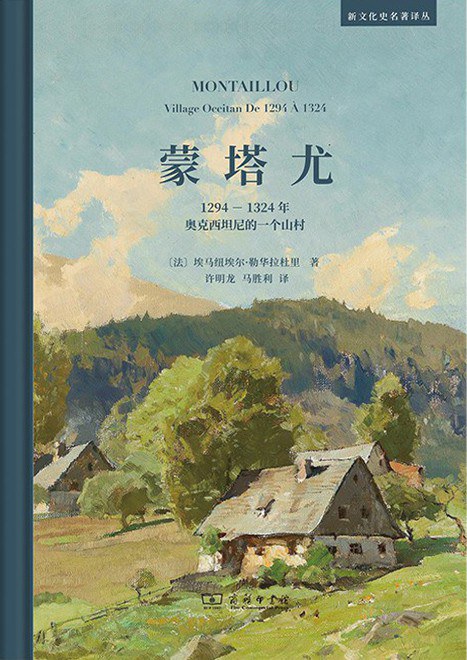
《蒙塔尤 :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年鉴学派第三代里的“布罗代尔主义者”
如果说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史家是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二代代表史家是布罗代尔的话,勒华拉杜里所属的第三代则是一个群体形象。在他之外,还诞生了雅克·勒高夫、马克·佩罗、弗朗索瓦·孚雷、让·尼古拉、米歇尔·佩罗、莫娜·奥祖夫、皮埃尔·诺拉、米歇尔·伏维尔、达尼埃尔·罗什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大都出生于1924-1935年之间,其中许多人是农民的后代或小学教师的子女。受惠于“共和国精英主义”的培养体制,他们在求学之路上步步登高,从小镇到省会再到巴黎。他们在少年时代撞上了二战,目睹了民族的悲惨命运和亲人的不幸遭遇,成年后又为当年没有能够参加抵抗运动内疚不已。
二战后,这一代历史学家大都来到巴黎求学,就读于巴黎高师或巴黎大学。当时的法国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逐渐恢复元气,迎来了三十年辉煌时期,法国也正在从农业国家快速地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法国的这一转变在精神上并不轻松,毕竟法国曾被德国占领,又建立过与德国合作的维希政权。虽然盟军赢得了胜利,但抵抗运动和戴高乐将军组织的自由法国运动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认可。战后又进入东西对抗的冷战时期,向来具有反思能力、为法兰西精神而自豪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文化观念领域里实现既非盎格鲁一撒克逊化,又非苏联化。在这种背景下,年鉴学派的存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出口,这也是这一代历史学家汇聚到年鉴学派旗下的一个原因。
他们在巴黎读完本科、完成高等研究文凭论文后,一般要经过一两年的辛苦备考才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然后再分流到外省的中学任教。在那个经济社会史鼎盛的年代,他们中有多人在中学教书之余跟随拉布鲁斯做博士论文,又同时求教于布罗代尔。拉布鲁斯不属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虽然曾被巴黎大学拒之门外,但这两大学术巨擘能够通力合作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共同提携史学新人,又帮助他们在巴黎高校或科研机构谋得职位。尤其是布罗代尔执掌的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为这一代人提供了不少职位。
进入60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后,年鉴学派第三代开始了学术突围,他们大都放弃了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范式,从“地窖爬到顶楼”,与新知识、新学科融合,开辟了政治史、心态史、书籍史、记忆史、死亡史、妇女史、儿童史等新方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
勒华拉杜里广泛参与了这场新史学运动。他开创了气候史,在1974年勒高夫和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第三卷《新对象》中撰写文章,讲述气候史的研究方法。他在1975年出版、后来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的《蒙塔尤》中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蒙塔尤村民的心态和社会交往,他还在其他著作中集中探讨了节庆、死亡、瘟疫、巫术、魔法阉割。他也是布洛赫所说的“好像传说中的食人魔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的丛林里到处搜寻人的气味。他专门研究过16世纪瑞士牧羊人托马斯·普拉特父子三人从乞丐到教授和王室医生的攀升之路,整理过18世纪法国乡村知识分子皮埃尔·普里翁的史料。他的书中不乏对人的生动描写,有14世纪蒙塔尤村在冬日的阳光里互相捉虱子的普通农妇和城堡主夫人,有16世纪诺曼底那位喜欢听女仆哼唱小曲儿的乡村贵族古贝尔韦尔老爷,有18世纪那位懂得与牛马交谈的勃艮第老农埃德蒙·雷蒂夫,还有19世纪贝纳西斯医生这位大刀阔斧的多费内山村的开发者。
但是与他这一代的很多史家以及后来兴起的欧美新文化史家不同的是,他所探讨的人和人群身处某个家庭关系、社会集团或权力层级中,被镶嵌在长时段的地理结构和生态环境中,生活在形塑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波动的气候中。他虽然爬上了“顶楼”,却从来没有忘记“地窖”,他始终坚持物质根基,致力于揭示形构人类日常生活的地理环境结构和深层力量。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布罗代尔主义者”,是年鉴精神的守护人。
他继承和发扬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渗透了他的总体史理念,试图综合社会经济史和心态史。他在导论中写道,他从研究土地目录开始,最终走向思考活生生的人,探讨朗格多克的农民群体。《蒙塔尤》同样是在总体史视野下进行的写作:从时段上来说, 该书由长时段历史时期中的蒙塔尤和1294-1324年的异端审判事件两大部分组成,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暗中呼应;从内容上说,该书分为两大部分,既阐述了蒙塔尤的生态,也考察了蒙塔尤人的行为举止、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在《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中,勒华拉杜里对总体史探索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依次探讨了从14世纪以来西欧每一年的气候波动,总结出每个世纪内十几年、几十年的气候波动趋势,还探讨了14世纪以来每一起重要的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法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或重要历史事件的气候背景。如果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从地理空间到结构局势再到政治事件,由远及近展现了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全景画,勒华拉杜里的《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则呈现出了一幅14世纪以来西欧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全景画。
他尽力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根基上。布洛赫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研究时间和变化的科学。布罗代尔希望借助长时段维护历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统摄地位。勒华拉杜里也倡导“使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历史学”。他收集广博的史料,进行田野调查,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采用系列史方法。他批判气象学家仅满足于廓清地球气候演变的大脉络,责怪地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尚未搞清楚气候本身的变化就从气候角度解读人类历史。他认为气候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借助历史学对时间阐述的精确性,同自然科学家交叉合作,编制出气象变化的主要系列。因此,在他开始研究气候史的近四十年时间内,他始终在做着“没有人的气候史”,小心谨慎地使用气象学、生物学和历史-统计方法,建构了公元一千年至今西欧一年一度的气候波动的精确系列,并按照年鉴学派的三时段理论,分层次地探讨气候短时段的波动和中长时段的演变趋势。这一充足的前期工作为探讨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学科根基,也使气候史摘掉了一度被同行嘲笑的“伪科学”的标签。
他与费弗尔、布罗代尔一样从法国人文地理学创始人白兰士那里吸取了“或然论”。《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超越了单一因果模式,从多个层次阐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一方面把气候因素的影响放置到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学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势中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受布洛赫的影响,“对一切可以比较的事物进行比较”,注重分析西欧各地同一时期不同的气候条件或不同应对措施造成的不同影响。
一个人的战斗
进入21世纪,年鉴学派前两代代表人物的弟子、还在坚守年鉴阵地的肖努(2009年)、古贝尔(2012年)、勒高夫(2014年)等历史学家先后离开人世,仍在公开宣称自己是年鉴学派后继者的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变得屈指可数,勒华拉杜里就是其中的一位坚守者。他紧握着年鉴学派这艘大船的方向盘,坚持物质根基和总体史观。他观察四周的形势,小心地调整着航向,尽力使事件与结构协调,对叙事史料妥协,主动向灾害史靠拢。他尽力避开暗礁,仔细辨明哪些属于年鉴学派,哪些偏离了年鉴学派,他与孚雷的观念史与诺拉的记忆史保持距离,又回过头肯定索布尔、勒马尔尚这些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计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在勒华拉杜里教授生命的最后15年,我有幸与他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见证了一位以史学为志业的老人最后的坚韧与孤寂。
2008年,我在巴黎人文之家从事“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博士后研究,勒华拉杜里正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而这时我听说他已患了严重的眼疾。起初我只是给他写了一封信,留下了联系方式,三天后便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充满朝气、听起来很年轻的声音:“我是勒华拉杜里,您想见我是吗?”就这样,12月17日那个周三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他位于巴黎15区的寓所。他夫人开的门,说勒华拉杜里先生刚打回电话,外面的rendez-vous(会面)还没结束,让我先等一会儿。于是他的夫人便把我带到了他的书房。
勒华拉杜里的书房要穿过客厅往左走,再经过一段走廊,是一个面向庭院的房间。书桌被安置在走廊这侧墙的书架前面,正对着宽大的落地窗,书桌前面与落地窗之间的大片空间被用作会客厅,摆放着一把椅子,左右两侧墙边还放置着两大排书架。房内的光线很好,即便是在阴天,开一盏小台灯便可以工作。宽大的书桌上摊开着一个大本子,旁边放着一个放大镜,紧挨着一个笔筒,里面放着笔、小刀、尺子,再往书桌下看,是两箱废纸,这大概是我们这位历史学家写作中产生的“垃圾”。就像孚雷一本文集的书名那样,这就是“历史学的作坊”。
这位当过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历史学家,把书房建成了一间正规的阅览室。书架上的书都编了目,每本书都贴有标签,写有编号,每一类别的书都放在一排,格子上贴着28a、28f、 38e、38fd等检索号。当我一个人坐在勒华拉杜里的书房时,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想寻找蛛丝马迹,看看《蒙塔尤》是怎样写成的。但我又提醒自己,不能在书房走来走去,更不能翻书,要不对主人是多么不尊重啊。我只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原地不动,环顾书架,突然,三卷本的《雅克·富尼埃宗教法庭审判记录簿》映入眼帘。三十多年前,勒华拉杜里就是靠这批资料重构了蒙塔尤这个小乡村的历史。
我又向四周查看,想寻觅更多的东西。我在《雅克·富尼埃宗教法庭审判记录簿》的右侧,看到了勒华拉杜里的另一本著作《诗人雅斯曼笔下的女巫》,在左侧看到了其他学者写蒙塔尤乡村文化的书。我在右侧稍远的地方,发现了勒华拉杜里的《法国地区史》以及几本有关地方史的词典。看完了左侧,我又向右侧书架望去,突然我看到了皮埃尔·肖努的大部头著作《巴黎死亡史》。20世纪70年代,“死亡史”研究风靡一时,肖努、伏维尔、阿利埃斯各领风骚,这个史学潮流自然逃不过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的视线,他也写了《奥克地区的金钱、爱情与死亡》。我想再往书桌后面的书架看看,可惜已经看不清了,只看到最上面两层摆着的是线装书,应该是一些经典文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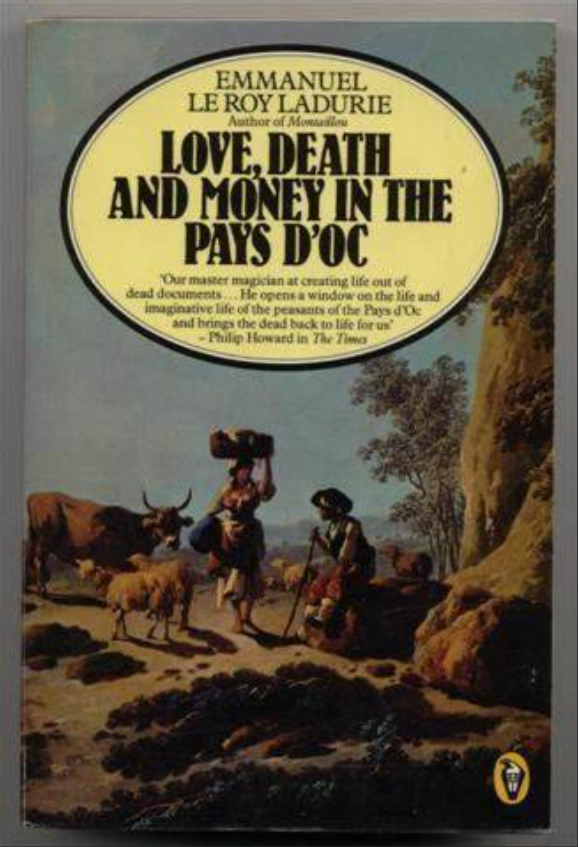
《奥克地区的金钱、爱情与死亡》
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听到了客厅里说话的声音,勒华拉杜里先生回来了。不一会儿,身材高大、步履蹒跚的《蒙塔尤》的作者进来了,他的眼睛已经不那么灵动,这应该是眼疾造成的。他摸着椅子坐在我对面的书桌旁,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与那天电话中朝气蓬勃的勒华拉杜里相比,今天的他可能由于刚从外奔波回来,已经显得比较疲惫。即便这样,他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我的一个个问题。他坐在那里,史实、数据信手拈来,还不时在纸上画出一个个气温变化图表。注重数据,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说话的风格,这大概是拉布鲁斯史学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访谈结束时,勒华拉杜里教授送了我两本书,并主动签名留念。但他一时弄不清我名字的拼写,便向我要了一张名片,放在书桌右侧投影仪下方,我姓名的拼音很快就闪现在了“屏幕”上。勒华拉杜里教授想摆正字母的位置,却怎么也弄不好。我去帮他,由于不熟悉这个设备,也没成功,他只好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让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名字,他再签字。他已经几近失明了,完全是凭着对文字的感觉在写。但是,学术的激情没有退却,研究计划仍在如期进行。他说,他还打算修订出版第三卷《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这是关于气候变暖问题的。他还笑谈道:“跟着这本书,我进入了20世纪。”
2009年,《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第三卷出版。2010年,阿努什卡·瓦萨克对他的访谈录《三十三个气候史问题》出版。2011年,勒华拉杜里又出版了《公元一千年至今的气候波动》。从2012年到2017年,他还接连出版了有关乡村文明史、法国旧制度农民史和旧制度断代史的著作。很难想象,这些丰硕的成果是一位几近失明的老人在夫人和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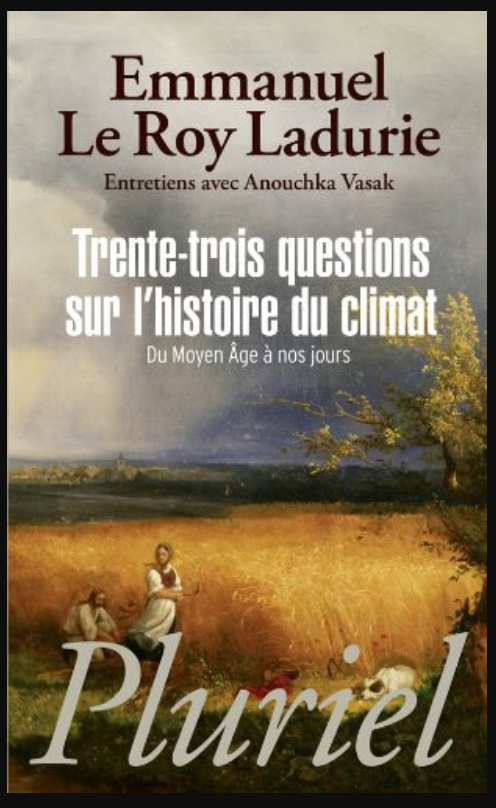
《三十三个气候史问题》
那几年,他一如既往地活跃,经常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宣讲气候史研究成果,讲述他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心史”(L'égo-histoire)。他不能出远门参加学术会议,便在家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各种推荐请求,他也总能爽快回应。2009年我回国后,他还写信询问我访谈在中国的发表情况,次年访谈在《史学月刊》发表后,我马上把样刊寄给他。2014年,我把刊发在《史学月刊》写他气候史研究的小文寄给了他,他还让助手翻译成法文,以便将来收入论文集出版。
又过了三年,2017年10月,我趁着在鲁昂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去巴黎拜访勒华拉杜里教授。这时,他双目已经完全失明了,在夫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到我面前的书桌旁坐下。我本来拟定了一个访谈计划,但是不管我问什么问题,总是被他拉回气候史。他讲述他研究气候史的心路历程,他说他是布罗代尔的衣钵传人,感叹当今的《年鉴》杂志把他边缘化了,没有给予气候史应有的重视。他遗憾没有培养出多少学生,对气候史的未来忧心忡忡。他还对中国的气候史感兴趣,问我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研究气候波动的代用资料,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是否可以成为参照,在那里生活的人群是否留下了什么记录。
气候史是他1955年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便致力于开拓的领地,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又成为他最后的学术执念。
他有他担心的理由。近些年来,法国的气候史研究虽说吸引了历史学界、地理学界、气象学界、文学界的学者加入其中,研究成果和发展态势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但是蕴藏着危机。一方面,法国当今研究气候史的实验室和跨学科研究组大都是以物理学家、地理学界和气象学家为主,他们缺少历史学的背景知识和问题意识,主要从灾害治理的目的和视角出发。在这些团队中,虽然也活跃着少数历史学家,但他们并不总能主导课题的研究方向,反而在项目的驱动下,向新的范式靠拢;另一方面,气候感知史、气候表征史发展起来,几位历史学家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新生代学者不懂计量史学,对考察气候本身的变化不感兴趣。总之,勒华拉杜里缺的是能够整合气象学和历史学,从总体史眼光推进气候史研究的后继者。
他也有他的遗憾。总体史的一个维度是全球史。布洛赫在《封建社会》总结出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还和拜占庭、日本的封建主义进行比较。布洛赫的《国王神迹》虽然主要研究的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法国王触摸治病的超自然性,但在附录里,他补充了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德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涂油礼的情况。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研究扩展到全世界”。 他凭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相关专家获得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史料,不仅在书中探讨了15-18世纪欧洲人口增加的趋势,还揭示了中国和印度相似的人口增长节奏。布罗代尔写道:“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物理整体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早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经济的相互渗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
勒华拉杜里又怎能不想探讨世界的整体性呢?他早在布罗代尔出版《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在《瑞士历史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通过跳蚤传播的巴斯德氏杆菌带来的全球一体化。气候的波动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的叙述范围往往超越法国,涵盖欧洲,有时还将美国、非洲、澳大利亚、阿根廷的情况纳入其中,但是基本上没有收入亚洲的情况。虽然勒华拉杜里发现,在1753-1756年,德国和日本都发生了饥荒,但他很快指出还没有材料证明两者之间是否真有联系。
勒华拉杜里应该不会没有关注到一些学者对17世纪欧亚气候危机的论断,但我想以他一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还是认为气候的人文和比较研究应该建立在精确的气候波动系列基础上。他首先想搞清楚的还是能够论证中国乃至亚洲气候波动的史料状况。我很后悔当年我对他的研究没有达到现在的领悟程度,没有想到把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成果整理给他看。我也遗憾他在学术精力还充沛的时候没有能够打开与亚洲学界的沟通合作渠道,虽然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建构他心目中的全球气候史的条件。
2023年11月22日,勒华拉杜里在他的家乡与世长辞。他的离去可能终结了一个学派,也可能带走了他一心要实现的那个科学的、总体的、人文的气候史的宏伟规划。但是,年鉴运动经过一个世纪的深入开展已经对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史学产生了影响。年鉴学派倡导的问题史学以及对多种史料的挖掘利用,所推进的跨学科研究,所高扬的人文关怀和分析视角,已经渗透进了法国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勒华拉杜里的一生担负起了一位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对人类未来所承担的责任,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纪念他的热潮终将褪去,但他将永远是法国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的历史学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