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邱雨评《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离开,或者开放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著,何啸风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232页,6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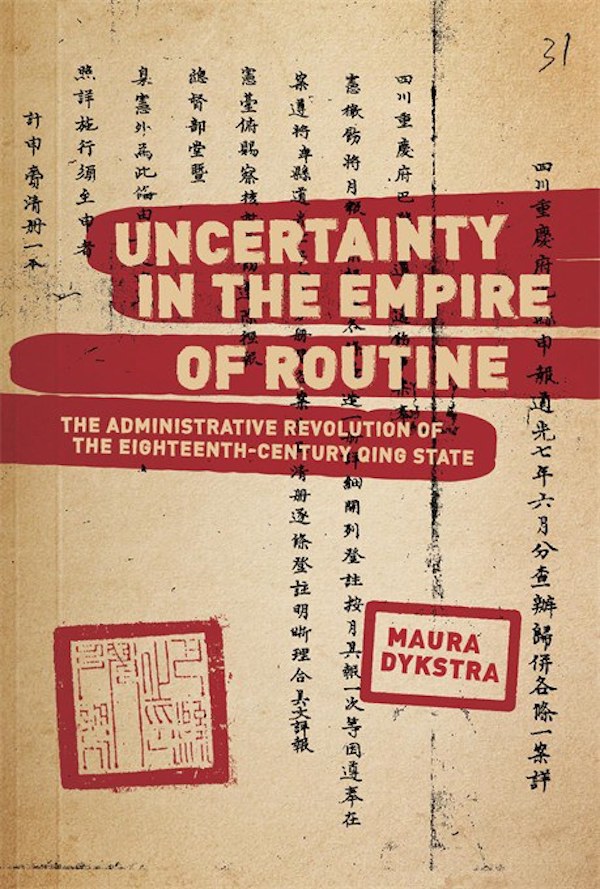
《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in the Empire of Routine)
近期哈佛出版社刊印的《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in the Empire of Routine)遭遇了华裔学者乔志健的激烈抨击,其内容含有诸如“概念混乱、事实错误、低级的史料选择问题”等极为严厉的指责。原作者戴史翠(Maura Dykstra)及其支持者则搬出了学术种族主义和政治正确的盾牌,反向指责批评者依仗其母语优势为一个非华裔的“女性”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过度设置语言障碍。
如果说人文社会学科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拥有认定真理权力的学者的个人判断,以及与“判断”相互建构的、负责提供资格认证并筑造准入门槛的那些机构(诸如颁发学位的大学,传布刊物和书籍的出版社等等)所颁发的“承认”,那么一旦复数的审阅者之间出现判断甚至品味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固化成山头式的利益集团,学术的知识秩序、权威基础就会暴露其漂浮在诸多社会文化网络和知识社群之上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学者们被迫或自愿与某种身份、政治立场绑定的时候。这种根植在人文学科典范内部的紧张,成为“以学术为志业”者不得不长久面对的风险之一。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被标举为严谨客观理性的实验室观测研究的成果,都不免于社会过程干预和支配。至少按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稳妥说法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的社会构造、关于知识和社会之关系的传统论述,都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即要承认“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那么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牵涉更深的人文社会学科,更无法宣布自己的知识基础如何坚固。这种较为脆弱的生态以及身处其中的影影绰绰的干扰者,往往会滋生出更多的来自实用立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信任感,以及研究者们自身的逃离欲求——也许有人会惊奇的发现,自己距离控制苏联生物学界的李森科神话并不遥远。
更令人恐惧的是,一如韦伯(Max Weber)坦言的,“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学者,要面对学院生涯的这种现实,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几年之内,时间长短不定,他必须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同时,他对自己将来是否能够得到一个职位却毫无把握”,面对研究机构日益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工厂的现实,唯有“机运”——可以理解为恰好符合某种主义的需求——才足以决定获得教授头衔和体面待遇。
专业化和将教职作为研究目的的取向共同窄化了学术探索的路径,并且将知识剪裁成了适应于学科体制和学院授课的碎片模式。极端的专业化被日渐膨胀的现代性知识数量(尤其庞大的研究积累)所困扰和限制,又被学术机构一去不返的官僚化进程和相应的绩效主义评价标准所推动和强化。这对于新晋研究者的直接影响是,不利于寻找教职的尝试被视为幼稚,不利于职阶抬升的写作则被称为“无用功”,研究者为攀上知识-权力的金字塔、进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头破血流、焦虑不堪。
这种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凭借奋斗和实力可以获取学术地位和象征资本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所编织的神话,它让研究者们将留在学界视作一种非此不可且唯一符合道德叙事的生活方式;更让人忘记,学科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寻求独立的空间,而非证明自己可以更好地为“垄断符号暴力”进行服务的投名状,也忘记了,学科的出现是足以撼动被视为自然而然的常识世界和思想传统的,具有内蕴的巨大反思力量和反抗精神的革命性事件。于是,离开学术界转而寻求新职业的风险和挑战,可能并不大于安于现状,相反,很可能是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Christopher Caterine)用其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克里斯托弗·卡特林(Christopher Caterine)
为消除学术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作者首先说明的是,学术生涯的上升瓶颈并非来自学术能力的限制,而是成为“另类行业”的学术触及到了提供就业的上限——令人震惊也令人释然的数据是,美国百分之一点二的人文艺术类博士在顶尖高校获得终身教职,2015年百分之七十三的教师是兼职工作——前仆后继进入行业的年轻研究者却被建议“一条路走到黑”,并应全身心投入学科的尖端、前沿部位,结果研究者对高等教育之外的知识一无所知,这些广阔的世界就被视为不可测量、一旦穿过就无法返回的“黑洞”。教职和评级的机会有限,但竞争者有增无减,自然结果就是时间精力上无休无止的过高投入,以及迟迟不见增长的薪金、职称——堪称学术资本投入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和恐怖的“内卷”。对现代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不发表就淘汰”堪称一道令人恐惧的紧箍咒。
针对这种困境,卡特林认为,及时抽身去领略更多样的工作不仅是“应当如此”,而且以研究生的素养完全可以做到。关键是实践、实践,是感知和适应新的话语模式的实践,也是根据这种反馈去自我改易的实践。按他意见,离开学术界的第一步要思考三个基本问题,我们“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从职业中得到什么”,以及二者如何协调,然后记得用日记等等方式将这些思考结果转化为切实可见的文本。第二步则是,用学术训练中获得的搜集文献功底,来获取并分析和职业有关的讯息。方法包括,寻找感兴趣的人并请求会面,积极参与互动并且主动调整自己的职业姿态;访谈的范围可以从熟悉的人逐步扩大到陌生人群,充分利用彼得诺维克发现的“弱连带的优势”,建立一个有助于求职的人际网络,也就是通俗而言的“积累人脉”;务必记住,不可毫无回报地索取他人的时间,并要心存珍惜和谢意。尤其要紧的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执迷于在学术生涯中培养起来的大量使用术语、分析冗长且晦涩难懂的旧职业病,也不能喋喋不休于自己在学术界的惨状,而是要形成一种直白、简明、高效的写作和行事风格。可以视之为从面向熟悉艰深表达风格的有限的学术群体发言,到面向对基础理论、研究前沿和抽象知识所知有限的多数人发言的转型。
凡此种种,最终会达成一个“在探索中重新认识自我”的效应,这个迭代过程中的重复和改进共同“产生了一股独特的冲劲”。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介入社群网络,并在其中寻找到合适的参与性观察的“田野研究”,以此来克服坐冷板凳时的孤僻,重新激活对自己与其他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关系的感受力。这不仅会逐步发现并建构出一个博士的非学术界就业的关系网络,而且,自己具备的写作研究分析能力一旦和特定主体和经验结合,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能量。在作者看来,这如同打开新世界,而且不久即可有所收获。
到此为止,卡特林在纾解了研究人员离开学术志业的道德愧疚之后,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然而,在第四章往后,他暴露了其古典学背景的短板——他试图说服包括雇用者在内的读者,学术背景、博士身份是能够为组织带来更多价值的,当然,通常是为资本家带来经济利益。可以理解,他必须用自己离开学术界的成功经历,来论证离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至于经济资本和学术-文化资本孰重孰轻,在不同的职业中展现和创设的价值,是作者无意也无法去解释的。毕竟,直面这个疑难,就会暴露出作者其实将离开与否简单处理成了一个趋利避害的行为,也就是研究者们应该将在学界无法展示的智慧、干劲,以及学术训练所带来的思考和写作能力,用来与未能取得硕博士学位的同事进行逐底竞争。既然如此,离开似乎不甚光彩。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给“离开学界”赋予意义,就不得不认可并主动拥护从事的新工作的意义。作者对“教育界中害人不浅的因素”义愤填膺,认为摆脱了“学术就业市场上压榨性的用工方式”、知识界内部貌合神离的虚伪闹剧,是让人如释重负之事,可是一旦新的工作完全产生了不亚于谋求终身教职的劳累、焦虑和痛苦,从而变成了可有可无、机械乏味、从业者只能自欺欺人的“狗屁工作”(大卫·格雷伯语),以致“地点、人际关系、职业轨迹、薪水、工作的意义感”(本书38页,作者认为离开学界有助于更好地掌控它们)继续无法被掌控,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
进而言之,很难说在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中存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的痼疾有什么本质差异,至少它们都体现为数字管理下的绩效主义,以及对学术的、经济的剩余价值的反复试探。如果漫长的学术训练时光和高额的学费支出,最终只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些文字处理上的工作能力,而不是让他们对造成“害人不浅的因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原因有更为深刻的体认,那么学术制度可能已经违背了增进智识的初衷。被这种制度以及同构的、关联的其他制度所围困的人,最多只能是在若干环境之间平移。
学术与现实的隔膜,当然不是“何不食肉糜”的无知单纯,更多的像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疏离与自我保护,并美其名曰“客观性”和“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总是拥有真理权力来宣布研究工作的意义性,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然后拿到各个圈层中收获认可赞誉和发表证明,并以此表明自己确实有认真完成“寻求真理”这个元叙事型的社会责任。这种对元叙事的坚持,对自己被雇用去贩卖的知识真理权力关系与文化霸权的生产一无所知,或者索性佯装不知,事实上让一些学者变成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形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的知识分子:沉溺理论架设,但是脱离群众运动。
在这种脱离的情况之下,人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改变世界、产生意义,或有关工作的知识话语中都蕴含或暗示了这一点,但实际上可能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产生,而这些蕴含的暗示是为了减轻工作者虚掷时光的道德负担和一事无成的焦虑。卡特林尽可宣布“一个组织所做的工作类型更多地取决于其使命、文化和价值观”,但事情很多时候如同齐泽克(Slavoj Zižek)的笑话所展示的:星巴克宣称顾客每购买一杯咖啡,就会捐一美分给贫困儿童,这其实是更高明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反消费主义的修辞,去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心安理得进行消费的道德安慰。
如果作者只提供功能性建议,几万字的“简明、直白”的行动指南足矣;如果他是为一抒胸中恶气——比如被迫阅读德语、在大学之间东奔西走的痛苦——在各色社交平台上,可能更有利于获得呼应。我们期待一本书籍所呈现的,或许不是如何从一种成功走向另一种“同构”的成功,而是将涉及价值意义的“成功”多元化,从而解脱出非此不可的焦虑和无意义的内卷式竞争。否则作者的论调,只会步入升职加薪的前学术界人士,面对较清贫的学者自我炫耀的陈腔——“离开学术界吧,外面更轻松,且赚得更多”。
事实上,对无数放弃教职、进入企业研究室的理工学生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用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话说,“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之前就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们许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以此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的支持”,换言之,它本身即无需大学提供的栖身之所,自然也不必以是否进入大学来论定自身的学科合法性。现在作者字里行间暗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们要证明自己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时间,确实获得了实用“技能”的回报,那么疑惑又绕回了原点——大学新生为什么不直接将时间成本投入到高收益、高回报率的职业训练中,或者成为在实用性上更站得住脚的理工科研究者呢?是因为文科无用抑或自身素质达不到理工科的基本要求?勘破此点,作者的说辞似乎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更不必说,作者在陈述“重新寻找工作”时落入了过度相信市场的陷阱,给出了极为乐观的许诺。另起炉灶所依托的,是美国社会整体自由宽松的求职、工作环境以及可观的报酬,足以提供职位和高额报酬的经济发展水准,当然还有保证相对公正的社会再分配的司法体系和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一旦上述支柱不复存在,离开学术界的风险重新飙升,研究者会继续涌入编制、终身教职或者在校生的避风港之中。换言之,作者并不能用更多利益来引诱读者们离开学术界,种种利益通常是既没有价值意义上的说服力,在现实、物质的层面也不够稳定和持续的。作者拥有非比寻常的行动力,但是本书无形中被处理成了一份充满成功学论调的求职指南,这份指南的稿费可以证明转型的成功。
虽然如此,迈出畛域、勇于尝试总是一件值得尊重赞许的事。要承认,本书的价值在于,用离开学界重新求职的实践,来提示所有的人文科学的研究生们,应该自觉地拉开距离去审视自己以往和将来的学术生涯,思考学术生涯对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究竟是帮助还是负累。审视和思考的结果应该是,发表论文、阅读文献、获得学位的种种行为,不应成为将人限制在获得教职、成为学术界的从业者这单一方向上的枷锁,而是一种帮助自身通向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指引。学术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所有方式。
不过,他们既不应在屡屡碰壁后才知晓谋求教职的巨大难度,也不应抱着发现此路不通,才决心改弦更张的实用主义的想法——归根到底不过是亡羊补牢,而是应该清晰认识到,一方面,教职是如何与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术场中的力量关系深刻纠缠,因此“离开”可以是主动地对“知识-权力”和符号暴力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许从开启学术生涯的那一刻起,研究者就不该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去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行零和博弈,而要意识到谋求教职与“以学术为志业”,或者热爱并追求真理的纯粹理想并无绝对的关联。如果学历之提升、研究之深入的代价是可以选择的生命形式的枯竭和窄化,那么需要被批判的就不该是“学术研究能力”,而是学科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否已经造成了对人的异化:研究者憎厌自己的研究对象,视研究为巨大负担,一边否定自己的形式一边不得不继续操持。
这个复杂的过程,一定有某个步骤是令新进之人产生出“从事研究是光荣”的观念,并且继而规训出便捷的学术知识生产技术。这个过程在不断地制造学术难民,他们为求稳定的雇佣关系在各个高校之国中不停迁徙,最终变成了一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被例外状态卡住而被迫失去其生命形式的赤裸之人的模样。进一步而言,为争取在学术之大历史中留下一点痕迹的集英取萃式的、在特殊的领域精准推进的能力,并不与对更广阔的思想和世界抱持兴趣相互冲突,而且最好不要冲突。
悲观的韦伯总体还是保留了一点希望火苗,他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最后说道,“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或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命运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单纯的”。只是需要小心的是,弹奏出来的音弦或许是伪装成感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发出的塞壬之歌,其目的是将聆听者“唤讯”为技艺单一、形式贫乏的学术流水线员工那般的主体,用以再生产出让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得以维系和合法化的知识产品;以及在一个“赚钱养家”的维度上,学历的通货膨胀、发表竞争的白热化以及微薄的薪水,总会让“平实单纯”的事情变得暧昧复杂。
于是,卡特林不期而然地对“学术之为天职”进行了个人经验上的独特解构:不再只有一种天职,不需要被单一的元素定义自己的身份;天职的感召可以是阶段性的,消散也无伤大雅;以及天职和现实职业的政治经济结构有难以调和的冲突。这时,“神之召命”或许可以理解为,不只是留在学术制度内部的劝说,而是对离开中心位置、越过边界的一种激励和鼓舞,毕竟“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有什么知识领域是被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沃勒斯坦如是说。让我们聆听一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自传中的呼吁吧,“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中,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打破碗之界限不保证能够“获得全世界”,却至少可增大其可能性——这大概是本书要说的全部道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