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侯孝贤: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

在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结束后,曾经共同发起这一运动的导演中,只剩侯孝贤还在拍电影。
他与好友杨德昌的作品,让台湾电影在一众琼瑶风格之外,有了新的面貌。杨德昌留美归来,擅长捕捉都市感觉,而从小生长在台湾南部小镇,喜欢古典文学的侯孝贤,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自然感,合作 30 年的好友朱天文曾将侯孝贤的作品比作小说,称其讲述的“是行云流水的生活,需要心胸,也需要真性情”。
今年 10 月,侯孝贤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消息传出,这一至今也没能找到疗法的病症,悄无声息地打捞着全球范围内的老人。从 1973 年,以场记的身份进入电影界,侯孝贤从策划、监制、编剧,甚至演员,转换为导演,通过记录他眼中的时代,留下了太多供后世想象的寓言。
在导演、作家唐棣眼中,侯孝贤这样的人“几乎绝迹”: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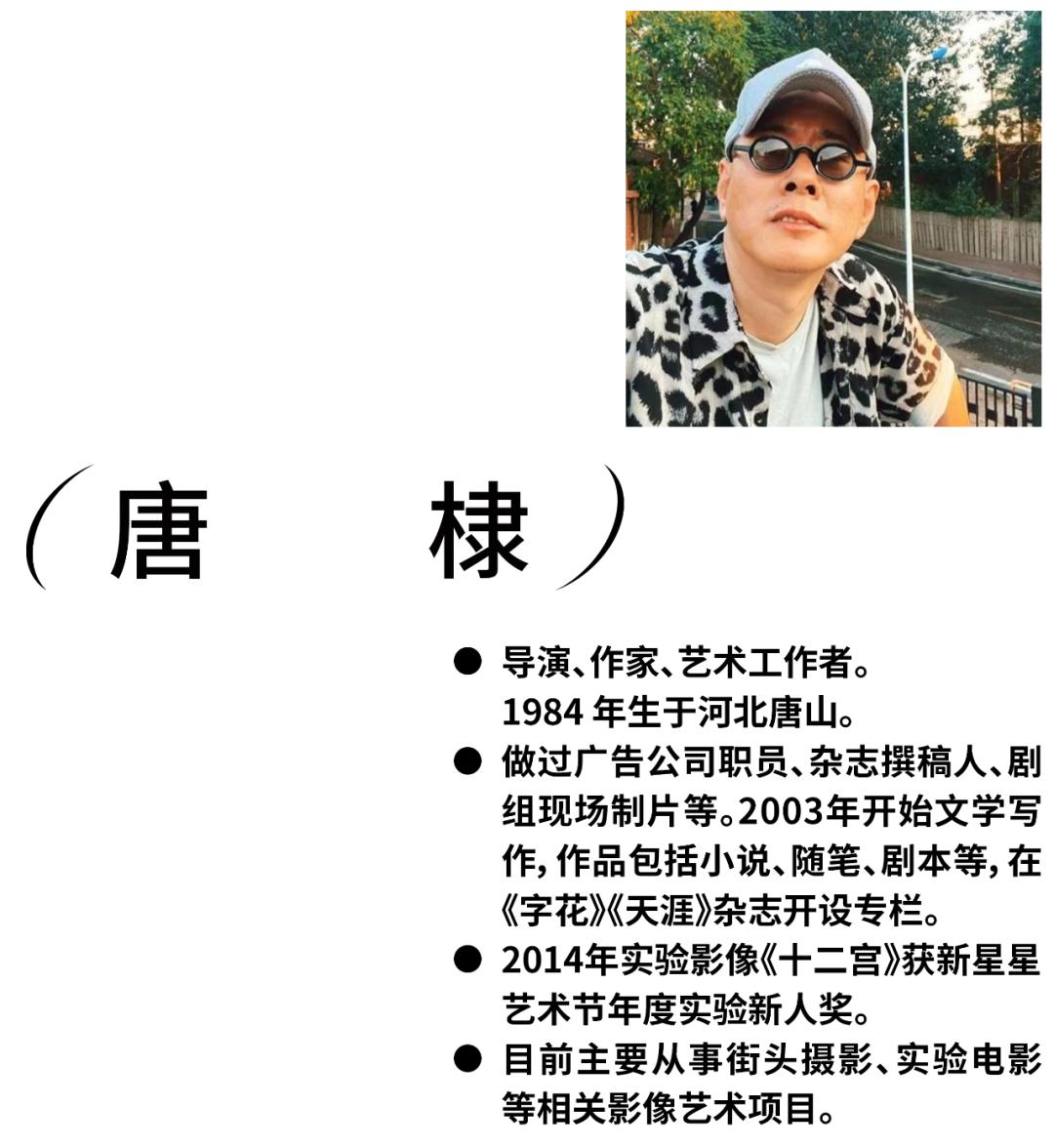

侯孝贤,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撰文:唐棣
台湾新电影,以 1982 年拼盘电影《光阴的故事》在台湾全省联映为序幕,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后来回台湾拍电影的杨德昌。第二年又一部拼盘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出来,拍过三部票房很好的爱情片的侯孝贤,加入其中。他改编的是文学界乡土运动代表作家黄春明的同名小说——每次文化运动,最早似乎都是从文学先开始的。
黄春明笔下的父子情,也成了侯孝贤镜头里最切中人心的东西——这种特别中国化的家庭感情(父子、祖孙、夫妻等等)也一直在侯孝贤后来的电影里延续。

电影《风柜来的人》
谈到电影风格,就要到 1983 年《风柜来的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情感状态,在侯孝贤的镜头里出现了,类似惆怅、疏离这种东西。早期,他的电影并没有不可替代的镜头感和视角,换句话说谁拍都行。
《风柜来的人》里那几个迷惘的青年人的生活,被固定机位和长镜头,远远地观察着,似乎有别以往。镜头有了态度,一代人终于不再懵着。以前的电影都在想如何带入观众,去看“打打杀杀”,侯孝贤眼中的江湖却在找打打杀杀背后的原因——这部电影有点儿推开观众,让大家冷静下来的意思。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台湾是武打片和琼瑶式言情片的天下。70 年代末冒出过很多色情或暴力影片,商业不商业,乡土不乡土。到 80 年代,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它同时面对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拉扯,一代台湾年轻人,就这样在生活中随风摇摆。
其实,台湾新电影和法国新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相比商业气息重的香港,台湾电影人传统的一面,使爱电影想表达的年轻人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在“电影江湖”上做点什么。

电影《恋恋风尘》
法国电影新浪潮出了戈达尔和特吕弗,台湾新电影有植根本土的侯孝贤,和从美国回来的程序员杨德昌。杨德昌带着西方视角,善于捕捉都市感觉,拍片子也更类型化。当时台湾的都市感属于一个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独特的味道在他的镜头里非常有标志性。
这两个人是台湾新电影的“双雄”。至今在他们的电影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面相。往大里说,如果不是杨德昌过早离世,台湾新电影会是另一种格局。

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风柜来的人》同年,杨德昌处女作长片《海滩的一天》一出来,就是风格之作。拍这部电影前,杨德昌看了许多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电影。他这部电影的剧情关于失踪。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冥冥中感觉要找什么东西,杨德昌用电影定义了那种不知名的东西。另外在结构上,他比侯孝贤的电影现代,还是多重叙事。
我记得侯孝贤在一个访谈里说:“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关注的方法可以变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个……杨德昌离开台湾去美国那么多年又回来,他的记忆跟他对当下看法的对比。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自然的成长和生活这就是我的眼光……”

电影《童年往事》
现代的概念在侯孝贤那里表现为杂糅而丰富,东方形式,东方思考,核心的观点又连接西方;到了杨德昌那里,则变得十分纯粹。电影和文学不同,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很多时候是一个视野,一种价值观,一种判断。观看的当下,没有足够时间去理解(后期慢慢回味是另一回事)。不过,对于表现台湾社会种种,全都是好事。
很快发生的是,平均年产 120 部左右电影的“美好时期”一去不返的现实,导致台湾影院关闭,没人再看这些台湾新电影了。
于是就出现了 1987 年 1 月 24 日《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台湾电影宣言》。宣言分“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部分。我特意去看了当年这些年轻电影人的忧虑和怀疑,都是特别真诚,他们提出: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
宣言的签名者分港台两部分,香港有方育平、方令正、文隽、徐克、潘源良、关锦鹏这些后来一直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台湾包括侯孝贤、杨德昌、陈映真、朱天文、朱天心、杜可风、吴念真、林怀民、金士杰、蔡琴、焦雄屏、赖声川等等文学、表演、导演界的人。

电影《悲情城市》
时代有时代的无常。无奈之后,大家的创作,不得不跟着市场和个人命运纷纷转向,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事,比如很多电影人不着眼于台湾本土的现实,也不从本土寻找资金,大部分钱来自国际电影节上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法国、日本方面的投资。(侯孝贤至今也是这样)这么做好处是可以不受台湾某些政策的影响,坏处是有远离现实、沉寂回忆之嫌。
在关于“台湾新电影”的资料里常见一种说法:“这场经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导演激发起的电影改革运动,在八十年代短短几年之间经历了兴衰成败,也成为台湾电影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电影《冬冬的假期》
高峰过后,很多人离开电影圈,只剩下侯孝贤一个人拍电影。并不是每件事,都要画上句号,有时我觉得,“法国电影新浪潮”为什么要划定结束呢?戈达尔活着,法国新浪潮就不能说结束;台湾新电影后出现了不少名词,比如新新电影(其实也可以谈论,但似乎没人再有这个谈性)。可以说在影迷心中,只要侯孝贤活着,台湾新电影,甚至某一种“新浪潮”电影的大幕就没有落下。
侯孝贤喜欢对拍电影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什么样的人拍什么东西,这是逃不掉的!”想拍,上去就拍。当年,法国新浪潮那帮人就是这么干的。

电影《戏梦人生》
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访谈里,有人问他街头戏的拍法。他笑着说,我们不可能像好莱坞那样有专业的群演,还要封街什么的,你直接去拍,没人看你的!反正现在机器很小。多年以后,这些生动的场景还能重温,多亏了电影。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海上花》那次,侯孝贤致词:《海上花》是二十一年前的片子,当时要求演员们讲上海话,是为了绝大多数观众不会听上海话,因此能造成一种距离感,甚至于距离的美感,当时哪里想得到有一天这部片子竟然会在上海放映……
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创造距离,穿越时间。而杨德昌电影《一一》里小男孩洋洋总是在问爸爸:“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呢?”很多事看不到后面,新浪潮也是。

电影《海上花》
这里还要说,侯孝贤不是我的电影启蒙,我没那个好运,除了小时候一点点看露天电影的经验,就是各种黑市上的碟片,决定了我电影审美的不健全。那时候基本上有什么看什么。我是通过看他的电影和关于他的文章,渐渐对他感兴趣的。
第一次在国内大银幕看侯孝贤的电影,已经到了 2015 年。在北方小县城的一家电影院,我和我妈花五十块钱就包场看了《刺客聂隐娘》。

电影《刺客聂隐娘》
我看过电影后写下一段话:
“《刺客聂隐娘》不讲聂隐娘如何成为刺客,而讲她如何没有成为刺客。首先,镜头定氛围。很多导演对着一群说话的人拍照时,侯孝贤关注着站在角落里的人,他在镜头之后,没牵着我们看什么,而是随着镜头的移动,一同去感觉里面藏着的东西,在说话人的附近始终徘徊着一双眼睛。”
我妈在看过电影后,以一个北方妇女朴素的审美判定,自己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电影。这是她眼中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电影里的美对一个北方农妇起了作用。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电影《千禧曼波》
后来,我没机会亲见过侯孝贤,却意外地认识他身边几个人,还有住在朱天文家附近的朋友,也经常跟我描述侯导坐公车去附近咖啡馆聊剧本的情形。其实,侯导演患失智症的事在圈子里传好几年了。我认为,媒体说一个导演退休相当无趣。
这几年间,侯孝贤新片《寻找河神》不时传来消息,但我总隐隐地觉得,可能看不到了。事实上,他完全可以让这些年培养的后辈去完成他的电影志愿,自己挂个名……一切只因他是侯孝贤,走过台湾新电影那段历史的,最有影响的,也是最真实的人。也许对有的人来说,电影是一份工作,而侯孝贤可能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最后一部电影命名为《寻找河神》相当意味深长——这个河神,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隐喻,所以他必须亲手去找。

电影《最好的时光》
像他过去那些电影一样,站得不够远,经历不够长,都很难看清什么:从 1983 年《风柜来的人》后,侯孝贤的形象越来越像“江湖大侠”,越走越孤绝,直到 2015 年《刺客聂隐娘》在戛纳电影节拿奖一刻,我心中忽然生出无限感慨。
在我看来,这条路上一开始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后来这样的人几乎绝迹。这样的人明明可以融入更大的“集体”(如调配流量明星和大投资),可他没有。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侯孝贤有句话常被人引用:一个人,没有同类。哪怕他的朋友杨德昌在世,他也完全有可能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是艺术家,所有真正的艺术走到最后,身边就不该还有任何人——艺术家也可以用此自证。这是逃不掉的!
那时,你将成为一个人。平时不觉得“所有人”这个概念虚无,一写到侯孝贤,它就显得有点大而无当!面对一个如此具体的人,那种实实在在,可亲可敬是最珍贵的。也许,在某种微弱的希望中,一个人又是所有人——这句话看着别扭,其实意思不复杂。烟消云散在所难免,有种东西会在人群流传下去。
(节选自“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专栏之七《美好时代,新浪潮的注解》,
原载《天涯》 2023 年第 3 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