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梁鸿、刘琼谈非虚构写作 | 真实是在每个人的心中

十年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当老师的梁鸿,厌倦了校园里的高谈阔论,背着包带着孩子回到梁庄实地探访。“觉得很烦躁、很空虚,无以自处,能写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定居北京数年后返乡,梁鸿在父亲的支持与陪伴下完成实地调研,写出展现梁庄几十年变迁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与探寻梁庄外出打工者生活轨迹的《出梁庄记》。
“他们想让我回答‘出于巨大的责任心’这样的话,最初的原因只是因为基于那种柔软而纯真的情感。”梁鸿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动力。
不只是梁鸿,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也被媒体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同样对非虚构文学有自己研究兴趣与实践。刘琼曾担任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等文学奖项评委,其散文《通往查济的路上》《姨妈》《祖父的青春》,传记作品《聂耳:匆匆却永恒》等获得颇多好评。
9月18日晚,梁鸿与刘琼共同做客河西学院“贾植芳大讲堂”,共同分享自己对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的看法,以及在非虚构文学创作方法上的思考与经验。
非虚构写作是关于真实的文学吗?
梁鸿:非虚构文学思潮的缘起,实际上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生,跟我们政府的发生,跟整个文化意义的发生都是有很大联系的。它不可能是一个独有的文学。当然首先是文学内部的嬗变,但这个嬗变一定跟整个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非虚构写作者在写作,正在慢慢被公众所接受、讨论、分析,当然也有批评。可能也就是2008、2010年左右。我觉得这非常好,这样使得一大批优秀的作者重新回到大家面前。
为什么这两年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涌现,是因为它容易掌握吗?我觉得不是的。首先我们对非虚构文学有一个误解,认为非虚构文学是关于真实的文学、关于社会的文学,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文学与真实文学与社会之间,一定有一层媒介,那就是文学是关于真实的描述,而不是真实本身。
为什么叫文学?如果我们以一个大框架来讲,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那么这个语言艺术背后包含着社会文化。语言和修辞相关,而修辞是跟你个人的各种希望相关,你的知识能力、语言能力,你的观察社会能力,你个人的成长背景、修养等等。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定义,大家也都在争论。我们要抽开具体、非本质的概念,稍微来找一下它最根本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关于真实的描述。
我们说到文学的时候,经常喜欢说这部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当我们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的时候,这里面是包含着个人的观点,它一定是有个人偏见的。
我想非虚构文学不是一致化的、一种声音的表述,我们的小说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非虚构文学的表述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法,每个作者都有进入世界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理解,这是我们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文学所描述的社会真实其实是一个有限度的社会真实。所以我们经常说这篇文章是关于客观的社会的一个什么样的描述,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
试想一下,即使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所谓稍微带有科学性的学科,它写的是关于社会现实的一个纯粹客观的描述吗?也不是,它里面也包含着对自己的观点,只不过它的框架更清晰、数据更准确。
那么文学呢,我觉得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评价它是否达到这种真实。比如说关于个人情感,这是我们从量化分析里没办法找到的东西,但也恰恰是我们所忽略掉的一个层面。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你只有意识到个人的限度,才对你所描写的对象有一个更加谨慎、平等的观察,这样你写的场景才有可能更加开放。这个“开放”指的是这个场景内在地被打开了。只有你意识到自己的限度,自己知识的偏见、个人成长的偏见,你的语言的不成熟性,你和你的写作对象之间才可能达成一种相互观察、相互思辨。
关于非虚构文学创作门槛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写作是有多个层面的,文学是一个雅俗共赏的东西,我们不要把文学提得太高,不是只有类似于我这种科班出身、拥有一点写作能力的人才能创作。
一个老农民在晚上唱着小曲,也是音乐创作,只不过没有被我们记录下来而已,当然在民间口口相传也是一种记录。非虚构文学也是一样,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写一些个人的故事、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是非常好的事情。
最起码这样一来,文学得到了大众的关注。我们之前的文学被放在象牙塔里,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趋势是越来越跟社会现实、跟整个社会的变革没有关系,变成一个少数人从事的所谓“高贵”的事业,其实别人也没看,对吧?我觉得反而是非虚构写得这样生机勃勃的、全民参与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我们的阅读有多个层面,我们可以读一些雅俗共赏的,也可以读一些非常纯粹的。那我觉得像我这样上这么多年学,又读了硕士、博士,又立志于从事文学事业,我觉得我最起码要有一份责任心。我要对我手中这支笔负责,我每写一个字、一个场景,都要小心谨慎,因为我对自己负有责任。这是我的态度,而不是说必须要有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非虚构写作不必很苛刻,它是各个层面的一种写作,每个人都能够表达。

图/视觉中国
非虚构写作如何更好地运用写作技巧?
梁鸿:如何使用技巧,这不单单是你的文学能力问题,其实也是跟你对你所描述的对象的理解能力有关系。所以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也是非常迷茫的,当我面对我所要表达的场景,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都涌了过来,你要表达的一些社会的东西怎么办?
经过反复的揉捏、思索,最终选取了先写谁后写谁,这样一个过程是必然的。所以任何的文学写作,不管是小说、散文、虚构、非虚构,背后的逻辑是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你个人的声音、个人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最终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使用什么技巧。
刘琼:我非常认同梁鸿老师说的。非虚构文学毕竟不同于新闻,退一步讲,哪怕是新闻写作也有个写作的主观性在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叫新闻写作,叫非虚构写作?我特别想补充下梁鸿说的非虚构写作里面文学性的问题。
非虚构文学里文学性的表达和真实的关系,这是我们历来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大家会评论它、争议它。事实上任何一种写作,只要是文学写作,它的本质一定是文学性的。
那么这其中非虚构写作的客观性我们是怎么去判断?我们可以判断它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还有一个基本要素的真实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选择角度,怎么去表达我们的理解、对事实的观察,怎么去谈我们的思考,或者去形成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其实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
我们都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她当时在领奖台上说了一段话,她说有人说过奥斯维辛以后,我们已经不能用诗来写作了,就是说在很多的重大事件面前,我们的诗被失传,已经不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所以她决定选择用非虚构这种写作方式。
因为真相已经断裂了,她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但其实里面有个哲学的逻辑在里面,就是真相在一个丰富的、巨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心中。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她想着我去访问诸多的受害者,收集诸多的事实,我用不同的叙述来把它表达出来,最后形成真相的各个侧面。通过各个侧面,最后我们形成迈向真相的一个途径,所有的侧面就构成了我们写作的一个路径。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大家都觉得有公认的不错的文本,其实往往写的是他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庭身上的,但是他写作的东西,一定是他熟悉的。
还有另外一种熟悉,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掌握。不熟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它很好地表达出来?非虚构写作的残酷性在于你写你不熟悉的东西,别人是一目了然。你在对真相的探索过程中,有没有接近一步,别人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在文学写作中,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人和事物的了解探究。如果你对个人和事物、对事实、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当下社会、或者人的生活状态的研究,写历史题材的时候对历史时代的细节、框架的掌握,不能有真正的探讨探索,哪怕我们的语言很好,我们也不能够打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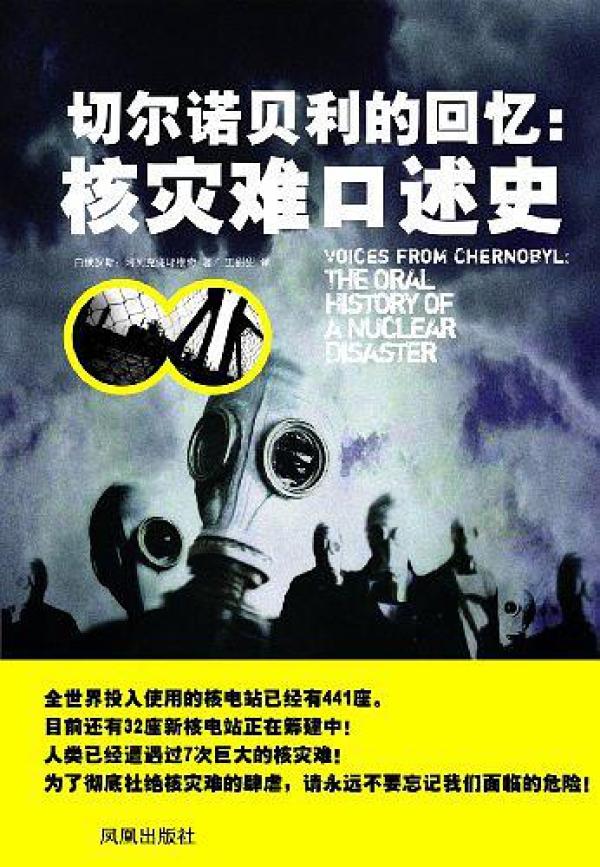
怎样呈现出打动人的细节?
梁鸿:关于 “细节”的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得了诺贝尔奖,很多人就觉得非虚构的春天来了,其实也没有这么乐观,但是它是一个象征事件。
我想具体讲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当时诺贝尔奖给她颁奖的时候,颁奖词里面有一句话,“她复调式的写作,堪称纪念碑,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苦难。”复调式是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一个文学理论,什么叫复调?就是多重声音、众声喧哗,就是你也说我也说,皇帝也说,民众也说,每个人都在这个广场上说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是平等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二手时间》。写的是俄罗斯崩溃之后,俄罗斯民众的一些思想。她没有从一个大的史学层面写,而是采访了很多人,比如采访农民,采访了俄罗斯社会崩溃之后那些富裕的、贫穷的农民,采访了清洁工、家庭妇女、工人,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的声音交织成一个大的时代交响曲。
这些东西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我们要知道,当这个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在说话的时候,关于一个社会的众生相就能呈现出来。这个众生相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是没有大统一的声音,就解构了我们的一些大的话语。
这种解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每个人心灵的变化、灵魂的变化,只有把每个人的灵魂的变化都写出来,我们这个社会才能被反映出来。所以《二手时间》这本书,其实它是关于社会各阶层的一个访问。
她的访问里面关于每个人的叙述还是非常讲究的。她在写一个俄罗斯贵族妇女的时候,她可能在厨房里聊着买东西的变化,花多少钱又买不来多少东西,这里面甚至有社会学的成分在里面。它可以反映出俄罗斯一个农户的变化、货币体系的变化直接导致的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变化,所以它具有社会价值。
这个社会价值不在于说它给了我们一个大的社会框架,它只是告诉你,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个人是这样子的,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人学,是写关于人的。
她还有一部作品叫《锌皮娃娃兵》,写的是关于阿富汗战争。当年俄罗斯去打阿富汗,是招募了一大批青年军人去,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阿富汗战争已经定义为侵略了。这个时候这群军人就变得没有价值了,他们本来是为了国家而奋斗,现在被定义为侵略,这种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锌皮娃娃兵》是从母亲入手写,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去参军了,过一段时间父母收到了一个锌皮棺材,就是俄罗斯政府给战亡士兵用的棺材。所以当锌皮棺材送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都不敢去开门,因为知道儿子不在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的时候有一批母亲就非常愤怒,说我怎么来安放我的儿子,他是怀着崇高的爱国理想去的,回来之后被定义为侵略者。我的邻居和朋友都会说,你的儿子不是个好人。
作者的着眼点非常小,就写这些母亲在厨房里的议论。厨房呢,在一个普通隐喻里面是一个闲言碎语的地方,但却有最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有作为一个母亲最真实的生命的表白。
所以你看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调查记者,但她所走出的道路远远超出了调查记者。因为她并非只关注事件本身。所以很多作家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我并不是说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鲜明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可能非常迷茫,这个时候你就去收纳细节,当众多的细节都汇集而来的时候,你脑子里一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东西会慢慢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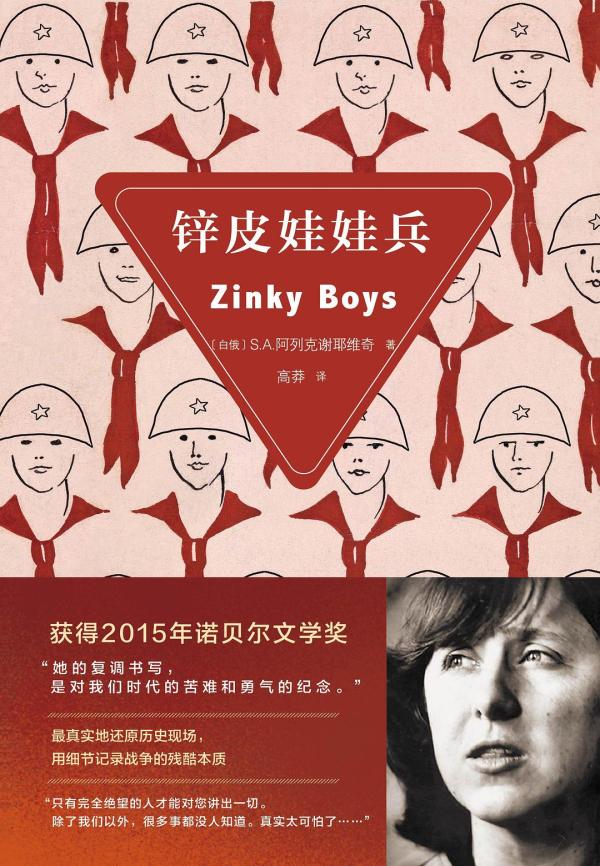
(学生提问)如何在从史学作品中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认知?
刘琼:像司马迁的《史记》,它其实也是写历史的文学作品,但我们都把它当成历史来读。虽然历史作品也是有作者的主观性在里面,但是历史写作的要求和文学写作的要求还有一个界限差别的。
历史是一个框架性的写作,要有历史走向、历史大的框架结构、历史中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但是这个框架搭起来以后,它里面需要什么?需要血肉,需要细节,这个东西是历史系统无法完成的。
我们去读所谓的《史记》,二十四史,它也会有一些描述性,但是描述性有限。那么重读这样的血肉的东西,历史细节的东西,谁来完成?我们怎样获取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认知?
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对唐朝、汉朝的认知,可能是从史书中去得来一些大的历史朝代变革、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状况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汉代或者唐代的认知,其实是通过文学史书、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判断一些,比如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它真实不真实,或者是它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想象、满足我们期待。我们的判断标准也是什么?是它对于当时那个历史朝代的细节表现,是否合乎当初我们认知的历史逻辑。
比如它的服装、饮食、语言方式,男女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母子父子之间的关系。当然历史会告诉我们,那时候有三纲五常。什么叫三纲五常?我们是通过文学阅读获得,文学阅读中有大量故事、细节,告诉我们父子关系是什么样的表现。所以这就是文学阅读和历史阅读的这样一个差距,也是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不同。
梁鸿:我们刚才谈的是文学里面历史的使用,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实际上是关于历史的相对确定性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即使是关于一个学科,它也在不断嬗变。
比如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说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历史学科打扮成客观存在的一个世界,我们忘了我们是在叙述历史,就是说你也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只不过你这故事好像是讲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故事背后的讲述性你忘掉了,比如说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讲秦始皇,那就是你个人的一个东西了,而并非是历史的客观本身。
所以说历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它也在不断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学科的(实现)客观性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你要读不同的历史著作,比如说关于清朝,你要读这个学者、那个学者,最好他们两个的观点相互矛盾,你要读懂,然后从中得出一个观点。
还有一点,历史也是被发现的。它并非就是一个现成的历史由你来讲述一遍。
美国有个学者叫孔飞力,他写了一本书叫《叫魂》,写的是1768年叫魂事件。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因为它通过一个民间的非常小的事件,当时乾隆年间发生的一个非常小的事件,其实当时很多村民害怕,说经常有人割辫子,说割辫子灵魂就没有了。本来是民间的小的恶性事件,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变成一个巨大的国家事件了,连皇帝本人都书面批示说一定要严查,所有浙江州县都被牵扯进去了。孔飞力就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民间事件,从一个给河建桥的匠人来写起,一直写到皇帝。
这个事件是他发现出来的。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的社会事件都非常多,我们不可能穷尽,但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他是能够发现一些赋予非常象征性意义的事件的存在,它从这样一个小的事件,一直勾连一直勾连,最后勾连出整个康乾年间。康乾年间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个盛世,当时白银的流量他都做了考察。因为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要详尽地考察,他的所有文物都来自于奏章,来自于皇帝批示,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严格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他告诉我们,在那样的康乾盛世,其实民众是没有安全感。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时的民众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一点点小的事件都会引发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轻轻一动一推,一整个联系起来。所以你看历史也并非就是说一个客观的事件,它当然是客观的,但是它有待历史学家发现。我觉得我们阅读历史也是一样的。
那么阅读历史跟文学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当你真的去阅读历史,真的有了解、有真正的理解的时候,当你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你关于历史事件的描写的想象、或者非虚构里边一定包含着历史的某种声音。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层面,我们理解历史可能会更加清晰那么一点点。
整理/王迪
“镜相研究室”首发独家稿件,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