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市化的乌托邦悖论:高度城市化后又会向往反乌托邦
【编者按】
乌托邦的观念源自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持久渴望,它植根于原始而富足的、具有社会平等特点的黄金时代。早在“乌托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乌托邦就已经存在了,但这个概念是随着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出版而更为清晰的。
在《乌托邦的观念史》一书中,伦敦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格雷戈里·克雷斯讲述了古往今来的诗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建筑师与艺术家构想中的乌托邦形象的变迁,并指出,可持续的乌托邦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当下消费主义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澎湃新闻经商务印书馆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乌托邦追求可在全然不同的两种传统中找到,一种是乡村的,另一种是都市化的。乌托邦的都市化特征只是其特点的一个方面,而与其本质更为贴近的则是它的乡村传统。乡下牧民在放牧牛羊的时候,他们对城镇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在自然条件优渥、气候宜人的地区生活,只需普通的陋室一间就可满足需求。在温暖的、可以让人身心放松的天堂般的环境中,草房一间,或者至多是可供家人合住的一处长棚,便几乎已经令人知足。生活于此,衡量人们内心满意与否的标准便是那一间草房和那一架长棚了。对于一些小型宗教社区来说,像在其他震颤派教会村一样,简单而不失典雅的木质住宅与基本的公共设施,已经足够。可是,随着社区规模日渐扩大,社区功能也需提升,原来的农业社会定居点逐步发展成较大的都市中心。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进程。

新和谐村,由罗伯特·欧文所创立
到了早期现代,都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已演变为一种借助乌托邦构想推行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这一转变既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又深深受到乌托邦构想的影响。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社会环境中的秩序都与社会习俗和礼仪的融合相关,秩序需要借助法律和宪法的配合,秩序必须依赖社会力量对潜在的有破坏性的行为(如挥霍浪费与性竞争)的监管。然而,此类维持社会秩序的限制性手段,并不会在理想的乌托邦式的乡村里获得重视。乡村社会的需求极易获得满足,彼时,社会秩序自然也就不再成为人们担忧的对象了。实现城市化的愿望越迫切,期待便愈强烈,人们的管理手段也会越发严格。
高度的城市化又会让城市向着它的反方向——反乌托邦发展。与极端的城市化想象相伴,密集化管理会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规模十分狭小、严格限制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以此最大程度地对个人生活实现控制。政权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公共空间与这些受到严格限制的个人空间是并存的。虽然人们心目中的一些理想都市空间〔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约1624年)中所描述的本萨勒姆、查尔斯·傅立叶的“方阵之城”以及罗伯特·欧文在19世纪初所设计的社区〕并不与这种治理理念有联系,或联系较少。但是,在其他很多的乌托邦都市形象中,林立的高墙和一些高楼建筑被一起整合进方便管理的监视系统中。因此,建筑、城市的规划,乃至整个国家的设计都在乌托邦设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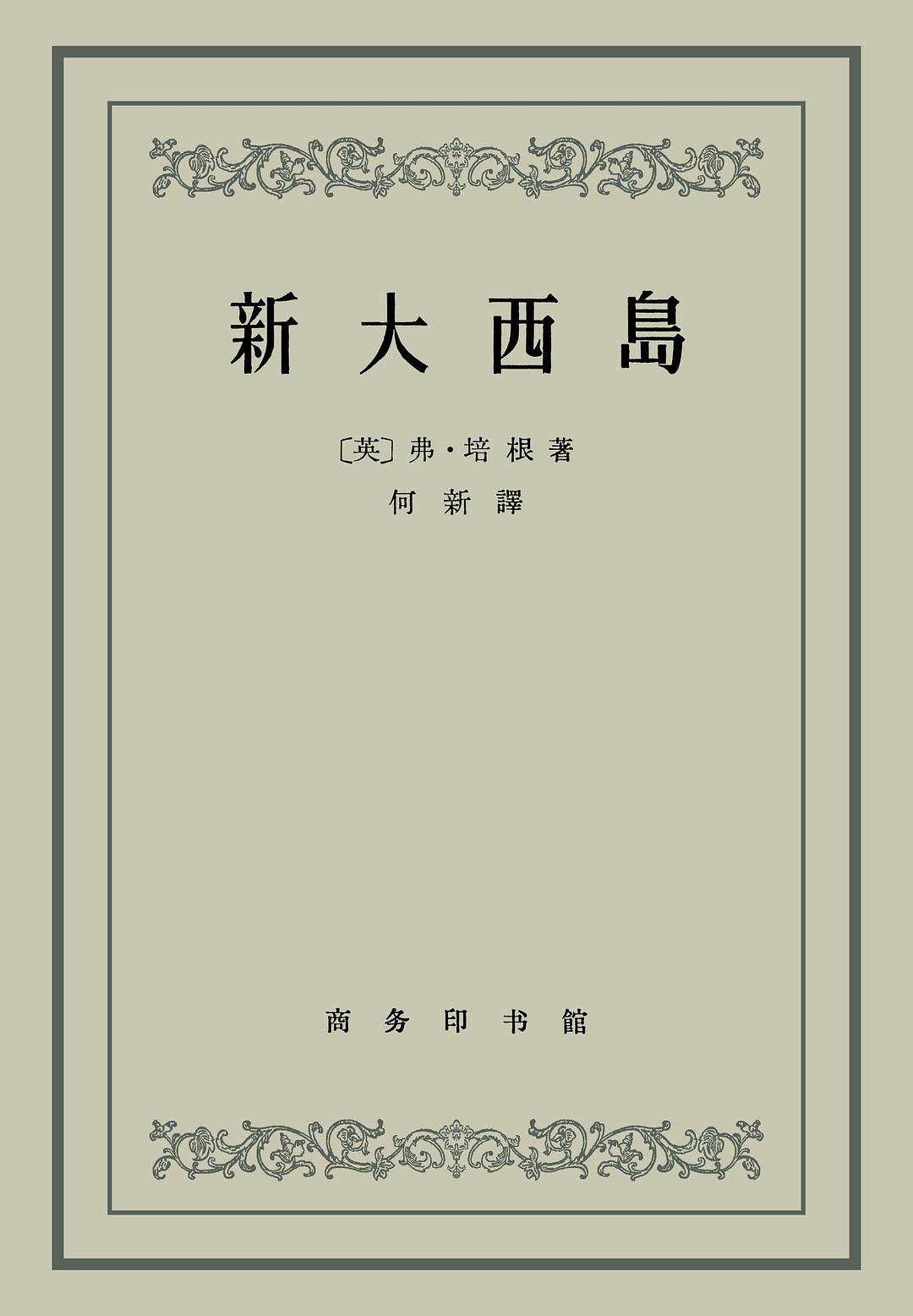
《新大西岛》书封
对城镇和都市的精心规划,古代世界已经司空见惯。古代都市往往围绕着军事防御点、河流、桥梁或贸易中转站而建,成片的农田旁边也是古代城市的最佳选址。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各帝国建立后的人口增长,成为刺激人们建立新的城市聚落的重要因素。埃及法老金字塔虽为死者而建,但从其居住功能和宣传功能来看——通过其纯粹的感染力,仍可视为有关城市空间的最早设计。希腊人为了满足居住需要,建造出网格状的城市,这种城市类型较多出现在其海外建立的殖民地。罗马人建立了更富有活力的城市,安全的水源、公共的浴池、良好的道路系统、寺庙、行政厅、兵营和体育场成为城市的必备,当然,居民用房占据了城市中最重要的地位。迦太基城被罗马摧毁,罗马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再建时已考虑到诸如此类的城市功能,许多罗马殖民城市和军事定居点也都呈网格状分布。罗马城市广场以及类似的壮阔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最初设计时便已考虑到了它们的特殊意义。这种设计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或是气势逼人,或是将宗教、政治和军事的象征意义结合起来,总之是要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此类现实问题,城市规划时还要考虑所谓的自然法则,既要符合数学原理,又要与人的身体比例、精神和宗教观念相协调。“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以及天堂观念在基督教早期就与理想城的观念糅合在一起。中世纪的欧洲也流行着多种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传说中,卡米洛特城的起源与6世纪对亚瑟王的描写有关,托马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1485年)重新提及,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出现,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1891年)中对此城的描述。卡米洛特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在撒克逊内战后长期保持和平的军事政权。其中,有关圆桌骑士的描述透露出当时的君主制并不巩固。据记载,卡米洛特是英国南部一个王国的首都,从神话中的一个小军事据点发展而来,汇聚了中世纪骑士英勇、勇敢、正义和为公共利益献身的精神。其中的宫廷魔法师梅林的美德和智慧时常被重构和修饰。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1886年)对其中理想化的宫廷生活进行了揭露,将现代民主与封建主义的衰退进行对比。

《乌托邦的观念史》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都市形象还应到那些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中世纪神话中去寻找,天上会掉馅饼的安乐乡在13世纪被首次提及。据资料记载,安乐乡有吃不完的食物,食物取用后又会自然长出新的食物,可供烹饪的动物会自己出现在食客面前,人们活到五十岁会自然返老还童,重新回到十岁时的状态,他们从不惧怕死亡。房屋是用糖建造的,街道上铺满糕点。在库卡那,意大利版的饕餮或饱腹的想象中,有腊肠做成的桥、流淌着牛奶或葡萄酒的河流、堆满奶油奶酪的山。工作被视为一种罪过。
理想城在中世纪通常是“新耶路撒冷”观念不同形式的反映,精神上体现为完美的“上帝之城”,美学上表现为都市空间的理想状态(就像巴比伦和罗马的沦陷被看作是人类灵魂的堕落一样)。理想城的许多圆形或多边形设计方案——如安东·弗朗切斯科·多尼在1552年描述的方案——是城堡建筑的变体,目的是强化王室的控制,如1593年建造的辐射状城墙环绕的新帕尔玛城。
到14世纪,通过城市设计来建立秩序的观念已十分普遍,包括锡耶纳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城镇墙壁上绘满了讽喻政府的涂鸦。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有关秩序、平衡、和谐以及美感的思想融入了15、16世纪各种风格的建筑中。菲拉雷特规划的理想城斯弗金达城(1457—1464年)可能是此类设计在意大利最早的出现,其中一项设计是将两个大型广场布置在一个16条径向辐条组成的圆内。此后,在锡耶纳出现的带放射状辐条的圆形广场开始流行。大量出现的塔楼,如圣吉米尼亚诺,是阶层向上流动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公民的财富、竞争力和不断上涨的房价。莫尔的《乌托邦》充满了对理性原则的应用,由十分相似的围墙环绕的54个城镇分布在24英里(约38千米)外的海岛上。20英尺(约6米)宽的梯形街道,街道后面是偌大的花园,自动门会自己敞开迎接所有人,在这里,财产是共有的;防火的屋顶设计和玻璃采光窗代表着技术的革新。类似的理性原则在许多被殖民的新大陆的早期城市设计中都有体现。印加的一些城市设计,如库斯科,同样不乏想象力。
修道院为理想城的其他变化提供了灵感。正如弗朗索瓦·拉伯雷在《巨人传》(1532—1569年)中描述的那样,德廉美(Thélème,源自希腊语,意为“意志”或“欲望”)修道院是巨人卡冈都亚为贵族阶层建立并给予补贴的庇护所。在这里,贵族成员拒绝接受修道院习俗的束缚,即清贫、纯洁和服从,也不愿接受知识和精神启蒙。对周遭的奢华风气,他们甘之如饴,却宽容地将奢华与众人分享。宽阔的花园、华丽的家具和众多舒适的设施供所有人纵情享受——这并不会导致放纵,而是一种规范的生活方式,且不受神职人员干预。修道院的中心建筑是位于卢瓦尔河谷的一个六边形的六层建筑,周围有六座塔楼。包含9000多个精心装饰的房间,其中还有一个壮观的图书馆。拉伯雷的小说被认为是对宗教虚伪的讽刺。文中将僧侣的生活与贵族的纵情声色相提并论,暗示需要净化基督教,严厉谴责敛财、法律欺诈和游手好闲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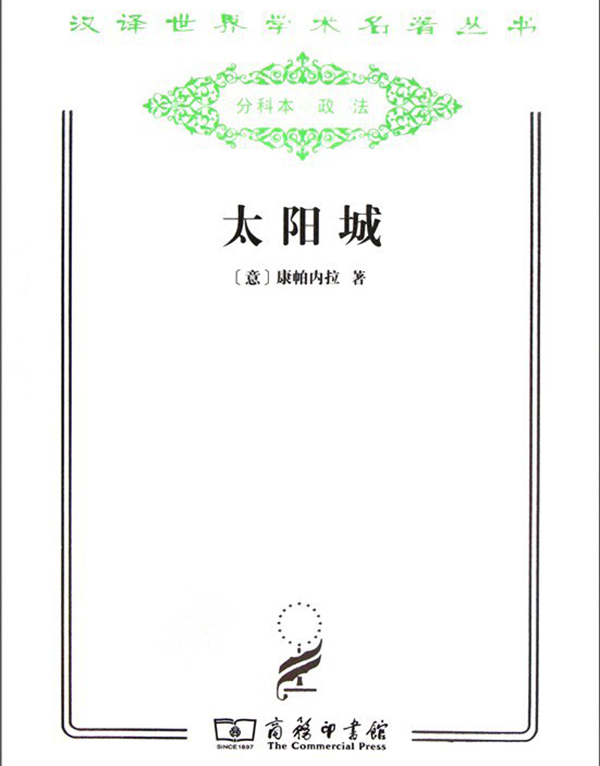
《太阳城》书封
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2年)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位于南半球的一座理想城市。这座城市由七个对称的圆组成,代表了乌托邦社会工程学与城镇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墙上的装饰激发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神灵的敬重以及对知识的渴求。财产为集体所有;在以健康生育为标准的柏拉图式系统中,妻子也是共有的。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是常态。自然科学与农业技能方面的全民普及教育有助于维护社会平等。他们十分重视对性行为的规范,禁止滥交,倡导身体健美,通过这些常见的措施对性行为进行管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康帕内拉认为这种情绪最终表现为服从于一个新的普遍(西班牙式的)君主制的形式——由太阳崇拜而获得巩固,每天四次的祈祷几乎成为一种制度。人们通过简单的饮食与严格的锻炼确保长寿。
更为精细的设计很快跟进。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年)描绘了一个约有400人的都城,城市是建在山上的,城周围是一个700英尺(约215米)的方形广场,广场周围有四座塔楼。城市中有一条公共街道,按照功能,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分别用于食品供应、健身锻炼、军事准备以及美化。城市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食物、药品和水源供应,以及防御安全。根据中世纪的行会规则,城市中的贸易和商业按区组织。大多数的技术行业占据市中心的位置,那里有圆形的寺庙和大型的图书馆。基督城里的居民共同参与道路修建、警卫和农业生产,同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职业。衣服、食物和生产工具由市政当局统一分配,他们的住房也是通过分配获得,以确保平等。但是,他们的进餐是各顾各的,并不在一起。他们的衣服和家具陈设相对很简单;“虚荣奢侈”和“罪恶的包袱”是被明令禁止的。孩童在幼年后便离开父母,尽管女人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教育,但她们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城市不许乞丐和其他无业游民进入,对他们的惩罚是相当温和的,惩罚只是为了纠正错误。正如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科学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
18世纪见证了建筑创新的各种尝试。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于18世纪70年代建造的著名盐场由一个带入口的大型环形城镇组成,城镇中心是管理者居住的公寓和一座教堂,从这里可以俯瞰周围的生产设施。工人们的宿舍与公共果园和菜园毗邻,宿舍在夜间有照明。较远处是管理者办公的行政大楼。尽管几何学的精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一时期的其他设计表明这些主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期间规划设计了几个大型城市,如圣彼得堡,以及各种较小的城市。
19世纪是欧洲社会主义社区运动的光辉时刻。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说明公社集体生活较之私人或个人生活的经济优势),社区常常设计为平行四边形布局,这一布局可以将人口大量安置在中心区域,通常是一栋建筑中。花园和人行道通常被规划在中心建筑的周围,工厂和工业设施与生活区保持一定的距离。1859年至1880年间,让-巴蒂斯特·安德烈·戈丹在诺曼底的吉斯建造了这种类型的建筑。院子中间设计了一个画廊,往来需绕画廊而行,这种设计提供了一片可供谈话的区域,既有较为开阔的空间,又保证了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网格系统似乎更适合较大规模的殖民地采用。例如艾蒂安·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1840年)中的伊加利亚城,50条林荫道与50条大道垂直相交,每个社区包括15座住宅和花园。城市中有三处市民中心,一处在城市中心位置,另外两处分别位于城市两端,各类有害的工业,如屠宰场等安置在城市周边,有助于城市秩序的规划。罗伯特·欧文以及他的合伙人的社区,如约翰·明特·摩尔根的社区,像斯特德曼·惠特韦尔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通常都遵循平行四边形的设计。其他遵循社会主义原则设计的典型城镇是由詹姆斯·西尔克·白金汉(1849年提出“维多利亚”镇的设计)和罗伯特·彭伯顿设计的,在这些设计中,罗伯特·彭伯顿的设计更适合殖民地。本杰明·沃德·理查森在《希格亚》(1876年)的设计中认识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
资本家在这一时期还设计建造了各种工业城市和村庄。19世纪50年代,泰特斯·索尔特在约克郡建造了萨尔泰尔村,公理会教堂位于公共房屋区的一端,另一端则是索尔特纺织厂的入口处。在英国,其他类似的村庄还有阳光港和伯恩维尔,前者是为了安置制作肥皂的工人而建,建成于1888年,后者由巧克力制造商乔治·吉百利在1895年建立。美国人也在芝加哥建造了此类工业城镇——普尔曼城。社会控制的理念在城镇设计中司空见惯,成为建筑设计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杰里米·边沁所设计的著名的“圆形监狱”模型把囚犯牢房安排在发散状的辐条上,从中央大厅可以径直观察到囚犯的活动。
随着世纪的发展推进,美国建立新的首都,风格在主题内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但大部分遵循网格系统模式,虽然自18世纪30年代的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开始华盛顿特区内有了一些圆形主题的变化。奥斯曼重新设计的巴黎,除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茂盛的绿植,还规划有许多宏伟的圆形建筑,常常被后人尊为欧洲最美丽的现代大都市。
19世纪末,城市规划也对工业化做出了反应,出现了一些新的设计方案,重新设想在城市生活中加入富有乡村气息的设计,这种变化在小说中最为常见。其中著名的有威廉·莫里斯关于中世纪情节的作品《乌有乡消息》(1890年)。有人认为,过于拥挤的大都市滋生了贫穷、酗酒等犯罪行为,并在社会中形成恶性循环。如布斯将军的救世军计划所设想的样子,将穷人安置到殖民地,可以让他们重新过上更纯洁和有道德的生活。或者,城市自身被彻底重新定义,正如帕特里克·盖迪斯等远见者的提议,实现“公民化”须将规模缩小,达到可以管理的限度,任何真正意义上乌托邦的实现必须从邻里关系开始。其中最为重要的努力应该是“田园城市”运动。有关城市规划的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最初是由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1898年)的出版引起的,此书试图纠正爱德华·贝拉米的过度强调城市化和技术治国论,同时希望地产能最终被废除。霍华德的成绩在于营造了莱奇沃思和其他的几座田园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住房、绿地与公民的精神关切之间的平衡被纳入优先考虑的因素。城市规划中通过道德层面的平衡来促进邻里合作的方案在之后的波西瓦尔和保罗·古德曼的《社区》(1947年)和另外一些作品中得以推广。这些著作对城市设计到底是为了居住还是为了商业提出质疑。表达对失去的乡村和小镇生活的怀念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流行开来,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1919年)。

查尔斯·T·哈维(Charles T.Harvey)于1867年在纽约格林威治街上骑高架铁路
19世纪,城市横向由内而外扩张,但在20世纪,城市则开始大规模在垂直方向上迅速发展。20世纪初的芝加哥和纽约等大都市,高层写字楼和住宅成为城市建筑的发展方向。不像后来的玻璃和钢铁构造,早期的建筑示范通常追求高精制,是立足青年风格和其他各类风格的精致创新。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方面的领袖是勒·柯布西耶(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的化名,1887—1965年)和托尼·加尼耶。在勒·柯布西耶的“三百万人的城市”(1922年)设计中,摩天大楼耸立于多个公园之间,优先考虑交通运输系统的设计和通信网络的铺设,住宅区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在“邻里计划”(1925年)中,勒·柯布西耶提议拆除巴黎市中心建筑,为摩天大楼让路,在后来的“光辉城市”计划中,他提议让所有人住在里面。他还为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蒙得维的亚、阿尔及尔等城市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并建造了宏伟的建筑,特别是在马赛(1947—1952年)。然而,蜂巢式的设计并没有吸引所有人。拉尔夫·博尔索迪等作家强烈呼吁采用分散式居住。富有创新性的个人住房由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汉内斯·梅耶等人开发,后者是包豪斯学校的校长,包豪斯学校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广亩城市的概念中,劳埃德·赖特提议重新让人们住进美国数千个分散的家园,从而消除农村与城市的差别。
一部分人发现,纵向发展的城市运动让人关系疏远,是非人性化的、丑陋的,也不富有个性;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所有规划都要服从商业目的的观念,尤其是要制造一个高效、可控、廉价娱乐的工人阶级,这一切都应该拒绝。20世纪中期,实验性的、以人为中心的建筑设计继续为巴克敏斯特·富勒等作家所提倡。他们试图用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来实现灵活移动的需要,自给自足的房屋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的独立性;刘易斯·芒福德,霍华德的弟子,同时也是勒·柯布西耶的反对者,主张城市再设计时可以与乌托邦思想联系。究竟是人类自身还是机器更重要?家是车间还是工厂的附属物,抑或情况相反?主流的家庭是回避到郊外的城堡,还是重新融入更为公开的所谓空间?正如哲学家西奥多·W. 阿多诺所坚持的,标准化总是意味着集中化吗?城市只能部分地实现,还是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罪恶之都而不是天堂之城?
到了20世纪晚期,城市发展的乐观前景受到挑战,人口向郊区迁移、城中贫民区数量激增、城市犯罪率攀升,以及早期租房结构恶化等因素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人口向郊区迁移的后果是郊区变成富人聚居的模范城镇,原来的许多城市用地退化为荒地,这种恶性循环在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中被记录下来,并在迪士尼乐园等主题公园里以漫画的形式进行讲解;也有一些在后来经历了城市的复兴。理查德·桑内特等社会学家认为,一定程度上的城市混乱、无序以及无政府状态都可能促进人类自由的发展。然而,高楼林立的新城仍在不断扩建。塔式大厦成为战后英国建筑设计者的首选;垂直方向的贫民窟取代了水平方向的贫民窟。国际大都市似乎成为未来理想的追逐方向。世界上最早的以现代化风格建造的大型城市是巴西利亚。在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等的推动下,苏联在1917年后产生了设计想象力的大爆发,其中包括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1929年的“绿城”计划,该计划的部分灵感来自傅立叶。苏式风格只是主导了一种独特的公寓楼的诞生,这种公寓楼提供的住宿条件很有限,狭窄且不舒服,被中国和其他地方效仿。建造绿化带和住宅卫星城,重新对莫斯科进行城市规划也仅停留在计划中,以重工业为中心才是当时共产主义发展的重点。
现代设计的政治作用在极权主义的建筑规划与实施中也十分显著。极权主义政权的公共建筑通常是气势雄伟、令人生畏、简朴严峻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大规模的集会场所,如纽伦堡体育场和红场等地,其功能主要在于对领袖的崇拜和对寂寂无名却团结的群众的威慑。宽阔的通道允许人群流动,同时也方便军事控制。建筑物可能是为了纪念特定政权意识形态方面的英雄或神话,正如在意大利经常进行的气势恢宏的谋划——作为希特勒最喜欢的项目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提出的柏林新愿景,将柏林更名为日耳曼尼亚。巨大的肖像、鲜明的旗帜和其他一些符号强化了个人对群体的服从。20世纪40年代的集中营将数百万人关押在反乌托邦特征最为明显的城市空间中,有关集中营的设计是考虑得最少的。在某些情况下,城市本身开始象征堕落与罪恶,只有小规模的村庄和乡村生活才受到推崇,在那里,“真正的人”——农民理想的纯洁性得以保持。

生物圈二号
到了21世纪,城市衰败的过程出现了明显的逆转。从20世纪60年代起,保罗·索莱里等建筑师的许多创新性设计将生态主题纳入他们的设计。像亚利桑那州的“生物圈二号”的设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核心目标。磁悬浮列车、风力发电厂和产出太阳能的广阔沙漠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描绘中常见的景象。
伟大的城市也需要引人注目的建筑,如罗马或巴黎的万神殿、大英博物馆,国王和贵族的宫殿,如布伦海姆宫或凡尔赛宫、华沙的文化科学宫、希特勒的总理府,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此外还需要娱乐场所,如歌剧院和剧院。伟大的建筑物往往是自成一体的小都市,在历史上大肆宣扬所谓的传统或现代美德,并以军事荣誉、宗教盛况和公民权力的象征加以美化。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如位于托比亚克的新法国国家图书馆,在20世纪末继续建造。但更常见的是购物中心的发展,这是由美国引进的,数百家商店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为消费者提供包罗万象商品和洁净的消费体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