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迷幻科学家,想让大脑重启关键期
原创 Rachel Nu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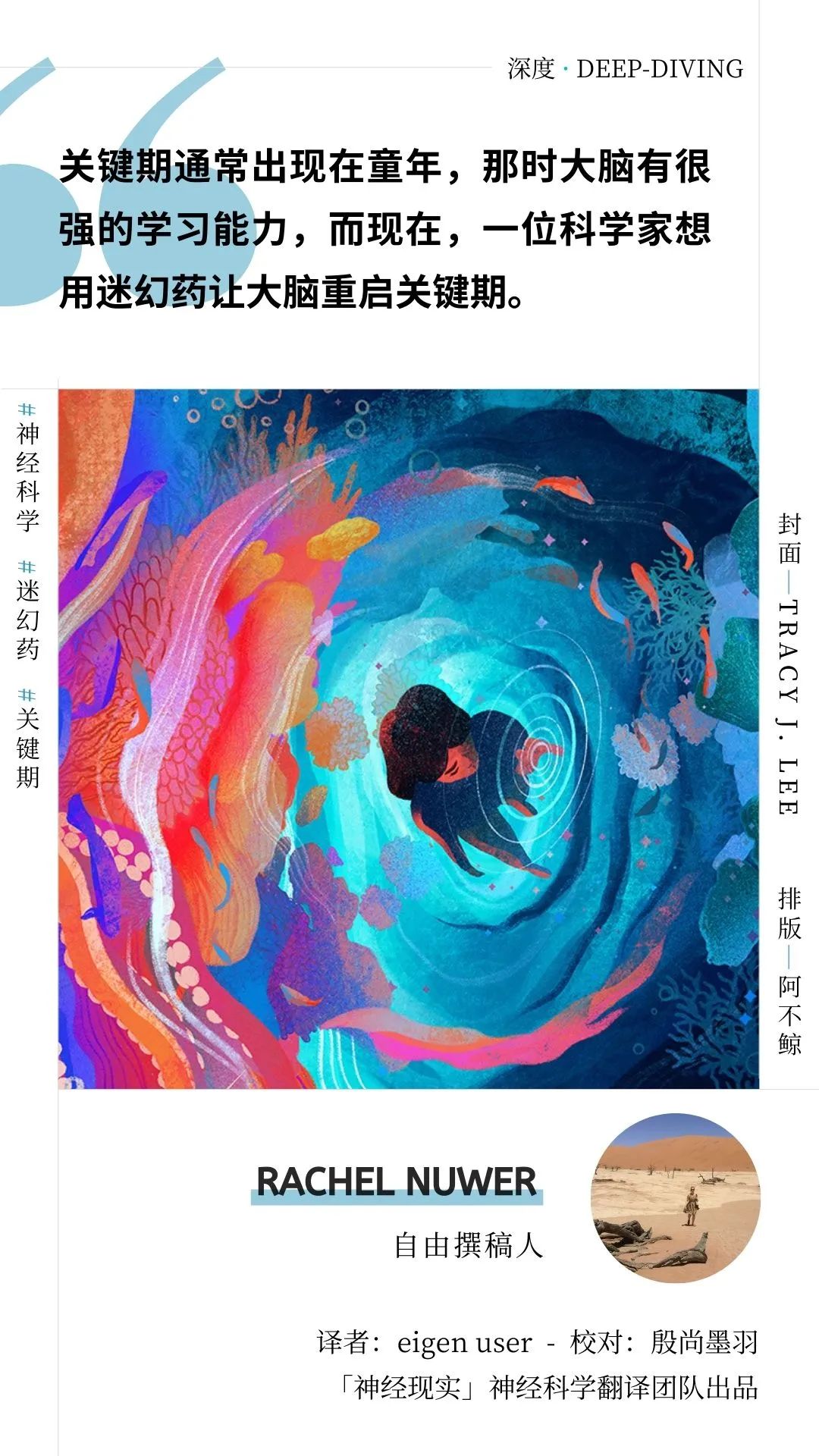
【阅前说明】:请读者朋友们注意,本文仅为科学研究的介绍和描述,不涉及任何药物推荐或治疗推荐,请勿非法使用迷幻药。
在2020年疫情封锁实施了大概一个月时,神经科学家古尔·多伦(Gül Dölen)注意到她开始从现实生活中脱节。她说,“所有东西都让我有些晕晕的”,就好像她处在另一种玄乎的状态一般。那时,她已经不再天天泡在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了,而是闲了下来。这是她生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一次冥想45分钟。
她的感官也变得出乎意料得敏锐。在巴尔的摩四月份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散步时,她能感觉到和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共鸣;她会笑着看着费尔斯角的乌龟们从墨绿色的水中探出头来;她也会陶醉于夜晚阴森空旷的大街上蟋蟀的合鸣;当她看到一个掉下来的鸟巢,而里面的鸟蛋都摔碎时,她会想象到“鸟妈妈深深的痛苦”,以至于她都快哭出来。
她感觉自己像是用了药物一般,或者像是在进行一次精神之旅,体验着寻求开悟的禅僧独自坐在山洞中的感受。有一天,她拿起一支笔开始写俳句。对于《知觉之门》一书中流存的,关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服用麦斯卡林后与一张椅子融为一体的体悟,古尔写了一段自己很喜欢的致敬诗:
渐进论道
我们间的距离
无穷 而又全无
这首诗体现了物理中的一个简单但深刻的道理——不论赫胥黎和椅子隔了一个房间,还是就坐在椅子上,组成赫胥黎和椅子的粒子都互相缠绕着。这也是古尔所体会到的,就好像支配着她感知现实的那个规则随着存在的不同层面变模糊。在这种迸发的创想中,她顿悟了。这种极端的隔绝封锁可能让她的大脑进入了一种特别的状态。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真是一个荒诞的巧合,因为这种状态恰恰是多伦大部分职业生涯所在研究的:一段叫做关键期的,通常位于童年的,具有高感知能力的时期。
关于关键期的古怪问题
关键期在神经科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眼中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关键期为一个物种的行为奠定了基础。关键期是从日到年不等的有限时间窗。在关键期内,大脑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有相当强的学习能力。
在关键期中,鸣禽学会啼叫,人类学会说话。同样的,对于走路,视听,和父母的联系,绝对音准,以及融入一个文化都有相应的关键期。有些神经科学家猜测每一个大脑的功能都有对应的关键期。最终在某个时间点,关键期就会永久的结束。在那之后,认知功能的开放程度便会衰减,甚至是不再发挥什么作用。

- Matt chinworth -
当多伦在巴尔的摩市中心如无形游魂般穿行时,或是独自坐在桌边吃着抹满了花生酱的紫菜卷时,她意识到她花了太多的时间操心她的研究生涯,而没有怎么关注她对于科学单纯的喜爱,也不太留意她有时提出的看似古怪的问题。正如她现在所想,如果她可以重启自己的关键期,自己的思维和生活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多伦相信如果她能破解关键期的密码的话(比如说如何安全地触发它们,或者是触发它们之后可以做些什么),那么一定会带来繁多的可能性。那些失明或失聪的人们或许能够重获视觉或听力;中风病人也可以恢复行动能力并张嘴说话;一个成年人或许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般轻而易举的学会一门语言或者乐器。几十年来,科学家们试图以安全简便的方式使大脑进入这种状态,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结果。虽然他们成功在小鼠上重启了视觉关键期,但是也只能通过把小鼠的眼皮缝上来做到。这种方法并不能用在人身上。
就在疫情封锁之前,多伦认为她已经接近了重启关键期的秘诀。因其治愈人而使人成长的能力,这种秘诀在原住民文化中已经被认可而使用了几千年。她猜测,这种秘诀就是迷幻药物。
西方刚开始利用迷幻药物的疗愈功效不久,而多伦现在可能已经对于这种功效有了科学的,基于大脑的解释。在疫情期间的那种非常不寻常的意识状态中,多伦意识到她需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认识到这点后,她似乎慢慢回到了那种默认的意识状态中,但是不同于之前的是,她现在决定大胆的追从她的好奇心,不论结果如何。
一切有迹可循
多伦认为她对于科学的执着可以追溯到她8岁时。当时她在土耳其度假时第一次见到了海胆。刚从地中海打捞出来的海胆被捧在她祖母手中。这种浑身漆黑,布满了凶狠的刺的奇异生物让多伦想到了她在德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老家的仙人掌。她的祖母给她看了海胆的人一般的牙齿和明亮的橘红色的内脏。多伦感觉自己像穿梭到了另一个星球一般。
就是在安塔利亚的海滩上的那天,她的祖母将她引入了自然世界的奇妙之中。多伦说,她就是通过这种孩童般的惊奇产生了对于科学的兴趣的。

- Zara Magumyan -
多伦说,自己上大学时执迷于那些所谓的大问题,比如说意识的本质,或者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她把自己的专业规划为“关于心智的比较视角”,里面一把囊括了哲学,神经科学,东方宗教,语言学,还有艺术。在这些学科里,她还是最喜欢神经科学。当时不断涌现各种有意思的新研究方法,像是基因组编辑,神经元培养,基因工程等。有了这些技术,神经科学家们就可以以之前未曾设想的方式探究大脑的各种细节。“大家都能察觉到这种趋势”,多伦说,“神经科学会有一次巨大的分子技术变革”。
在多伦最喜欢的一节课“药物、大脑,和行为”中,她学习到迷幻药会介入脑中自然发生的分子机制。当她的教授向大家展示了血清素和LSD的分子结构有多么相像时,她立刻意识到或许迷幻药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帮我们接近主观现实的本质。多伦惊羡地意识到,一个人的所想所感,那些带来独一无二的生命力而使人能够感知世界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些分子罢了。只要把那些分子换成迷幻药,你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尽管多伦意识到迷幻药可以完美地帮我们探究意识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那时候还是90年代中期,也就是药物战争进行的正火热的时候。于是多伦暂时搁置了她对于迷幻药的兴趣,去读了布朗大学和麻省理工合办的MD/PhD双学位项目,加入了一个研究学习和记忆(也包括关键期研究)的组。
当时多伦主要研究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即一种被确认为自闭症主要原因的神经发育障碍。她研究了患有脆性X综合征和自闭症小鼠脑中一种特定的受体,发现以某种方式重塑它可以使自闭症状减轻。这个领域的人们都觉得这项发现有改变生活的潜力。

- Lili des Bellons -
但是在人类志愿者身上开展的临床试验失败了。多伦说,“我当时很灰心,因为我满怀希望觉得一定能行,但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出问题”。多伦和她的一些同事们开始怀疑或许不是物种间的不同导致了试验的失败,而是年龄的差异。实验用的小鼠都还在青少年,但是人类试验者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或许这种治疗能对年轻小鼠起作用就是因为相应的关键期还是开启的。但是对于这个假设,大家也并没有进一步探究。
这个试验的失败意味着多伦需要开展一个新的课题。于是她加入了斯坦福的一个研究大脑奖赏系统的实验室,特别研究可卡因一类的药物是如何侵入大脑制造出强烈快感的。然而她很快注意到,这个组里没有人研究“那个最明显的天然的奖赏”,也就是社会奖赏,指小鼠或人类等群居动物从与别的个体相处中获得的快乐。当时没有什么神经科学家会认真对待这个课题。
她的导师对她关于社会奖赏的点子不太买单,但还是同意让她去研究。在数年的艰苦工作——包括制作了自己的工程鼠——之后,她拿到了第一批数据。她发现催产素和血清素一起作用于一个叫做伏隔核的脑区,能够让大脑从社交互动中感觉良好。用多伦的话总结,就是“催产素加上血清素等于爱”。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但多伦还在继续向上探索。
研究关键期
在2014年她刚在约翰霍普金斯成立自己的实验室时,整个领域已经倾向于相信社会行为是有研究价值的了。为了凸显自己的不同,多伦购买了一整套昂贵气派的神经科学仪器,准备开始寻找下一个“古怪而待探索的兔子洞”。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探索会将自己引领到可以说是现存最古怪的神经科学现象,也就是迷幻药及其对大脑的影响。

- Tracy J. Lee -
在多伦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化石,贝壳,多肉植物,还有古早的科学海报。她把她站立式办公桌后的一整面墙都改造成了黑色的可擦板,在我到访的那个十二月的寒冷下午,上面用荧光记号笔画着各种分子结构,脑区图,进化树,或是爱因斯坦的名言。但是要是你到访她的办公室,你一定会注意到真正占据这片空间的是八爪鱼。所见之处都是八爪鱼马克杯,八爪鱼艺术品,八爪鱼摆件,还有八爪鱼玩具。这些都是她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出彩的论文后收到的礼物。
如果你之前听说过多伦,那大概率就是因为那项出彩的研究。在那项研究中,多伦给一些八爪鱼用了MDMA(即俗称“摇头丸”的主要成分),让这些本来缺乏社会性的动物有了一些像人类用药一般的反应,比如变得放松,在它们的水箱里面到处舞动,或者甚至是反常地对它们的同伴们产生了兴趣。它们并没有像平时一般避开自己的同类,反而是试着找到对方,用触手给予一个紧紧的拥抱。八爪鱼的大脑并不像人类的脑子,而是更像蜗牛的脑子。这个研究中八爪鱼展现出了类似于人的行为,表示了血清素——也就是这项研究中MDMA所模拟的一个重要的脑内分子——在社会性中扮演了一个原始而至关重要的角色。数不清的媒体报导了这篇论文中的研究,多伦也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迷幻文化圈里的大众英雄。但是于多伦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她对关键期的研究。
要不是她的一个书呆子气的法国博士后罗曼·纳度(Romain Nardou),多伦也不会开始关注关键期的研究。纳度在加入多伦的组之前,留意了多伦自己的博士后研究中一个脚注式的发现:小鼠越老,从社交中获得的欣快感就越少,也就意味着很可能社交功能也有一个关键期。但是最一开始当纳度告诉多伦他想要进一步探索这个现象,比如研究随着小鼠成熟催产素信号传导是怎么改变时,多伦的反应是“哦就这”。
她和纳度说,对于一个学界新手来说,他的研究提案在技术方面太平平无奇,实在没法引起别人的兴趣。她说,“我想要你利用好我们所有的乱七八糟的炫酷技术做出点东西”。
但是纳度很固执。他坚持道:“我很确定我的研究会很有意思的。”于是最后多伦还是同意让他试一试。

- Jon Han -
在2015年,纳度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数据的收集。他的实验基于一个简单但是成熟的设计:小鼠先被放在一个有可卡因(或者其它药物)的窝里,然后会被转移到另一个不一样的窝里,只不过这次没有可卡因。小鼠之后就会明显更喜欢呆在那个和成瘾药物联系起来的窝里。每个年龄段的小鼠都会展现这种偏好。多伦指出,“对可卡因的奖赏学习不存在什么关键期,老小都爱”。
在纳度版本的实验里,他把可卡因换成了其它小鼠。为了测试小鼠的偏好,他提供了两种鼠窝:在一种窝里小鼠可以和同伴舒服玩耍,另一种里则要孤独受冷。他反复做了这个实验,从15个年龄段的900只小鼠收集了数据。多伦说,测出的数据可以画出“优美的曲线”。
纳度找到了明显的证据可以说明社会奖赏关键期的存在。年轻的小鼠,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小鼠,特别喜欢在与同伴有关的窝里呆着。成年的老鼠则不关心这些窝有什么区别。它们不会将其与陪伴的乐趣联系起来,但是那些极容易受影响的年轻鼠却会做出这种联系。多伦解释说,“就如同视觉和嗅觉一般,社交也是需要习得的”。并不是说年长小鼠就反社会,而是它们不再像青少年一样焦虑而缺乏安全感,也不会根据同伴的价值取向形成喜好。

- Melissa van der Paardt -
多伦用自己最喜欢的工具之一,即全细胞膜片钳,和纳度一起验证了这个发现。这个实验会取一小片鼠脑,在单个神经元表面放置电极,然后测量该细胞的电生理活动。当他们接上幼年小鼠的伏隔核神经元,并且用催产素(即多伦博士后时发现的与社会奖赏有关的一种激素)去刺激它们时,这些细胞有了强烈的反应。但成年小鼠的伏隔核神经元没有反应。
关键期重启
一个新发现的关键期已经是值得发论文的事了,但多伦还想做的更多。她想要重启这个关键期。从既往的科研文献中,她了解到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感官剥夺。她当时觉得“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自愿剥夺自己的感官”。
当她反复思索可行的办法时,她突然回忆起她在火人节*看到的几十个人紧紧拥抱的画面,而那些人大概都是MDMA磕嗨了。她也想起用临床上使用MDMA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有效性,以及其它能够说明MDMA导致催产素大量分泌的科学证据。会不会MDMA也可以用于重启关键期呢?多伦说到,当她和纳度这个“各方面都和反主流文化没有联系”的直刃族**介绍她的想法时,纳度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同意试试导师的想法。
*译者注
每年夏季在内华达州沙漠举办的狂欢节,宣扬社区精神,自我表达以及非理性。
**译者注
英文为Straight-Edger,原指那些反对消极生活态度(如酗酒吸毒等)的硬核朋克听众。
和之前的研究一样,他们这次也用鼠窝做了实验,只不过这次额外给老鼠用了MDMA。果然,用了药的成年鼠在两周后表现如年轻鼠一般,也喜欢睡在和其它鼠一起呆过的纸絮或木屑窝里。当他们和平时一样检查那些成年鼠的神经元时,发现了催产素仿佛让这些神经元返老还童了。
在2019年,多伦在《自然》上发表了这些成果,并且认定这项研究差不多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纯粹出于勤劳,她决定用LSD再做一遍一样的实验。这种迷幻药通常不会让使用者抱团,而这次实验结果却与其相反。
在一个挤满了仪器设备的实验室里,墙上钉着药物先驱亚历山大·舒尔金(Alexander Shulgin)和安·舒尔金(Ann Shulgin)的海报*,而在舒尔金夫妇慈祥的注视下,博士后研究员泰德·索亚(Ted Sawyer)摆弄着神似出于1950年代科幻电影控制板的一堆旋钮。他面前的一块显示屏上是显微镜下的一块培养皿中内容物的放大图像。对于外行来说,这看起来可能比较像南极洲一张暴雪后的卫星俯视图。而对于操作了几百次的索亚来说,这显然不过一个250微米薄的小鼠大脑切片。
*译者注
为夫妇。亚历山大·舒尔金是化学家,因其对于多种精神活性物质的研究而成名,最著名事迹为亲自测试了MDMA的效果。安·舒尔金则是心理治疗师,首当其冲将致幻剂引入治疗。
没用几秒钟时间,索亚就找到了目标区域:一个悬浮在人工脑脊液中的神经元显示出无比模糊的轮廓。他小心翼翼捻着控制面板上的一个黑色旋钮,远程操控着一个极细的玻璃吸管,让它的尖端几乎碰到神经细胞。接着他转向显微镜边上,拉下口罩用嘴去吸连着玻璃吸管头的塑料管,制造出一个真空腔去让他能够测量神经元的跨膜电流。索亚电脑上显示的阻值有了突跃,说明细胞已经吸上去了。然而细胞通常都很娇嫩脆弱,于是一开始接触成功后,读数便不停往下掉。他弄砸了。索亚和我说这个实验“每次注定要坐上很久搞砸很多次”。运气好的话可能能让他成功测到十二个数据,每个数据都能提供一些见解,比如这个神经元所属的鼠脑是可以形成新的社交依恋,还是成年般地固化了。
当多伦决定研究LSD时,她已经知道用了LSD的人通常想一个人呆着。但是纳度,索亚以及其他人收集到的数据都指向一些别的结论。LSD在重启小鼠关键期,激活它们社会奖赏学习机制上的效果和MDMA一样好。她当时指责自己,觉得肯定是弄错了,就干脆再做一次实验好了。但是同样的结果反反复复,而且也应用于其他让人想独自呆着的药物,比如说氯胺酮(一种解离性药物),裸盖菇素(也被叫作魔力蘑菇),以及依波加因(来源于一种非洲植物的迷幻剂)。同时,在被给予可卡因的小鼠身上,关键期却依然是紧闭,说明迷幻药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大脑。
多伦说,她一直觉得MDMA是一种“超级催产素”。现在她觉得MDMA的促社交效应只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冰山一角。或许在流行文化里,MDMA和拥抱以及恋爱有不可分的关联,但如果多伦不让小鼠去社交,而是做听觉训练的话,她怀疑小鼠的听觉关键期也会重启。通俗来说,就是个“心境和环境”*的问题,即一个人用迷幻药时的内在心境和外在环境。这些环境上的细节也解释了为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用了MDMA锐舞一整晚后不会奇迹般治愈,反而在充满支持的环境里,比如说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同样的药物可以引导他们进行有疗愈效果的认知重评估。同样令人着迷的是,不只是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不管是中风,视听矫正,或是学习新语言和技能之类,只要简单改变用药时所做的活动,几乎任何对应的关键期都能被打开。
*译者注
原文为Set-and-Setting,为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提莫西·赖利(Timothy Leary)在196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迷幻物质,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
一些别的证据也支持这种论断。比如说在2021年,奥地利的一些研究人员无意间发现氯胺酮在小鼠上重启了视觉相关的关键期,但是仅仅当这些用药的小鼠同时进行视觉训练时才有效。多伦在看到奥地利的这项研究后,越来越相信迷幻药或许能成为重启任何关键期的万能钥匙。这种药物在神经方面让小鼠(或者是人)为学习做好了准备;用药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那件事对应的关键期就会重启。
新的领域,新的挑战
这一系列药物有这些潜力,也意味着有些深层次相通的东西使其能改变心灵。目前为止,多伦的研究表明,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并不如科学家们之前所想,发生在脑区或神经元受体的层面,而是与基因表达有关。到现在,她的组已经筛出了65个疑似与这个过程有关的基因,这么多基因的参与也说明了为什么迷幻药的作用时间会远久于欣快的高峰期。多伦怀疑,为了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有关机制,她接下来十年都有得忙了。
同时她也有其它重要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说,每种迷幻药都能让小鼠的关键期激活不同长短的时间。药物作用时间越长,关键期开放的就越久,或许也就意味着疗效也更持久。对人类来说,氯胺酮一般维持半个到一个小时,在小鼠身上则能够重启关键期达两天。裸盖菇素以及MDMA对人有四五个小时的作用时间,却可以让小鼠的关键期开放两周之久。LSD在人身上八到十小时的作用时间,对于小鼠则是三周的关键期开放。依波加因(人身上持续三十六小时)至少让小鼠四周都处于关键期开放的状态,多伦也没有继续测它最多可以使关键期开放多久。

- Jon Han -
假设这些药物也能在人类身上重启关键期,这项多伦和同事在六月份发表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接受迷幻治疗的人来说,在药物作用数天、数周、甚至数月后,他们的大脑可能还会保持着利于学习的状态。多伦说,这意味着接受治疗的人在用药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且会持续从药物作用中获益。
外部专家普遍对多伦的研究有着高度评价。人们通常把迷幻疗法就比做人类心智的“重置按钮”。纽约市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精神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说,在多伦的这项研究之前,没有人能够科学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作用时间如此短的药物可以产生那么长久和转变性的影响”。她也补充道,多伦的研究“恰恰是这个领域所需要的新想法”。
这种方法当然有些潜在问题。在小鼠身上,关键期开放过久会导致神经紊乱。一些专家担心,对人来说,随随便便敞开个人发展的大门可能会抹去他们自身的习惯和记忆,使他们的身份概念摇摇欲坠。关键期同时也是脆弱期。尽管童年通常充满惊奇与魔力,小孩子们也更容易受影响。多伦说,“比起成年人,小孩子更容易毁掉”。这就是为什么直觉会告诉一个负责的成年人,要保护小孩免受那些恐怖的东西的影响。多伦还说,“你会想让小孩学些新东西,但不会想让他们从日本成人片里学日语”。
如果落入坏人之手,用这种方法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的成年人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创伤。最坏的情况下患者还很有可能被虐待。多伦说,无良的咨询师和潜在罪犯可能会通过迷幻药操纵他人。这不仅是一种偏执的猜测。包括多伦在内的不少专家都认为,查尔斯·曼森之所以能对其追随者进行彻底洗脑,就是因为他在灌输仇恨演讲和谋杀命令前会给他们使用大剂量的LSD。
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多伦认为用迷幻药侵入关键期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她只是将其称作一种“极其不可知”的工具。
迷幻疗愈
我面前一整面墙一样大的屏幕上,偶有一两个气泡向上漂过茫茫蓝色,顶部则渗透进一些亮光。从暗处,某个物体游进视野中央:是一只微笑的海豚。一块字幕则写着:“你好,我的名字叫班迪(Bandit)。我们今天要踏上一趟特别的旅程。创造我的人想用我来治愈你。那么就请连到我身上,让我动起来,去吃掉那些美味滋补的小鲨小鱼吧。”这只海豚于是发出一声尖鸣。事实上,这声海豚叫是在巴尔的摩国家水族馆里真实录制的。
这水下发生的离奇一幕随之被屏幕左上角出现的一个小方块打断。在方块里我可以看到站在房间另一头的自己。我的实时图像上布满红色小点,也就是说一个3D跟踪摄像机已经锁定我了。现在我和这只海豚就融为一物了。动动我的右手,班迪就会笨拙的向右边转向。小鱼在屏幕上飞快游过,这么快的速度对于我笨拙的虚拟化身完全不可能抓到。但当我来回挥动我的手时,我开始掌握了窍门。我意识到了我在操控的水世界其实是3D的,于是便开始融入一些前后的移动。最后,我追上了第一条鱼,班迪也很开心地吞掉了它。又抓到几条鱼后,我完成了第一关。为表庆祝,屏幕上放了几束烟花。这个小游戏出人意料的让人上瘾,但我很遗憾没有更多时间看看它还有什么别的内容。

- Jon Han -
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脑护病房,我见到的海豚班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卡塔设计工作室(Kata Design Studio)十多年来努力的结晶。一开始,他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帮助中风病人重获运动能力。3D跟踪摄像头可以让海豚准确反映病人的动作。卡塔工作室的软件主管普罗米特·罗伊(Promit Roy)解释道,“我们会说游戏玩家被塞进了动物身体里”。这个游戏就是非常有趣,从而能激励患者练习并保持一些复杂的运动机能。
在中风后极短的一段时间内,患者是有可能重拾自己丧失的一些功能的。中风的那一刻,关键期会自然而然地开启,并且在几个月后关闭。虽然没有人知道原因,但是多伦提出一个论断:就像疫情时代的隔离让社会变得“加剧不稳定”一样,中风也会使患者的运动机能变得急剧不稳定。患者的运动皮层不再能从肌肉获取信息。于是中风带来的运动能力的突变可能会开启运动机能的关键期。多伦认为,这些天然的关键期是大脑适应根本而剧烈变化的一种方式。

- Jeeeoook -
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治疗通常也只能帮助中风患者补偿一些运动的灵敏度。他们无法恢复全部的运动能力。卡塔工作室和多伦目前正在筹备一项研究,想看看使用致幻剂是否可以帮助中风患者在真正意义上康复。卡塔工作室的一员、中风医生兼神经病学副教授史蒂芬·蔡勒(Steven Zeiler) 称其为“一个惊人的厉害点子”。
如果多伦对于迷幻药的预测是对的,那么海豚班迪和迷幻药双管齐下时,不管中风后多久,我们总可以从外部引导大脑重启运动学习的关键期。要是这个设想成真,只要研究人员能够定下来合适的方式去开启相应的关键期,那么诸如消除成瘾、治疗社交焦虑、恢复受损的知觉,有了致幻剂都不是梦。 在一个典型的巴尔的摩小馆子伯莎餐厅(Bertha's)时,多伦一边享用着青口贝和洋葱圈,一边半开玩笑对我说,她甚至想着用迷幻疗法治疗她对狗、猫还有马的严重过敏。她笑着说: “我用不着治中风。我就是想骑马!”
目前这一切都还是纸上谈兵——但多伦却在这上面大胆押宝。 她成立了一个新的科学小组,专门研究迷幻药是如何解锁并重启各种关键期的。 多伦在做梦时,给这个小组想到了个有点绕口的名字,全称是“迷幻疗愈:利用开放延展性的辅助疗法”,简称就是“PHATHOM” *。多伦说自己 “凌晨两点醒来时,脑子里就有了这个名字”。她还说,她之所以用“深处”的谐音取名,是因为一部分人在用迷幻药时会体会到“类似于海洋的无际感”,而且她也喜欢“让深不可测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点也是重启关键期对她个人全部意义。
*译者注
谐音Fathom,意为深处。这里小组名称的全称是“Psychedelic Healing: Adjunct Therapy Harnessing Opened Malleability”。
她可以想象在将来,迷幻药会与多种治疗结合使用,以增加成功的几率,就像手术前总是会用麻醉剂,或者膝关节置换术之后进行的理疗。 但是我们暂时先不考虑实际应用。
如果迷幻药真的是这把万能钥匙,那么科学家们手上突然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用来推敲我们身份的定义与边界。 毕竟,关键期为我们的习惯、文化、记忆举止、好恶以及作为个体和物种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也对我们的意识体验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是如充满爱和拥护的童年一般美好,还是像被创伤磨损的生活一样暗淡。
鉴于关键期重启可能有着类似于意识状态改变的感觉,那么研究迷幻药的作用机制甚至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深入了解意识的本质。 时间回溯到多年前,当时多伦凝视着投影仪上并排的LSD和血清素分子,并突然意识到,或许致幻剂可以为我们提供那些“神经科学大难题”的最终答案。
多伦说,“什么是意识? 我们又是如何知道东西存在的?这些是大多数神经科学家最开始感兴趣,但最终放弃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本科时的多伦是对的,那么塑造我们心智内在景观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些分子。 但是这些分子却构成了一切差异的来源,比如成人与儿童、健康与创伤、记忆与健忘、以及你我之间的的区别。
作者:Rachel Nuwer
译者:eigen user | 审校:殷尚墨羽
排版:阿不鲸 | 封面:Tracy J. Lee
原文:
https://www.wired.com/story/the-psychedelic-scientist-who-sends-brains-back-to-childhood/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