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假如我和母亲互换人生,我们会怎么选|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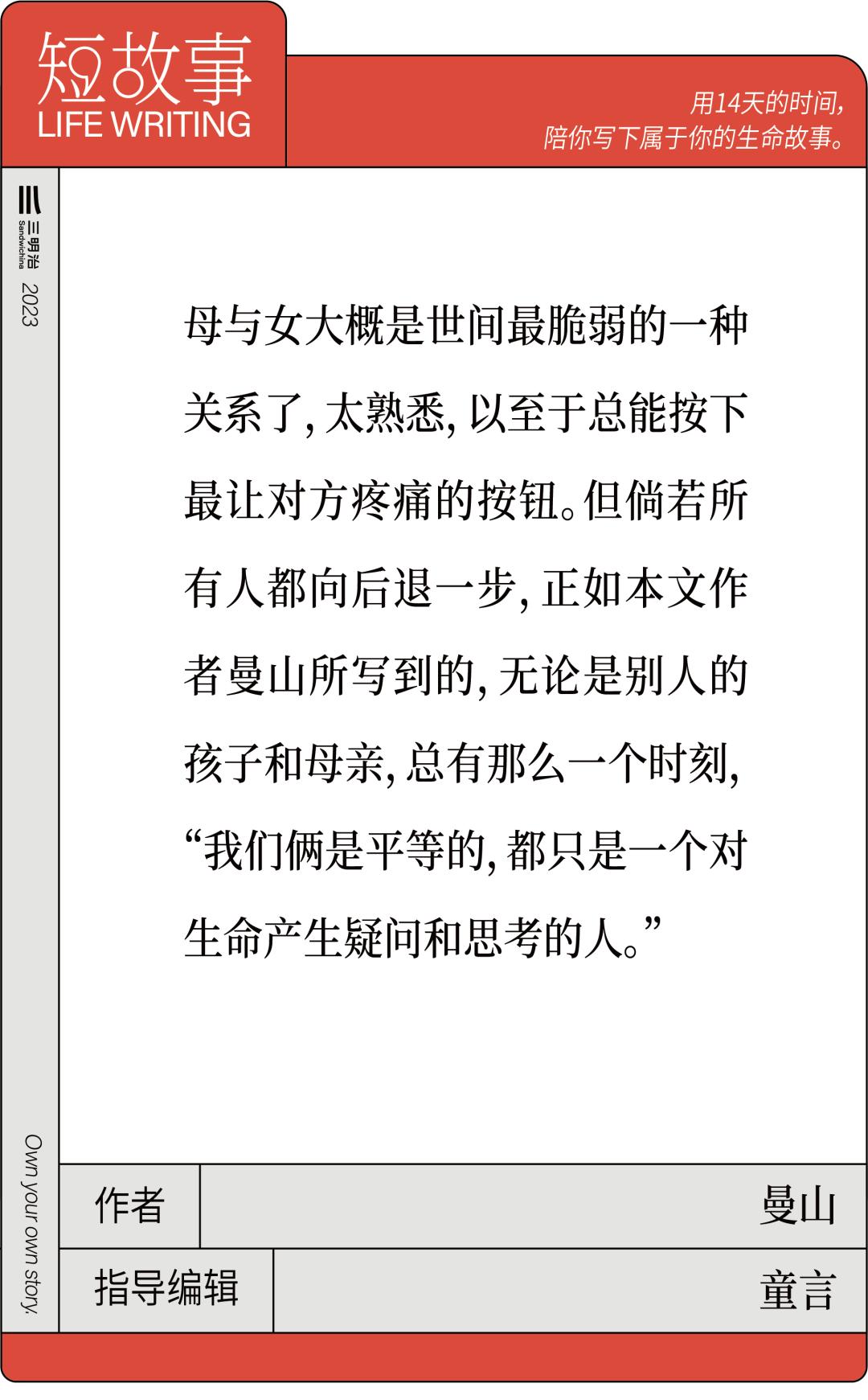
我平时很少自拍,那天,我竟然在大马路上光明正大自拍了起来。一只手举着相机,一只手比出一个“耶”;把头靠在母亲的背上,眼睛闭起来;手举过头顶,翘起嘴角眉毛上挑。那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了许多自拍的灵感,在母亲的电动车后座上,我像一个小孩一样兴奋。
那是我和母亲第一次单独约会。像平常一样,她是那个骑车的人。以前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骑电动车送我,从家到高铁站大约40分钟的路程,她总是不停地跟我讲话,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她总有讲不完的话,好像要把我不在的那些日子都塞给我一样。有的话重复讲过很多遍,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没有在听。有一次下着小雨,我坐在后面,钻进母亲的红色雨衣里,尽管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在母亲的电动车上,我总觉得,我还是一个被接送放学的小孩。虽然在我上学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

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四岁时,母亲离婚了。也许在她心里,我是陪伴她走过那段黑暗日子的人,但实际上,对于那段往事我是没有记忆的。我只记得小时候见过一张照片,是母亲学厨艺时跟同学们在楼顶颠锅,我在一旁拿着一个破掉的锅片有模有样跟着学。那时候母亲下定决心,要带着我开展新的生活。她说我小时候很懂事,走在街上,我总是对很多事情感到好奇,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问个不停。但每次问完,我都会说“我只看不买”,小小的我已经懂得体谅母亲的不容易。
我七岁那年,母亲再婚了。两年后,母亲又生了一对双胞胎,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家从来不是什么模范家庭,父母经常吵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训斥、挨打,还有永恒的贫穷。我觉得从小我就怀揣着两个巨大的秘密,一个是我不是亲生的,另一个就是家庭的争吵和贫穷。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是我心目中的超人。她无所不能,带给我绝对的爱和安全感。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时,我笑称那时的她是“双一流”妈妈,做饭一流,缝纫一流。小时候虽然物质并不富裕,但我的母亲是一个对生活很讲究的人。她总是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还会自创很多美食,那些围着妈妈期待着她变出新花样的日子,不可能不快乐。我至今仍记得母亲为我缝制的第一个书包,它不是像其他小朋友的那样斜挎的书包,而是一个拥有背带的双肩包,有可以拉开的拉链,还有书包外面的口袋,装饰的图案,简直比商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我眼里变成了一头野兽?时而咆哮,时而流泪,让我感到厌烦和沉重。高中时我们两个因为报考学校的事大吵大闹,她希望我读师范院校,这样可以省下学费,但我厌恶当老师,觉得那种工作无聊透顶。她希望我在河南读书,可我偷偷报的全是外地的学校。
我记得母亲第一次跟我讲述她的过去,那些包裹着家庭暴力、性别歧视、家族矛盾的往事一股脑向我涌来时,我是多么惊愕。我以为只是贫穷和争吵的家庭,又有了这么多屈辱不堪的历史。可我能为这段历史做些什么呢?母亲的眼泪和请求,那时的我根本不懂。我只是怀疑为什么这些会降临在我的头上,我甚至有些埋怨母亲,为什么不继续让这些过去保持沉默?
我能对她的眼泪和不幸做点什么呢?我唯一想到的只有逃离。当我不停往外跑时,母亲总是以死相逼。她会说,早知道你长大后会这么自私,我就不该让你读书变得有出息。吵到激烈时,她甚至会扇自己耳光,以这种自残的方式威胁我,好像在说,你凭什么可以享受自由?
她那么拼命想要留住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她像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哪怕是毁灭,也要大家在一起。那些漫长的争吵背后她到底有多么不安,我要到十年之后,才能慢慢理解。
这几年,我逐渐开始向母亲靠拢。当我真正开始思考独立、自由,当我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的一生到底要如何度过时,我的母亲又回到了我的生命中,成了我的一部分。
为了找回和母亲的亲密,我试过很多花招。但这些尝试都以一次性的失败告终。

母亲今年54岁了,那天出门时,她还专门画了口红。她的眉毛也是纹过的,那是去年我送她的生日礼物。她把头发梳的很光滑,在后脑勺扎一个丸子。路口等红灯时,我喊她拍照,她扭过头,嘴巴微张,摆出一个微笑的弧度,她总是嫌自己大笑时会有皱纹。
在这座小城,她熟悉每一条道路,从来不用导航。她二十多岁时,这里曾经承载着她的梦想,那时候她渴望做大厨,赚大钱,然后顺利成章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后来,她还是回了农村,结婚生孩子,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了高中,她又一次离开了农村,到城市里找工作。有一次我问她,这座城市对她来讲意味着什么?她对我说,这里对她而言就是一个机会很多,可以赚钱的地方。像所有城市一样,这里讲究公平,你可以凭本事挣钱,没有那种“黑白颠倒”的人情关系。然后她加了一句,就像北京对于你一样。
对我而言,这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我记得初中时我们班有一个转校生,她的爸爸是从市区调过来的老师,她也跟着来到了这所学校。她是我们班唯一戴眼镜的人,而且她只会讲普通话。那时候我多么羡慕她,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能考全班第一,也有很多同学羡慕我。但那时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样子就是戴着眼镜,说一口普通话。她的爸爸有很多书,比我们小学时图书室里的书都还要多。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城市里的人的样子。
到了高中,我的疆域从我们乡到了靠近市区的镇上。我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封闭式的寄宿学校,每个礼拜只有一个下午的放风时间,每个月放两天假。我上高中时赶上新校区第一年启用,欧式的建筑风格,犹如大学一般的现代化校园,市区和县区混杂的学生,仅我们那一届就有36个班,我的同学中有1/3来自市区,还有1/3来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其他乡镇,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口音到穿着,我被一种新的东西席卷。而且在诺大的校园和庞大的年级排名中,我不再是焦点,我从第一名一下子变成了班级里的中间。于是我不再是那个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的好学生,我给自己找到的新的位置是坐在教室的角落,看着课外书,经常和朋友一起逃课,带着耳机听音乐,自习课上写日记,总是忧郁和颓废的样子。在那个封闭的高中王国,我为自己塑造了这样的形象,并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沿用了这个身份。

我想那是一个拐角,是我和母亲开始往不同方向走的起点。
当我的母亲留在家里,每天要去预制板厂开车赚钱,又要种地,还在重复养育弟弟妹妹时,我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而活在一种精神世界里了。
那时候我开始不再跟母亲讲我的心事,我甚至没有办法跟同学讲。一方面我是精神世界向外敞开但困在应试教育体系里的郁闷少女,另一方面,我是饱含着愧疚无法向父母诉说的女儿。我常常在日记里写,我很想努力学习,高考扬眉吐气,但那股动力不来自于我,而是为了报答父母。我的内在渴望是辍学去流浪,去参加新概念征文比赛,那时的我一心想要坐上火车离开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否上一个好学校不重要,去哪里才重要。而那个地方一定要足够远,远到可以把过去甩在身后。
母亲总说,那时候的我像变了一个人。她也许早就看出了我的虚荣。她记得有一次送我去学校,还没到校门口,我就让她回去了,然后头也不回的独自往学校走。
我从来不邀请同学来家里玩。因为我害怕她们看到我的家庭是怎样的。我也没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家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开间,长大后的我睡里面的卧室,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挤在外面。我们家的大门是木头板拼成的,爸爸生气时踢了个洞,一直没有补上。我们家没有固定电话,我在同学录上留的是姥姥家的电话,然后告诉同学们我常常住在姥姥家。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之后的很多年,我与家庭都是疏离的。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基本上一个月才会有一两次通话。我也很少回家,每年最多回去两次,待不了几天我就买票离开了。
日常通话中我很少讲自己的事,母亲通常也就是问一下我的吃喝拉撒,然后就开始分享家里的事。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在认真听,但母亲的电话是我跟家庭唯一的联系,我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于母亲,好像只有在和母亲通话时我才是有来处的人,我才会开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今的一种身份。
我曾经试过写回忆录,跟着书里的指示,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让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体渐渐游向各处,然后等待某个记忆找到你,最好还能让你流下眼泪但又不至于情绪失控。
第一次做这个练习时,找到我的记忆是高中时我和母亲的几次外出。
我记得高三时我实在不想继续上学了,班主任就把母亲叫来,她没有批评我,而是带着我出了学校在镇上的餐馆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和母亲第一次单独在外面吃饭,我记得那天我们吃了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吃完饭她带我在镇上逛,还给我买了一本畿米的《布瓜的世界》。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学校,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翻着畿米的漫画,好像学校生活又变得可以接受了。而母亲自然又回到家里,继续她的生活。
第一高年考成绩不理想,母亲说希望我再复读一年。我说想试一下艺考,我的母亲就带着我去艺校咨询,老师让我试着画一幅素描,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绘画天分,后来老师说让我再考虑考虑。那天晚上我和母亲睡在艺校的上下铺,那一晚是我第一次失眠,我掂量着自己并没有的天分和家里要供我学艺术的投入,最终我说我还是努力学习参加高考吧。母亲好像松了一口气,同意给我买一个mp3,于是,我带着它回学校复读了。
这些记忆击中了我,是因为我想起在我的高中阶段,那时候我敏感、叛逆、虚荣、任性,有无数的想法和渴望,我的母亲总是陪着我去经历,尊重我的意见,让我自己做决定。那是怎样的爱啊,尽管我当时也非常感动,但好像后来我逐渐遗忘了。

我们到了ZuZu艺术空间,这次约会的内容是一起做手工。我想起韩国恋综里男女约会时,也会去类似的地方,tufing,做玻璃饰品,没想到小城也会有这样的地方。纯白色建筑外观,玻璃窗和门都是圆拱形状,进去之后,木头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做手工的小零件,墙上的凹槽里有一罐罐的毛线球,小珠子,小卡片,到处都是手工成品,肌理画,毛球画,咕卡,还有满墙的拍立得照片,记录来这里做手工的人的温馨时刻。来这里的大多是学生,年轻的情侣,或者好闺蜜。只有我是和母亲一起来的。我选了做毛球画,母亲做手机壳。拿好材料后,我们两个坐了下来。
母亲说,她经常在学校里看到幼儿园老师带着学生做手工,她们学校的老师可以用粘土做出各种造型,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我的母亲在一所幼儿园做生活老师,每次回家她都会不停讲学校发生的事。我给她选了一个穿着红色波点泳裤的大屁股女孩粘土造型手机壳,然后母亲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做了起来。
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是幼儿园的同学。她看着我做的毛球画说,你这个果然很好看啊。她做一会儿,就询问我做的怎么样,好像在等待我的肯定,然后她才可以继续做下去。我没想到,一贯强势的母亲,会有这样的一面。而就在前不久,我们两个还爆发了一次争吵。
那天她在给我缝窗帘,我跟她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独立女性,后来我想了想,其实你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你所向往的那种生活,还是儿女绕膝,男主外赚钱,女主内顾好家庭。”然后我们就聊到了独立,梦想这些东西。
母亲突然很生气,她大声地跟我说,“我没有权利提梦想,完不成任务,不能提梦想。”
我说独立女性就是首先为自己而活,不能为了子女的事牺牲掉自己。
她反驳我,“你就是啥心也不操,反正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的牵绊太多。我不配提独立女性,我也独立不了,我也没有长了本事,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越聊越大声,争辩中开始触碰到彼此的软肋。我没有办法忍受母亲说我自私,在我看来,追求自我是人的天性,是正当的。母亲没有办法忍受我指点她的命运,她总是把命运挂在嘴边。我们之间横亘着的那道鸿沟,掩埋着两代人说不出的伤痛。
我想起有一次我和母亲约定互相采访彼此,我写了长长的提纲,因为我有太多疑问和好奇,但母亲并没有提前准备,她默认我才是那个提问的人。轮到她提问时,她问了我一句:为什么当初报考学校时你都报外地的,甚至还想出国?
我没有想到,母亲对我的疑问竟然是这个。我以为这很好理解,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谁不渴望外面的世界呢?母亲难道没有渴望吗?
但如果她是带着对儿女在身边的温暖日子的期望,带着对女儿这么多年疏离的失望来向我提问,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好像我总是不懂,母亲无缘无故的愤怒从何而来?我只是说了一句,我发现你原来并不是追求成为独立女性的。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有哪一个女性没有渴望过儿女绕膝,被男人疼爱呢?但实际上,在这个家,母亲何尝依赖过父亲?她已经独自扛起了这个家,难道不比一些宣称独立女性的人要勇敢、有担当的多吗?
我说我是独立女性,我是吗?
我把我和母亲放在了对立面。大概这是母亲愤怒的原因。她愤怒命运让她无法选择,而她给了选择机会的女儿却反过来问她,你明明有选择的,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独立女性?
母亲总是以“我只是个老农民”为借口来逃避继续跟我探讨,而我竟然也顺口说出了这是在搞“阶级对立”。口无遮拦里却是我们内心最天然的伤口。
假如我和母亲互换人生,我们会怎么选?
如果是我,会在别人欺负自己的母亲时拿着棍子跟人拼命吗?
如果是我,会有勇气从那段充满暴力的婚姻中挣脱吗?
如果是我,会为了父母和孩子放弃在外打工的机会回到农村吗?
如果是我,会为了孩子而选择忍受没有爱的婚姻吗?
如果是我,会从这个烂摊子的家一走了之吗?
如果母亲是我,她会留在河南读书吗?
如果母亲是我,她会更早一点结婚吗?
如果母亲是我,她会更有决心做出选择,做出一番事业吗?
如果母亲是我,她会给予家庭更多吗?
我们是我,既是天生的性格,也是被过去所塑造的,哪怕是我们还没出生前的过去。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道德都不一样了,我们的父母家庭也不同,这样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

过去的一年,我和母亲有许多共同度过的日子,但真正能让我记得的并不多。
我记得母亲冬天穿的黑色羽绒服上一股油烟味,那是她的出租屋的味道。那一天,我陪她去考科目一,她骑电动车过来接我。
我记得小侄子生病的那天,妈妈一夜没睡,我跑过去看她们,我带着小侄子在外面玩,妈妈在床上睡着了,小侄子因为生病眼袋都出来了,我陪他玩,后来哄他睡着,然后放在我妈身边,他们俩躺在床上,打鼾声此起彼伏。那天阳光多好啊,街道上还传来轧棉花的机器的轰隆声。
我记得妈妈骑电动车带我去拿鲜花的那天,我们在路上经过空旷的街道,竟然聊起了活着的意义。不知道那时我们是否已经开始一起躺在沙发上看《平凡的世界》。但我很确定,那次聊天,我们俩是平等的,都只是一个对生命产生疑问和思考的人。
我想记住的,让我感到放松的记忆,都是母亲展现出真正的脆弱的时候。她的生病、疲惫会让我心疼,她表达自己的疑问、困惑,让我感到不止是我在疑问中活着。
在家的日子,母亲总喜欢一边干活儿一边不停跟我讲话,好像要把她的人生演给我看。她会就任何小事咨询我的意见,比如吃什么,买什么样的拖鞋,好像我是导演,要负责帮她写好剧本一样。
做完手工之后,天都黑了。我把毛球画举过头顶,母亲给我拍照。然后店员给我们拍了合照,好像这是我们的毕业典礼。我想,真好啊,人生中第一次,我和母亲站在了平等的位置。

写下这些文字对我来讲并不容易,它就像一把刀,切开了我的过去。
关于我和母亲,是我从十六岁就开始书写的主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依然没有办法真正写出我们之间的故事。又或者,我很好奇,如果由母亲来写,这个故事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写这个故事时,我反复在读安妮·埃尔诺的书,她说自己的写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的基础之上,对此我感同身受。
我希望自己的文字是坦诚的,反思的,无所畏惧的。一次又一次,向自己开刀,直至痊愈。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原标题:《假如我和母亲互换人生,我们会怎么选|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