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霍金最后的理论:《时间简史》的视角错了
【编者按】
史蒂芬·霍金生前最后的论文,是与他的亲传弟子兼同事托马斯·赫托格合著的。在文章中,他们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新宇宙学,颠覆了他在《时间简史》中提出的关于时间起源的观点。他们认为多元宇宙并没有那么多,宇宙的演化在整体上是平滑而有限的。托马斯·赫托格如今是世界著名宇宙学家,身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引力波中心主任的他,根据霍金遗志,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写作而成了《时间起源》一书。近日,《时间起源》中文版推出,本文为该书第6章《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霍金和托马斯·赫托格
我曾经问过史蒂芬,他认为什么叫有名气。他回答说:“就是知道你的人比你知道的人更多。”直到2002年8月,当他的名气解决了一个小小的紧急情况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回答是何等谦虚。
那是我刚从剑桥毕业后不久,我们合作也有几年了。我和妻子正沿着丝绸之路前往中亚旅行。我此前决定,如果我要用余生研究多元宇宙的话,我最好先再看看我们这个宇宙。然而到了阿富汗, 我们正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那座伟大的天文台(其于15世纪20年代由帖木儿帝国苏丹兼天文学家兀鲁伯建立)的途中,史蒂芬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敦促我去剑桥看他。我们有点儿担心,于是马上就出发了。然而,在试图离开阿富汗时,我们被困在横跨阿姆河(该河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一座苏联旧桥上。驻扎在桥中央的只有一位卫兵,他解释说,为防止人们进入阿富汗,边境过境点已关闭。我告诉他我们是想出去,而不是进来,但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试图通过谈判而通过,我向好心的乌兹别克斯坦领事展示了史蒂芬那条敦促我回去的简短信息。结果他是史蒂芬·霍金的粉丝,几分钟后,他亲自开车送我们过桥进入乌兹别克斯坦,这样我们就可以前往剑桥了。[1]
这时,DAMTP(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已经搬离剑桥市中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数学科学园区的一部分,该园区新建于市西郊的圣约翰学院操场后面。史蒂芬宽敞、光线充足的角落办公室[2]可以俯瞰校园,里面塞满了家居装饰,还经常换来换去,这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银街的那个尘土飞扬、昏暗无光的办公室有着天壤之别。当我冲进去看他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兴奋,我大概知道为什么。
史蒂芬跳过了他习惯性的寒暄,直入正题,打字也比平时快了一两个档次。
“我改变主意了。《时间简史》的视角错了。”
我笑了。“我同意!你告诉出版商了吗?”史蒂芬抬起头来,满脸好奇。
“在《时间简史》中,你以上帝的视角看待宇宙,”我解释道, “就好像我们在从宇宙的外部观测宇宙或其波函数。”
史蒂芬扬了扬眉毛,用他的方式告诉我,我们是在同一个频段上。“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这么做的。”他说道,似乎是在为自己辩护。他继续说道:“上帝视角适用于实验室实验,如粒子散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制备好初始状态,然后测量最终状态。然而,我们不知道宇宙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我们当然也就不能尝试制备出不同的初始状态,去看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宇宙。”
我们都知道,实验室的设计就是为了从外部角度研究系统的行为。实验室科学家会一丝不苟地让他们的实验与外界保持完全隔离。(CERN的实验粒子物理学家更是应该远离他们的高能碰撞以确保安全!)正统的物理学理论反映了这种分离,它把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动力学行为和代表着实验安排和系统初始状态的边界条件在概念上明确地切割开来。前者我们设法发现和检验,而后者我们则努力控制。这就是二元论。
定律和边界条件之间的这种泾渭分明使实验室科学可以进行严谨的预言,但也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因为我们很难将整个宇宙都塞进一个实验室中。我预料到了史蒂芬的想法,于是果断回应道:“在宇宙学中,上帝的视角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是身在宇宙之中,而不是在宇宙之外。”
史蒂芬表示同意,又集中精力地码下一句话。“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敲着字,“我们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物理)哲学思想来为宇宙学服务。”
“啊哈,”我大笑道,“终于轮到哲学了!”
他点了点头,抬起眉毛。他暂时将对哲学的怀疑抛开了。我们已经明白,林德与霍金之争不仅仅是一种宇宙学理论与另一种宇宙学理论之间的争论。这场多元宇宙之争所围绕的是一些关乎物理学理论更深层次的认识论本质的核心问题。我们与我们的物理学理论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关于存在这个大哉之问,物理学和宇宙学的非凡发现又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霍金在他剑桥的办公室,拍摄时间是2012年,他70岁的时候。背景中的是“第二块黑板”,上面有本书作者将宇宙视为全息图的第一次计算。晚年的史蒂芬认为,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宇宙理论和观测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它创造了我们。
自从现代科学革命以来,物理学一直在蓬勃发展,它得益于一种类似上帝的宇宙观——这并不是说它真的像一个造物主,至少不完全是——而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的。
当哥白尼挑战古人的地心世界观时,他想象着自己是从恒星间的一个有利位置去俯瞰地球和太阳系。他假设行星是在圆形轨道上运动,这说明他的日心模型并不准确,但当时的天文观测也不准确。然而,在构想地球和行星的时候,哥白尼把自己视作凌驾于它们之上,并由此开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思维方式来思考宇宙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他发现我们可以从一个遥远的视角(可以被称为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阿基米德点[3])来看待研究对象,以促进客观的理解。尽管这一想法启发的新科学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完善并改变了世界,但哥白尼革命只花了几十年时间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中,人类不再是宇宙的焦点。
今天我们知道,哥白尼的著作只是人类对阿基米德点不懈追求的开始。几个世纪以来,哥白尼的视角在物理学语言中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在今天的物理学中,无论我们研究什么,是加速粒子、合成新元素还是捕捉微弱的CMB光子,在推理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象自己是在自然之外的一个抽象点上来处理自然——你如果愿意的话,可称这个点为“天外之眼”。物理学家们并非真正身处“天外”,他们仍然在地球上,受地球条件制约,但他们已经设计出了更加巧妙的方法来处理和思考关于宇宙的问题,使得我们似乎可以客观地看待宇宙。
朝着这一追求迈出的最大一步,莫过于牛顿发现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牛顿明白,数学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困扰着科学家,这一关系涉及动力学和演化,而并非永恒的形状和形式。他的定律的成功和普适性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科学正在发现关于世界的真正客观知识。牛顿试图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天外之眼”,他想象出了一个固定空间所形成的舞台,由遥远的恒星所标识,所有的运动都以这个固定舞台为参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变化也不运动的绝对空间。他的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决定了物体在舞台上如何运动,但绝对空间本身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在牛顿物理学中,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就像坚如磐石的脚手架,是上帝赋予的固定而永恒的竞技场,一切都在其中上演。
然而,牛顿的绝对背景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能作为一个客观的参考点。他的定律的简单数学形式只适用于这个宇宙舞台上一部分享有特权的演员,他们不用相对于绝对空间旋转或加速。比方说,假设你是一座正在旋转的宇宙飞船里的一名“不享有特权的宇航员”。如果你往窗外看,你会看到远方的恒星也在旋转,并且与你的宇宙飞船旋转的方向相反,哪怕没有任何力作用在它们身上。这违反了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即物体在没有力的作用下保持静止,或保持匀速直线运动。因此,牛顿优雅的定律只适用于那些绑定在绝对空间上的特殊观测者,对他们来说,运动定律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比其他人要更简单。
这就足以让爱因斯坦对牛顿定律感到不满了。我们所描述的自然竟会使某些演员享有特权,让世界对他们来说更简单,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运动方式,这对他来说太讨厌了。对爱因斯坦来说,这是前哥白尼时代世界观的遗迹,这种世界观亟需被废除。他说到做到。爱因斯坦用一个新的、互相关联的动态时空概念取代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他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物理定律的数学表述,使所有观测者眼中的方程形式都是同样的。广义相对论方程(Gab=8πTab)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以何种方式运动。为了解释对于任何一名给定的观测者来说,他的观测结果如何依赖于他们的位置和运动,该理论还配备了一套变换规则,将不同观测者感知到的现象相互联系起来。这些规则允许任何人从这个普适的方程中提取自然的“客观内核”,至少在经典引力范围内是可以的。
相对论实现了爱因斯坦的梦想,即任何人都不应有特权。对爱因斯坦来说,现实的真正客观的根源并不存在于特权观测者的特定视角中,而是存在于支撑自然的抽象数学体系中。他使物理学对阿基米德点的探索超越了空间和时间,进入了数学关系这一超凡的领域。这一愿景巩固了科学界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具有超越物理宇宙的现实性的根本定律是存在的,它们提供了真实的、符合因果性的解释。诺贝尔奖获得者谢尔登·格拉肖也许是持这一立场的地位最高的发言人,正如他在1992年所说:“我们相信世界是可知的。我们确信,存在永恒的、客观的、超越历史的、社会中立的、置身于世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多元宇宙学不顾重重阻力,坚持认为物理学最终建立在牢固、永恒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宇宙理论把阿基米德点移得更远,它比阿基米德、哥白尼甚至爱因斯坦都要大胆得多。多元宇宙学设想具有某种先验存在的多宇宙元法则,并由此再次重申了这样一个范式,即把物理现象的构造空间嵌入固定背景结构之中,而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视角来理解并处理。这又回到了牛顿的观点。
虽然在实验室这样一个可控环境中,物理定律的本体论地位几乎无关紧要,但当我们思考它们更深层次的起源时,问题就会在我们面前暴露出来,更不用说要研究它们的亲生物特性了。我已叙述,当人们冒险进入这些更深层次的谜团时,多元宇宙理论如何陷入自我毁灭的漩涡的。这让我们怀疑,整个大厦或许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宇宙学中的哥白尼钟摆是否过于偏向绝对客观性这一边了?
事实上,哥白尼和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困惑,并没有逃过早期现代哲学家的眼睛。我们这些注定要生活在地球环境中的人类,怎样才能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呢?哲学家对现代科学时代黎明的第一反应不是胜利的狂喜,而是深刻的怀疑,这始于笛卡儿“怀疑一切”的理念,该理念质疑真理或现实这样的东西是否存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格诺拉莫斯”(即“我们不知道”)这一伟大的见解引发了科学革命,也打击了人类对世界的信心。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就曾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一针见血地阐述了这一令人不安、喜忧参半的处境:“伽利略的伟大进步证明,人类的思考既会带给我们最糟糕的恐惧,即我们的感官可能背叛我们,也会带给我们最大胆的希望——希望宇宙外部有个阿基米德点,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解锁普世知识。二者只会同时变成现实。”
对于科学革命,笛卡儿的回应是将阿基米德点向内移动,移动到人类自身,并选择人类的思想作为最终的参考点。现代的黎明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从“我怀疑故我在”,到“我思故我在”。因此,科学革命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况,即人类转向自身内部,而人类的望远镜,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实验和抽象,则向外部扩展,延伸至宇宙深处的数百万乃至数十亿光年。5个世纪过去了,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趋势的结合让人类感到迷惑不解、不知所措。在某种层面上,现代科学和宇宙学揭露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网,它将宇宙的本质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存在相互联系起来。从几代恒星中的碳聚变, 到原始宇宙中星系的量子种子,我们对宇宙的现代理解揭示了这样一个奇妙的综合体。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即史蒂芬试图揭示的层面上,这些发现让人类对自己在大宇宙方案中的地位变得非常没有把握。现代科学在我们对自然运作的理解和我们人类的目标之间造成了一道裂痕,这侵犯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归属感。史蒂文·温伯格是一位狂热的还原论者和极具天赋的阿基米德式的思想家,他在《最初三分钟》一书的结尾处表达了这种焦虑,他在书中写道:“宇宙看起来越容易理解,就越显得毫无意义。”
我不禁感到,温伯格在这里所表达的情感是源于他对物理学法则的柏拉图式理解。在这样一种科学本体论中,我们与物理学和宇宙学最基本的理论是不搭界的。因此科学允许我们发现的宇宙看似毫无意义,从而使其亲生命的特性变得完全神秘且令人困惑,这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如果我们不采用上帝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那又将如何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天外之眼,而是把自己也和其他一切东西一道拉入我们想要理解的系统中,那样会怎么样?在真正完整的宇宙学理论中,不应该分出一个什么“宇宙的其余部分”来指定边界条件, 或维持一个绝对的形而上学背景。宇宙学是一门由内向外的实验室科学——我们是在系统内部,抬头向外看。

“是时候停止扮演上帝了。”当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时,史蒂芬笑着说。
新数学园区的食堂与旧的DAMTP熙熙攘攘的公共休息室相去甚远,后者造就了很多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亲密的友谊。这个新食堂的主要问题倒不是东西难吃,而是它不允许我们在桌子上随手写方程式。
这一次,史蒂芬似乎同意了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的物理学理论并不是免费生活在柏拉图式的天堂里,”他敲着键盘,“我们不是在天外窥探着宇宙的天使。我们和我们的理论都是我们所描述的宇宙的一部分。”
他继续说道: “我们的理论从未与我们完全脱节。”
宇宙学理论最好能解释我们在宇宙中的存在,这一点显而易见,看起来像一句废话。我们生活在银河系的一颗行星上,周围布满了恒星和其他星系,沉浸在微波背景的微光中,这一明显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宇宙有一个“由内而外”的视角。史蒂芬称之为“虫眼”视角。我们是否必须学会接受虫眼视角中固有的那些微妙的主观性元素,才能获得对宇宙学更高水平的理解?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啊。
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史蒂芬的办公室已经变得像鸽棚一样。从同事到医护人员再到各界名流,人们来来往往,但史蒂芬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喧嚣。我意识到,和往常一样,他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嘈杂环境来集中注意力。在我们习惯性的下午休息期间,他给了我一杯茶,同时自己狼吞虎咽地吃了大量的香蕉和猕猴桃。然后,他开始再次仔细审视多元宇宙学的经典基础,并将其视为宇宙学中长期以来的上帝思维的罪魁祸首。
“多元宇宙的拥护者紧抓住上帝视角不放,因为他们认为,宇宙在整体上有着单一的历史,其形式上有着一个明确的时空,有着良好定义的起点和唯一的演化途径。这本质上就是一幅经典的图像。”公平地说,多元宇宙学是经典思维和量子思维的杂合体。一方面,人们想象随机的量子跳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岛宇宙。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发生在一个巨大的、预先存在的暴胀空间内。后者就是多元宇宙理论的经典背景——它也是一个脚手架,与牛顿的竞技场本质上类似,只不过这个会不断膨胀。这种背景使得我们有可能——也很想要——宛如置身于其外般地去思考这个岛宇宙形成的大拼图,仿佛产生岛宇宙与在普通的实验室里做一个实验没有根本的区别。
史蒂芬继续敲着键盘,试图将这一点解释到位。“多元宇宙带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宇宙学哲学,”他说,“在这种哲学中,人们设想宇宙在时间上是向前演化的,并以此来预言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作为一种解释方案,多元宇宙理论赞同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本体论纲领及其对宇宙本质上的因果性和决定论推理。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相关表现就是,人们会认为在多元宇宙中,给定岛宇宙的居民有着独一无二的、明确的过去。
“但你和吉姆同样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构思了你的无边界理论,”我说道,“尽管这种方式应该是量子的。这种有缺陷的因果论观点就是你在《时间简史》中提出的愿景。”
我的话似乎触及了一个关键点。史蒂芬扬起了眉毛,很快又敲起键盘来。
在等待他造句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从身后书架上找到的他1965年的博士论文。在论文快到结尾处,我看到了一段话,他详细地阐述了他刚刚证明的大爆炸奇点定理,并指出,这意味着宇宙的起源是一个量子事件。史蒂芬后来发展了无边界假说来描述这种量子起源。然而,他是通过经典宇宙学的因果透镜特征来解释他的无边界理论的。
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无边界假说描述了宇宙从无到有的创生。该理论被视为另一座柏拉图式的大厦,仿佛它矗立在空间和时间之前抽象的“虚无”当中。吉姆和史蒂芬第一次提出他们的无边界宇宙创生说时,他们渴望对宇宙的起源做出一个真正的因果论解释,不仅要解释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还要解释宇宙为什么存在。但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案,无边界理论预言了一个空宇宙的产生,没有星系,没有观测者。这使得该理论极具争议,这也可以理解,我已经描述过了。
史蒂芬停止了敲击,我倚向他的肩旁去读那些文字。“我现在反对宇宙具有整体上的经典态这一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量子宇宙中,所以应该用费曼的历史叠加来描述它,每个历史都有自己的概率。”
史蒂芬开始念起了他的量子宇宙学咒语。为了判断我们是否仍处于同一频段内,我把我所认为的他的意思重新表述了一遍:“你是在说,我们不仅应该对宇宙中发生的事情——诸如粒子和弦的波函数——而且应该对整个宇宙采取全面的量子观。也就是说要放弃 ‘存在整体上经典的背景时空之类’的这种想法。相反,我们应该把宇宙看作是许多可能的时空的叠加。因此,即使在最大的尺度上,哪怕远远超出了我们宇宙学视界,就像在与永恒暴胀有关的尺度上 一样,量子宇宙也是不确定的。林德和多元宇宙支持者们认为存在一个永恒的背景,而这种大尺度的宇宙模糊性将颠覆这一观念。”
他的眉毛再次上扬,又开始敲击键盘,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这次他的动作更慢,好像是在犹豫。但最后出现了这句话:
“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是宇宙学中唯一合理的起点。”
现在,神谕的级别肯定是在上升。隐藏在他桌子上的一件装饰品中的除湿机正在喷出白色蒸汽,使得这种感觉更为明显。史蒂芬正在把哲学家们通常所谓的宇宙的事实性——即它存在着,并恰好是它本身而非别物这样一个事实——搬向中心舞台。这听起来很合理,但它要把我们引向何方?他准备好重新思考一切了吗?我有很多问题,但我早就领教过,史蒂芬说某件事“合理”的意思是指这些想法他无法完全证明,但基于直觉又觉得必须是正确的,因此并不打算讨论。因此,我试图把对话继续下去,迫切地想知道量子宇宙学更广阔、更流畅的历史观——无论是单个历史还是许多可能的历史——是否能以某种方式让宇宙学理论的整个框架摆脱阿基米德点。一个合适的宇宙学量子理论能否在将我们的虫眼视角纳入其理论框架的同时,还能够坚持基本的科学原理,而不像人择原理那样呢?在哥白尼理论被提出的500年之后,这将是某种意义上的非凡统一。
面对着这场库恩式的范式转变过程中我们所遭遇到的重重迷影,史蒂芬鼓足了所有的精力,再一次慢慢地写了一句话:
“我认为,(对宇宙的)正确量子观将带来一种不同的宇宙学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我们自上而下,在时间上往回演化,从观测所及的表面上开始工作。[4]”
我大吃一惊——史蒂芬新的自上而下的哲学似乎把宇宙学理论中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但当我向史蒂芬提到这件事时,他只是笑了笑。他显然正享受着新发现的甜头,没有退缩。在我们离开的路上,他以其特有的简练和雄心,向我们清楚地阐释了这一全新的视角:
“宇宙的历史取决于你问的问题。晚安。”
注释
1.后来我们在试图离开乌兹别克斯坦时却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因为通过关闭的过境点入境是非法的。
2.角落办公室(corner office)位于建筑物的一角,拥有两面窗户,通常被认为是地位较高的管理人员的象征。
3.来自叙拉古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用杠杆做了举起重物的实验。据传说,他使用杠杆的伟大之举让他说出了这句名言:“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4.史蒂芬所说的“表面”是指四维时空的三维切片。严格地说,“我们观测的表面”就在我们过去的光锥内。举个近似的例子,通常可以考虑处于某个时刻的三维空间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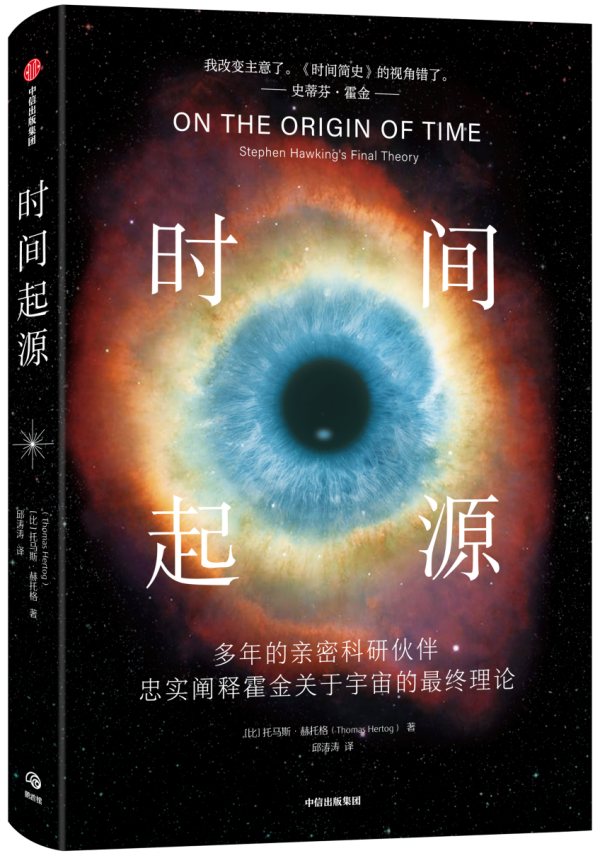
《时间起源》,【比利时】托马斯·赫托格/著 邱涛涛/译,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3年11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