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写作者与读者身上的“文学病”,这位西班牙作家准备好了诊断报告
致
书虫的文学病

“如果生活在一座大城市,图书馆那么多、书籍那么多、讲座那么多、信息超量,有时候会觉得不患上一种文学病有点说不过去。当然这种文学病背后也是对我们生命本身的追寻,因为生命是通过追寻而获得的,这个追寻过程就是阅读,就是通过阅读对象的那个世界来开拓自己的内在空间。”在近期举办的新书《蒙塔诺的文学病》分享会上,诗人胡桑如此描述当下的“文学病”。
《蒙塔诺的文学病》作者来自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他著有《巴托比症候群》《似是都柏林》等四十部作品,并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曾获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等诸多重要奖项。他对现代人的“文学病”有着精准深入的描述,曾有三部小说分别指向了三种“文学病”:
第一种是“巴托比之病”,意思是突然放弃写作的行为。巴托比更早的原型来自作家麦尔维尔笔下的人物,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中的主人公突然停下了自己的工作。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曾把这种现象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巴托比,觉得人的潜能不在于“能”,有时候“不能”是一种更强大的能力。
第二种是“帕萨文托之病”,比拉-马塔斯有一本书叫《帕萨文托医生》,帕萨文托是一个精神分析医生,他专门分析人,关注的是人的消失。
第三种正是《蒙塔诺的文学病》一书所聚焦的“蒙塔诺之病”,这是一种被文学、文本侵袭和占有的病,内心世界里面全是文本、作家、引文,如果没有这些,读者甚至会觉得内心处于一种空虚的状态。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在《蒙塔诺的文学病》一书中,文学批评家罗萨里奥·吉隆多和儿子蒙塔诺都患上了“文学病”,症状却恰好相反:蒙塔诺遭遇写作瓶颈,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的他,疯狂地想要回归文学;罗萨里奥则陷入了对书的病态般的狂热,倍感室息的他只想将文学彻底忘掉。二人的病症都源于文学在生命中的过度存在,亦即所谓“蒙塔诺的文学病”。为了拯救自己,罗萨里奥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心灵之旅,足迹遍及法国南特、智利瓦尔帕莱索和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随着旅行渐趋尾声,他的“文学病”却更加严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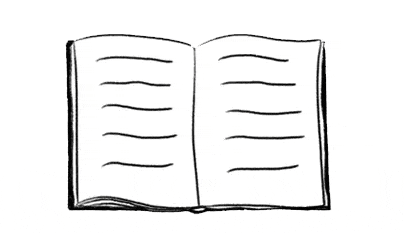
译作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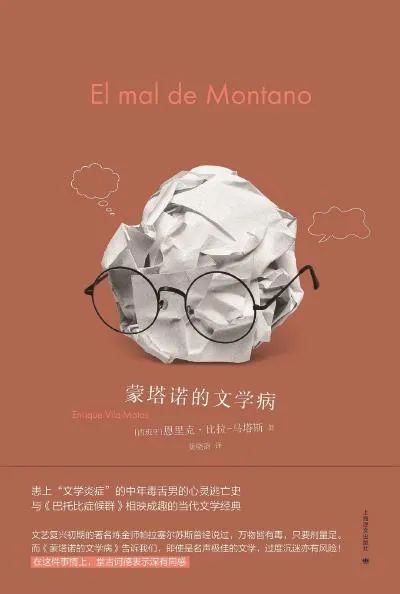
[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黄晓韵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蒙塔诺刚发表了一部危险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些作家放弃写作的离奇事件。随后他便困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无论怎样强迫自己,他还是彻底地陷入了堵塞、停滞和可悲的无法写作的状态。
二十世纪末——确切地说是今天,2000年11月15日——我到南特探望他。正如我所料,他悲伤而枯竭;用普希金的这几句诗来描述他再贴切不过:“他活着并犯错/在森林的昏暗中/用危险的小说。”
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一面,我的儿子——因为蒙塔诺是我的儿子——由于“在森林的昏暗中犯错”而恢复了对阅读的某种热情,我也因而有所受益。在他的推介下,我不久前读了胡里奥·艾华德最新发表的小说《自我边界的散文》。我一直以来对这位作家并无太多好感,在我眼里他不过是小说家胡斯托·纳瓦罗的分身。
今天,我向儿子道谢——当然不仅因为这一件事——感谢他向我推介了胡斯托·纳瓦罗的分身写的那本书。自从他写了那部小说后,他变得不那么像分身了。那是一本好书,我边读边屡屡想起某天在电台节目上听到的胡里奥·艾华德说的话:“一位女性朋友曾经跟我说,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分身,他们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长着跟我们一样的脸,过着他们的生活。”我还记起胡斯托·纳瓦罗某天说的话——有时我还会以为是自己说的:“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自我边界的散文》的叙事者是生活的异乡人,同时又像来自荒诞故事的一位英雄。他有一个隐秘的孪生兄弟,确切来说那是他的表兄,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甚至跟他叫一样的名字,二人都叫科斯梅·巴迪亚。
分身的主题——以及分身之分身、通过镜子折射出无穷的主题——是胡里奥·艾华德的小说迷宫的中心。这部小说——我已经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在评论了——是一部虚构的自传,作家借科斯梅·巴迪亚之口,讲述那不属于他的记忆,编造了那两个表兄弟的世界,他仿佛在回忆那个世界发生的事,并且时刻体现着福克纳所说的:“小说是作家的隐秘生活,是隐秘的孪生兄弟。”
也许文学是这样的:虚构另一种本来可能属于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分身。里卡多·皮格利亚说,讲述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是分身手法的一种变体,但同时也是对文学体验的一个完美比喻。我刚才引用了皮格利亚的话,并且我确定,在我身边充满着关于书本和作家的引文。我是文学病患者。长此以往,文学可能最终将我吞没,就像漩涡吞噬一个玩偶,直至让我迷失在它那无边的领地里。我在文学的世界里越来越感到窒息,五十多岁的我,每每想到自己的命运可能是变成一部行走的引文词典,便焦虑万分。

今天在蒙塔诺位于南特的家中,我确认他陷入了不能写作的困境。于是我试着宽慰他,讲那些关于分身和分身之分身的故事。
“有些巧合和偶然,”我对儿子说,“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这不是胡斯托·纳瓦罗说的吗?”
“也是胡里奥·艾华德说的,不久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剽窃了这句话,也许你还没读过。”
蒙塔诺顿时变得神色焦虑。“全世界的人都写作。”他说。他身旁的艾琳,他的伴侣,向他投去了深切的同情目光。艾琳是个漂亮、安静和聪明的人。我对她了解不深,只在她某两次到巴塞罗那时见过面,但我对她感到安心,我们相互信任。我的妻子罗莎——蒙塔诺的继母——认为她是我这个难以相处、喜怒无常的儿子能找到的最好的伴侣。
“你一定在想,”蒙塔诺对我说,“我很担心,因为自从那本书出版以后,我便不能写作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我不能写作,他人的想法不时地进入我的大脑,它们突然到来,从外面闯进来,并控制了我的大脑,”此时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所以,事实是没有人写作。”
我对他的话有些许怀疑,便问从外面闯进他大脑的都是什么样的想法。他向我解释说,比如,就在我按他家门铃的时候,胡里奥·艾华德的个人记忆刚刚来访。
“我无法相信你。”我跟他说。
“但你应该相信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奇怪的事实。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渗进了我的脑海,我看见了马拉加城加里加·维拉街的拐角,那正是艾华德的住处。我看见了这个场景——就在你来到这个房子、感谢我推荐你读他的小说之前。显然,在你第一次跟我提及艾华德之前我就看见了。我看见了他居住的街道拐角,还见到了康莫多罗阅读酒吧,那是他模仿胡斯托·纳瓦罗写的那本糟糕的小说中出现的酒吧。不仅如此,我还看见了格拉纳达堂西米恩浴场的游泳池,那是他在童年时跟父亲去过一次的地方……”
我无奈地觉得那是他的幻想,也许这位可怜的作家正以一种幼稚的方式掩饰不能写作的焦虑。然而在他那错乱的眼神里,有一种出奇的、真实的宁静。

由于旅途疲惫,我与他们道别后回酒店休息了。毕竟他们要到明天才能招呼我;他们在南特经营一家书店,今晚要与书店的客户共进晚餐。他们坚持让我住在家里,但我不愿意。在南特逗留的这几天,我可不愿当他们的电灯泡。他们开车送我到拉贝鲁兹酒店,并约好第二天我到书店找他们一起吃午餐。到了酒店门口,我在下车的瞬间忽然想看看,那些渗入我儿子大脑里的艾华德的记忆究竟是不是他一时的胡言乱语。我开玩笑地问他,就在那一瞬间,他是否仍在接收艾华德的记忆。
“没有,现在没有,”蒙塔诺认真地说,“但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来访了。应该说,他的记忆正在渗进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中。”
艾琳看着我,仿佛是在为蒙塔诺的话道歉,她觉得他说这些话也许是班门弄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不能写作的、头脑空白的可怜的年轻人。
“你能知道那些来自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是什么吗?”我问他。
“白天的那个记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假装成你。”他回答道。
对此,我表现出了英式的冷静,跟他们说了明天见。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原标题:《关于写作者与读者身上的“文学病”,这位西班牙作家准备好了诊断报告》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