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纪念|乔健:一个人类学家的理想国
【编者按】著名华裔人类学家乔健于2018年10月7日下午在台北去世。本文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小军在2014年乔健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所写,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乔健先生是笔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笔者就读的人类学系当时是香港地区唯一的人类学系,1979年由乔先生创办并担任系主任达11年。此外,乔先生还曾于1978年创立了“香港人类学会”并担任创会会长,并在1986年创立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1994年,乔先生又为家乡的山西大学创建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荣誉主任至今。1994年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后,到台湾东华大学创建了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并在东华大学创建了“原住民民族学院”并担任首任主任。乔健先生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论著丰硕,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贡献卓著。他先后撰写及编辑有三十余种论著,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约百篇。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乔先生的学术情怀可以归结为三个核心概念或者说三个研究视野:人类、中国、民众。
一、人类的理想国
对“人类”的关怀,或许应该是人类学家的“天性”。早在大学时代,乔先生就从对大自然的感受和领悟中开始孕育着自己未来的人类学之路。在描写他心路历程的学术随笔《飘泊中的永恒》中,他曾这样说道:
我并不曾将自己永远关在冷门里,也常常和冷门外的同学接触,但反而感到寂寞。我曾独自奔波于山地,却与万物同有欣欣向荣之感。然而在大学里却觉得单调与沉闷。虽然大自然依然有声有色,大学生却已经缄默了,似一片无风的沙漠,无声无息。
乔先生在大学二年级从历史系转入人类学系时,恰逢人类学的低谷,同届8个人类学的学生全部转出他系,使得当时入系的乔先生成为那个年级唯一的一名学生。不过,系里有着诸多大师级教授,如著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李济、凌纯声、卫惠林以及芮逸夫等先生。这使得他有机会跟随先生们做了岛内当时九个族群的大量调查,并得到了先生们的真传。在台大人类学的学习,培养了他对少数族群的深厚情感,也影响到他在美国选择印第安人研究,到拿瓦侯保留地做田野研究近一年,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传统的延续:拿瓦侯与中国模式》。乔先生在当时是对印第安人做田野调查最长的一位中国学者,对印第安人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和同情。这样一种对少数族群的情怀一直保留着,有一次谈及在法国与红头瑶的同胞聚会时,他深情地说:
我一面陶醉于他们歌舞的优雅,一面却想象这支民族如何于千余年中,自华中而华南而东南亚,由亚洲而欧洲,辗转迁徙数千里。然而他们却能始终保持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特色,终于将这些特色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里植根生长,这是多么动人的一篇史诗啊。
在此,乔先生抒发出人类学家的特有情怀——一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尊重、感动和珍惜。然而对比如今,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许多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十分冷漠,甚至将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鄙之弃之。一个民族若丢失了自己的文化灵魂,将是多么悲哀的一幅场景啊。
亚(洲)美(洲)的文化关联,是乔先生长期的学术关注之一,这是一个十分“人类”的话题。乔先生在美洲的拿瓦侯、祖尼和玛雅研究并非简单的猎奇,而是有着人类的视角,因此他十分注重与中国社会直接比较的研究。《拿瓦侯沙画与藏族曼陀罗之初步比较》的论文是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和西藏早期社会的比较研究,另一篇是《藏族〈格萨尔〉史诗讼唱者与拿瓦侯族祭祀讼唱者的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背后,有着乔先生自己曾经述说的心底的一个咒语,即是他在赴美留学前一位前辈关于“Indians”的话。
这位前辈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中国,是殷商灭亡之后向北迁徙的殷人后裔,哥伦布1492年到巴哈马群岛误以为到了印度(由此有Indian)的说法,其实是当地人说我们是“殷的”(谐音Indian)。前辈瞩托他研究印第安人的“咒语”,不想影响到他对族群的研究和上面亚美关联性的研究。对此,他特别提到著名语言人类学大师萨皮尔(E. Sapir)的一个夙愿是论证北美的拿德内(Na-dene)人的语族与汉藏语族可能同源,而萨皮尔的高足中有一位中国学生,就是后来曾在清华任教的李方桂先生,李方桂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拿德内语言的。萨皮尔的推论十分大胆,不论这个推论是否正确,在这样一种将亚洲和美洲关联起来的跨越的想象中,包含着两个十分有深度的视野:一是超越国家的全球视野,二是超越种族民族的人类视野。这两点对于今天的人类颇为重要,因为当今国家和种族之类的争斗,正是现代社会战争、不平等与贫困的伴生物。人类学家是有国界的,但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和贡献却应该是跨国家的。
对于亚美关联的研究,后面的关心是世界文化的形态及其变化。例如两种文化之间是共通还是分割?是破裂还是连续?是一般还是特殊?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是超越“国家”的,是以“文化”来考察的。一个有趣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或者文明比较欧美文化是更加连续的,而欧美文化则是破裂出来的。乔先生在《印第安人的诵歌》中引述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连续的文明即“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张先生认为这种连续的文明更加体现在亚洲。扩展来看,所谓美亚文化或者西方与东方谁更连续的问题,是一个整个人类的问题:谁更近自然,谁更近文明?今天,与自然更加连续的文明被斥为落后,而那些以掠夺自然为特征的断裂的文明却成为人类的主流。这不能不引起人类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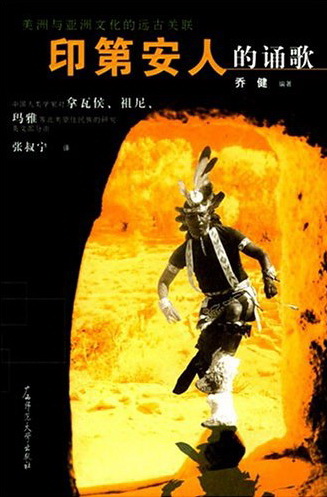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是华裔人类学家的共同关心。乔先生自幼离开大陆,但是家乡的情结十分深厚。他从美国回到中国港台地区任教,相信也与这种情怀有关。乔先生的中国研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如大陆少数民族和族群的研究(《瑶族研究论文集》《惠东人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族群》《瑶族及瑶族研究近况》《惠东的常住娘家婚俗:解释与再解释》等)、台湾少数族群的研究(《文化变迁的基本形式:以卑南族吕家社百年经验为例》等)、中国家庭等领域的研究(《中国家庭及其伦理》《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国家庭及其变迁》等)、底边社会的研究(《乐户》《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等)、香港文化的研究(《香港地区的“打小人”仪式》等)、探讨中国本土概念的研究(《关系刍议》《人在江湖:略说赛场概念在研究中国人计策行为中的功能》)以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领域的论著和论文。
2014年11月上旬,受麻国庆教授之邀,我有机会到20世纪80年代乔先生研究的粵北连南排瑶村寨考察,在三排镇的南岗村和油岭村,看到了两个村寨完全不同的对比景象:南岗被公司圈寨,重新修复的房屋景观很美,但是因为百姓被迁出,村寨文化已经空壳化;油岭村坐落在老瑶山顶,人口七百多人,房屋已经破损严重,却顽强生存着淳朴的瑶民。如何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保住他们的文化,又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似乎是对人类学者永远的挑战。远眺喀斯特起伏的山峦,令人感到一种山地民族的沧桑和人类学责任的凝重。
乔先生一直关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中,乔先生指出了四点困境,其中之一是功利主义的压力,很多学生会问人类学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说有什么用处。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可以应用于现实问题的一面,他列举了潘光旦先生关于土家族研究的例子,也提到“民族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变异,说蔡元培先生在1926年的《一般》杂志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说民族学》一文,清楚说明“民族学”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可惜这个译名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它带给学科的误解依然存在。这其中,作为一门西方发展起来的学科,传到中国之后,的确有一个所谓“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问题。
人类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几代学者的追求和困惑。在乔先生看来,所谓本土化并非另搞一套封闭的学科体系,中国学者要对世界学术有理论贡献,就要有立足本土的深入研究,由本土概念、本土案例去建立理论。乔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了“关系”的概念、江湖“赛场”的概念和计策行为模式的理论。此外,乔先生还主编了《中国文化中的计策问题初探》。他认为:
在现代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研究中,不断有人尝试以概括性的概念来捕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貌。比较早期的如费孝通(1947)以“差序格局”为中国社会的特征,胡先晋对于面子问题(1944)、杨联陞对于“报”(1957)、芮逸夫对五伦及礼(1972)以及许娘光对于父子轴(1965、1968、1971)的讨论都是著名的例子。从事这种研究方式的陆续有人,譬如对于“面子”以及“报”的研究一直没有断过,比较新的则有对于“人情”(金耀基1981)、“关系”(乔健1982)以及“缘”(杨国枢1983;李沛良1982)等的研究。
概念在科学研究中是一种工具。对于事实的描述,用什么概念描述得到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上面的“关系”“人情”等概念,都是对中国文化事实提炼出来的概念,对于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在1982年的《关系刍议》一文中,乔先生是第一个提出本土的“关系”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在他的研究之后,才引起阎云翔、杨美惠等人的陆续研究。
尽管中国研究具有地域和国家的特征,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的“民族主义”,在《飘泊中的永恒》前言中有如下一段话:
大部分的瑶族一方面固然是飘泊无定,但另一却对他们历史上或传统中的远祖居地有着永恒的思恋。于是笔者写了本级中的第八篇——《飘泊中的永恒》。人类学者虽不断改变他们的研究题目,却也在始终不懈地追求一种永恒长久的东西——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规律与结构——这种东西要比瑶族的远祖居地更为古老。
乔先生藉由瑶族对自己祖居地的永恒思恋,想到人类学家的永恒追求。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他者或者异文化的研究,永恒的追求并非只是一国、一族、一乡、一地的研究,而是探索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规律与结构,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学视野:理解人类之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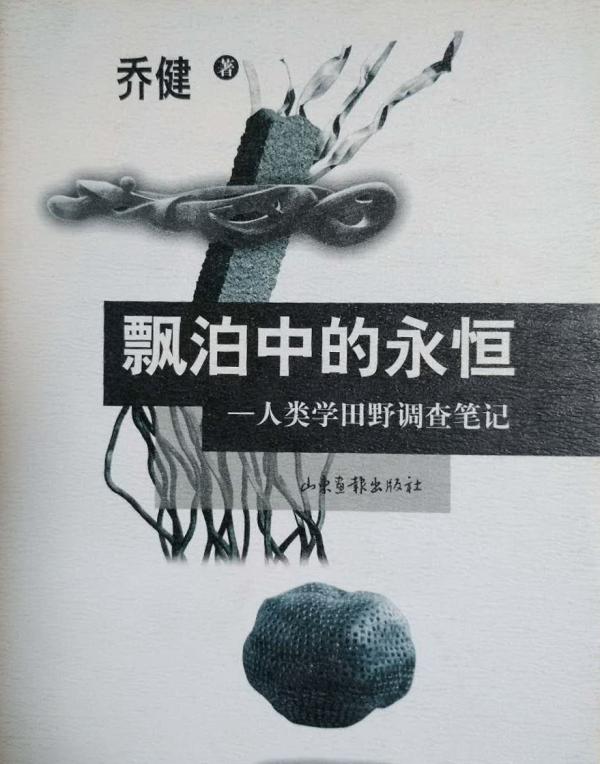
人类学家常常关注底层人群的研究,《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是乔先生主持多个研究项目的结晶。包括乐户、北京与河北底层艺人、刹头匠等的研究,台湾底层社会的研究,以及大陆城乡新底层人群的研究。乔先生使用“底边阶级”来表述这一历史和当代社会的现象,并使用特纳的“阈界”概念来进行理论点分析,在《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中,他谈到自己在乐户研究中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这种文化震撼既是来自对庞大的底边社会过去的疏于理解中,也是来自一种深深的人类学关怀。这样的情怀在乔先生的家乡研究大作《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的序言中有所表达:
贱民是生活于传统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阶级,笔者称之为底边阶级,过去对他们的研究极为少见。但他们毕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部分。不了解他们,何能了解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貌?
乐户研究是抢救性的研究,也可以算作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作为一个有着长久历史传统的群体,在乐户身上浸透着“国家”的血液。他们本来是国家仪式的一部分,曾经享有着“乐籍制度”。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乐户从国家的舞台上逐渐消失,并在后来逐渐跌入社会的底层,但他们却以民间的方式,继续吹奏着国家的曲调。如今,当这样一个人群被纳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底边生存,还有着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流淌。
说到“文化”这个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乔先生在《异文化与多元媒体》中有一个发展,即“异文化(alter-culture)”概念的提出。从英文看,alter这个词具有改变、变化等含义,直译当是“(变)异文化”——变体、变形、变态或异体、异形、异态等,乔先生在书中论及异文化包括了“次文化(subculture)”和“他文化(hercullure)”,十分贴切。在异文化的研究后面,是对相对于主流文化或自体文化的次文化和他文化的关注,因为深层是文化权力的问题。特别是在阶级文化之下,可以看到文化权力的差异。
对于次文化,女性文化或可以算作一种。在乔先生参与主编的《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中,他写了一篇小文:《性别不平等的内衍与革命:中国的经验》。文中他使用内衍(in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这对概念,从历史的视角来解析性别不平等。认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来自父系社会,而是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权力集中的程度和政治一体化是女性不平等观念内衍的主要原因。”另外一篇相关的小文章发表在《瑶族研究论文集》中,题目是“广东连南排瑶的男女平等与父系继嗣”。从这些小论文中,可以体会先生对社会平等的理想期待。
随着社会的巨变,人类学家也需要不断地适应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近两年的研究中,乔先生开始关心家乡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而这在先生的早期台湾的研究中就已经开始了有深度的思考:
在急剧的变化中,台湾少数民族不论在深山里还是平地上的,都已经全部或局部地扬弃了规律的、保守的、稳定的与特殊的固有文化形式,而呈现出一种失调、复杂与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既非藉老头目、老巫师的追述与解释可以了解,亦非我所学到的那套机械的、形式的、单纯的理论与方法能够圆满地加以研讨与表达。我开始觉得,现代的社会科学家,除非甘心为陈旧的名词作填充与解释,否则便需进一步探索一种更细微、更贴切、更活泼、包容更多的方法与观念,来处理这繁复多变的现代的社会,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
这样一种理解,充满了挑战既存理论概念的勇气。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最近两年,乔先生在自己的家乡山西省介休市积极推动文化保护的实践,也体现出先生对家乡的浓浓乡情。十多年前,我曾参加法国远东学院的水利研究项目来到介休市,研究洪山泉和源神庙碑刻,碰巧来到了乔先生的家乡洪山村,在对洪山泉和源神庙的研究中,体会到山西民间社会中深厚的文化土壤。洪山泉(古称鸑鷟泉)的水利灌溉体系,就是一个难得的文化典范,围绕源神庙的民间水利管理,凝结了洪山人的古老智慧。我曾经发表过研究论文,但仍难以表达这片土地中深厚的文化思想。在这样一片文化沃土之上,从先生一腔人类情怀之中,吾辈更加体会到身上的传承责任。
值先生甲午年八十寿辰之际,笔者谨冒味代表师门弟子,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也祝愿大家共同的人类学事业兴旺发达!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