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知青在北大荒一待就是30年 |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①
编者按: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考察时说:“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共和国把这里作为战略基地、把农业作为战略产业发展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发生了沧桑巨变”。20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到了70年代末,95.5%的知青返城了,80万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今年正值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当年的留守知青如今年纪大的已年过古稀,年纪小的也将近花甲,作者从采访过的数百位对象中选出19位最有代表性的知青,这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了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述说着从下乡到坚守的过往岁月。

返城机会?机会倒是有的,1975年,我妈妈退休,我让妹妹接了班。她是六八届毕业的,去北大荒投奔我,下乡到十三连。我让她回了上海。
恢复高考头一年,我们家付中义就叫我去考。
我是六六届老初三的,我记性很好,(读书时)学习一直不错,毕业后才“文革”。
付忠义说:“你复习复习,肯定能考上。”
我说:“我不考。”
付忠义工资低,四十多块不到五十,要养两个孩子。老大在上海我母亲那儿,月月寄钱,再供我上大学,一笔钱分四下,哪够啊。1972年,我结婚那年,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退休了,也没能力供我读书。
怎么下乡到北大荒的?1966年初中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在家待了两年就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家姐妹五个,五朵金花,我老大。父亲是工厂的工人,母亲以前是家庭妇女,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就工作了,在一家工厂的食堂。
我妹妹是六八届的,老师吓唬我们:“你们两个得有一个去北大荒。”我想,我走远一点,我妹妹就能离家近一点儿。我有五个闺蜜,两个选择去北大荒。我说我跟你们去北大荒吧,我不太喜欢南方的水田,也有到外边闯荡闯荡的想法。
我是1968年下乡的。刚下乡的时候,我在农工班,本地小青年说我长得漂亮,又冷又傲。机务排的本地的多,他们看到城里的姑娘想接触又不敢,就调皮捣蛋地逗逗。我跟他们是不说话的,个别淘气的来拉我的手一下。我拿出手绢擦擦手,把手绢扔了。
我在连队很不得志,也很压抑。珍宝岛局势紧张后,成立武装连队,我家庭出身比较清白,把我调了过去。武装连队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把我弄下来,去了农工排。你心高气傲,人家不拿你当个东西,你傲什么傲呀?
收割时正好是雨季,麦子涝在水里头,连抢带割一个多月,来例假都不让你请假。立秋后,黑龙江边已很冷了,脚得咬着牙往田里踩,在水里头一浸浸一天,早上出去穿条干净裤子,回来时脏得都洗不出来,都是褐黄色的泥。下工回到宿舍洗完脸洗完脚,拎着脱下来的裤子到小水沟去洗,洗完晾到外面的晒衣绳上。第二天早上起来,裤子根本不干。很多人身体就这样弄坏了,造完了。我的腰椎间盘突出、腿疼就那时落下的。
8月草最肥美,荒草垫子里面蚊子大着呢,就听见蚊子在你跟前“嗡嗡”地飞,吃饭时张开嘴,弄不好就带两个蚊子进去了。东北打草你见过吗? 男的拿大扇刀,长的80公分,短的也有50公分,靠着腰劲一扭“唰”的一片,一米来宽的草就割倒了。女的没劲,用小镰刀割。冬天牛羊马吃的草料,苫屋顶、编盖粮食用的草帘子,都靠割的草。
刚下乡时的指导员很好,部队营级转业干部,后来提为别的团的副团级了。他走前特意把我叫到家,他老婆也在。他说,新来的指导员生活作风不好,跟小姨子乱搞过,小姨子怀过孕,你长得太漂亮了,要提防点儿他。
新指导员上任后,总有意无意想接近我。我故意疏远他,离他远一点。跟我一起下乡的“小辣椒”偷出我的信件给了指导员,他就借这个引子引诱我。父亲上班路上认识了一个送牛奶的男孩。送牛奶有车,他就让我父亲搭一段路,两个人就熟了。他是1946年生的,属狗,我父亲也属狗,两个人像有缘似的。我父亲有意把我嫁给他,说得也不太明白。那小子上我家来过几趟,可能有那个意思吧。后来,他参军走了。他是上海郊区的,我下乡时为什么没去郊区农场?我那样不等于送上门了吗?跟他又没什么感情,家里来信跟我又说起这个事。指导员见我没上他的当,他就告诉手下的人打击我。
“小辣椒”为了保送上大学,跟指导员发生男女关系。结果没走上,她就把指导员咬出来了。我说,他那时候那么勾引我,我要想上大学,应该头一个走。“小辣椒”还不是自己立场不坚定。
我怎么认识老付家?老付家两个小子跟我在一个连——一连,我老婆婆在一连的缝纫组,跟我挺熟。青年刚下乡那会儿,男孩缝缝补补都不会嘛,我老婆婆手比较巧,一般衣服什么的都会做,给小青年缝缝补补的,跟大家处得挺好。
付忠义的表妹,他大舅的二姑娘跟我睡一个炕。我俩挺说得来的,没事领我去她姑家,离得都很近。他表妹总领我去老付家,就有给我们牵线的意思。当年小青年说我这个人很傲,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弟弟付忠喜却看中了我,他跟他妈说了。他妈说,你大哥还没结婚,你倒先想结婚了,给你大哥吧。我老婆婆有这个意思,时间长了也就成了。
谈恋爱?其实也没谈什么恋爱,说不好听的话,我们结婚前连手都没拉过,我找付忠义,就是寻思找个当地的,有个靠山,不被指导员欺负。当时上海、北京的知青都找我,我不跟他们谈。老付是党员,不归指导员管,只要跳出他这一块,他奈何不了我。我有这个想法才找的付忠义。
我们家老付这个人别的好处一点没有,就是一个老实。老付有过一个对象,赫哲族姑娘,沾着点亲戚,是他二姨夫那边的,属于父母包办的。老辈跟苏联通婚的也不少,以前赫哲族女人难产,苏联动用飞机接到那边去生产。我老婆婆都准备给他们结婚了,领导就找他了。那时跟苏联关系紧张嘛,领导说你刚入党,组织对你还在考验中,不好跟“苏修”扯上关系,这事儿就拉倒了。
我们家老付那时在八岔邮局上班,一米七四,不黑,他们哥们长得挺像的。他13岁就上邮局上班,挣钱养家了。那时,他只要回来了,两个弟弟就偷偷告诉我:“我哥回来啦,叫你去呢。”我就上他家玩一会儿。他两个弟弟都在跟前,我们也没什么好唠。
指导员找我谈话:“听说你谈对象了?”我也不敢承认啊,那时不允许知青谈对象,承认不是找挨斥儿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没有?我都听说了。”我来脾气了,我说,说我有啥关系?说你指导员的都有。他说,怎么个说法?我说,别人说你的话,我信,我也不信。我不相信你指导员能做那个缺德事。他说那你怎么又相信呢?我说我相信呢,因为说这个事儿的人不是小老百姓,不是一般人,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实际上是告诉他别动我的脑筋了。他恨我恨得要命,处处想捏死我。
我爸比较开明的,知道我谈对象,就问了一句:“民族政策你了解吗?赫哲族风俗习惯你知道吗?首先不能违反政策,别到时候一杯苦酒喝下去,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听说我要结婚,我母亲给我寄了两床被面、两套衣服。我婆婆给我做了两床新被。老付要跟我结婚,调回了勤得利邮局。我们是1972年1月结的婚,我22岁,老付是25岁,他比我大3岁。
结婚生了小孩,我就调到农场物资科去了。老付是物资科的支部委员,邮局就他一个党员,业务归县里管,组织生活要在当地过。人家对我比较客气,物资科有几个上海知青也比较谈得来,不像在一连,指导员偷偷摸摸总想弄你,我的日子就比较好一点了。

我们家付忠义说:“你考吧,我供你。”
他想让我发挥更大的能力,觉得我这辈子干啥都拿得起放得下。
我说:“一方面我如果考上了没有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我不想欠你的情。”
为什么不想欠?我们文化差异本来就够大的了,他才(读)小学五年级,我初中毕业;他是乡下的,我是城市的,见识比他强,处事比他果断。虽说我比你高一点,距离还不算太远,还可以平起平坐。如果我考上大学,我们文化上的差异拉得更大了。没有了共同语言,硬捆绑在一起,对谁来说都不好,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我要瞧不起你嘛,人家说我没良心,我也委屈我自己,我也不想这么干。我要上大学不可能再回来了,两个孩子他带一个,我带一个,孩子缺爹少妈,这个家分成了两半。人家会骂我是“女陈世美”,还有两个“孽债”,我不想这么干,所以我就没考大学。
遗憾肯定有的。我家姐妹五个学习都很好,我从小就被我爸当男孩养,他一心想培养我。我爸跟我商量过:“供五个女儿上大学,我是没那个力量。你是老大,英语学得很好,长得也不错。”父亲想让我初中毕业考外语学校,将来当翻译。
我父亲出生6个月过继给了有钱人家,6岁上学读书,读的是1949年前的贵族学校,跳了好几级,11岁就初中毕业了。他本来是苦出身,爷爷奶奶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他毕业时那家破产了,养父死在监狱,父亲只得到洋行做事。他的英语特别好,能说能写。19岁时,他觉得老给人家听差脸面上过不去,就不干了。
没考大学是个遗憾,我考上大学不是也圆我爸一个梦吗?
知青大返城时,我想不想回来?也想回来,可是我知道家里没有实力,父亲已经走了,母亲没有那个能力,另外回上海有份好活儿还行,没有活儿谁养活我?我一个人回去了,假离婚要变成真离婚也不好,我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

刚结婚的时候,总有一点互不相让,也吵过闹过。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的大男子主义。
我老婆婆爱出去玩,我们家老付就不知道帮我干活,老跟我急眼,觉得我干多少活都是应该的。他们哥们家务活都不干,这一辈子我也挺伤心的。就说洗衣服,老付根本不洗,都是我洗。我还是上海那个习惯,脏衣裳从来不过夜,今天换下来的衣裳今晚必须洗掉,内衣三四天就要换。
勤得利那时候穷,不少人都没有内衣,冬天就是一件小棉袄,外面套一件大棉袄,进屋把大棉袄脱了。一件小棉袄穿一冬天,他们也不洗澡啊。我跟老付结婚的时候,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那旧衣裳也不能不穿吧,我拿出来一看,我的天哪,他年轻时身上透油啊,棉毛衣裤穿在身上像纥帛似的,梆梆硬,穿在身上能贴身吗?我就给他洗,搞热水泡泡,打上肥皂溜滑,使劲搓,搓干净了,再打肥皂,再沤一会儿,沤好了再搓,搓完了在开水里头煮,来回洗几遍,那件衣裳才洗出来了,软和了。结婚后,他的衣服拿出来除了破的,没有一件乌七八糟的,都清清爽爽的。
在东北,有些人家孩子的尿布子是不洗的,用完了往火墙上一搭,烤干了再用。我们跟前有个老太太,孙女是8月份生的,比我家老大大一点,他们的家不能进,一进屋尿骚味儿打鼻子。我都是弄点水搓搓,搓干净了再拿开水烫一下,完了再搁火墙上晾开。用的时候拿手搓搓,搓软和了再给孩子用。孩子的衣服不多,没有一件穿得嘎巴嘎巴洗不出来的,薄的每天洗,绒的最多两三天洗。
头一个孩子9月生的,再冷的天儿,一周也要给孩子洗一两次澡。连小叔子都服我,说这么冷的天,你还敢给孩子洗澡?小苏(桂兰)就不行,给孩子洗一回澡,孩子感冒一次。我们两孩子洗澡时,冻得嘴唇发紫,洗完澡喂饱他,包好了睡一觉,一出汗,啥事儿都没有了。
我的两个孩子身上奶腥味、尿骚味儿都没有,都很干净。我是属鸭子的,天天要洗的,洗脸洗脚洗屁股,一天不洗都不行。我们家老付叫我改过来了,他要不洗,我说你别碰我,你也别上床,你不讲卫生我要得病的。我老婆婆不怎么洗,她洗头洗脸,夏天到江里头泡一泡,游游泳,搓搓澡,冬天能不洗就不洗了,也算是干净了。
上海男人洗衣做饭都会,舍不得老婆干活的。我爸可心疼我妈了,以前没有洗衣机,我们家姑娘多嘛,小的衣服——背心裤衩、夏天的衣裳我妈洗,冬天的大厚衣裳、被单都是我爸洗,我妈从来不洗。上海女人也比较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女的一直是上班挣钱,不像东北男的出去挣钱,女的在家伺候老的小的。男的拿着大老爷们的架子,对老婆吆喝来吆喝去。
东北的男的,总是有一股大男子主义。老二9个月时,我在物资科食堂,冬天轮着到煤厂帮忙卸煤,到点没去喂奶,孩子不闹嘛。正好邮车也来了,老付要分信,分报纸,分包裹什么的,等不来我就把孩子送过来。他把孩子往地下一扔就走了。孩子哇哇哭,我抱起来。这把我气的,我说我要是出去玩也行,哪有你这么样的,你上班我也上班,你是治我呢,还是治孩子?
我是上海人嘛,比较会做饭,他舅舅在邮局,经常到我们家吃饭。他们的风俗是家里来了客人,男的陪着喝酒吃饭,女的不能上桌。我婆婆属于老一辈的,可以跟客人一起坐。等男的吃完了,女人再上桌捡点儿剩。家里做点儿好吃的,两个小叔子回家,大嘴一扒拉做多少吃多少,等我上桌什么都没有了,就剩点儿菜汤,馒头蘸菜汤,菜汤泡点饭。
我怀孕了,你得想办法叫我多吃点,对吧?人家根本不管,我跟我们家老付吵过好几回。我说你太不像话了,太不知道心疼我了,我吃饭不是给我一个人吃,肚子里还有孩子。你说你什么都不给我留,生出来的孩子长得瘪瘪瞎瞎的怎么整?
我父母拿我当掌上宝似的,到婆婆家拿我当根草似的,确实不能忍受。他舅舅比较开明,就说小韦一起来吃一点吧,别光顾着做了,就是允许我上桌了。我们家不是那种小炕桌,我们有地桌,有凳子,我说你们吃吧,我这边做差不多再来吃。饭菜都弄好了,我也上了桌,挤着吃一口,我不管那些,该上桌就上桌。
赫哲族老辈人生孩子是不能在家生的,要去外面生,在外面搭个小草棚,生完孩子才能回家。我老婆婆的三个儿子都是这么生的。我寻思怎么这么野蛮?本来女人生个孩子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我回上海生孩子。后来没等我回上海,我父亲就去世了,不能回上海生了,最后是在家生的。坐月子的时候,我们家老付不会照顾,我婆婆伺候得挺好,一天几顿饭做着。两个孩子都是九十月份生的,那时候鱼好钓,我婆婆做好饭伺候我吃完就说,我去钓鱼去了,拿个小盆去钓鱼了。一两个小时就端着半盆子鱼回来了,嘎牙子啊,鲫鱼啊,给我熬一盆汤,全是野生的,没什么土腥味,我其实肉吃得不多,鱼吃得多,下奶最好。
我老婆婆挺能耐,爬树、游泳、打猎都会。她在赫哲族女人里头属于漂亮的,比较聪明、开通的一个人。以前的老人跟现在的不能比,当婆婆的总端着个架子,但是她跟我还可以。我在东北呆了三十年,她有将近十五六年是跟我过的,跟小苏过了七八年。
婚后生活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可以了。可以了也不行,那阵儿东北时兴跳舞,我挺好动的,出去跳舞。八点半,不到九点,他上舞厅找我,说这么晚了,回家吧。我就跟他回去了,路上我跟他说,我这次给你面子,明天你再这么来叫我,第二天你就上民政局来找我,我能说到也能做到。我说没有这么管的,管得太狠了,我出去玩玩,也没乱搭咕。乱搭咕你管可以,跳跳舞怎么的?我还不到五十岁,就应该像老太婆似的守在家里头啊?我连上大学都没去,没离开你,你要这么样管我,我可受不了。从那以后,他就不管我了,我爱玩就玩吧。

你等着,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1993年儿子高中毕业,本来想叫他考大学,却赶上邮局最后一批接班。我说,邮电局多热啊,你不如接我的班呢。他想想也是,考大学也不外找个好单位,邮局不就是好单位么,他就接了我的班,我也就退休了。这一步走错了,应该叫他考大学,有文凭还是好的。
1997年,听说上海有政策,知青退休后户口可以迁回上海。邮局那时候也松,只要你提出来退休就给你办。1997年6月给老付连同儿子一起办了退休。9月,我和老付回到上海,11月户口就办了回去,一切都按照我想的,办得挺利索。不过,儿子没带回来,那个时候他刚结婚。我说,你等着,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我本来没想到退休以后还能回上海,在东北还盖了一个房子,120平方米,花了6万块钱。
我们俩在赫哲族里头是老大,比我们小不少的都管我们叫大哥大嫂。我回东北,回同江,回勤得利,他们都抢着请我吃饭。我上八岔也好,街津口也好,到谁家都受欢迎,好比说今天没打着鱼,想办法出去给我弄条鱼回来。杀鱼做鱼丸子,拿鱼油烙饼,拿熬好的猱头油炸做窝窝头,那个好难吃啊。
赫哲族比较纯朴,我们俩结婚时,付忠喜花80多块钱买一个红灯牌收音机,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30多块钱。我生儿子的时候,老三可高兴了,说哎呀,我们老付家有根了,大嫂,这个月的工资都给你。两个小叔子对我是没什么说的,大嫂长,大嫂短,对我都挺好。
我们家老付有个表弟,结婚比我们早,两个孩子比我们的大。他说,嫂子你来。我去了他家,他用白面、鱼油给我烙了一张饼。那时候白面很少,大都是大馇子、高粱米、小米。他那两个孩子看着我吃,眼珠儿扑腾扑腾瞅着那个饼,我就咽不下去了,我就把那个饼分给他俩吃了。
赫哲族喜欢喝酒,老一辈没有不喝的,一天一宿不落桌地喝,没菜也喝,干拉。打一斤酒,就个咸菜疙瘩,弄两棵葱,两瓣蒜,沾点大酱,就这么喝。这是喝酒嘛?这不是作践自己吗?肝肾都损伤了。
按说上海人不喝白酒,我倒是喝白酒,我在家的时候,我父亲一小就培养我像男孩子那样,抽烟喝酒我都会。刚下乡那会,过年过节他们打酒喝酒,我拿个缸子也去要酒了,他们说你还会喝酒?我说为什么不会喝呢(笑)?他们跟我打赌,说你能喝多少?我说喝就喝,跟他们喝了。后来他们都知道我会喝酒。我们家付忠义不喝酒,他说我看那帮老的喝酒就没个人样,喝完就作妖,自己身价都掉了。
我老婆婆喝酒,我从来没有限制过她。那时候打酒不像现在,哪个商店都有打的,我跟我老公不在邮局么,哪个连队都走,哪个连队的酒好,我们上哪个连队去打。那时,十四连烧的酒好,告诉他们送点儿酒过来。
我说喝酒就要吃点儿菜护肝保肾,对吧?酒精对肝损伤很大的,亲戚朋友端我的饭碗,是瞧得起我,我招待他喝酒,拌个凉菜,再炒个菜,反正好的我没有,春天搞点韭菜,炒两个鸡蛋;秋天弄两个辣椒炒炒;冬天了,炒个土豆丝,白菜粉丝里放点肉丝。不管喝好喝坏,待客之道嘛,怎么也得给他们垫巴点。老的小的都愿意上我们家来。
我们家肉从来不断。我不像他们有肉的时候一炖炖一锅,干拉的肉。我没有,我把肉切成一二两一块,炒菜了拿一小块,切点肉丝就够了,借个味儿嘛。我过日子始终是细水长流。付忠喜打猎打到野猪了,我们大家伙都帮着往回抬,往回拉,弄回来大家再分着吃。打到鱼,回来也给我们分点。小苏做点好吃的就来叫我,我做点好吃的叫她,反正两家人处得亲。人家一说起来老付家,都挺羡慕,好像哥仨挺有本事的。你在上海看不到这些,这是一家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刚回上海时,我们住在我老妈那儿,那种两三家合租的公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我老妈有两间房,我妈住一间17平方米的大屋,我住一个12平方米的小屋。妹妹都结婚搬出去了,我回去有地方住,也算很不错了。
2000年3月,我花9万在奉贤区买了一套86.55平方米的房子。我考虑到母亲百年之后,这房子姐妹要争,另外按当时的政策,一次性付款买80平方米的房子给解决蓝印户口,这样就可以把儿子一家的户口解决了。
哪有钱?1996年儿子结婚,1998年姑娘结婚,手里没有钱,全是借的,9万元对我来说已是天文数字,我就敢借这笔钱买房。以前的房子?谈恋爱时,婆婆江边的房子拆了,一连给了间小草房,俩弟弟在连队住宿舍。结婚后,我们住在邮局,靠着江边。赫哲人离不开山水。有两个房间,我们住大屋,婆婆住小屋。婆婆做饭给我们和两个弟弟吃。二弟结婚时,我们已搬进银行的空房子,有两大间,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后,电厂分了房子,他们才搬走。
在老付家三兄弟中,我做事往往出乎他们意料。盖房子时小苏他们还议论,说就凭他们俩的工资,两个孩子在外面读书有钱盖房子?她能盖得起来吗?结果我盖起了,还给儿子娶了媳妇。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听说我在上海买房,他们说这家伙好厉害,人家又在上海买一套房子!现在上海那套房子值200来万了,这在他们民族引起了轰动,不管勤得利的,还是同江的都说我有远见。赫哲族对我比较信服。我的经济头脑可能遗传了我爸爸。

1997年我回上海时,女儿已经二十七了。
女儿两岁半时,我把她送回了上海。我在东北待30年,她基本上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她跟我在心理上总像有点儿隔阂似的,不是十分亲。
什么原因把她送回去呢?这个就跟我老婆婆有一点关系了。我们结婚早,那边又没有幼儿园,没人带孩子,应该是老的帮忙带吧,我老婆婆却爱串门子,上她兄弟姊妹那儿去玩玩,一玩就十天半个月。她一走,这两孩子我弄不过来呀。
我父亲过世了,女儿回去后,我妈跟她好像有点相依为命似的,走哪儿带哪儿,左右邻居都说她是我妈的第六个女儿。我妈也给她撑腰,四个姨要管她,她就告诉外婆。外婆就说人家小孩爹妈不在跟前,由我管,不要你们管。她就很横了,谁都敢顶,谁都敢吵。
孩子不在跟前,我在物质上能满足就满足她,她就觉得好像有人撑腰的,跟她几个姨就明着干仗了。我回去看家里的杯子不多了,就买了2盒24个杯子,都叫她打了。几个姨说你怎么又打杯子了?她说你管得着吗?那都是我妈妈买的。
小学四年级前,她都在上海读的,寒暑假也不回来。长期跟我不在一起,心里头还是有阴影。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回上海无意中看到她写的日记,说爹妈不要我了,把我自己扔在上海。开家长会,别的小孩都是爸爸妈妈去,我没有爸爸妈妈替我开家长会,都是外婆去。上下学别的小孩有爸爸妈妈接,我没有。她有点儿被抛弃的感觉。
我就跟她说,我原想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弟弟留在上海。你外婆生了五个姑娘,没有男孩,让她领着外孙子;你奶奶生三个儿子,没姑娘,领着孙女。可是你精啊,知道上海条件比东北好,说啥不肯回去了。你弟弟比你小十四个月,哭着闹着要跟我走。不是我们抛弃你,是你要留在上海的。
她说是这么样吗?我说是的。
五年级她回到东北,没有上海户口,不让考中学,升到初中后,1986年还是八几年,黑龙江发大水,县里发了一个文件,说有亲的投亲,没亲的靠友,我就拿着这张通知书,找到上海有关部门说,我们那边学校都没有了,发大水了,我的孩子只能回上海来。上海挺支持,二话不说都收了。儿子在上海读到小学毕业,女儿初中毕业,没有户口升不了学,必须回来嘛,两个孩子回到东北,女儿进了齐齐哈尔民中。
1986年高二学年结束时,政策下来了,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回上海,我就把她办回去了。上海高中的教学进程比东北快,再说南方跟北方的教学质量也不一样,她只考了个大专。填志愿的时候,正好我妹妹在自来水厂,人总得喝水,自来水厂是不会倒闭的,她报了,毕业后就去了自来水公司,在控制室当调度。1997年厂里培养后备干部,她是少数民族,又是女的,就让她去读专升本,读三年。
我们回去时,女儿还没结婚,未来的女婿在携程网站下边的公司当土木工程师,通过校领导给我在通河高级中学找了个活儿,管理学生宿舍。那些学生也不太好管,结果最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挺听我的话,学校管不了的,我都给他们管好了。第一个月600元工资,第二个月就加到800元。
两年后,那位校领导调到了吴淞中学,通河中学不要我了,我就回家了。他们找了一个宿管老师,根本压不住那些孩子,学校又来找我,想叫我回去干。我说我不干,你们既然已经不要我,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没去。
吴淞中学请我过去,也是管理学生宿舍。我去了,在吴淞中学干了三年,月工资一千。
我们家老付?回到上海他没做什么,他就协助我,帮我看管学生,我一个人也干不过来,对不对?我吃饭的时候他帮我四处看看,学校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给他干,不合算嘛。
学校给我一间房,中午管一顿饭。我有一顿饭,他没有,一大荤,两小荤,一个素菜,加一个汤,食堂阿姨也是临时工,跟我关系搞得挺好,学生扔的鞋子、衣服我捡回来,谁能穿谁拿走;有时我打开洗澡间的门,让她们进去洗洗澡,打饭的时候总是手下留情,多打一点,别人给一小勺,给我可能是一大勺或两大勺。我自己再做点,我和老付基本上以中午那顿饭为主,晚上买一些蔬菜,去学校饭堂打点汤。汤是不要钱的,早餐买两个馒头,很省很省的,一个月200块钱生活费就够了,那段时间我俩攒钱挺快的。
姑娘结婚时跟老婆婆住在一起,很小的两间房子,没有客厅。她买了一套跟她老婆婆一样的房型。前年又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她现在在一个企业当书记。过年给我拿点儿钱,拿点儿东西,感情交流不多,小时候不在身边的缘故吧,这也是一件憾事。
到上海后,我就给我们家老付买重大疾病保险,体检时发现他的肾一大一小,而且两个比正常的小。我最小的妹妹是大夫,他们医院让做ECT。妹妹说:“大姐,做ECT要将近800块钱,你舍得吗?”那时候,我退休工资也就700多块钱。我说,那也得做,不做咋整?这人没了每月七八百不也就没了吗?做吧。结果出来了,肾功能不全,尿蛋白没有,肌肝偏高,尿酸高。
医生给开了一种药,很贵,50来块一盒,每月要吃四五盒,这就要200多块吧,还要吃一些降压药,我都给他买。十五六年过去了,他的肾功能恢复正常了。他现在73岁了,头发白的少,老二付中喜基本全白了,老三60岁时就全白了,现在已经去世了。老三老婆也不知道珍惜,现在后悔了,什么都晚了。
我们家老付在上海待不惯,说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老吵着要回去,后来我们买了新房,装了空调,冬天不冷了,夏天不热了。我还跟他说,“你要是在勤得利可能早就作古了。”

北大荒?我们这些知青经常聚会呀。聚会就聊北大荒的事,在北大荒那些年收获的确挺大。我们这批人吃的苦最多,遭的罪也最多,我现在腰椎间盘突出、腿疼,都跟那段生活有关系。
本文摘选自《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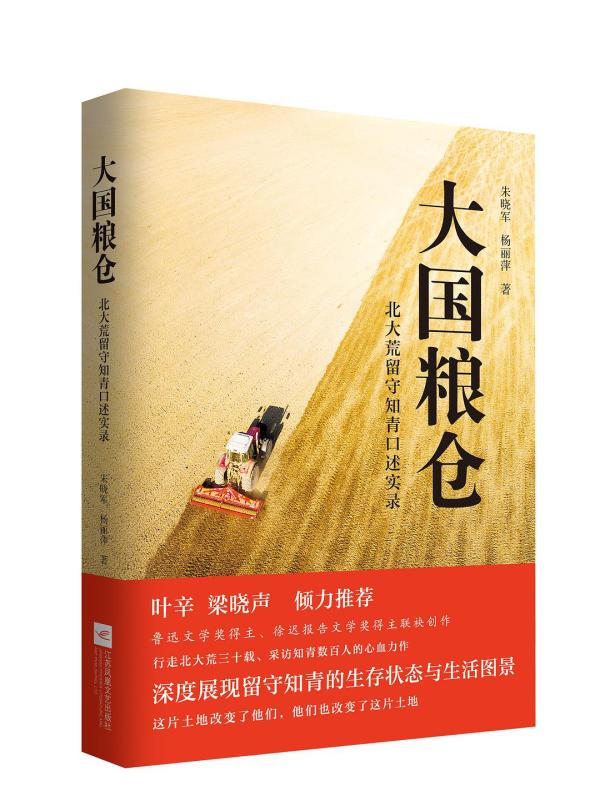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