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伪虚实之间——《五代九章》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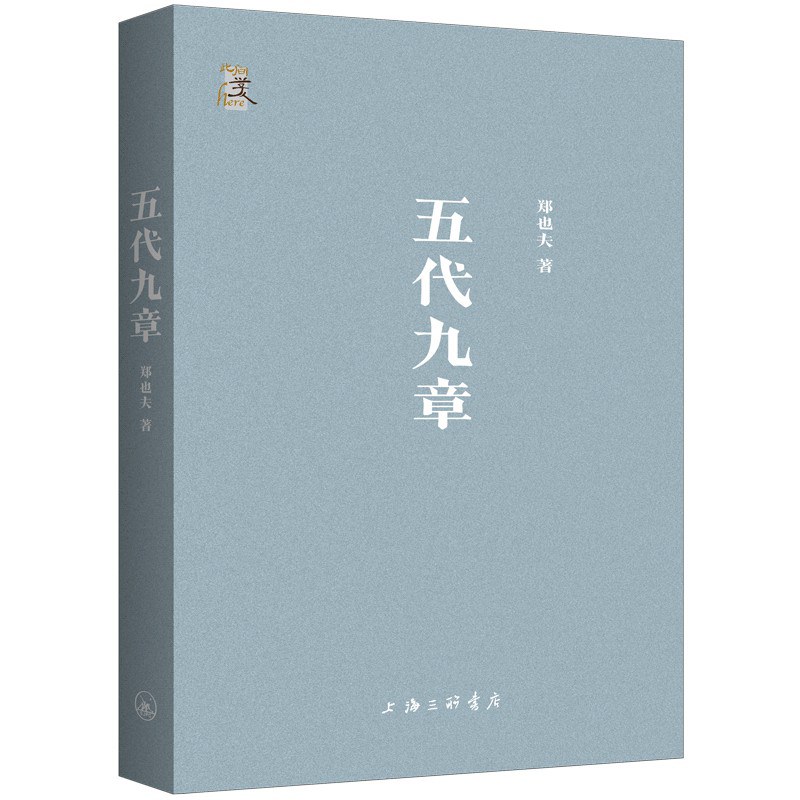
《五代九章》,郑也夫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
本文为郑也夫新著《五代九章》的前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发。
一、缘起:戏词—话剧—学术
剧作家、亡友李龙云和我聊天时,嘴里频次极高的词汇是“戏词”。可能因为这是他日思夜想、寝食不忘的事情。我从小爱看话剧。但龙云口中的这个关键词还是提醒着我。话剧与电影的重要差异,是话剧更重视语言的味道、蕴含、动感和冲击力。
绰号“演出大鳄”的钱程和我是莫逆之交。他被迫去京赴津后,推出了轰动性的大话剧。彼得堡话剧团的“兄弟姐妹”八个小时,中间要吃一顿饭。法国话剧“2666”十二个小时,中间要吃两顿饭。每次演出,敝人都出席首演前的酒会和演后与剧团的座谈。这些大话剧与常规话剧,含量不可同日而语。
看这些大话剧的当口,我在阅读中遭遇了冯道。我被他在那个特异时代的行状,以及历代围绕他的无休止的争论,深深吸引。他打动我的原因不一而足,其中算不上第一,但颇具冲击力的是他的一段段“戏词”般的语言。乃至,一个念头涌出:写个冯道的话剧本子。如果没有领略这些大话剧,我不会产出这个念头,因为常规话剧的时长无法表达复杂的冯道。魔鬼进了脑子就再难撵出。而我三十余年的学者生涯,决定了我必须做足案头功课。买来了薛居正和欧阳修的九本新旧五代史,以及蔡东藩的《五代史演义》,等等,毕竟我要写的是通俗的东西。很快我就完成了一个判断,大话剧也太难容纳冯道,因为他复杂,更因为五代是个纷乱如麻的时代,时间短讲不明白。但是魔鬼不走,它魔怔着,引诱我去考虑电视片。至少,这是我继续深入阅读五代史的阶段性动力。
今天反省起来,再往后的发展是路径依赖。我打算搁置电视片的写作,先完成一部五代史的学术著作。
二、非典型:社会学—历史学—通才
我没有写过剧本,这是全新的挑战。我也没有做过历史研究,七十岁了写历史同样是挑战。可能是觉得,即便历史学不是“轻车”,写学术书毕竟是“熟路”。对决策的作用力,感觉是不输给理性的。我做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感觉当家。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我熟悉学术路径,先易后难。通过学术研究,对那段历史深入理解后,回过头来写剧本不迟。
但毕竟隔行如隔山。而且历史学是信息量巨大、专业门槛很高的学科。专业史家对我动人家的奶酪,一定不乏侧目者。不管人家这么看,首先要说服的是自己。但以我的性格和走过的道路,没什么可顾虑的。我虽然做社会学,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社会学家。特征之一,一向借助多学科的思想资源,写作中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资源恐怕四分之一都不到。其二,当下中国社会学的热门课题我基本不做。其三,我的研究和写作转向太快,题目太杂,没有一个题目超过五年。有的同行私下说我不是社会学家。匠气足些的专家会这么看的,而当下学问做的稍好的学者中又是匠人居多。我自知是异类。故常常对媒体的朋友说:我必须也只能在一个院系领工资,这个系是社会学系,如此而已。至于我做的东西是哪个学科的,我不关心,只要自己有兴趣,对社会有意义,就行了。所以做五代史研究,我心理上没什么可纠结的。不过是,过去本学科视你为异类,现在兄弟学科笑话你是民科。
我的非典型是与多数学者对比而成的。如果多数学者像我这样“杂耍”,那么“专家”型的学者就成非典型了。而学术生态走到今天这般光景是个历史过程。古典社会学时期不是这样。杜尔凯姆研究过社会分工、教育、宗教、自杀等等。韦伯研究过新教精神、工作伦理、世界经济史、统治形态、世界几大宗教等等。二位涉足的多样性尚不及同代社会学家齐美尔。因当时欧洲的反犹思潮,失去教职的齐美尔索性在学院外的多种场合演讲,撰写形形色色的杂文,其讨论时尚的文章前无古人。而继古典社会学之后四大理论中的三项: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都是齐美尔开端。1990年才谢世的埃利亚斯堪称古典社会学风格之殿军。他研究文明进程、权力、知识社会学、宫廷礼仪、历史转型时代的音乐家莫扎特,以及体育。这几位,特别是埃利亚斯,深深地进入历史学研究。社会学奠基人的学风何以演化成今日专家占主导的学科,足够写一两本专著。其实很难说是谁“走偏”了。专家、杂家、通才,理当共存,各扬所长。
古典时代的少数学科演变成当代众多学科,或许是专家成为主流的成因。但在这众多学科中,有两个学科与众不同,即历史学与社会学。只要研究古代的事情,就属于历史学。而古代社会中帝王贵族,贩夫走卒,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你选择哪个题目都为学科所容纳。这是其他学科比不了的。不错,已经有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的设立。但是传统史学家仍保有研究古典文学、艺术、科学的余地。因为他们有专科史研究者不具备的横向优势。在选题的自由上,历史学得天独厚。仅次于它的是社会学。略逊一筹的原因是,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厚今薄古,其争夺更多的不是历史学而是社会学的地面。尽管如此,在选题的自由上,社会学家能居第二。放弃自由是社会学家自己的问题。
社会学与历史学,除了研究对象的时差,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研究者是今天的人,他的研究也是为了今天的人。他要敏于今日,才能从历史中找到有意义的题目。当然不排除某些史学家的研究目的,是为史学家们打好史料(包括真伪、版本之类)的基础。毕竟多数史学家有理解今日社会的必要。而社会学家要从历史学那里寻根。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历史与今天的天然关系,使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考,特别是意识流,彼此贯通。今天的读者愿意读余英时、许倬云,是因为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埃利亚斯对莫扎特的理解是历史学和音乐史专家都达不到的,是因为埃氏打通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那是古典社会学大师的特质。
社会学家跳到史学领域,不是该不该、对不对的问题,只是能不能、行不行的问题。后者是我做不做五代史研究的主要考量。如果我着迷的不是冯道,而是魏征,大概不会有写一本书的打算。因为我知道要读的书太多,读不完。唐史研究者众多,很难找到我插嘴的地方。五代史有所不同。需要读的书少得多。大学中讲五代史的教师要么是主攻唐史的,要么是主攻宋史的。我很可能是不自量力。但我不自量力的对象只能是五代史、上古史这些史料较少,给想象力留下更多空间的时段。
三、本书简介:九块积木——三只风筝
上面说到的——放弃了剧本写作,不受学科藩篱束缚——都不是写作本书的充分理由。决心写,是因为阅读五代史时产生的一些问题令我痴迷,探究它们的心得累积到一定程度,写作开始了。这些问题有其各自的独立性。乃至,伺候的不是一个主题,完成的是九块积木。循着它们在五代史中的位置及彼此的关系,排列积木,构成本书。以下简述各章,集中于有新意处。
第一章点评了“五代”的十四位帝王。“十国”中亦有称帝的君主,甚至不在十国之列的刘守光也称了帝。故选择十四位非理所当然。如此选择仅在于,新旧《五代史》的作者以其正统观选择了这些帝王,故《五代史》中他们的史料更多,可供我们解析;且《五代史》中留下了作者对这些帝王的评价,供我们批评。李克用不曾称帝。耶律阿保机父子更不在帝王本纪中。笔者不拘泥名号,注重历史作用。李克用率领沙陀军立定中原,后唐、后晋、后汉都是其亲子、义子、麾下军人所建。李嗣源、李从珂、安重诲三者的关系,埋下了后唐覆灭的种子。李嗣源不糊涂,是对养子李从珂的情感令他拒绝安重诲的谋划。如此看,皇权政治真的容不得一丝人性。石敬瑭理应重新评价。当时中原与契丹君主都是胡人血统,彼此长幼相称不在少数。中原政权求助契丹者不计其数。大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辽史》是二十四史的一部。这三大理由还不够吗?郭威称帝,从新旧《五代史》的材料看,未必蓄谋在前。柴荣英雄情结过强,走的招招都是险棋。
“用兵之道”排在第二章,因它与第一章关系最近。军事谋略是帝王权谋中的核心部分,何况五代是军战的时代。阳光下面没有新鲜事。本章所述黥面、义儿军、赏钱、斩首,都有传承。舍此就说不清五代的用兵之道。故打通与前后历史的关联成为本章,乃至本书的特征。其中赏钱与斩首,貌似微观,实则宏大变革之产物。唯雇佣军才有赏钱,而封建时代本无雇佣军。首级是请功的证据。封建制下血统继承的爵位,正是率先被军功爵位刺破。本章努力对五代的黥面、义儿军、赏钱、斩首,做出详尽的陈述。“博弈魏博”一节刻意放在本章,以帮助解析梁晋征战之转捩,及历史演变之偶然。
“忠岂忘心”以其在五代的重要性列在第三章。但这是一种特殊含义上的重要,“为臣不忠”是后人为五代贴上的一号标签。自宋代第三、四代皇帝始,君臣合力宣扬:忠的丧失是五代王朝走马灯般覆灭的原因——重要性是此时获得的。后经历代君臣合力打造,推崇死节、贬损贰臣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事实上,贰臣是五代期间朝代频繁更替的后果,不是其原因。笔者统计了《新五代史》中的233名文臣武将。死节与死事者仅10人(4.2%)。新旧《五代史》记载,新君主立朝后均立即招降纳叛,杀除前朝大臣极少。即五代时期君臣心目中鲜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溯本清源,《论语》中忠的重心是为人之道,非为臣之道;孟子不讲忠君,讲“民为贵,君为轻”。荀卿、韩非是忠君观的奠基人,董仲舒是其完整阐述者,宋人借批判五代再度加固之。明朝覆灭时死节者极少,但多数贰臣承受巨大内心压力——此即数代打造忠君观的全部收获,而明末清初对死节观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第四章“列国时代”讨论三个问题:纪年法,正统论,“五代”名称之由来与正误。周代开始实行王位继承法。天子与诸侯王在自己辖区内各自纪年。汉武帝开启了年号纪年法,即皇权纪年法。这一转换是皇权立于一尊、封建淡出历史舞台的结果。汉武帝以后,史官统统使用年号纪年法。谁是正统本来是问鼎者之间的争吵。梁启超以六个标准说明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堪称正统。即正统无关逻辑。史官为前朝写史,写史要以年号纪年,其为正统帝王垄断。面对分裂的前朝,确定正统就成了史官也要参与的问题。“五代”是宋人的命名,选择它是宋朝帝王的意图。以后质疑的言论不绝如缕。在人口、疆域,享国时间上,“五代”并不高出“十国”一个量级,何况还有契丹的存在,它兼跨国与代。故这五十二年的恰当称呼是“列国时代”。
第五章“乱世君子”。阅读五代史前,笔者以为一个权力频繁更迭、杀戮家常便饭的时代,官吏一定都是奴颜婢膝,猥琐阿谀。读后惊异欣喜,见识了众多精彩多样的人格。笔者拣选十一人。因冯道内容太多,单辟一章。本章十人。孙鹤的事迹勉强见于新旧五代史,其做沧州宾佐仅留下一笔。连缀碎片方见其行为因果与人格构成。笔者对其人的概况是:“骨鲠,谋略,报恩,三位一体,难得。”赵凤则是合二而一:极其敢言,频唱反调;同时又极擅进言。敝人以为韩延徽属于“一级历史人物”,可惜记载少而又少。笔者已竭力打捞。在忠心侍奉君主又坚守理念与尊严上,宦人张承业令大多数朝官汗颜。郭崇韬人格高尚,他固然以悲剧终结,但他屡屡直谏君王并未致罪,说明了五代君臣关系尚可,也是本章之人格得以彰显的背景。李愚几乎在践行非礼勿言,其人一丝见风使舵的心态都没有,却又不是书呆子。桑维翰是石敬瑭的精神后盾,后晋主和派的领袖。临危时,主战派贪生惜命,唯桑维翰慷慨赴死。这反差说明勇气与主战主和无关。和凝,神采射人,能文能武,此已属稀罕。《花间集》的作者,不期竟然还是案例集之开先河者。杨凝式,这位少年时为避政治风险的装疯者,竟然是唯一从大唐到后周,历官六朝之人。他还是承唐启宋的大书法家。王朴则磊落行藏,是献国策、编历法、匡音律的不世出的人才。本章结束于古今治乱中之人格的思考。
第六章“冯君可道”。我与五代史的缘分起自冯道。这章的广度深度,还算对得起这缘分。笔者的主要观点如下。侍奉多朝者不乏其人,讨伐贰臣拿冯道开刀,是因为其中冯道官职和声誉最高。其实冯道成为不倒翁的一大原因是他不掌实权,五代的权臣和高风险的官职是枢密使,不是宰相。有多个扎实的例子证明冯道是敢谏之臣。冯道为官的主要作为是,为君主讲治国之道,主持雕版九经的刻印。
以上六章所述均系五代史之重镇:皇权、军事、忠君、合法性、出彩的人物。虽然讨论第二、三、四章时,一再与之前的历史联系对比。但主要说的毕竟还是五代的事情。
以下三章则像三只风筝,从五代史放出,高高地飞上去。三章的目的与其说是讨论五代的事情,毋宁说是讨论三个通论专题:天命观、音乐、宦官。五代的戏份在其中不是很大,特别是最后两章。但毕竟是受五代史的启发,飞到哪里也有一根线连着五代。
第七章“天命知否”。讲述了五代中对天命与术士的误信者、不信者、骗子。新旧《五代史》中的相关记述,给人们的综合印象是,骗子很多,笃信天命与术士的人较少,决策时人们常常不听术士所言。本章检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关于天命的论述,发现其中的主流认识竟然与五代君臣的实践相似。
第八章“雅乐胡歌”。比较了孔子、柏拉图、席勒关于音乐或艺术的思想。三人都认为音乐与艺术有助于道德形成。孔子、柏拉图认为有些音乐有害于道德,务必杜绝。席勒则强调艺术的王国是独立的,惟其独立才能繁荣。为什么孔子与柏拉图思想相似,而以后在音乐上西方繁荣,中国停滞。笔者以为,是因为中西政体的不同。柏拉图的音乐思想在西方多元的封建社会中不被广泛接受。而孔子—刘德的音乐观与大一统的政体结合,制约了音乐的繁荣。西域音乐文化的涌入与李世民的开明,导致唐朝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峰。唐之后的五代产生了多位胡人君主。他们爱好歌咏,正是这些小情节吸引了敝人。论理他们似乎应该继续大唐以胡乐为主的音乐。但是在合法性上,李世民极度自信,而五代君主颇为自卑。故后者不敢去光大他们喜爱的胡歌,有条件时反而尽力恢复编钟雅乐。乃至唐代的音乐繁荣一去不复返。
第九章“阉人宦官”。这是放得最高最远的一只风筝。但确实是五代史中的一个情节诱发了笔者。就是朱温通令尽杀大唐太监,且他称帝后不设太监。这在认知上刺激笔者思考。而风筝飞起后,五代的宦官不再是主题。花费笔墨研讨阉割,系笔者嗜好所致。接着讨论了秦、汉、唐、明代的宦官。历史上帝制下阉人的数量远超封建制。故秦、明两朝的阉人数量是世界史上的双峰。宦官是帝制肌体上的毒瘤。古代史家对宦官的批评充满歧视与偏见,既是因为他们不敢批评皇权,也是因为朝臣与宦官的权力之争。宦官把持了唐代最后九位皇帝的继位。但若是外戚或顾命大臣把持,可能李氏王朝早已改姓。宦官的把持让这出戏安稳地唱了百年。不是说这样好,是说其利弊之评判绝不简单。明代宦官的数量被官员学者们夸大了数倍,说明他们找错了明代政治的病灶,忽视了包括皇权在内的其他若干问题。朱温杀掉挟持天子的宦官后,他先是挟持后是取代天子。宦官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它是透视皇权的特异的视角。
四、大段引用:古文—今人
本书行文方式的一大特征是,大量引用五代史中的原文。
最早看到这种文体,是读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书是写给专业史学家的。本书的读者是什么人,我说不清,没有清晰的意向。我著书从不考虑读者是谁,只考虑社会意义,以及自己的兴趣和审美。我期待作品与读者相互寻找。但拙作肯定没有聚焦在少数史学专业人士上面。那为什么要走陈寅恪的路子?
出于三个考虑。其一,古文翻译成今文会变形,甚至误译。理解从来都有差异的。而今人理解文言要比理解白话的差异更大。差异的理解是有意义的。笔者乐见读者对原文的略有差异的理解,不愿舍弃原文,将自己认可的译文强加给读者。其二,原文是走进古代的路径。读《旧五代史》就是进入了薛居正等五代—宋人的讲堂;读《新五代史》就是进入了宋代人欧阳修的讲堂。中国人幸运,可以直接阅读先贤一千年前的文字。当代历史作家何苦要隔断文字上的直接联系,做蹩脚的向导呢。其三,新旧五代史的文字水准本来就很高。我的引文又是精心挑选的,既是有料有趣的段子,又是精美的文字。敝人写不出这么好的、戏词一般的字句。不如选择重要的段落直接呈现给读者,附上一些必要的注释。
五、训诂:故事—历史
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且多半读过、听过某些严肃或戏说的历史,乃至不管是史学家、史学爱好者还是普通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自己的历史观。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自觉意识到,有些不自觉。敝人嗜好理论,故史观的自觉意识更强些。这种自觉意识既体现在明白自己的特征,也体现在努力从一般意义上思考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写作这篇前言时,说说史观的念头突然涌现,不吐不快。与本书间接的关系总是有的。
我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只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入校时,老师们说几年来教工农兵学员,没准备好教你们这样的学生,第一学期竟然开不出历史课程。我自学一本非常浅显的海斯著《世界史》。书中第一句朴素之极的话深深打动我: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故事。我在第二学期的作业上写下这句话。老师在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批语:错,历史不是故事。
讲述历史观,我们从历史是故事说起。讨论历史是不是故事,我们从训诂入手。
“历史”一词很晚才在汉语中流行,笔者猜想是日本人以“历史”翻译history所致。此前国人使用的是“史”字。“史”有两意,其一是官名,后来主要指史官。其二,史册以及史实的意思。后一意思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其文则史”(译:其笔法如史书)。再说“故事”一词。故是过去的意思,事是事情。望文生义,“故事”就是“过去的事情”。其最早见于《商君书》:“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译:农民不离开他们过去做的事情,就必定垦荒)。字面与用意一致。“过去的事情”,不就是历史吗?五代史频繁记载,皇帝要老臣说“唐故事”,那当然是要他们说唐朝的规矩及朝廷上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要老臣虚构。话本、小说的产生,比“故事”一词晚得多,故其词义的转变是后来的事情。至于故事还带有传说的意思,早期的历史何尝不是传说。殷代才有文字。我们不谈争议纷纭的夏代,就是商代早中期的历史,是靠传说继承下来的。综上所述,在古汉语中,史(史官之外的含义)与故事几乎是一个事情。
我们接着讨论英语中对应的这两个词汇:history(历史)与story(故事)。两个词汇的拼写非常接近,不由得不让我们想到它们的关系。二者确乎是同源,都源自希腊语名词historia,其字面意思就是“智者所知道的事情,智者对过去的事情的叙述”。它进入英语后,分化成了两个单词:history和story。笔者的兴趣不在于讨论英语中二者的意思,知道二者同源就够了。
中西殊异的古代历史与语言文字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一致的情形,毫无疑问揭示着一个道理:历史与故事之同源。
六、连续谱:虚构—非虚构
演化到现代,这两个词汇当然不再是一个意思。图书馆文科图书的重要分野是虚构与非虚构。历史著作在非虚构之列,故事书在虚构之列。但图书的划分不要误导了我们,以为历史作品非虚构,无故事。
虚构与非虚构是连续谱,中间没有鸿沟。
文学的虚构中有真实性。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虚构的故事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酷似现实,是这类作品的取胜之道。昆德拉说:小说是探索可能的生活。其小说观虽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并不背离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是纯牌虚构。文学作品中只有一部分是纯虚构:魔幻与科幻。而它们不是文学的主流。
历史作品中颇有虚构的成分,原因有二。其一以想象填补空白。还有其二,留待下节。古代史家书写历史的时候,手中拥有的常常只是历史的碎片,诸多空白有待填补。难道不可以为追求真实,将碎片的历史呈现给后人吗?那是人们,无论是读者还是史家,都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合人性。人类的精神世界适应和需要某种完整性、某种“结构”——故事的、逻辑的、乃至数学模型,不然无从把握。于是空白必须以某种想象和加工去填补。而几种结构中,故事是最古老的,也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伟大的司马迁就是如此填补空白的。他必须这么做。碎片是不成其为历史,无法传递、留存下去的。司马迁兼通写实与虚构,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是考据大师也是故事大王。司马迁以降的古代史家,不同程度上都要以自己的想象连缀历史碎片。
尽管古代史家凭借想象做出了填补,留下的历史依旧充满空白。而追求真实性的当代史学家告别了太史公的路数,且在这个方向走到极端。多数人一方面已经完全不诉诸想象,另一方面以为写进正史的都是真实的史实。只转述正史,完全不去想象那空白中会发生了什么。他们将空白处的想象拱手让给历史小说家们。其实历史的空白处更需要专业的史学家去过问。与历史小说家不同的是,专业史学家在有史料处分析、推敲和质疑,在史料空白处才诉诸想象。今天的史学家可以超越司马迁的是,告诉读者其作品中哪里有根据,哪里是想象。这一工作难度很高,非专业人员做不来。
历史的特征,除了碎片,还有片面。留下来的历史都是极端片面的。一部二十四史完全贯彻着帝王将相的历史观,社会生活的记载少之又少。而这样的历史一直被接受着。到了现代,尽管对此已有足够的反省,可是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祖宗留下的史书。我们只好努力从中寻求和透视一些其他的信息,辅以地下发掘的文献、文物。任凭如何再加工,得到和完成的不可能不是零星、片面、局限的东西。
七、史:粉饰—作伪
书写的历史中有想象的成分,如上所述。还有作伪的成分,系本节讨论的内容。
正史的笃信者是怀疑者的千百倍,但两千余年来怀疑者也不绝如缕。其中最突出者是古代的孔子,现代的顾颉刚。《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先天、本性的意思,“文”是后天、文化的意思。“野与史”均背离君子的品性。“野”是粗糙无礼的意思。“史”比较费解。古汉语“史”兼有史官和史书的意思。与君子对应的当然是史官,而非史书。故“文胜质则史”可以译为:后天压过本性,文饰压过自然,就如史官一般虚伪了。由此我们看到孔子对史官的菲薄。不是批评某一史官,而是将史官的共性看作低下的品性,说明孔子时代为君王文过饰非是大多数史官的作风。说这话时,孔子不是评价史官,而是讨论君子,惟其不经意的表述更反映他认识的底色。如此,孔子眼中史书之虚假可以定性。
《论语八佾篇》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译文:夏代礼制我能说出,其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礼制我能说出,其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因为杞、宋两国的历史文献不足。如果充足,我会引征的。)文献不足,为什么孔子能讲出来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凭借想象力去连缀已知的碎片,填补其中的空白。孔子当然不耻于他说的“史”。即在他看来,他这样的人凭借想象力填补历史空白与史官伪造和歪曲历史存霄壤之别。(参阅顾颉刚,1926,120)
我们再讨论顾颉刚(1893—1980)对古史的疑问。他在1926年撰文说:“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从战国到两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1926,7、2、6)他认为动机是当时人多尊古贱今,乃至在托古中编造。顾氏对编造者的评价要比孔子对史官的评价客气得多。顾氏还说:“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同上,1)这道理则是中国古人很难说出的,晚近西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时间、生死、胜负,有可能确证。人口户数,因为有隐瞒意图,只能推断一个大概。而双方博弈的过程,几乎永远无法确知真相,因为那是人言人殊的罗生门。
最令笔者欣喜的是,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真伪时屡屡提到笔者喜欢的概念“故事”。他提出:“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他是戏迷,且读过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很多戏剧、小说经历过一次次改编。由此,顾氏马上看到人们在史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对古史一代代添加内容。他由此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说:“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变化的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顾颉刚,1925)这么做是有些意义的,而搞清哪个是真大多不可能。笔者发现,根据上下文判断,这段引文中被笔者打成黑体的“故事”,其实是“古史”的意思。这说明,“故事”与“古史”在顾颉刚心中已成相似的东西。“故事的眼光”在顾氏眼里,除了“层累演变”,还有古史中的故事性。他说,古史中伊尹周公的足智多谋颇像戏剧小说中诸葛亮,古史中桀纣的穷凶极恶颇像戏剧小说中的曹操秦桧。(同上)笔者不以为“故事性”必然颠覆古史的真实性。因为戏剧小说的出现晚于古史,不存在古史效仿后者的问题,且权力博弈过程大多不乏故事性。抛开逻辑,这些表达透露着顾氏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古史相似于故事。顾颉刚还说:“战国大多是有意的伪造。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我们对于他们一概原谅,我们决不说:这是假的,要不得。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面而放在战国史里。”(1926,177)
综合本节与前两节所述,史书中包含着不在少数的虚构,或为猜想,或为伪造。故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要持怀疑态度。但是对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讨论的意义不必怀疑。即使是辨析一个虚拟的案例,仍然可以开发智慧,增进认知。何况古代史家讲述的事情是事实与故事之合一。
以上史观在多大程度是影响本书写作?有,但未必很大。唯因它是在本书写作中不自觉地、间断地思考着的。故在前言中一并铺陈出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