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夜读|棉花白,云卷舒
又是深秋。
天气明朗,大朵白云垂挂在湛蓝的天幕上,变换着姿态游走,立体而生动。两行钻天杨泛了黄,叶子打着旋飘落,被风一吹,发出“唰啦啦”的轻响。思绪顺着秋色逆流而上,一路奔跑,在青葱年少的棉花地驻足。轻轻掀起岁月一角,朝时光深处窥探。
少年时,父母在小村庄西边很远的地方种了一片棉花。我家的棉花地四周,是绵延到远方的别人家的棉花地,犹若开满云朵的森林。一条蜿蜒的小路在其中若隐若现,我和妹妹骑着自行车去摘棉花,一路走一路摁响铃铛,在金色的阳光里,洒下无数欢乐。
妹妹告诉我,母亲叮嘱我们只摘大朵的,要开得最好的。我点点头,为了我们的新衣服,当然要把最好的棉花摘回家!
每年,母亲都把棉花弹成蓬松的棉絮,搓成细细的棉花筒。晚上她坐在炕头上,我躺在被窝里,看她架起纺车,“嗡嗡嗡”声在耳边响起,单调却让人心安。橘红色的灯光下,棉筒在母亲手里拉成一条长长的线,缠绕在锭子上,再变成一个胖胖的线穗子。最后,这些线被织成各种颜色的布,经母亲裁剪缝纫,穿在我们姐妹身上。
摘棉花和新衣服划了等号,棉花便摘得愉悦。
深秋很寂静,浩瀚的银色海洋里,摘棉花的人弯腰过去,把大地犁出一条一条或长或短的分割线,广袤的棉花地便成了一组五线谱。我和妹妹是跳跃的音符,弹奏一首秋的交响曲。
棉花叶子摩擦发出“嚓嚓”声。“姐,咱俩比赛谁摘得快!”妹妹挽起袖子,用手轻轻一捏,一朵雪白在掌心轻盈。她两手上下翻飞,逐渐把我落在了后面。我比妹妹大四岁,怎么能服输?可使尽力气也赶不上她。这个比赛输赢连个奖励都没有,索性不追了!妹妹在前面摘棉花,我悄悄把装棉花的袋子铺在地垄里,躺了上去。
柔软的棉花是我躺过最舒服的床,好惬意。等了一会儿,妹妹还没有注意到已经消失的我,稍有失落。坐起来看妹妹忙活着越走越远,有做了坏事没被发现的得意和窃喜,复又躺下,等着妹妹发现,然后和我嬉笑打闹。
无聊时,蚂蚱落在眼前的棉花叶子上,发出“嗒”的一声响。我把它捧在手心,捏着它的两条大长腿,看它不住冲我点头鞠躬。它展开翅膀试了几下,却飞不走,便颓废地放弃挣扎,一动不动了。可怜的小家伙,我把它又放在叶子上,看着它展翅飞走。眼神逐渐朦胧,我睡着了!
“姐——姐姐——”终于发现我不见了的妹妹惊慌失措,她带着哭腔的喊声已经来到我身边,那一脚差点踩在我脸上。
我坐起来一把抓住妹妹,她吓得“妈呀”一声扭头就跑,我笑得前仰后合。她折回来打我,我就绕着圈跑。我们笑啊闹啊,气喘吁吁,一起坐在棉花袋子上。“姐,你吓死我了,找你一大圈,你却在这偷懒睡觉。”妹妹说完扭过头擂了我一拳。我“嘘”了一声,指了指天空。妹妹疑惑地仰头张望。
彼时,夕阳西坠,映出群山的轮廓。从阴影处一抹红霞升起,缓慢向东蔓延。头顶天空悠远深邃,朵朵白云像硕大的棉花,舒卷自如。在东边视野的尽头,棉花和白云交汇在一起,不知道哪片是棉花哪片是云。
我和妹妹再没有说话,沉浸在那美景里,不能自拔。
时光荏苒,母亲已经离世,妹妹也远嫁他乡,我两鬓斑白。只是在深秋时节,看着白云悠悠,便会想起那年棉花白,云卷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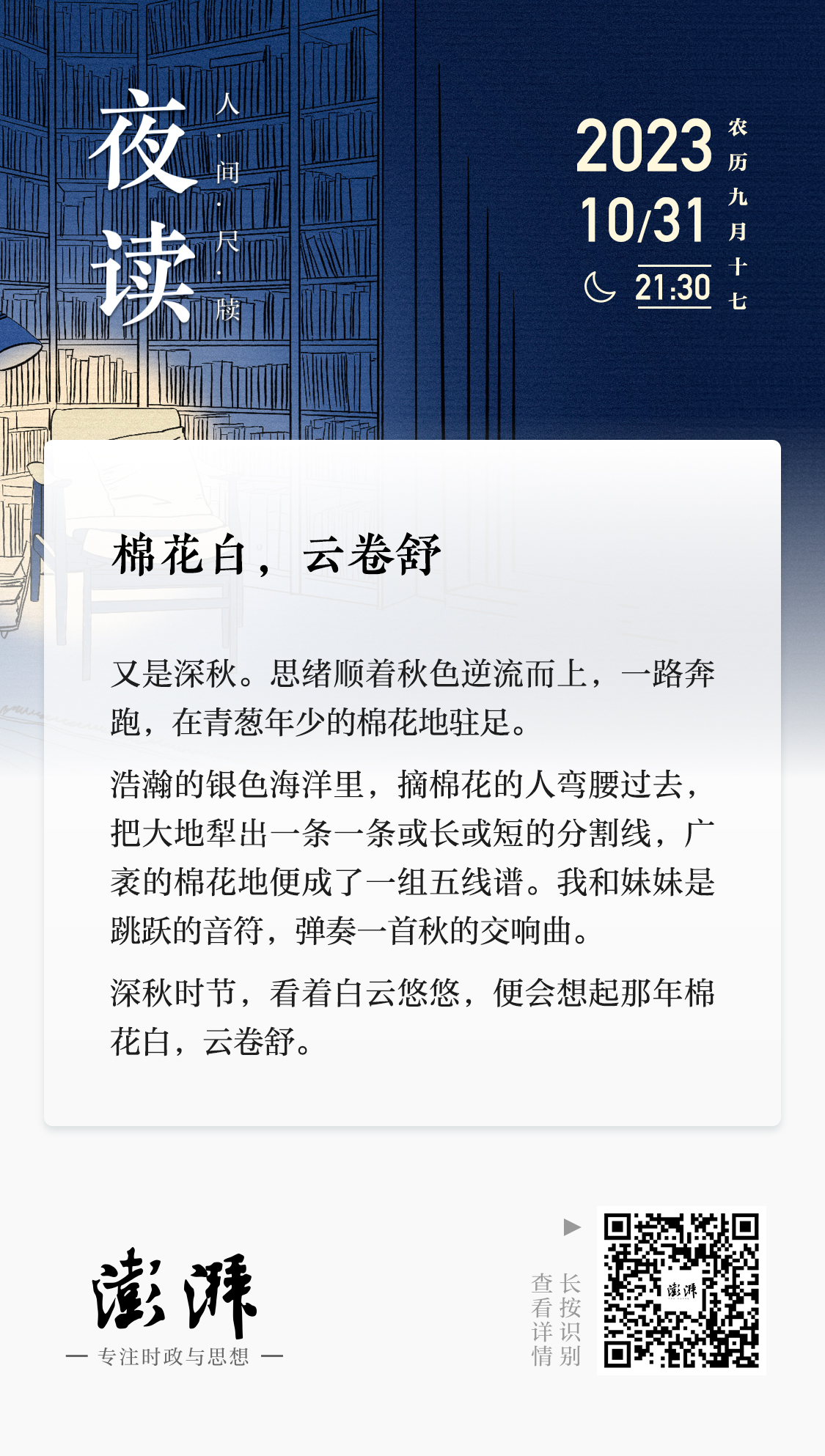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