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你还一无所知,不知道迎接你的将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将诞生在怎样的世界……”这是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写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女儿信件的开头。
与他的代表作、3600页的六部自传《我的奋斗》中对自我的终极探讨不同的是,克瑙斯高“致女儿书”的内容集中在那些最日常、最平凡的事物——苹果、塑料袋、太阳、口香糖、黄昏、保温瓶……这些事物或现象,在克瑙斯高的信件中,被一一重新解读。
“人要是活了好多年,就会对开门关门习以为常。对房子习以为常,对花园习以为常,对天空和海洋习以为常,甚至对挂在夜空中在屋顶上闪耀的月亮,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是克瑙斯高的担忧,他怕“习以为常”会让人丧失对世界的感受力,而这些由一个个名词串起的信件,使得我们随着作者字里行间试图传达的爱意,重新去感受被忽略的那些“习以为常”,由此或许平凡的世界确实也可以过。
下文 6 封信件摘选自《在秋天》,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 致未出生女儿的一封信
流经血管的血液,在土壤里生长的青草,还有树木,在风中摇曳的树木。
这种种美妙,你很快就会遇见了,但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就像有千千万万的人,错过的方式也有千千万万种。所以我要写这本书给你,向你原原本本地展示这个时刻在我们周围的世界,究竟是哪般模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睁大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
是什么赋予了生命活下去的意义?
没有哪个孩子会提这种问题。在孩子眼中,生命是不言而喻的。生命会为自己说话:不管它是好是坏,都无关紧要。这是因为孩子们并没有在看这个世界,没有关注世界,也没有思索世界,但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世界当中,无法区分世界和自身。当他们终于分得清了,他们和世界之间产生距离的时候,问题就会浮现:是什么赋予了生命活下去的意义?
是向下按压把手,把门推开的感觉吗?感受门是如何在铰链上轻轻松松地向内或者向外转动,然后走进一个新房间?
没错,门就像翅膀一样打开了,仅仅如此,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意义。

《我是山姆》剧照
人要是活了好多年,就会对开门关门习以为常。对房子习以为常,对花园习以为常,对天空和海洋习以为常,甚至对挂在夜空中在屋顶上闪耀的月亮,也都习以为常了。世界会为自己开口宣言,但我们听不见。由于我们再也无法沉浸在世界当中,也不再将其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去感受,那对我们而言,世界仿佛就消失了。我们打开一扇门,但这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也不是,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从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房间而已。
我想向你原原本本地展示我们的世界,展示它此刻的模样 :门、地板、水龙头、水槽、厨房窗户下靠墙的花园椅、太阳、水和树木。你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观察世界,你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过你自己的生活。我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主要是为了我自己:向你展示这个世界,小家伙,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
太 阳

《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剧照
自打我出生以来,每一天太阳都一直在那儿,但我从来没有真正习惯它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它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事物都不相同。
作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罕见的自然现象之一,我们无法接近它,因为那样我们将化为乌有;我们也不能发送任何探测器、卫星或是飞船,因为这些东西也会化为乌有。
我们也不能用肉眼看太阳,那样会导致失明或是视力受损,有时这感觉像是一种不合理、几近侮辱的存在:它就这样挂在高空中,地球上的所有人和动物都能看到它,面对这个燃烧着的巨大天体,我们甚至不能注视它一眼!可现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直视太阳几秒钟,视网膜上就会布满晃动的小黑点,假如我们盯着不放,那黑点就会像吸墨纸上的墨水一样在眼内扩散。
换言之,我们的脑袋上悬挂着这么一颗燃烧的球体,不仅带给我们所有的光与热,也是所有生命的起源与基础,但同时它又是绝对无法接近的,并且对其所创造的事物漠不关心。

《无尽之夏》剧照
读到《旧约》中一神论的上帝时,很难不联想到太阳。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一基本特征便是,人们不能直视上帝,必须低下头。上帝在《圣经》中的形象就是火,它代表神圣,也始终代表太阳,因为世间的所有火都是其分身。
托马斯 · 阿奎那写道,上帝是不可动摇的推动者。与他同时代的但丁将神圣描绘成一条光明的河流,在《神曲》结尾描绘了对上帝的一瞥,其形象便是一个永恒发光的圆。人们若没有宗教信仰,就只是任意的生物,境况的奴隶,可但丁这么写,让阳光下的人变成了意义重大的存在,而太阳只是一颗恒星罢了。
尽管对现实的观念有兴有衰,有爆发也有消失,现实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其存在的条件不可改变:先是东方的天空亮了起来,黑暗缓缓从田野上消退,当空气中充满了鸟鸣,阳光洒在云层的背面,云朵由灰色变成粉色再变成明亮的白色;与此同时,寥寥几分钟前还是灰黑色的天空变得蔚蓝,第一缕阳光洒满了花园,白昼来临。
人们往返于烦琐的工作,阴影起初变得越来越短,随后又越来越长,和地球自转的节奏同步。当我们坐在屋外的苹果树下吃晚饭的时候,空气中充斥着孩子的吵闹声、餐具的叮当声,还有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没有人注意到太阳挂在客房的屋顶上,不再是如火的金黄色,而是披着橙色的外衣,不动声色地燃烧着。
✉️
海 豚

《海豚礁》剧照
我们划船出游来到峡湾,天空灰蒙蒙,有些阴沉。面前坐落着许勒斯塔山,细长的山峰高几百米,笔直地耸立在峡湾之中,浓雾深处如一面深黑色的岩板墙。我的头发被峡湾的水汽弄湿了,用手指掸一掸雨衣的袖管,聚积的雨水就会沿着手指流淌下来。
船桨和桨叉之间的摩擦声和击打声听上去难得那么清楚。这些声音通常会离开小船,慢慢消逝在开阔的水面上,现在却被雾气包裹着,阻挡了去路,同时雾气也隔绝了其他靠近我们的声音。当外公停下划桨的动作,收起船桨时,四周一片寂静。水流缓缓移动着,形成微微晃动的大波纹,水面却很光滑。
我和表兄把渔网的铅锤放下去,铅锤迅速沉入船下的深处。附近突然传来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表兄抬头看了眼,但外公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窸窣声开始加强,伴随着微弱的哗哗声,有东西从水中游了过来。表兄用手一指,外公转过头。就在几米远的地方,一群海洋 生物的脖子和背部在水面上跃起、降落。
我精神一振。
它们一共有五六只,隔着很近的距离一起游动、冲浪,每次冲破水面时,都能激起白色的浪花。我永远忘不了那阵嗖嗖声,忘不了它们是如何用欢乐却又专注的动作,在我们周围的水域里滑过的那一幕。它们灰褐色的皮肤十分光滑,圆圆的身体跟孩子的身高等长。我还瞥见了它们的眼睛,像是两个黑色的小圆点,嵌在凸出的鼻子上方,还有嘴巴,看起来仿佛在微笑。

《蓝色海洋》剧照
后来,当它们从视野中消失后,外公说看到海豚会带来好运。他老爱说这种话,他相信预兆和警示,但即便我乐意听他这么说,我却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是真的,一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过。可现在我相信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幸福和不幸是怎么分布的,不是吗?
在当今这个理性时代,如果是按照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幸福和不幸产自人的内心,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幸福与不幸,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的时代,“自己”又是什么呢?是否只是一堆细胞,是基因的产物,又受到了经验的修改调整?这些细胞在小型的电化学风暴中激活又失活,人们才有了一定的情感、思想、话语和行动吗?由此引发的外部结果是否创造了新的内部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情感、思想、话语和行动?
这种推论既荒谬又机械,但将海豚归纳为具有某种特性和行为模式的海洋生物则更荒谬,更机械。因为对于所有经历过这一幕的人来说,它们不仅来自海洋的深处,也来自时间的深处,经历数百万年的光阴却分毫未变。他们知道,看见海豚时,心灵的某个地方会有所触动,仿佛是被它们触及了一样,而见证这一幕的你,是冥冥中被选中的幸运儿。
✉️
黄 昏

《月升王国》剧照
在写这篇文章时,屋外已是黄昏,已经看不清外面的草地是什么颜色,也看不清对面房子的木墙,只有那面粉刷过的外墙还反射着微弱的灰白色光线。
屋顶上方的天空要稍稍亮堂一些 ;最先变黑的是地面。在屋顶后大约三十米处,沿着经过墓地的那条路,有七棵树枝分叉的大树。在稍稍亮一些的光线背景下,可以巨细无遗地看见树枝所构成的网络。
当我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草地上时,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黑暗像一汪小小的湖水笼罩在草坪上。与此同时,屋子里的房间仿佛凸显了出来,填满房间的黄色光线穿过窗户,变得越来越亮。
今晚,屋子里有六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刚刚上床睡觉了,手里还端着瓶牛奶,她现在应该睡着了吧。六七岁的孩子应该正坐在床上,一边玩着他们的 ipad,一边大声聊着正在做的事。还有两个八岁的孩子,刚才爬到了花园尽头的篱笆上,又从篱笆爬到了树上,我猜他们此时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最后那个十岁的孩子,前脚刚从朋友家回来,现在应该正躺在二楼的床上玩《模拟人生》。
屋外渐渐淡去的光线,并不是他们脑中正在思考的问题。对他们而言,这只是所有夜晚中的一个,好像无穷无尽,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他们的童年。过两三个星期,他们或许还能记得今晚的一些情景,好比说我们晚饭吃的是千层面,但之后便会永远消失在他们的记忆中。

《月升王国》剧照
然而,要知道哪些记忆会保存下来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上周末,我和八岁的女儿去城里转了转,她告诉了我一些她所谓的“从小”就记得的事情。有一些小细节和随意的一瞥,她自己都记不清是来自什么地方了,到底是马尔默、斯德哥尔摩、约尔斯特还是我们曾经度假的某个地方。
一道背靠大海的栏杆,一辆驶过博物馆的小火车,还有森林里的一条长凳,她曾经坐在那儿吃过午饭。在马尔默的公寓里,她从一岁一直住到了五岁,根据她的描述,她还记得那儿的台阶,往上走就能到卧室的门廊,有一回她曾坐在那台阶上。
在写这篇文章期间,有两位母亲过来接走了各自的孩子,屋外已经是漆黑一片,一切都黑蒙蒙的。唯一亮着光的是窗户内的房间,从我所在的这栋小房子里看过去就像是个水族馆。
在餐厅的灯下,我看见六岁的儿子向前伸着脑袋,很有可能在看ipad上的某一集电视连续剧。八岁的女儿刚刚去了厨房,根据她的手势动作,我猜她在给面包片抹黄油。很快我就要起身走到他们跟前,在抗议声中关掉电视机,督促他们去刷牙,最后再给他们读睡前故事。
之后他们便会闭上眼睛,躺在黑暗中等待睡意来袭,睡梦之桥将会把他们带往明天,而我则在2013年9月15日,星期一的格莱明格桥,写完这篇关于黄昏时分的文章。
✉️
麦茬地

《麦田》剧照
还有什么比转过城市的某个街角更令人兴奋呢?那儿有各种可能性等着我们。这是维托尔德 · 贡布罗维奇在他的日记里所发出的惊叹。我们不确定,或者一无所知的事物,不仅仅属于形而上学,不只关系到重大的问题,例如上帝是否存在,或者人死后会遭遇什么,还与最稀松平常的事物有关。
贡布罗维奇没有子嗣,如果他有,这是否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世界怎么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并不确定,但对我来说,在没有子女时和为人父后阅读贡布罗维奇的日记,是两回事,因为在养育孩子或是在和孩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世界可以预知,有条不紊,且时刻能被认知。
对孩子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错,就是有种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的感觉。因此,当戴着面具的圣诞老人在平安夜走进家里时,孩子会哭。我们内心深处有种对未知,或是对不可预知之物的恐惧感,这自然是因为未知的事物曾经能够威胁生命。
为了消除未知带来的这种恐惧感,人们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婴儿会被重复的动作安抚,十二岁的孩子在外界不受控制时,会依赖于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这个四十六岁的成年人转过某个街角时,我对一切会如预期那般深信不疑,于是这便成了现实的本质,而非纯粹的想象。

《麦田》剧照
奥拉夫 · 豪格写道,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这句话想表达的一定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但他是出于无奈才这么想的,因为对他来说,幻想与疯狂相联系,其后果就是限制行动的紧身衣、药物治疗和精神病院里平淡无奇的生活,有时候要在那里逗留数年之久。即便如此,幻想的价值仍是巨大的,因为它不仅令人感觉,还让人确信存在另一个层次的现实,会给生活带来截然不同的刺激。
对我而言,这是宗教狂喜的一种形式,只停留在理论上。我读过豪格早期写的诗句,觉得它们就是克制这种狂喜的体现,也是埋葬狂喜的一种方式,而其后期的诗歌,被其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称为“冷锻”,却完全脱离了那种维度。
是的,虽然在早期的诗歌中,他试图从自上而下的狂喜中抽离,但在后期的作品中却通过随手可得的一系列工具,如鸟与苹果、雪与斧头等,试图自下而上唤醒这种狂喜。尽管没有结果,这些事物和动物却永远保留在了具体的意象当中。当然和以前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在豪格的凝视和文字里,它们闪着微弱的光芒。
这就是我开车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时的想法,沿路会经过坐落在田野中的浅棕色麦茬地,当秋日低矮的金黄色阳光洒在那上面时,它偶尔也会发出微弱的光。
但通常来说,情况恰恰相反,麦茬地和秋日的所有风景一样,仿佛会吸收阳光,在暗淡的浅色天空下,显得苍白、潮湿。所有的风景会慢慢收拢,就像各种各样的事件朝同一个方向发展那般——风刮个不停,雨水从空中降落,汽车正朝山坡上驶去,左边是麦茬地,右边是土壤,天空呈灰蓝色,光线稀疏,海面被雾气所笼罩,驾驶员身子前倾,想透过雨水打湿的挡风玻璃,看得更清楚一些,一只猎鹰展开宽大的翅膀突然俯冲而过——
但风景就是风景,驾驶员在几秒钟内体验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强度,这不是因为某件事的展开,恰恰相反,是因为事物的聚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随之而来的伤感,被憎恨崇高概念的贡布罗维奇于对微小事物的思考所化解。
✉️️
鸟类迁徙

《迁徙的鸟》剧照
秋日的一个午后,我把干净的餐具从洗碗机里取出来,一边煎着香肠,一边煮着通心粉。洗碗机清空后,我把端早餐的盘子放进去,接着把吃剩下的半碗燕麦片刮到垃圾桶里,这些燕麦片吸了好多牛奶,都快溶解了,还有一个刮得底朝天的鹅肝罐头也一起扔了。
我把垃圾袋系好,从桶里拎出来,再调低炉子的温度,拿着袋子出门扔垃圾。外面下着雨,天空灰蒙蒙的,空气很宁静。突然我头顶的某个地方响起了嘎的一声,接着又响了一声,我抬起头,大约有十只大雁以人字形飞了过来。
它们伸展着脖子,在天空中振翅翱翔,我能听见翅膀拍动的声音。等它们飞走后,我继续走到垃圾箱旁边,把垃圾袋扔了进去,然后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眺望了一眼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或金黄或浅绿,或是变成了棕色,所有植物都闪着水珠的光泽。如果我走到草坪上,我肯定我的鞋跟会踩穿草皮,陷入土壤里。
屋子里切成块的香肠因为热量的缘故,表面变成了棕黑色,尤其是边缘部分,不仅如此,它们还微微发胀,变得圆鼓鼓的。通心粉在冒泡的沸水里打转,也煮好了。我把它倒入水槽的漏勺里,然后晃了晃。在我心里,鸟类迁徙这件事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我没去想它,但它就在那儿,在我多愁善感的思绪中,偶尔会定格成画面。那些画面并不像照片那般清晰分明,因为外界的事物在我们心中并非一笔一画描绘出来的,而是像一条条被撕开的口子 :一些黑色的树冠,天空,还有几双翅膀在空中拍打的声音。
那声音唤起了某些情感。是什么样的情感呢?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我便思考着这个问题。我对它们了若指掌,但那只是单纯的情感罢了,并非明确的想法或概念。四十年里,每年秋天我都能听见几只大雁在约十五米高的空中挥动翅膀的声音,每年大约两到三回吧。

《迁徙的鸟》剧照
在我的童年里,世界一度是无边无际的。非洲、澳洲、亚洲和美洲,这些是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距离一切都那么遥远,那边有取之不竭的动物和自然储备资源。如果能够去那些地方旅游,那就同去我当时读过的许多本书中的某个地方旅游一样不可思议。我并不是突然茅塞顿开,而是渐渐地开始明白鸟类迁徙的含义。鸟类迁徙意味着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飞过千山万水,意味着世界并不是无穷无尽,而是有界限的,不论是故乡或新家,它们去的从不是抽象的地方,而是具体的存在。
没错,当我把锅铲伸到香肠下面,把它们铲到绿色的盘子里,然后将通心粉倒入玻璃碗时,感受到的就是这些。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我们总是身处某个有形的地方。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
✉️✨
曙 光

《本杰明·巴顿奇事》剧照
这里的几栋房子呈马蹄状,开口朝东,所以我一年四季每天早晨都能看见日出。要适应这景象挺难的。并不是因为日出有多惊人,毕竟我知道太阳每天早晨都会升起,知道阳光会消退黑暗,更多是因为日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日出给我的感觉非常美好。
这种感觉很像你冻坏了的时候泡个热水澡,身体仿佛恢复到了基本状态时所得到的满足感。当真的达到正常状态后,这种满足感便消失了,我们鲜少会思考自己的身体处于完美的体温状态,这一点和日出一样。让人感觉舒服的并不是光线本身,因为光线的存在,比如说下午两点半吧,我们会习以为常。舒服的是光的过渡。不是地球转向静止不动的太阳时,照射在地平线上的阳光,而是几分钟前阳光的反射,看起来如同黑夜里苍白的光束那般,微弱到几乎像是没有光,只是黑暗中一个弱光点。
这种无比美好的淡灰色光芒,不知不觉间在我周围的花园里缓缓弥散开,花园里的树木和房子的外墙也同样慢慢地显出身形。当天空晴朗时,东方先开始变蓝,第一束阳光倾洒下来,是亮橙色的。刚开始,好像只是出现了这么一束光,除颜色外没有任何属性。但下一刻,当光线像巨大的光柱坠落在大地上时,它们才开始显现其真正的特性,大地被抹上了色彩,显得灿烂无比。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如果天空并不晴朗,而是多云,那这一切就会像秘密般进行:树木和房屋会从黑暗中渐渐显形,黑暗随之褪去,大地被抹上绚烂的色彩,却看不到导致这种转变的源头,只能看见天空中有一块不大透光的地方,有时候是圆的,如果云层不厚的话 ;有时候难以辨认,看起来就好像云层自己在闪着光。
通过这种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发生的现象,我们也了解了自己。曙光永远是事物的开始,就像黄昏永远是事物的结束。我们知道黑暗在几乎所有文化中代表着死亡和邪恶,而光明则象征着生命和美好,日与夜之间的这两个过渡地带便代表了我们被卷入的一出伟大的存在主义戏剧。
当我站在花园里,注视着东方破晓的晨光时,我很少会思考这些东西,但这又是必须思考的,因为看到曙光的感觉太好了。黑暗是永恒的规则,光明则是其例外,正如死亡是永恒的规则,生命则是其例外一样。光明和生命是反常的事物,曙光是它们亘古不变的证明。

《在秋天》
作者:[挪威]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译者:沈赟璐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年:20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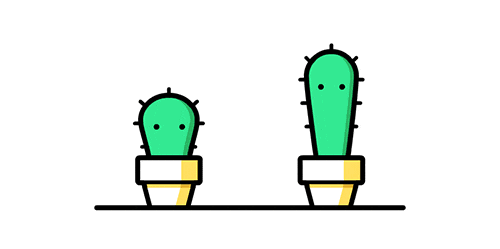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