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钦评柄谷行人《探究(二)》|专名与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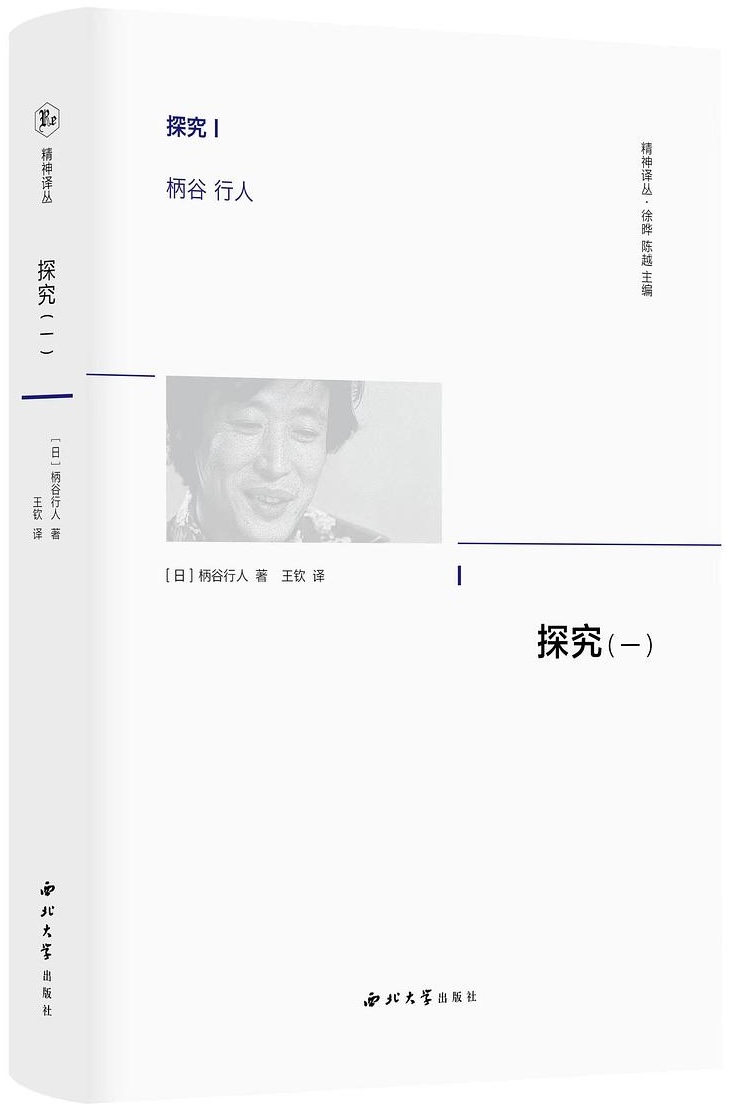
《探究(一)》,[日]柄谷行人著,王钦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56页,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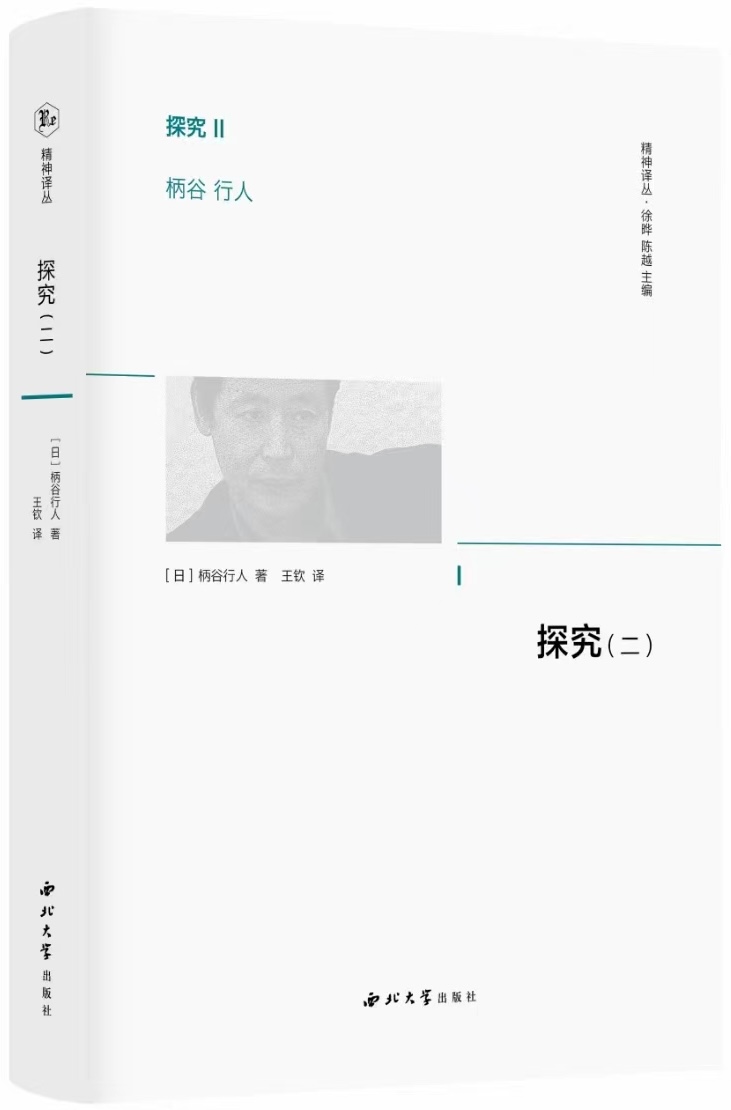
《探究(二)》,[日]柄谷行人著,王钦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360页,88.00元
柄谷行人对于“专名”问题的最为详细讨论,出现在1989年出版的《探究(二)》一书中;也可以说,《探究(一)》中作为关键概念和问题意识出现的“他者”,在《探究(二)》中通过与“专名”问题相联系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因此,简要地考察一下柄谷对于“专名”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在柄谷思想中贯穿始终的“外部”“意识”等议题,如何在他经历了思想“转回”而撰写的《探究》中得到发展,并进而与其后以“跨越性批判”为题出版的“探究(三)”的工作形成紧密的关联。
在1991年的一篇题为“个体的地位”的文章中,柄谷就“专名”作为哲学和语言学问题写道:“如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家所说,语言(langue)和指涉对象或意义无关,它是差异性的能指的关系体系。然而,由于专名是固定指涉,它就偏离了这种关系体系。因此,语言学家在考察语言的时候就排除了专名,认为专名正是将语言和指涉对象结合在一起的谬论的源泉。这是一种与认为可以将专名还原为确定谓述的思考相平行的论述。”(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講談社学術文庫,1999年,23页)在这篇文章里,柄谷没有继续阐明这两种“平行论述”之间的关系,但他所提示的这条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启的语言学“内在研究”的进路,却和他“前期”的思考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这种“平行论述”却对之存而不论,或许是一个关键提示:柄谷在讨论“专名”的时候,已经放弃了他此前的论述和思考方式。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仍然陷于此前的思考框架,那么“专名”问题的思想启示就无法得到阐明,故而必须进行思想上的“转向”。此话怎讲?
让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性质做出的规定。在讨论语言的一般性质时,索绪尔开宗明义地将外在指涉(即实在对象)排除出语言学讨论的范围:“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1页)于是,在索绪尔的论述中,构成符号的音响形象(能指)和概念(所指)的两个层次,都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运作并通过差异化而产生意义(价值),整个过程都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与指涉”的关系截然不同。对于上述差异关系,索绪尔解释道:
我们在这些例子里所看到的,都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同前,163页)

索绪尔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系统中,能指通过与其他能指的差异性关系、所指通过与其他所指的差异性关系确定自身的意义;同样,在索绪尔的另一段话中,符号的一切意义都被还原为差异性:
如果价值的概念部分只是由它与语言中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构成,那么对它的物质部分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中略)起作用的只是符号的差别。(同前,164页)
通过以上述方式规定语言符号的两个层面,索绪尔否认了所有试图在语言和实际指涉对象之间确立因果或对等关系的尝试。同样,作为音响形象的能指和作为概念表象的所指之间的结合的偶然性,截然不同于,也不可还原为所谓语言符号和实际指涉之间对应的偶然性。“专名”所预设的语言符号与实际指涉之间貌似天然的联系,自然也就无法在这样一种差异性符号系统中找到一席之地。那么,柄谷如何理解索绪尔的这种论述?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柄谷在不止一个场合讨论过索绪尔,而每次讨论的侧重点乃至结论也未必一致(在这一点上,尤其能显示柄谷的思考“转向”的无疑是他写于1992年的《书写与民族主义》一文,在这篇与德里达的索绪尔批判展开对话的文章中,柄谷就索绪尔的“内在语言学”进路写道:“必须指出,索绪尔坚持‘内在语言学’,不是因为无视‘外在’,而是为了批判将‘外在’事物的产物予以内在化的语言学。他通过‘内在语言学’的主张,反而将‘外在’事物的外在性揭示出来了。换言之,索绪尔始终把语言学的对象局限在声音语言,不是出于声音中心主义,反而是为了暴露历史语言学的声音中心主义的欺骗性。”参见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講談社学術文庫,1999年,72页);在此,我们可以选择以1980年代初期撰写的《内省与溯行》中的讨论为例——哪怕仅仅是因为这部被批评家浅田彰称作“惊人的失败的记录”的著作标志着柄谷的“前期”理论思考的顶点。针对索绪尔的差异性体系,柄谷在收录于《内省与溯行》中的主要论文《语言·数·货币》(1983)中写道:
语言从来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不单单是差异体系(形式体系·关系体系),而是自我谈及·自我关系性的,换言之,语言是这样一种差异体系:它对自身而言是差异性的。在自我谈及的形式体系或自我差异性的差异体系中,不存在根据,不存在中心。或者,它是尼采所谓的多中心(多主观),索绪尔所谓的混沌和过剩。语言(形式体系)存在于自我谈及的禁止之处。(柄谷行人『内省と遡行』,講談社文芸文庫,2018年,171-72页)
这段对于索绪尔的创造性重写和批判的要点在于:柄谷强调,索绪尔的差异体系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成立,端赖于一种回溯性的视角,即从已经产生意义的差异关系出发来想象性地重构意义产生的过程,仿佛这个符号系统从一开始就是封闭的、给定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依从索绪尔的上述讨论而将语言学研究限定在某个“语言系统”内部,进而在能指和所指的层面谈论彼此差异的时候,“差异”关系实际上已经被还原为能够生产意义的“对立”关系(比如“cat”和“hat”“cut”等等的对立)。柄谷用一种非常具有德里达色彩的口吻告诉我们,在这样一种有关“差异”的论述中,恰恰是纯粹的差异、自我与自我的差异、无法通往意义的生成和确定的差异,被事先排除在外——依靠一种柄谷所谓“究极的所指”的缝合,所有差异性关系都得以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
究极的所指封闭了无限后退的连锁,以此来完成符号系统。反过来说,无论是哪个符号系统,只要是系统,暗中就会以这种究极的所指(超越者)为前提。如前所述,语言学·符号学只有在现象学式的还原那里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符号只有在对意识来说某物(声音也好事物也好)有意义的情况下才是符号;而只要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所发现的就不可避免的是封闭了的系统(语言)。即便主张能指与所指之结合的任意性,或两者的偏差的可能性,根本而言,能指与所指的二分法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体系性(使系统成为系统的东西)才能成立。(同前,218页)
所谓“究极的所指”,就是本身并不在能指和所指的差异性系统中出场,却保证了系统的封闭性和意义生成之规则的“不在场”的所指。在这里,就系统之为系统而言,这种“究极的所指”是在结构上被预设的前提——换句话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再现这种所指(它与其说是不可能被再现的,不如说是一个必要的“缺席”),甚至不是这种所指是否真的“存在”,而是这种在结构上作为系统成立之可能性条件的、占据“超越者”位置的“符号”,在系统运作起来之后便被遮蔽了,仿佛各个符号从一开始就仅仅是在一个给定的、差异性的稳定系统中形成彼此关系并生产意义。柄谷将这种“究极的所指”称作“符号0”:
符号0……是对缺席的消除。但是,由符号0消除的是自我差异性(自我谈及性)。这种缺席的消除,恰恰就是对根据的缺席——因而“不均衡”才是常态——的消除。(同前,219页)
尽管柄谷在这里似乎是从积极的角度描绘“符号0”的作用,但我们需要时刻记住的是,柄谷讨论的并不是一种时序性的发展或生成,仿佛的的确确先有一个超越性的“符号0”(无论它是什么),然后再通过它的消除(或自我消除)产生封闭的差异性系统,就如《圣经》里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过程那样。事实上,“符号0”仅仅是将貌似封闭的差异性系统的差异化过程推到极端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追究系统之成立的可能性条件的后果。正如“早期”柄谷经常借用哥德尔定律表明的那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形式系统都无法在自身内部给出自身之自洽性的完整说明。但正因如此,柄谷在《内省与溯行》等著作中试图做的工作,就是严格把自己限定在系统内部,通过不断加剧差异化来寻求“向外”的突破口——“符号0”便是他找到的、似乎可以通往“外部”的关键所在。
因此,经历了思想的“转回”之后,在1985年为《内省与溯行》所写的“后记”中,柄谷如此回顾自己在过去数年里尝试的理论工作:
我在《内省与溯行》中第一次从正面开始思考语言,这时候我封闭在所谓“内部”。或不如说,我所发现的是,无论人们怎么想,他们都已经被困在“内部”了。要想从单义的、封闭的结构,也即从“内部”迈向尼采所谓“巨大的多样性”的“外部”、作为事实性的外部——换言之,作为缺席的“外部”——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当时认为,这只能通过将内部或形式体系进一步彻底化,以此使它自我破坏,才有可能做到。可以说,我是积极地将自己局限在“内部”的。(同前,322页)
但是,即便发现了“符号0”的悖论性作用——它既是系统成立的前提条件,也是系统无法再现却始终遮蔽的“缺席”——柄谷似乎也无法跳脱出自己这种与“内部”的搏斗,正如批判始终无法摆脱它的批判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柄谷揭示的“外部”似乎反倒成了“内部”所产生的另一个效果,尽管是一个颠覆性或解构性(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的效果。
于是,根据柄谷自己的说法,经历了思想“转向”后撰写的系列随笔《探究》,便成为对此前工作的“根本批评”(同前,323页)。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于《探究》的理解,需要在柄谷迄今为止的问题意识以及对此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延长线上进行。反之,如果仅仅在知识的意义上执着于柄谷对于具体思想家的具体解读,点评哪些部分恰当哪些部分不恰当,不仅有见木不见林之虞,甚至完全无法把握柄谷的意图。而如果将《探究》与《内省与溯行》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柄谷自始至终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与“外部”产生交流。具体来说,《探究(二)》中涉及的“专名”问题,提示我们柄谷对于“外部”进行思考的新方向。
***
在《探究(二)》一书中,柄谷对于“专名”问题的探讨,是与对于所谓“独特性”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柄谷就区分了“独特性”与“特殊性”:如果后者与“一般性”相联系并呈现为某个一般性的概念范畴下的个例,那么“独特性”就跳脱出了一般概念范畴的规定。柄谷举例说明:
在此,我把“这个我”或“这条狗”的“这个”性(this-ness)称作单独性(singularity),并把它区别于特殊性(particularity)。如后文所述,单独性并不是只有一个。特殊性是从一般性出发得到的个体性;与之相对,单独性则是决不属于一般性的个体性。(柄谷行人『探究II』,講談社学術文庫,1994年,11页)
有意思的是,柄谷的入手点——即所谓“这个”——正是罗素所认定的、唯一真正的逻辑“专名”。不过,在罗素那里,“这个”“那个”被认定为最基本的简单事实或逻辑原子,是沿着他的“摹状词理论”对名称进行分析和化约之后得出的结果——如不少论者所说,将这两个词视作真正的“专名”不啻“一场逻辑灾难”(斯特劳森语)。另一方面,柄谷指出,“独特性”问题的悖论在于:事实上,我们无法通过(例如)“这只猫”这样的表述来表达它所指涉的猫的独特性,以至于“这只猫”无法抵达所指涉的猫的“这个”性,因为一旦“这只猫”通过特指而被从一般意义上的“猫”那里选定出来,它就在同一个过程中预设(并且回到)了一般意义上对于“猫”的概念规定上。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试图用“这只猫”来表现眼前这只猫的独特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重新理解或界定“这个”,否则这个表述反而会使我们希望表现的“独特性”淹没在“特殊性”之中。对此,柄谷写道:
“这个我”或“这条狗”里的“这个”,不同于指示某物的“这个”。指示某物的时候,“这个”将“我”或“狗”等一般存在给特殊化了(做了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坚持“这个我”,便是主张我如何与他者不同,也即我如何特殊。不过,这么做的前提恰恰是把他者也当作“我”,即一般意义上的“我”。(同前,21页)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颇为关键:正如“这只猫”的表述无法呈现眼前这只猫的“独特性”,在“这个我”式的唯我论的思考方式中,“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回收到自我同一性的视野之中,以至于“他者”一开始就遭到了排除。换言之,如何揭示“独特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与“他者”相遇的问题。那么,对于柄谷来说,如何从“这只猫”这一表述通往事物的独特性呢?
的确,“这只猫”中的“这”从逻辑上无法提示猫的“独特性”,而只能把所指涉的猫还原为特殊性的一个事例。但这一逻辑事实无法抹去的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恰恰试图通过“这只猫”这个表述来(不可能地)表达“独特性”,不然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使用“这只猫”的表述就是不可理解的。请注意:这并不是把问题还原为经验主义或心理学问题,仿佛重要的只是言说者自己的想法或意图;恰恰相反,我们在此谈论的仍然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也即“这只猫”的“这”恰恰提示了它所指涉的猫和其他猫的差异,尽管这个表述无法积极地再现这种涉及“独特性”的差异。一旦试图将这种差异命题化,我们就落入了“特殊性/一般性”的窠臼,但这一困境并不会使差异消失。正是在这里,“专名”问题与“独特性”问题的联系呈现了出来:
单独性不属于一般性。但是,单独性不是孤立而游离在外的东西。单独性反而以其他事物为根本前提,并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得到揭示。但单独性不是那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深邃之物。前面已经提到,[单独性]出现于专名之中。(同前,22页)
在柄谷看来,之所以“独特性”出现在“专名”那里,是因为“专名”并非仅仅是对事物的命名,而更涉及“如何看待‘个体’”的问题(同前,29页)。换句话说,“专名”之无法还原为一连串谓述,其原因和“这只猫”无法表现所指涉的猫的“独特性”如出一辙:例如,通过将“富士山”还原为一系列描述性的特征(假如真的可以做到穷尽性描述的话),我们也恰恰在此过程中丢失了“富士山”这个专名中包含的固有性。或者,用一个更显豁的例子加以说明的话,这里的问题类似于“谁”(whoness)和“什么”(whatness)的区别:当我们问道“谁是柄谷行人”的时候,回答可以是诸如“当代日本左翼知识人”“著名思想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作者”等等;但是,这一系列特征性描述所回答的问题都只是“什么”层面的问题,而无法触及“柄谷行人”这个专名所指涉的是“谁”。
反过来说,如果“专名”提示的固有性或“独特性”无法在所指涉事物的描述性特征那里得到揭示,那么“专名”在语言上的形式标记也决不是看上去那么明显的事情;毋宁说,与它希望揭示的“独特性”一道,专名的形式标记消失在了(例如)“这只猫”的表述所包含的、无法在形式上做出区分的两种不同方向——(1)将所指涉的猫还原为“特殊性”的一个特殊事例以及(2)提示所指涉的猫与其他猫的纯粹差异——之中。在语言的形式标记层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将自己的猫命名为“狗”甚或“猫”,尽管一般认为“猫”“狗”是普通名词而非专名。在这个意义上,“专名”对于事物的“独特性”的提示,前提就是之前提到的、“专名”所标记的差异性——没有什么明确的形式标记可以区分作为“专名”的“猫”与作为普通名词的“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两者都可以还原为一连串谓述,而恰恰显示了“专名”与言说者的密切关系。在同一时期所做的一次题为“关于专名”的讲演中,柄谷对此说道:
通过专名指示的“独特性”,不是“仅有一个”意义上的“独特性”。就算只有一个,我们也未必会用专名来称呼。某样东西的“独特性”,只有在我们用专名来称呼它的时候才出现。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某个语词能够成为专名,并不是由于我们以它来指示个体的个体性,而是由于我们用它来指示“独特性”。(柄谷行人『言語と悲劇』,講談社学術文庫,1993年,393页)
重复一遍:当柄谷强调某个语词是否是专名取决于我们是否用它来提示“独特性”的时候,他并不是把“专名”对于事物的指涉关系彻底还原为言说者的意图或主观性;毋宁说,这里的“我们”不能被等同于“我”,因为它涉及克里普克对于罗素的批判中提出的共同体。延续上面的例子,只有在他人知道我把自己的猫叫做“狗”的时候,才能理解当我使用“狗”这个语词的时候,我有可能是在用这个“专名”指涉自己的猫,而不仅仅在说一般意义上的狗。在这里,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将“狗”这个语词从一般性的使用中抽离出来,让它变成一个独特的“专名”;相反,“狗”(或“约翰”“小花”等等)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对自己的猫的命名,离不开与“专名”及其指涉无关的一个“外部”背景,即“命名仪式”所处的共同体之中的交流。甚至在“这只猫”的表述这里,情形也同样如此。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柄谷的一段话:
然而,罗素的“这个”就仅仅是“这个”,不带有“这个”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可能性。但与此相对,[“这个”指的是]“不是其他而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当我说“不是其他”的时候,已经将“其他(或多个)”作为前提了。专名与这种“不是其他而就是这个”有关。专名所指示的“这个”,是在“其他=多个”的可能性中被揭示的。换句话说,克里普克作为出发点的“现实世界”,不是单纯的经验世界,而已经是在可能世界之中被揭示的世界。
他并不是在下述意义上思考“可能世界”的,即唯有经验世界是现实的,其他都是想象的。相反,恰恰在诸多可能世界或诸多可能性中,才能思考现实世界或现实性。从现实世界出发思考“可能世界”,事实上相当于说,已经从可能世界出发来思考“现实世界”了。将专名置换为限定摹状词,会在可能世界中产生不合逻辑的情况——这就说明:专名所涉及的现实性,已经是包含了可能世界的现实性。(柄谷行人『探究II』,59页)
在这段话中,柄谷对克里普克的罗素批判进行了颇为独特的阐述。我们可以将他的解释整理如下:克里普克所谓的“可能世界”,并不是如莱布尼茨笔下的情形那样,呈现为抽象的、与现实世界无关的设想;相反,它是为了说明现实世界的“这个”性——或偶然性——而被提出来的思想实验。从“可能世界”出发来思考“现实世界”,意味着将现实中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不可改变的事物特征还原为偶然的结果:某物在如其所是的同时,也提示着它不必如此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由此一来,如果“专名”既不能被还原为事物的描述性特征,也不能被还原为言说者的意图,那么“专名”之所以为“专名”,就完全是一个关乎交流之形式性的问题:正是在与他人的实际交流过程中,“专名”被确定下来。当我说出“这只猫”的时候,这个表述所指涉的猫的“独特性”恰恰是在我用这个表述来与人交流(哪怕是未知的读者)的情况下得到提示的。正因如此,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我完全可以设想这只猫在特征上的不同变化,而无需确定哪些性质是本质性的,而哪些不是。只要交流可以实现,哪怕在“可能世界”中我用“这只猫”来指涉一种莫可名状之物,“这只猫”在“专名”意义上的指涉作用仍然不会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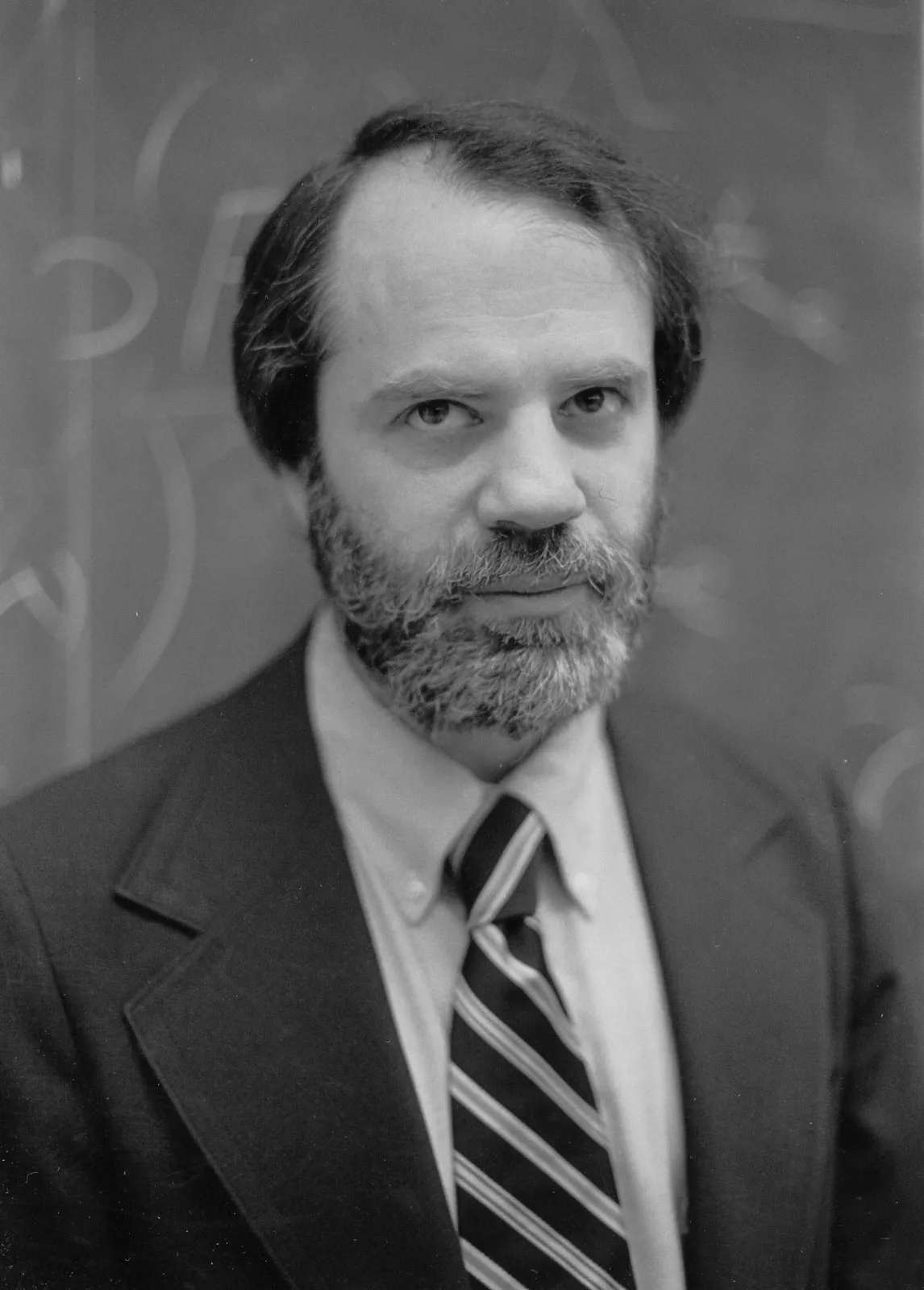
克里普克
同样,拥有相同名称的事物(例如同名同姓的人)尽管很多,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某个“专名”的时候,不需要特意说明我们以此来意味什么;事实上,当我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使用某个常见的名称时,根本不需要做出任何说明,他人也不会要求确认这个名称的指涉。(在特殊的场合下,也许对方的确会出于惊讶或疑惑而提问说:“你说的是那个柄谷行人吗?”但与其说这个问题是在向言说者请求确认“柄谷行人”这个“专名”指涉的对象,不如说是以双方共同认知的对象为前提、以这个“专名”所指涉之对象的非含混性为前提,表达自己的惊讶或疑惑态度。)
那么,如何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就“专名”达成合意?我们是否要像克里普克表明的那样,将“专名”的稳定和传递追溯到某个初次的、起源性的“命名仪式”那里,追溯到某个恰当意义上的“述行句”那里,以至于所有“专名”都必然隐含一句“我在此将此命名为……”?当然不是。事实上,关于“专名”之传递的上述想象,恰恰是“专名”作为“专名”成立之后回溯性地追认的一条线索,它是“专名”发挥作用的效果而非原因。因此,克里普克那里假定的、我们仿佛在其中习得“专名”的用法和意义的那个共同体(系统),本身也是交流达成合意之后产生的效果之一。关于这一点,柄谷论述道:
名称传达者和接受者的关系(遭遇)是外部的、偶然的。也就是说,这是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同前,62页)
简言之,“命名”的偶然性,不过是语言交流的偶然性的一个环节;反过来说,“专名”所揭示的内容,正是我们所有的语言交流都包含的内容。在《探究(一)》中,柄谷通过对于维特根斯坦笔下著名的“语言游戏”的讨论指出,交流并不发生在既定的规则基础上;相反,交流的规则只是事后才被确立,并被回溯性地规定为仿佛一开始就存在于那里。而在每个实际交流的现场,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交流双方达成合意。柄谷从而借用克尔凯郭尔的说法,将交流合意的实现称作“致死一跃”。同样,在实际的交流过程中,与其说我们在对其“起源”习焉不察的情况下使用着“专名”,不如说对于“专名”的“起源”的想象本身,也是“专名”发挥作用的效果之一。“专名之所以可以固定指示,反倒是因为它带有无法在共同规范的意义上被内在化的那种关系的外在性。”(同前,63页)
在这个意义上,在放弃了将自己局限于系统内部、试图以内部的自我瓦解来发现“外部”的思考进路之后,柄谷选择以“专名”问题为线索而讨论“他者”“外在”等主题,并不是因为“专名”天然地指向语言的“外部”(否则就退回到传统认知上的语言符号和现实指涉的对应关系上去了),而是因为“专名”之为“专名”所包含的外部的交流或交流的外在性:
专名看上去保存了和语言体系外部的联系,这不是因为专名支持外部对象,而是因为它含有语言体系之内无法内在化的某种外在性。(柄谷行人『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24页)
如果说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和所指在各自的差异性系统中通过消极性的差异而产生积极意义的过程,需要一个“符号0”的“缺席性在场”,需要一个本身无法被表征的超越者来确保系统的封闭性,确保差异向意义的生成,那么柄谷提醒我们:“专名”在我们日常交流过程中的使用和指涉,并不需要经过这样一种超越者的中介,或者不如说,超越或外在于“专名”及其现实指涉的,正是对“专名”而言不可或缺的、言说者与他者的交流本身。在此,“前期”柄谷苦苦思索的问题通过一次看似简单的颠倒得到了消除:我们不需要通过彻底的“内在化”而寻求“外部”,因为所谓的“外部”无时无刻不构成我们交流、理解、认知的前提。归根结底,“前期”柄谷所批判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所遮蔽的,并不是只有通过彻底的内部差异化才能窥见的“符号0”,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却无法被系统内在化的交流的外在性和偶然性。
柄谷的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是要拥抱或赞美偶然性、强调事情本来可以是另一个样子,那么就如有的批评者所说,批评家小林秀雄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更加“深刻”地指出了我们作为“偶然如此”的存在者的有限性和悲剧性。通过强调偶然性和差异性的不可还原性,柄谷究竟想要说明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专名”与言说者的关系上:如前所述,“专名”不仅提示了所指涉的对象的“独特性”,而且提示了言说者对于该对象的态度或位置(尽管不是言说者的意图)。不仅在我说出(例如)“柄谷行人”或“这只猫”的时候如此,当我使用“我”这个语词的时候同样如此。这里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我”作为言说者经由“我”这个语词而被收编到一个差异性的符号系统内部,从而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仅仅是语言的效果——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理解——不如说恰恰相反:当我使用“我”这个语词的时候,我希望借此提示的、与他者之间不对称的差异性(作为言说主体的“我”并不是在通过与其他“我”的对比中得到“我”的固有的差异性,而正是通过说出“我”这个语词来显示形式性的、不可还原的差异性),无需经过某种抽象而一般的、关于“自我”或“主体”的先验性规定才能得到揭示;通过言说“我”,作为言说主体的“我”已经包含了无法被语言系统内在化的、差异性的“外部”。重复一遍:这里说的不单是作为经验事实的外部存在,而更是对语言使用而言不可或缺的交流的外在性。
对于“他者”“外部”乃至“差异”的揭示无需经过一个“缺席性在场”的超越者,这进一步意味着:对于任何话语和制度的批判和反省,不需要批判者占据一个超越性的“元立场”。在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行阐述时,柄谷写道:
“主观”只有在笛卡尔以后的哲学中才显现出来,这如果说的是先验结构的首次显现,那么的确如此。因为如笛卡尔所说,在此之前的哲学从属于所谓“语法”。但是,在笛卡尔那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这种先验结构那里出现的“主体”,一旦仅仅作为认识性的主观而被积极地确立下来,那么它就消失了。(同前,97-98页)
在柄谷看来,如果我们依照笛卡尔主义的主客二分法来表达所谓的认识论主体,那么这一做法已经使得我们落入了一种围绕所谓“先验结构”而确立起来的有关认识的封闭系统之中。在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柄谷所强调的并不是所谓主体的“消失”,就像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在批判“主体”时所做的那样;相反,柄谷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无法被语言系统内在化的、关系的“外在性”,那么在面对“批判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反思何以可能”等貌似处于“元层次”的问题时,我们不必为自身的批判或反思建构额外的条件,仿佛只有从一个抽象而高高在上的“普遍性”——无论它被叫做“理性”“人性”还是“精神”——出发,我们才能对种种“特殊性”做出价值评判。相反,在每一次的交流中、在每一次与他者的偶然关系中,都包含了批判的可能性,因为每一次的交流(或用柄谷强调的一个词:“交通”)中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主体位置的“跨越”:
作为先验结构的主体的场所,或作为场所的主体,不是在“深处”而是在“旁边”;换句话说,必须把它称作“作为差异性的空=间”。当然,这不是心理意识,也不是客观空间。(同前,104-105页)
因此,柄谷指出,在笛卡尔的“我思”那里得到揭示的,便是主体的这种“作为差异的场所”——不是一个稳定而抽象的思考主体,而是一个处于不断移动中的、在“交通”过程中进行思考、比较和批判的主体。不固着于某种“主体的先验结构”,而是以“交通”过程中与他者的偶然关系为着眼点: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柄谷在《探究》《跨越性批判》到《世界史的构造》的一系列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和论述姿态,也是我们评价其“交换样式”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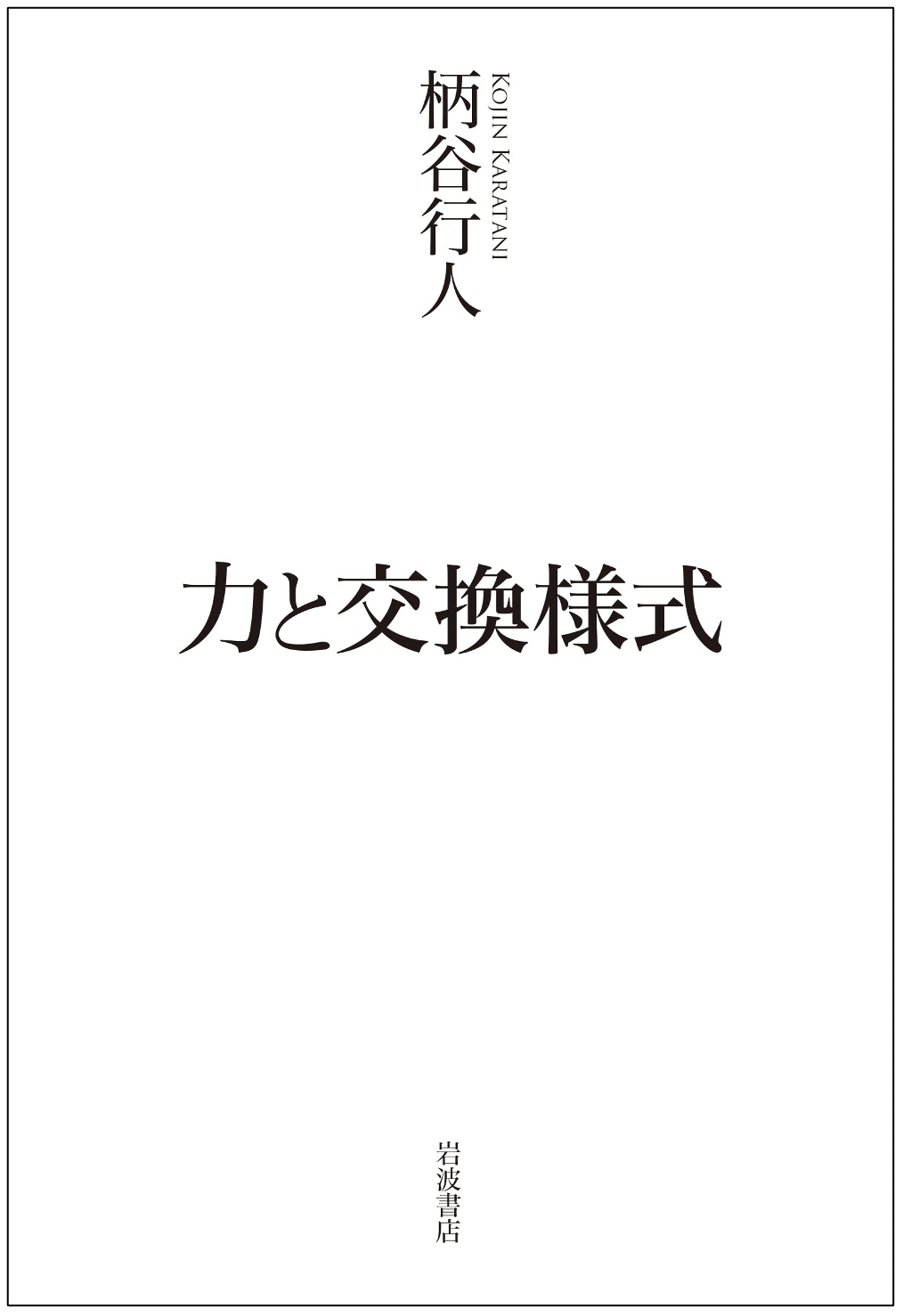
柄谷行人『力と交換様式』,岩波书店2022/10/5刊行
结合专名的讨论,柄谷关于“我思”的讨论告诉我们:在日常使用语言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专名”的意义上使用语言;我们无时无刻不与语言(的所谓字面意思)之间保持着一种无法还原的距离——不是一种物理上可勘测的距离,不是“先验主体”与经验之间的距离,不是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而始终是作为“差异性的场所”而存在的、标志或烙印着言说者之主体性和独特性的距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