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齐美尔逝世百年︱郑作彧:齐美尔的社会学与计算机仿真技术

二十世纪以前,诸学科之间尚未泾渭分明。其时许多伟大的学者,如今看来,仿佛都是跨领域的通才。齐美尔即是如此,研究遍及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然而各科之中,或许只有对于社会学,他才是不可替代的。人们已有共识,齐美尔位列“社会学之父”:只有社会学才是齐美尔的亲生孩子,齐美尔也只能算是社会学的父亲。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德国社会学会在柏林初创时,众人一致推举齐美尔出任学会的首任会长,却为他婉拒。是年12月14日同里克特、15日同韦伯的通信中,他道出了原委:社会学研究于他,与更主要的哲学工作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至少在德国,较之他对哲学相对深入的掌握,他自认为他的社会学研究水平与其他学者的成就相去甚远,不足以任其位(Georg Simmel, 2005, Briefe 1881-1911. Gesamtausgabe, Bd. 2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 752, 755)。这一方面自然是自谦之词,否则他不会被参与学会草创的另外三十八位学者推选;但另一方面,若确如其所言,他的社会学研究相较于其他工作有特殊性,并且众所周知,他后来已将主要研究精力转向生命哲学,那便不难理解,以今天社会学角度观之,齐氏社会学理论有不够完满、令人意犹未尽之处——比如社会学方法论。
在许多学者看来,齐美尔未能如另两位社会学之父涂尔干和韦伯一样,为其社会学理论提供一套充分的方法论。就连他自己也曾说,他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更多是直觉式的(Georg Simmel, 1908,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p. 13)。不过,齐美尔的不少社会学分析不光精辟、精彩,而且极具风格,既然极具风格,便意味着他的研究并非随心所欲,而亦有一套特殊做法,只是没有予以澄清。
今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已是洋洋大观。从齐美尔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概念出发,衔接上社会学发展的现状,我们或许能使齐氏在方法论方面的“直觉”,变得柳暗花明。
齐美尔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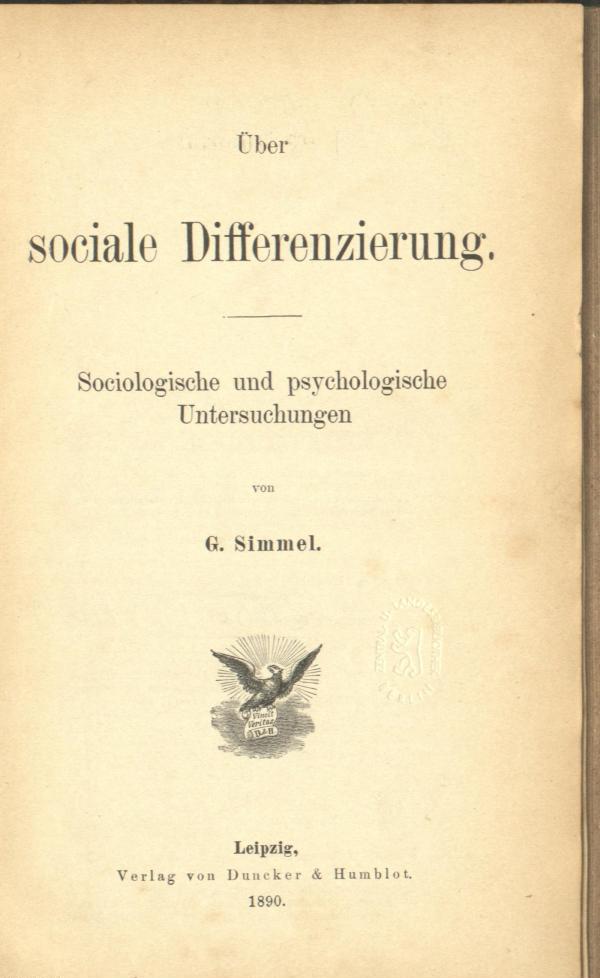
自第一本社会学著作《论社会分化》开始,齐美尔就确立了他整个社会学理论最重要的两个基本概念:“相互作用”与“形式”(Georg Simmel, 1890, Über sociale Differenzierung. Soc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二者基本概括了他对于社会是什么,以及如何观察社会的看法。
齐美尔认为,不是诸多人类个体集聚在一起就会构成社会。社会之形成,必须由诸多人类个体彼此之间产生相互关系。但关系不是静态的。关系的形成,有赖于人类个体对其他人类个体——直接或间接地——做出有意义的实际行为,且这一意义行为对后者造成了实质影响;与此同时,其他人类个体也相应地做出有影响作用力的意义行为。此即齐美尔所谓的“相互作用”(Georg Simmel, 1896, “Zur Method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Bd. 20, p. 581)。
随着相互作用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不断发生,关系就会持存,人们便可以通过概念来综合、命名、掌握这种关系,让相互作用成为概念整体,如政治、宗教、市场。齐美尔称如是概念整体为“形式”。当人们更统括地去看所有相互作用构成的最大范围的概念整体,便得出了 “社会”。换言之,“形式”是一种用来把握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的概念:就像液体是特定温度当中,分子相互作用下“液化”的结果,恐龙化石是恐龙尸体被泥沙掩埋后,与沉积物相互作用下“石化”的结果一样,社会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下“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而成的形式(Simmel, 1908)。

在这样一种关于社会与社会学的定义下,齐美尔特别强调,社会学讨论的,既不是微观的个体生理、意识或沟通交流的举手投足,也不是宏观的政经法规等静态制度,社会学应该分析各种动态发生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怎样的形式(Simmel, 1908: 17; Georg Simmel, 1917, 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Berlin/Leipzig: G. J. Göschen'sche Verlagshandlung, p. 15)。不过,齐美尔所谓社会学不探讨社会形式的零散内容,并不意味他认为社会学不该论及人类个体,毋宁说,社会学对于个体,需要有另一种想象方式:所谓“人类个体”也是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形式。
言下之意有二。首先,将整体形式拆分成基本元素,是一种可以无穷尽的过程。社会可以拆分成人,但人也可以拆分成细胞,细胞还可以再继续拆分成分子、原子。如此一来社会的基本元素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人类个体。但这种无限还原对社会学没有意义。拆分、还原某一单一整体形式的底线,由学科关怀旨趣而定。社会学常将社会拆分、还原止于人类个体,是因为社会学关心的对象是人。
其次,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个体,是由主体意识、文化、角色、身份地位、生命历程等无数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丰富的整体形式。当某个人被社会学地看待,他或她便不再被视为生物,而成了社会的缩影。如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故事,身上缠绕着无数的相互作用。齐美尔说,不只社会是社会化的结果,人类个体也是“社会化的存在”(Vergesellschaftet-Sein),是一种相互作用下的形式(Simmel, 1908: 26)。于是,社会便具有个体和集体的双重状态,因为社会世界是一幕幕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差别只在于我们用怎样的观察角度综合地把握它们(Simmel, 1917: 11)。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齐美尔时常花费大量心力分析各种“琐碎”之事,例如“用餐”“竞争”“都市生活”,抑或是“女性”这种如个体一般的社会“形式”。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齐美尔遭到了众多批评。同时代的奥地利社会学家施潘(Othmar Spann)指摘道,如果按齐美尔所说,社会是相互作用构成的形式,那局部的相互作用为何,又如何是一个概念整体,或曰形式?甚者,齐氏的相互作用,说穿了不过是多重因果关系,却无端将(社会)科学的因果解释弄得繁复不堪,必然会遇到方法论瓶颈。施潘的意思是,如果相互作用仅在两人之间,经验研究尚不难进行,仅需探讨两次不同作用方向的因果关系即可,但若在三人间,情况就变得比较困难,而一旦超过三人,至无数多人,必然过于复杂,难以作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Othmar Spann, 1905,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Gesellschaftsbegriff zur 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Erster Teil: Zur Kritik des Gesellschaftsbegriffes der Modernen Soziologie. Dritter Artikel: Die realistische Lösung.”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61, p. 318 ff. )。就连齐美尔的好友韦伯也认为,相互作用的概念将社会现象复杂抽象化了,妨害经验研究操作,因此否定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而更倾向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将人类个体视为研究单位(Max Weber, 1985, “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In Johannes Winckelmann ed.,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J. C. B. Mohr, p. 439)。


简言之,施潘和韦伯都认为,从相互作用到形式,意味着一种多重因果关系的复杂情境。齐美尔不光要求社会学研究这种复杂情境,还要求社会学家掌握这一复杂作用如何产生出一种可以用概念加以整体掌握的形式。然而,相互作用是局部的,并且是复杂的,至于形式则是整体的,而人类的观察视角又是有限的——社会学如何能够在掌握所有局部的复杂相互作用的同时,还能掌握由此而来的整体形式?不得不说,齐美尔提出的社会学是一项要求极高的研究任务,但他却没有仔细交代社会学家该通过何种具体而系统的操作程序,对相互作用突现出形式的过程进行经验分析。如前文所述,齐美尔自己也承认,他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仰赖于一种观察敏锐度,这个回答亦为后人诟病。
但是齐美尔从未放弃他的观点。显然这个概念在其社会学思想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尽管他不曾对施潘和韦伯的批评做出回应。不过,当代德国著名的齐美尔研究者利希特布劳(Klaus Lichtblau)却为齐氏抱不平。他认为,在量子力学、复杂性理论蓬勃发展的今天,非线性因果关系已经受到广泛重视,也发展了出丰富的研究方法,这足以为齐美尔的理论翻案(Klaus Lichtblau, 2011, “ ‚Kausalität‘ oder ‚Wechselwirkung‘? – Simmel, Weber und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 In Klaus Lichtblau ed., Die Eigenart de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Wiesbaden: VS Verlag, p. 183)。可惜的是,利希特布劳没有进一步交代该如何翻案。但如果跟随他的思路,从复杂性理论来思考相互作用与形式研究,不难发现,今天的确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专门讨论相互作用突现出形式的研究方法,即计算机仿真技术。
为齐美尔翻案:智能体模型里的种族隔离和时尚
眼下,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鉴于计算机计算的多样化与复合性,一般的统计软件、人文地理空间分布模型等都可归入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范畴。在计算社会科学中,与齐美尔的相互作用概念最具相关性的方法是“智能体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以下简称ABM)。
ABM不是某种特定的计算机程序,而是利用计算机从事社会研究的建模方案。基本做法是:利用计算机,在一个虚拟空间中,设计数个同质或异质的行动者(agent),每个行动者被设定了自身的行为规则,以及遇到其他行动者时的反应规则,继而,让这些行动者在虚空间当中行动,研究者借此观察它们在相互作用下,会产生出怎样的宏观整体形式(Joshua M. Epstein and Robert Axtell, 1996, Growing Artificial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Bottom up.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最经典的ABM研究,当属谢林的隔离模型(Schelling’s Segregation Model)。该ABM来自经济社会学家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研究种族隔离的模型构想(Thomas C. Schelling, 1971, “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2): 143-186)。谢林假设在某个平面空间中有两个种族,每一族有数名行动者,最初这些行动者在平面空间上是混居的。根据假设,每位行动者对居于周遭的不同族邻居的忍受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同族邻居低于一定比例(比如百分之三十),行动者就会选择搬家,直至同族邻居的比例不再低于百分之三十为止。最初,谢林模型利用极为复杂的计算来呈现相互作用的演变结果,现在人们则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建模。比如设计五十乘五十的网状平面,每个行动者作为两族之一的成员,占据一个网格,初始随机分布在网状平面上,周边八格为同族或异族的邻居,也可能无人居住。当邻居同族比例低于百分之三十,行动者会往四周迁移。凭借ABM,谢林模型快速、直观、可重复地呈现了出来。而即便在百分之三十这种同族比例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随着众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仍会突现出周遭邻居同族度超过百分之七十方才达至稳定、不再有行动者搬迁的整体显著种族隔离形式。

知名的ABM社会研究者爱普斯坦(Joshua M. Epstein)认为,虽然相互作用过于复杂,人们无法径直找出其中的直接单一肇因,但可以通过ABM发现形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相互作用要素,观察哪些要素可以让行动者的相互作用“长出”(grow)与历史事件一致的形式。借此,社会学家虽然无法对某个社会事件作因果解释,却可以解析出其关键的突现要素(Joshua M. Epstein, 2006,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除了回顾已知的社会事件,ABM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尽可能建立当下所有已知的行动者状态,模拟行动者接下来可能的相互作用,预测未来可能突现出的社会形式(Charles M. Macal, 2016,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Journal of Simulation, Vol. 10, p. 148)。

可以说,ABM正是一项专门研究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形式的技术,与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构想不谋而合。实际上,确曾有两位意大利学者——佩东(Roberto Pedone)和孔德(Rosaria Conte)有意识地将ABM与齐美尔的相互作用概念关联起来,设计出名为“齐美尔效果”(the Simmel effect)的ABM。
“齐美尔效果”研究的是齐氏时尚理论留下的一个经验研究问题。在《时尚哲学》一文,齐美尔指出,时尚同时是对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的追求。这反映在了社会阶层形式的形成与破坏:位居社会上层者模仿彼此的生活风格,形成时尚,以同下层的生活风格相区别,而下层想模仿上层的生活风格,向上层靠近,一旦上层的生活风格被太多人模仿,差异消除,时尚便不成其为时尚了,上层于是开始躲避没有差异性的生活风格,另外共同追求具有差异性的时尚。社会阶层形式便形成于如是模仿与躲避的过程(Georg Simmel, 1905, “Philosophie der Mode.” In Hans Landsberg ed., Moderne Zeitfragen, No. 11. Berlin: Pan-Verlag, pp. 5-41)。这一理论遗留下一个内含矛盾的问题:社会阶层形式究竟是形成自模仿,还是躲避,抑或模仿与躲避兼备?佩东和孔德以模仿与躲避的过程为研究主题,设计了一套名为“齐美尔效果”的ABM (Roberto Pedone and Rosaria Conte, 2002, “The Simmel Effect: Imitation and Avoidance in Social Hierarchies.” In Scott Moss and Paul Davidsson eds., Multi-agent-based simulation.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MABS 2000, Boston, MA, USA, July, Revised and Additional Papers. Berlin: Springer-Verlag: 149-156):在一个由多个方格构成的平面上,有三大类行动者,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阶层,每个行动者占据一格方格,初始状态随机分布在平面上,可向四处移动。模仿意味着较低层行动者向较高层行动者靠近,躲避意味着较高层行动者远离较低层行动者。当同层次行动者在平面上汇聚,且汇聚程度在卡方检定上呈现显著时,代表形成了社会阶层形式。佩东和孔德根据(1)只有躲避、没有模仿;(2)只有模仿、没有躲避;(3)兼具模仿与躲避,但只模仿或躲避高一层的行动者;(4)兼具模仿与躲避,且模仿与躲避的是所有较高层或所有较低层;(5)以模仿优先;(6)以躲避优先等参数,建立七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类型,进行了七种齐美尔效果实验。

在模拟实验前,佩东和孔德的设想是,必须模仿与躲避兼备,才会产生显著的行动者汇聚效果,形成阶层。但他们研究发现,仅仅是模仿,就会出现显著的汇聚效果,只不过这仅属于异质汇聚,不成阶层。而仅仅躲避,则无法造成任何汇聚效果,更谈不上形成阶层形式了。至于七种相互作用类型中,阶层显著性突现得最高的,是兼具模仿与躲避,但只模仿或躲避高一阶层,且在同时遭遇模仿与躲避的情况下模仿优先的行动者。有趣的是,任何兼具模仿与躲避的相互作用类型当中,只要加入“躲避优先”要素,就会减少阶层显著性。佩东和孔德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颇令人意外(也颇有争议)的论点:形成社会阶层形式的关键要素是类聚,不是群分,后者甚至对阶层形式是负面要素。

对于突破齐美尔社会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不足,齐美尔效果无疑是十分重要、具有启发性的开端。然而显见的是,齐美尔效果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模型。如果ABM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模仿真实社会,且尽可能与真实社会等同的人工社会,齐美尔效果显然距离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事实上,ABM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程序设计往往缺乏透明性,缺乏研究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标准,缺乏一个通用的ABM的程序设计平台(关于ABM至今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参阅Ulrich Frank et al., 2009, “EPOS –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imul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Flaminio Squazzoni ed., Epistemological Aspects of Computer Simul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 1-11)。但对社会学而言,计算机只是一种工具,虽然可以编写和运作程序,但程序该怎么设计,终究牵涉到程序编写者对仿真对象的想象:认为所要仿真的对象是怎样的,编写出来的程序就会怎样(罗家德等:《论社会学理论引导的大数据研究──大数据、理论与预测模型的三角对话》,《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五期,118页)。如此,显然有必要思考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与ABM这套技术该如何互相补充完善。
齐美尔的遗产与社会学的未来
近来,美国ABM研究者马卡尔(Charles M. Macal)指出,今天一般统称为ABM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设计层次(Macal, 2016)。

第一种层次是“个体的ABM”,在虚拟空间中设计数个异质行动者,规定行动者的特定行动方针,运作程序、让行动者去行动,研究者观察其突现出来的宏观形式。这多半用于交通科学研究,比如仿真某区域的车流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根据既定的规则僵化行动,忽略了现实社会中个体的自主动力。第二种层次是“自主的ABM”。自主的ABM中的行动者被设计拥有多种行动方针,并且能辨别环境状态,据此调整自身的最佳行动方式。这种设计层次与个体功利主义的观点高度亲和,因此常用于经济学研究。但它忽略了在现实社会当中,行动者在相互影响下并不一定会充分获得关于环境的信息,也未必只会选择利于自身的最佳行动方案。第三种层次即“互动的ABM”,其行动者会观察所能观察到的(亦即有限理性地观察)其他行动者的行动,根据后者做出相应的判断与反应。研究者借此考察相互作用下突现出来的整体形式。这是现今社会学最普遍采用的ABM设计层次,前述“谢林的隔离模型”“齐美尔效果”基本都属此类。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互动的ABM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是一种会学习、会改变的生物。马卡尔建议,ABM未来应该向他所谓“适应的ABM”(adaptive ABMs)——第四个ABM设计层次迈进。在适应的ABM中,行动者虽然有依据当代社会现有数据而设定的初始状态,但在模拟的过程中,行动者会记忆、反思、学习,并有一定的随机情感要素,形成新的角色定义,进而改变自身初始的行为模式,产生新的行动者形式。于是,研究者既可以观察诸社会在相互作用下突现出怎样的集体型态,也可以聚焦于行动者,观察行动者在相互作用下突现成何种个体形式。
相较于ABM设计的前三个层次,适应的ABM显然是更契合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的技术。因为这一设计方针不仅关注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宏观的社会形式,也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呈现个体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形式。爱普斯坦近年来设想了“零号行动者”(agent_zero)的设计取径(Joshua M. Epstein, 2014, Agent_Zero: Toward Neurocognitive Foundations for 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即在ABM设计中,结合神经认知科学,让每个行动者尽可能有细致的情感、思考等“更像人”的要素。不过,适应的ABM涉及人工智能技术,而目前,单个人工智能体的设计尚且面临巨大挑战,遑论设计无数同时运行的、趋近真人而又彼此异质的人工智能行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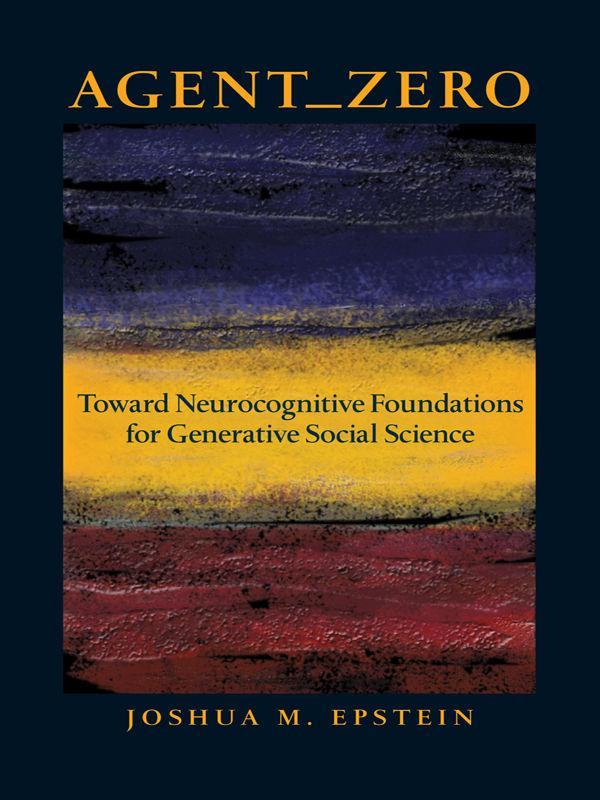
然而以科学进步之迅猛,适应的ABM可望在不远的未来飞速发展。到那时,齐美尔设想的社会学研究,也许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能以新颖的面貌出现。社会学家不再囿于看不到活生生个体的定量统计模型,或是难以处理社会整体的定性理解诠释,而是诉诸计算机,设计出无数有血有肉、贴近真正社会人的行动者,让它们在虚拟的环境里彼此产生相互作用。社会学研究可以无数次地重复这群行动者的生活,观察在无数重相互作用中,会产生怎样宏观的与个体的社会形式。通过新技术,齐美尔的社会学遗产或能被激活,令他在过世一百年后,仍然展现出无穷的思想生命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