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忙?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不仅仅意味着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同时也意味着更民主的工作场所、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劳动分配。这是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也是当下的大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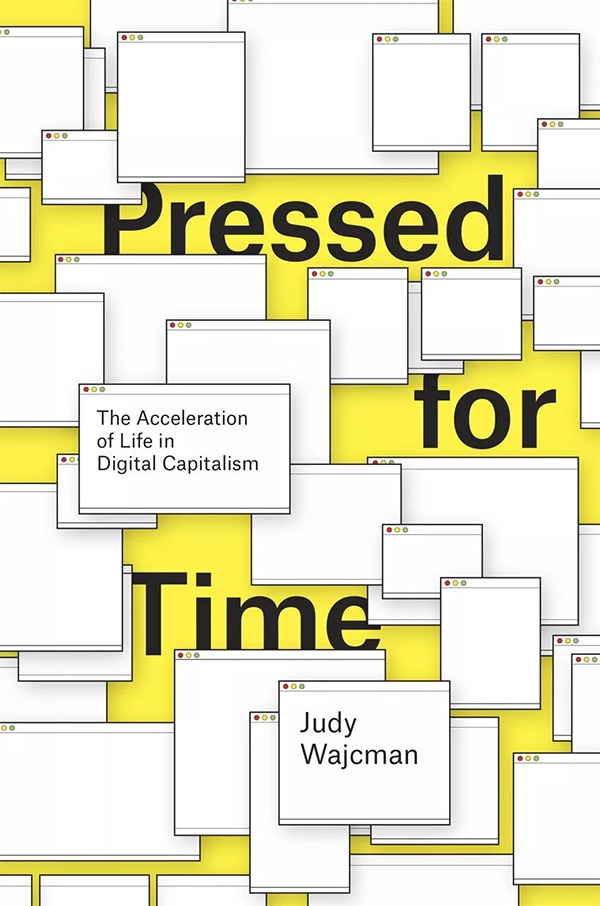
时间已来到2018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物质和闲暇都极大丰富的时代吗?就物质来说,全世界某些地区的匮乏依然触目惊心,但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已经享受到了丰富的涌现;就闲暇来说,反而是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行色匆匆,深感时间紧迫。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进步的巨大悖论。
作为研究时间利用、工作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专著,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的《时间紧迫:数字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加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自然也提到了凯恩斯的预测,并且其主要目的就是解释,为何先进的数字技术没有能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而是让我们更加感到时间紧迫。但时间紧迫真的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造成的吗?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时间上的紧迫感吗?如何看待技术对人们的时间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如何才能慢下来,享受高品质的闲暇,从而享受真正的自由?瓦克曼的这本书将工作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及女性主义熔于一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一、时间紧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现代都市中的居民最为常见的抱怨之一就是“忙忙忙!”。现代技术如各种自动化机械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我们的劳动,为何我们还辛劳不已,无法摆脱亚当的诅咒(the curse of Adam)?前文所引凯恩斯所说的劣根性原文即是“the old Adam”,指的是人类不得不劳作并忍受劳苦的命运。尤其是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似乎进入全面加速的时代,原本线性的钟表时间趋向于消失。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甚至发明了速度学(dromology)来解释人类所面对的加速化世界,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瞬时的时间(instantaneous time)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等。
这些概念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加速社会。的确,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交易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伴随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而伴随着交通网络的发展,人和物的移动更是超越了日千里。因此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变快,因而就感觉繁忙不堪。但是难道技术不是会节约时间的吗?因此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闲暇吗,为何会感到更加的匆忙?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
但我们的闲暇真的变少了吗?瓦克曼通过数据指出,自“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减少,其实还有所增加。但为何人们还是感觉时间紧迫?当然,对时间的感受本就很主观,人们可能在量上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但如果在享受闲暇的同时还要担心工作内容或者家庭事务,这也会造成时间紧迫的感受。因此,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瓦克曼解构了太过概括性的时间紧迫话语:男性在家庭内的劳动时间要少于女性,对家务在精力和情感上的投入也弱于女性,这当然造就已婚已育女性在时间上更加紧迫的后果。
当然,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家庭空间不也自动化了吗?洗衣机,微波炉,烤箱等家用电器不是大大节省了我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吗?的确,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很多原本属于家务劳动的活动都被社会化和商品化,如制作衣服、养殖家禽家畜、酿酒、腌菜、甚至于做饭,以至于很多社会学家认为家庭只存在消费功能。但是家用电器依然需要有人操控,这就产生了很多额外的活动。另外,像准备饭菜,照料老人与孩子的活动依然属于劳动和时间密集型的活动,无法被机械化,也无法加速,大多时候都是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另外,当下文化对于卫生、对于与孩子相处的“品质时间”(quality time)的重视都让家庭活动的内容有增无减。尤其是对单身母亲来说,她们可以说是时间紧迫感最为强烈的群体。
因此当我们说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要分清不同群体——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精英与大众——所面对的不同时间体制。换言之,时间紧迫感是一种多维度的现象。
时间或者说钟表时间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有着紧密关联。正如芒福德(Lewis Munford)所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都是根据自然节奏以及上帝或者神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作息。关于这一点不得不提E.P.汤普森的经典研究《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中,这也是瓦克曼非常重视的文本。农民会根据自然节气来安排农时,欢度比现在多得多的宗教节日,而教士则会根据教堂的钟表来安排每天的活动。因此有论者认为圣本尼迪克特的信徒们及其严格的工作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奠基人。
汤普森所指出,在农业社会,时间标志法曾被描述为任务导向(task-orientation)。完成这种任务不需要计时,农民有活就干,无活就歇,因此也就没有“生活”与“工作”的区分问题,因为工作完全是自主的(前提是不至于土地荒芜而颗粒无收)。最后,与需要计时的(工厂内的雇佣)劳动相比,这种劳动不慌不忙,毫无紧迫感,甚至显得浪费时间。因此前工业社会并不需要精确的计时工具,不需要那样分秒必争。
在韦伯看来,作为入世禁欲的新教滋长了现代工作伦理,从而也确立了现代的工作社会和工作意识形态。新教徒不再通过神迹或巫术来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所拣选,他们的标准更为客观,那就是在禁欲的前提下勤劳致富。因为所有禁欲的新教教徒为了确认自己的“恩宠状态”,无法再借助任何巫术—圣礼手段、忏悔赦罪或个别的虔敬善功而获得保障,最终只能诉诸自己的行为举止。最终就是“着眼于彼世而在现世内进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财富,于是劳动或者做工(如《约翰福音》9:4所说,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就成了绝对命令。任何对于时间的浪费,如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绝对是应该加以道德谴责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虽然未曾听闻,但其背后的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教徒的懒惰有损于上帝的荣光,现代工人的懒惰则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对此汤普森写道:“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必须有所利用,必须销售掉,使用掉;劳动力白白地‘消磨时间’(pass the time),这是一种错误。”
于是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工作伦理越来越成为一种虚假意识,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无法从工作中得到财富,更不要说拯救了。工人会通过怠工与造反等方式反抗这种工业生产方式,于是作为驯服工人机制的工作意识形态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会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有赖于各种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在高兹(Andre Gorz)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之为工作社会(work-based society)。在工作社会中,作为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的时间当然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即创造财富和剩余价值。因此所谓的时间紧迫悖论也就很好理解:一天二十四小时要在(“我的”)自由时间和(由老板所支配的)工作时间进行分配,前者必然不断为后者所侵占或者殖民。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生产力如何发达,资本总是要剥夺越来越多的劳动,而不可能主动削减劳动时间,满足于已经极大丰富的生产。在《资本论》和《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论述均是从穆勒的一句话开始的:“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这个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抽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瓦克曼没有注意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所造成的劳动时间的不减反增,这无疑是巨大的盲点。
《时间紧迫》指出,在过去5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事实上,在1965—2010年,当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感觉匆忙的时候,他们的自由时间其实在增多(第64—65页)。那问题就来了,时间紧迫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而且主要是工作女性尤其是工作的单身母亲的问题?
二、都是数字技术的错?

在瓦克曼看来,这种时间紧迫感更多由现代的“忙文化”所造成的。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精英阶层的重要标志是大量的闲暇,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事政治与艺术等高贵的活动,而普通民众只能从商或者从事生产性劳动——后者被认为是“鄙事”,属于小人所为。但是在今天,这种价值秩序似乎颠倒了。今天的英雄是那些创业型企业家,他们在媒体中的形象是勤劳且智慧的成功者,是有着多方面追求的生活家,最典型的就是马云,他不仅在商界呼风唤雨,而且也想在艺术界留下自己的印记。即便是富二代,他们也要表现出勤劳聪慧,如此才能得到大众的接受。“今天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不是对闲暇的炫耀性消费,而是投入时间密集型工作的程度。”换言之,是繁忙,而非闲暇成了“荣誉勋章”。这可以说是工作意识形态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些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文化中必然要受到歧视。有研究表明,失业所造成的伤害比失去亲人还要严重。这是工作意识形态对人的内在心理所造成的压迫。
当然,忙也分为穷忙和富忙。两者除了收入上的差别之外,心态上也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主要是从事低端行业的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可能从事好几份兼职,每天疲于奔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这些工作中除了收获微薄的工资之外,无法获得任何成长的经验或者生活的意义;后者虽然繁忙,但是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节奏,并且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而大多数人介于这两者之间,将“忙文化”内化进自己的心理。因此当一般人抱怨“忙忙忙”的时候,他们既是抱怨,同时也不无炫耀。加班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瓦克曼也注意到了工作的极化问题——她给出的说法是好的MacJob(以苹果公司中的高科技高收入的工作为代表)和坏的McJob(以麦当劳中的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为代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重复性和程序化的白领和蓝领工作逐渐被消灭,中产阶级萎缩,坏的McJob大肆泛滥。但瓦克曼并没有沿着这条线索论述下去,来解释当下的时间紧迫感。作为科学与技术研究出身的学者,她选择了对技术与时间紧迫感之间的关联进行阐释。
一般对待技术存在乐观论和悲观论两种态度,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如更丰富的物质产品,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便捷的生活服务;后者则认为技术总是走向乐观期待的反面,不是带来解放,而是带来更深的奴役。在瓦克曼看来,无论是技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本质上都是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必然会带来某种社会结果,而她则属于技术的社会塑造论(a social shaping approach to technology):技术并非外在于社会的抽象理性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互动的结果。换言之,技术设备与时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些设备如何进入并融入我们的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模式中去。技术设备并不直接决定我们的时间感,而是受到社会制度、日常生活文化等要素的中介。也就是说,可以将技术视为某种编码,而如何对其进行解码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实践。
瓦克曼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来破除如下流俗之见: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是让我们感到时间紧迫的罪魁祸首。作者基于自己的实证研究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电子邮件并不一定会加快工作节奏,因为员工即便在工作场所之外收到工作邮件,他们也可以决定何时回复。手机也并没有让工作时间侵占“我的”时间,相反,它可以让我们有更加灵活地安排时间,与亲人朋友进行更多的互动,从而建构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手机并没有“偷走”我们的时间,只是改变了我们安排时间的方式。
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似乎的确没有感到时间紧迫的理由,似乎时间紧迫更多是工作女性尤其是单身母亲的感受。瓦克曼给出了一定的解释,那就是很多人对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随时随地的互联的担忧——工作时间侵占“我的”时间,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场所即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必须在如下语境中进行考虑:严酷的经济气候以及相伴随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当经济气候不好并且造成工作不稳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感到时间不受自己掌控,疲于奔命却无济于事,那种时间紧迫感才是最为迫切真实的。
三、新的工作形式造就了越来越强烈的时间紧迫感
但瓦克曼并没有对经济气候和不稳定状态展开论述,当然也没有论述工作形式变化所造成的时间感的转变。瓦克曼用“在过去5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来反驳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所提出的美国人过度工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劳动时间差别甚大。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欧洲的国家政策,因为欧洲比美国更为平等,更是因为相较于美国,欧洲劳工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因此欧洲劳工所争取的“我的”时间要多于美国劳工。正如肖尔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我所称之为的‘长工作时间’。最终之所以能夺回闲暇,是因为工会和社会改良家们展开了漫长的争取更短工时的斗争。”事实上因为德国工会的强大,他们正在争取将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缩减至28小时,其诉求之一是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而美国则显然因为工会力量的衰落,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劳动者则明显过度工作,缺少闲暇。
瓦克曼写道:“工作性质、家庭构成、关于抚育子女的观念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所有这些与技术变革的共同作用让我们感到世界在加速”。如今,随着离婚率的提高,单亲妈妈越来越多。另外,随着国家的退出和社会福利的紧缩,再生产的任务完全落到核心家庭或单亲家庭头上,而家庭内的无偿劳动则主要落在妇女头上,这就造成女性相较于男性的时间紧迫感。另外,现在对孩子的(过度)关注的确造成了父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品质时间”的后果,这也造成人们闲暇时间的缩水。再者消费主义的浪潮将大部分劳动者都裹挟其中,人们通过消费去制造幸福的幻象,然后再拼命工作以维持收支平衡。正如肖尔所指出的,长时间地工作,长时间地看电视,大肆购物,拥抱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不会增进幸福感,反而会让人变得抑郁、焦虑。这些要素在瓦克曼的书中都有详细论述,但作为工作社会学家,瓦克曼对于当下工作性质的转变却着墨甚少。而在我看来,工作性质的转变是造成劳动者时间紧迫的最关键要素。
瓦克曼的确通过引用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来指出长期稳定雇佣关系的终结及其对人格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详细分析具体是什么样的终结。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确立所产生的雇佣的不稳定化,即不稳定阶级(precariat)的产生。他们没有稳定安全的工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有的只是少得可怜的工资和自己难以认同的工作身份。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指出:“全球的非正规工人阶级(与贫民窟居民有交叉,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约有十亿,这让其成为地球上增长最为迅速、史无前例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群体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拥有瓦克曼所说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自由不仅意味着免于贫困的自由,而且意味着掌握时间的自由,在朝不保夕的工作的驱使下,他们不能不感到时间上的紧迫。
另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各种各样网络平台的出现,企业抛弃了传统的雇佣方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派任务(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优步、Facebook等)。这样企业不需要与劳动者缔结任何劳动关系,它们只需要发布任务,然后等待合适的人来竞争获取并完成任务。这种新时代的计件工资形式一般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种工作形式看起来很美好,好像劳动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像个企业家那样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从事零工经济的主要是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待并且竞争企业平台所派发的任务,而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而因为他们不是企业的员工,因此也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有组织预测,到2020年美国全职就业将会变得稀缺,超过40%的劳动力将是自由职业者、合同工或临时工。
在不稳定雇佣的背景下,劳动者很难分清工作时间与“我的”时间,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工作任务的内容,因为他们总是在焦急地等待任务,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关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学者,瓦克曼在最后的部分强调了如何正确对待家务劳动以及数字技术。但瓦克曼只是提及了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利用,形成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零工经济就是当下新兴的剥削形式。如果我们想要夺回更多的闲暇,那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从而提出更为激进的时间政治。
瓦克曼似乎接受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只想保卫这40小时之外的“我的”时间不受侵犯。但作者忘记了在美国30年代曾经出现的争取30小时周工作时间的运动。事实上,工人运动从最开始就在争取更短的工时,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庭和社区以及自我的发展中。从根本来说,争取更短工时意味着解放,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来说。马克思也将“工作日的缩短”看作是“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历史学家亨尼卡特(Benjamin Kline Hunnicutt)考证了另一个被遗忘的“美国梦”:逐步削减劳动时间。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曾经是比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美国梦更高的梦想。
瓦克曼的结论没错,数字技术的确不是造成现代人时间紧迫的元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技术所处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但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获得时间主权,那就必须削减工作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工作时间不断渗入“我的”时间,获得时间主权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不稳定劳工时刻都要担心或者操心工作。
但这根本还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作者在书中提到,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另外,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即在工作时间之外可以无视工作电话或者邮件。但是对于那些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来说,断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随时处于在线状态以接收任务。他们无法控制工作的日程和内容。这种工作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有学者和活动家主张用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rperativism)来代替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的根本在于这个平台必须由依赖或参与平台经济活动的成员集体所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掌握自己的工作日程和时间。
当然,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职业都要消失,其中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岗位,如记者,律师,医生等,剩下的工作将寥寥无几,而且的确呈现出极化的趋势:高收入且能带来成就感和意义感的工作越来越少,低收入且只能带来挫败感的工作越来越多,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零工。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应该尽可能消灭后一种工作形式,同时对前一种工作进行更为普遍的分配,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像凯恩斯所预期的那样,每天只需工作很短时间,但又不必担心失业的前景。这是诸多“后工作”理论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荷兰等国家也在实践这种分享工作(work-sharing)的形式:每人都有工作,每人都少工作。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不仅仅意味着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同时也意味着更民主的工作场所、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劳动分配。这是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也是当下的大政治。
本文首发于中国图书评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