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是所有科技,都会走向“《奥本海默》式”结局

“我的确喜欢思考未来,但其实没有做过太多预测,我并不是要和别人打赌未来一定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试图用一种有效的方式去谈论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
作者∣朱恺
编辑∣谭山山
题图∣受访者提供
当年逾七旬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昵称KK)站在面前,你可能会感到一丝诧异:
这位以“未来学家、互联网观察者、科技乐观主义者”闻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任何科技产品。他身上只带了一台iPhone8,“手机上会记录屏幕使用时间,我每天只看5分钟;也没下载任何社交媒体,里面只有时钟、日历和打车软件”。
凯文·凯利,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第一届黑客大会发起人,以及科技网站Cool Tools主理人,著有《失控》《必然》等畅销书。他第一次为公众熟知,便是电影《黑客帝国》主演基努·李维斯在采访中提到,剧组将《失控》列为必读书目,“我也因此在好莱坞获得了15秒的名气”。
的确,科技是他身上最大的标签。《失控》出版于1994年,在书中凯文·凯利提及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社区等概念,其中不少关于未来场景的预测,在当下一一应验,他也因此被誉为“互联网预言家”。
他也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当人们担忧AI将取代人类工作、引发一波失业潮的时候,他表示,AI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人工智能更像是由不同音符组成的交响乐。比方说,计算器在数学运算上比人类聪明,GPS的空间导航能力远胜我们,但是人类将这些功能组装到汽车里,才实现了自动驾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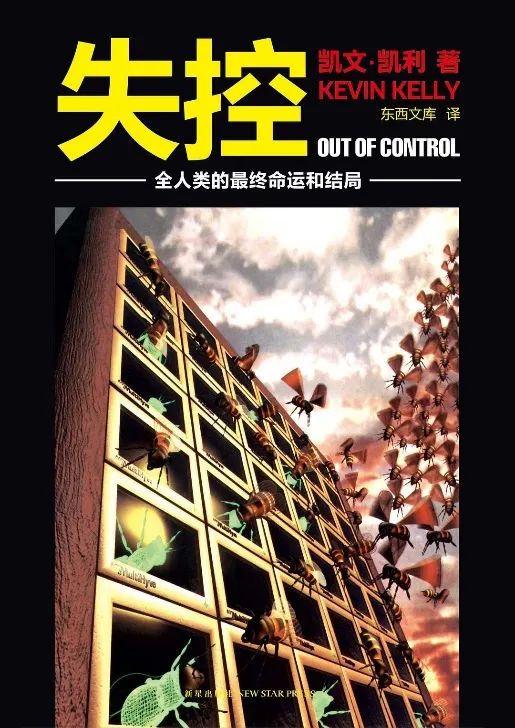
《失控》(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封面。
中国读者认识凯文·凯利,也是因为《失控》——2010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内地。彼时,中国的社交网络刚刚起步,凯文·凯利也因此赶上了走红的时机,正如他自己所说,“出现得太早或太晚都不会有这种效果”。《失控》豆瓣评分达8.6分。“微信之父”张小龙曾表示:“如果有一个大学生来面试,说他看完了这本书,我一定会录用他。”
当然,这并不是凯文·凯利与中国的唯一渊源。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二十出头的凯文·凯利便背上一部尼康马特相机,在亚洲展开了近10年的背包客旅行。最终,他用4万张照片记录了亚洲各国的文化和传统。
在中国,他拍下烟雾缭绕的黄山,也拍过白族人的笑颜。“我一直以为中国画家绘制的岩层以及云后隐藏的隐居之地,是一种浪漫的表现手法,直到亲眼见到这些景象,才知道并不夸张。”
1979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拍摄当地的复活节仪式,因为回去太晚而被关在旅馆外,只能在教堂的石板上度过一夜。醒来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设置6个月的死亡倒计时——“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做些很疯狂的事,比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去深海潜水,但最后我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陪伴家人,6个月的时间里都在做这件事。”
从那时起,家人成为凯文·凯利的生活重心。度过68岁生日的时候,他沿袭爱尔兰的古老习俗,为孩子写下了68条简短的人生建议,同时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没想到,这些建议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持续撰写这些人生建议,数量达到500条后,被集结成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
9月上旬,飞机落地还不到12小时,凯文·凯利已经准时出现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和我们聊了聊他的新书、对科技的观察和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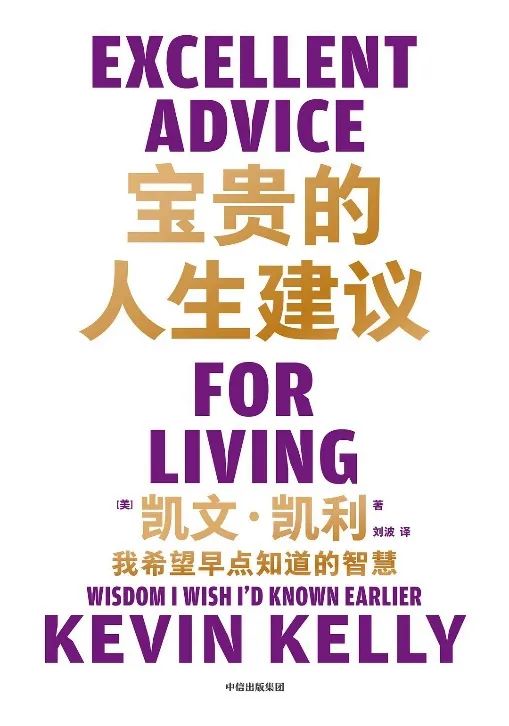
《宝贵的人生建议》(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9月版)封面。

“如果你的工作会被AI取代,
说明你做得很糟糕”
新周刊:你在中国有很多读者。在互联网上输入你的名字,会出现“互联网之父”“未来学家”这样的标签,你觉得它们准确吗?
凯文·凯利:并不都准确,我都不知道“互联网之父”这个说法从哪来的。我听过“未来学家”这个标签,我的确喜欢思考未来,但其实没有做过太多预测,我并不是要和别人打赌未来一定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试图用一种有效的方式去谈论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
比起“未来学家”,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记录者,或者像一个创意收纳袋——我自己是一个主编,经常归纳别人的想法,同时还在运营一个播客,每周都会介绍各种新兴的科技工具。
新周刊:听说《黑客帝国》剧组将《失控》列为必读书目。《黑客帝国》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符合你的想象吗?
凯文·凯利:我不认同。我觉得《黑客帝国》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背景设定——用人类给母体供电,包括其中一系列反乌托邦的情节,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乐观,并不是说盲目相信我们遇到的困境会比想象中小,而是相信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比想象中大。这不是人类想要的未来,你会想生活在这样的未来里吗?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科幻小说或者电影描绘的未来是我认可的。《星际迷航》中的情景有一点符合我的想象,但是它发生在太空,不是在地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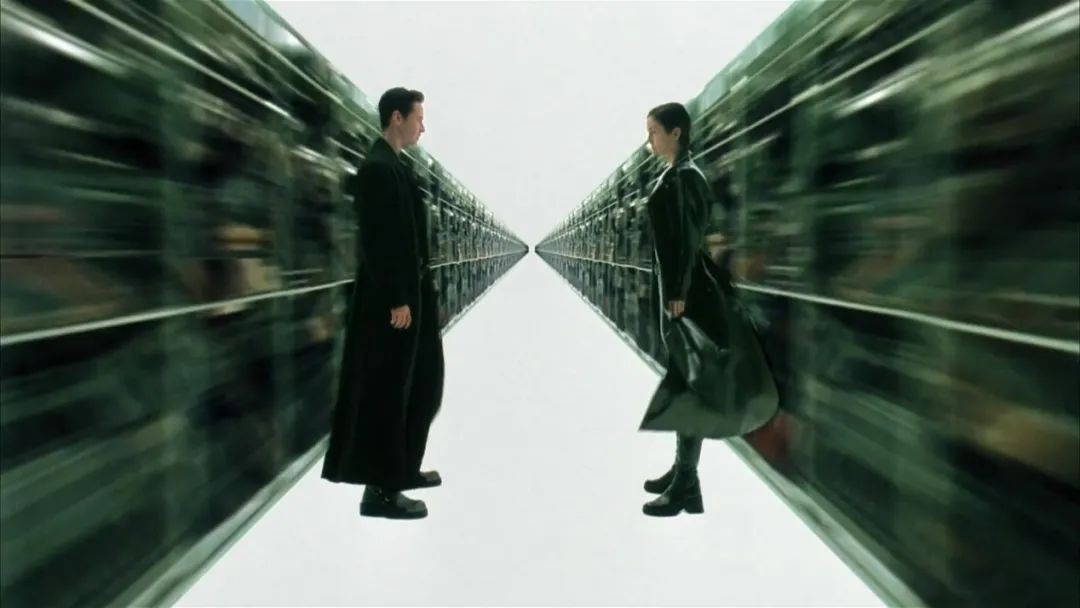
(图/《黑客帝国》截图)
新周刊: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一波AI讨论潮。你怎么看它的前景?
凯文·凯利:我现在每天都会用ChatGPT做各种事情,回答问题、提炼内容、提出建议等;还会用Midjourney和DALL-E2来创作图像。几年前我用iPad画画,现在我和AI共同创造艺术。
我觉得ChatGPT的革命性进展在于,它实现了对话的功能。如果你去谷歌搜一个东西,它会在海量内容中提取一段文字,并附上来源链接。但ChatGPT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你还弄不明白一件事情,你不需要退出页面重新检索,而是可以跟它一直对话。比如:“蝙蝠有几个肾脏?”“大一点的蝙蝠呢?”“我听说好像不是这样?”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ChatGPT也非常有价值,它是检索资料的好助手。
新周刊:有很多文字工作者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在你看来,为什么新技术的出现总会引发担忧?
凯文·凯利:我只能说,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被ChatGPT取代,那你一定是个糟糕的作家,因为它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是平庸而已,还谈不上优秀。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具体哪一个人是因为AI而失业的,我只听说过有人用AI做一些重复性较高的工作、生成体育赛事比分这类的快讯报道。大部分时候,人们只是想象其他人被AI解雇,而不是自己。
我的朋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所担忧的“科技”,其实是在自己出生之后发明的任何东西。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我理解人们对科技的担忧,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尽管人们总是将作出改变挂在嘴上,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欢作出改变。
大多数人不喜欢改变,因为这需要付出努力——你有成形的观点、固定的习惯,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你需要改变想法,而这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如果你习惯了在路边拦一辆出租车,现在出门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学习如何使用优步打车,看上去的确很麻烦。当ChatGPT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我要继续用谷歌,我不需要改变”。
我现在还是习惯使用现金支付,对于外国人来说,用微信或者支付宝进行电子支付的确很难。但是,当你真正学会一些东西,你会明白这样更好。

“世界互联网将融为一体”
新周刊:很多人相信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奥本海默》导演诺兰在中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科学家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的……如果他们不建造这个装置,纳粹将建造它并且会用它对付他们”,并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你怎么看?
凯文·凯利:我在《必然》中谈到过这个话题。大部分科技在当下的环境里是必然会诞生的,比如说人工智能一定会出现;但具体到谁拥有这项科技、谁将它进行国际化推广,以及它面向公众开放还是关闭,这些不是必然的因素。
《奥本海默》中的情景也一样。我觉得,核科技的进展未必会在一声巨响的爆炸中结束。在不同的世界和历史中,我们仍然会发明原子弹并且证明它有效,但是把它扔出去还是用于政治博弈,是不同的选择,大家可能最终达成一致,决定永远不使用它。
银河系中的任何行星文明都可能发现核能、用核能研发原子弹,但不是每个文明都必须部署它。我说过,最邪恶的事情,反而往往是认为自己在与邪恶斗争的人做出来的,像纳粹真的觉得自己在“消除邪恶”,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试图消除邪恶,要谨慎行动。

(图/《奥本海默》)
新周刊:社交媒体的出现,会加剧社会原子化和信息茧房出现吗?马斯克说要限制推特用户的使用时长,让他们多陪陪家人。
凯文·凯利:首先,你可以无视马斯克的言论,那些话看看就好。但我觉得大家高估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我不认为它会导致严重后果。
有很多人担心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但我觉得,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会好奇和痴迷某件事情,你很难把教育的责任归咎于某个科技或者年轻人使用它的频率上。你可能会建议孩子缩短看手机屏幕的时间,但这轮不到政府或者企业来做。
当然,我认为信息茧房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观点会更好,就像美国人可以看《环球时报》,中国人的新闻也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一样。你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类似的、收集了各国主要出版物的新闻网站,在一个页面上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我觉得,如果你想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或观点,并没有想象中难。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你曾经有一个观察:中国互联网从照搬国外的商业模式,进化到了如今开始实现自主创新。但未来还要培养一种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文化基因,即宽容、容忍失败和质疑权威。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凯文·凯利:通过多年的观察所得吧。我和中国读者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会更关注事业的发展,比如应该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把事情做成功等。很多中国青年企业家在美国学习、交流过,有人选择留在硅谷,有人选择回到中国创业——同样的人接触同一种文化,会产生不同的选择,所以这个结论也不是绝对的。
当然,中国的科技发展的确迅速。我看好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前景,我觉得中国人会做出性价比更高的电动车,比特斯拉好。此外,我也有听同行讨论过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它在业内做到了顶尖水平。

大疆运载无人机。(图/dji.com)
至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喜欢用一个App实现所有功能,在互联网构建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美国的互联网形式则更加自由,竞争也很激烈。我觉得有竞争是好事,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世界互联网将融为一体,如果20年后你告诉我还有两个独立、平行的互联网存在,我会很惊讶的。
我认为互联网也需要一定的监管,但是不宜过早,应该晚点再出现。毕竟它依旧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对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还没有足够到开始监管的地步,对吧?

“我也有不听劝的时候”
新周刊:你在新书中一共写了500条人生建议,其中有不少是你希望自己年轻时能早点明白的道理。你还记得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建议吗?
凯文·凯利:我不太记得了。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我10岁左右学到的第一个道理:如果有人要拿走你的夹克,你就把自己的衬衫也给他,再多给他们一些;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应该转身让他们打你的左脸。这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宽恕吧。
新周刊:你的每条建议都尽可能压缩在140字以内,像原推特那样,为什么这么做?
凯文·凯利:当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大部分都不是书本,而是推特、微信等社交媒介。我希望自己的建议被尽可能多的人看到并记住,这也意味着它们要以更容易被转发的形式呈现,变成一段段简短的文字后,如果你喜欢其中一条,就可以马上发给别人。长文很难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会越来越碎片化,你很难看到它们的全貌。
同样,我认为一个作家未来也不仅仅是写书,还要学会制作短视频。我也在学习制作视频,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YouTube网红,哈哈。
新周刊:很多人喜欢向他人寻求建议,也有很多人觉得“听完了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你有过不听劝的经历吗?
凯文·凯利:有。我年轻的时候,不太相信乐观这件事情,或者说很难去想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觉得去想这些事情没有意义。但现在我的观点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相信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发生,才是实现它们的第一步,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经验和教训,确实要等年轻人自己试错之后才能更好地体会,但你也可以避免犯一些别人犯过的错误,两者并不冲突。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可以一边学习过来人的教训和经验,一边自己去发现新的智慧和道理。

年轻时的凯文·凯利(左)与弟弟在登上珠穆朗玛峰5550米处时合影留念。(图/@Vanishing Asia)

“中国现代化的速度难以置信”
新周刊:你提了很多有趣的建议,比如说有机会要去最遥远的城市和地区旅行,还有在年轻的时候花6个月时间体验低成本生活。这与你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吗?
凯文·凯利:是的。不仅仅是旅行,我年轻的时候在条件艰苦的地方长期生活过,住在一个狭小的单间里,每天只吃燕麦片和米饭。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我平时也会去徒步旅行或者露营,要把所有东西都背在身上,这会迫使你去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用来生存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你在以后的冒险和尝试中,会有一份安全感和底气。比方说你得到初创公司的一份工作,这意味着你有可能创业失败、一无所有,但你知道自己会没事的——最糟糕的情况,大不了就是回去吃米饭,对吧?
我鼓励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去旅行,去不同的地方生活两年,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里,事物是如何运作的;面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2021年,凯文·凯利为自己的旅游画册《Vanishing Asia》展开众筹。(图/@Vanishing Asia)
新周刊:你确实喜欢旅行,1970年代就走遍了亚洲。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发展起来,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凯文·凯利:语言隔阂是很大的问题。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人会说英语,我的日语也很差,所以沟通起来非常麻烦,一方面靠手语,另一方面尝试用英语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他们看。现在情况好多了,在亚洲,很多地方的路牌上有英文,在火车站、邮局之类的地方都有工作人员会说英语。
以前信息匮乏,关于一些偏远地区的资料很少,你去之前甚至没有详细的地图,也没有关于当地餐馆或者景点的评价,更不可能提前预订旅馆。你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大多数时候是真正地四处游历,临时决定下一站要去哪儿。
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们更习惯于在网络上制定行程计划,提前订好酒店和机票。虽然大家掌握了更多信息,却也少了随心所欲地探索一个地方的乐趣,不会有即兴旅行,有得必有失吧。
新周刊:你来过中国很多次,有没有感受到比较大的变化?
凯文·凯利:我第一次来中国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带着两个女儿从广州坐大巴去桂林,再去昆明等地方旅行。我们坐了整整一天的大巴,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太辽阔了,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地区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异,部分城镇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村庄模样,一些农户在田里耕作,而有些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未来主义。
后来我和家人一起重返丽江,那里和我最初看到的模样相比,已经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变得现代化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确实难以置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高速铁路网络。

1990年代,凯文·凯利途经茶马古道时拍到的一幕。(图/@Vanishing Asia)

“不要做最好的一个,
要做唯一的一个”
新周刊:书中还有多少建议源于你的亲身经历?
凯文·凯利:基本都是。我写建议的时候遵循一个准则,就是它必须能准确地代表我的想法、价值观和经历。大部分建议来自我的经验,有些别人说过的话,我亲身验证过、明白这个道理,也会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体会,放到书里。
有一条建议是:“不要做最好的一个,要做唯一的一个。”根据我对成功人士的观察,他们往往是在无人涉足的领域取得成功——就像我喜欢的音乐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他创造了“氛围音乐”这个概念,当时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
一旦你想和别人竞争,比如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会计师,你就会发现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太可能成为第一名,因为第一名只能有一个。我的建议是,与其和别人竞争,不如去尝试没人玩过的游戏。

凯文·凯利说,与其说自己是未来学家,不如说像一个“创意收纳袋”。(图/kk.org)
新周刊:你有一条建议:人们应该趁父母在世的时候,用录音软件去采访他们,再把它变成个人史、纪录片或自传。你自己在这么做吗?
凯文·凯利:是的,我采访过自己的父母,这很有趣。你以为你了解自己的父母,但其实你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如果我不做这次采访,我永远不会知道父母还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故事。
现在你甚至不用自己操作全部流程。我有一个助理是墨西哥移民,她雇佣了一家专业公司来拍摄剪辑,花几个小时坐下来聊聊她父母的故事,最终做成纪录片,送给她的父母做礼物。
其实人们一直等着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们有倾诉欲,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故事。一旦你问他们,他们就会开口讲述,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多么波澜壮阔,而这会给双方带来力量。
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是在30岁左右做这个事情的,先采访了我父亲,从一些简单的问题问起,比如:你在哪里出生?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你所在的社区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和你的朋友呢?
就从这些问题开始,然后一直问更多问题。如果你有兄弟姐妹,还可以让他们从另一个视角谈谈自己的感受,比如他怎么看待家庭中发生的一件大事?最好的问题是:请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事)。
校对:邹蔚昀,运营:小野,排版:付赢
原标题:《不是所有科技,都会走向“《奥本海默》式”结局》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