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兴对谈袁长庚:了解死亡,是为了有意义地过完这一生|涟漪效应

过去三年,医学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显得格外突出。
人终究要面临生老病死,是否有一种预防措施,能让我们学会更好地面对自己或亲人的疾病,甚至是死亡呢?孔子有句话“未知生,焉知死”,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聊聊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老病死”。
以下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或【点击此处前往小宇宙App收听】,效果更佳。
王兴
北京大学肿瘤学博士。先后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博士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已出版作品有《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怪医笔记》《癌症病人怎么吃》《胸腺外科学》(英文版)等。
袁长庚
人类学者,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2016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译有《城市里的陌生人》《大房子,小天堂》(即将出版)等。
【本期主播】
吴筱慧
澎湃新闻·镜相栏目编辑
【收听指南】
02:30 医生眼中的死亡,人类学家眼中的死亡
08:39 理解死亡会让我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吗?
23:30 我们人类的生命很多时候是由荒诞性构成的
28:31 人的感性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
37:12 为什么中国是医患矛盾高发的国家
43:23 更安全的人生策略是什么?
45:55 年轻人谈论死亡是否为时过早
55:18 走向医学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解自己的过程
57:23 大家一起表演一场葬礼
01:01:45 为什么说死亡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01:06:20 怎么样才算是完成了哀悼这件事
01:11:41 50 后和 60 后走向衰老甚至是走向死亡,会非常孤独
01:16:32 如何做好临终关怀这件事?
01:22:20 四种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01:26:48 医生与人类学者的互相答疑环节
01:38:47 听友提问环节
【本期书单】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王兴
《最好的告别》阿图·葛文德
《乡土中国》费孝通
《疫苗的故事》保罗·奥菲特
《打开一颗心》斯蒂芬·韦斯塔比
《说吧,记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本期配乐】
Keegan DeWitt - Nothing Shows
José González - Stay A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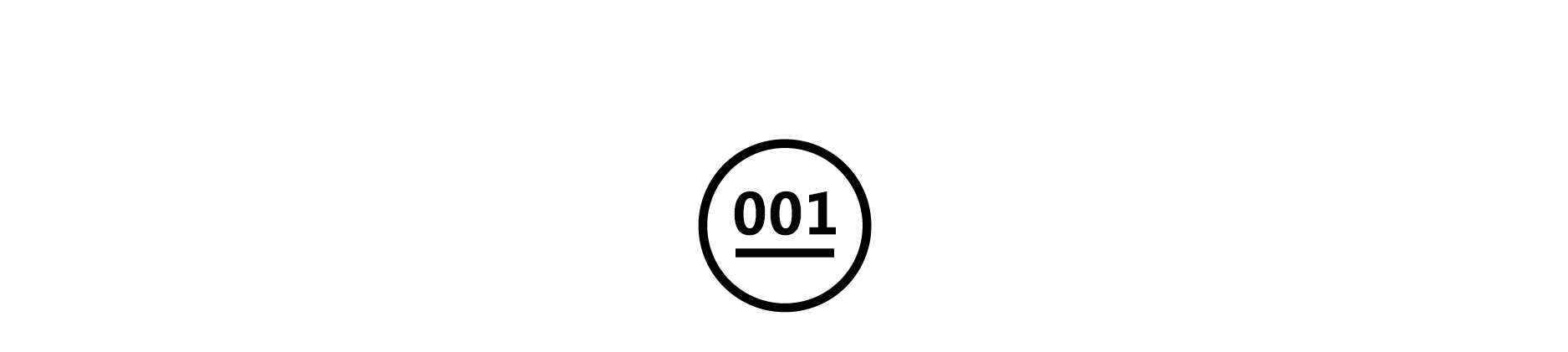
处置死亡,一块缺失的拼图
吴筱慧
我们知道医生每天都会面临无数的死亡,那么王兴医生,您眼中的死亡是什么样?从医生角度,处置死亡是什么样的流程?另外您之前在采访中还提到过“真实的困境,大都被隔在了医院院墙之外”能否跟我们讲讲医院之外的困境有哪些?
王兴
人从生到死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解剖标本,也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像同一列火车上的人心率血压没有了,然后呼吸没有了。人走了那之后我们还会跟护士一起做一些简单的尸体的护理,像一些粘球,像一些这个缝针会去除,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感觉,原来人走是这个样子的。而我们跟家属的交流当中,才感觉到原来家属在病人离世的最后的一天,一个小时之内是这么一个状态,它是一种脱离了悲痛的,会完全陷入一种事务性的错乱。
那为什么我说很多关于死亡的探讨会隔离在这个医院的院墙之外,就是像昨天也有一位老师会请教我,他父亲的临终还有两个月,问我怎么办,会发现普通人在家人可能离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一方面缺失的是像袁老师这样的学者,告诉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置,共同去思考。另外一种层面是在流程上、手续上,我们好像在死亡这一块就缺了一块,我们有这么多的月子中心、有这么多的幼儿园,告诉我们怎么去迎接一个生命,怎么去让一个生命从无到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从有到无的这个过程,似乎就是都是由我们每个家里人、每个普通人用一些千奇百怪的方法把它给渡过去了,但它缺乏一种让我们觉得舒适的、有安全感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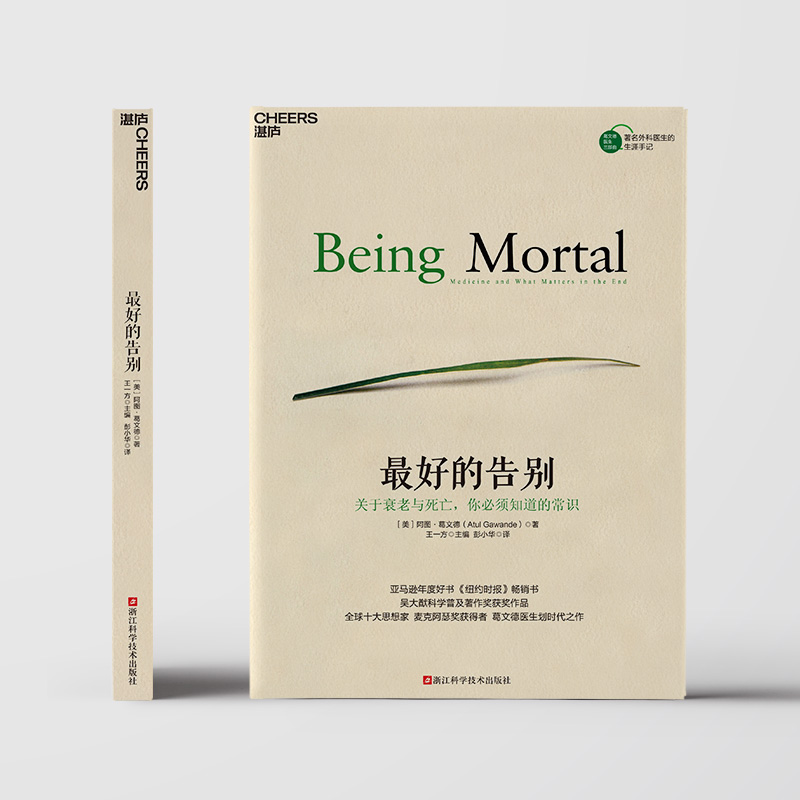
《最好的告别》
吴筱慧
记得美国的葛文德医生有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这本书里说“你不要觉得死亡这件事情,只跟我们最后这一刻有关系。”袁老师之前也说自己特别同意葛文德医生的观点,那么您怎么看王兴医生提到的这个情况,另外作为人类学者,我们也想知道您眼中的死亡是什么样的?
袁长庚
现代医学发达以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最后是在医学干预的过程当中走向死亡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已经理解了,死亡不只是最后生命体征正式消失的那一刻,可能还包括整个就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人的死亡在生理性的生命终结之后,其实社会意义上的生命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留下很多的社会关系,留下很多的牵绊。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有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用一种比较妥当的方式讲述他的离开,他的死亡才能够暂时告以终结。

寻梦环游记 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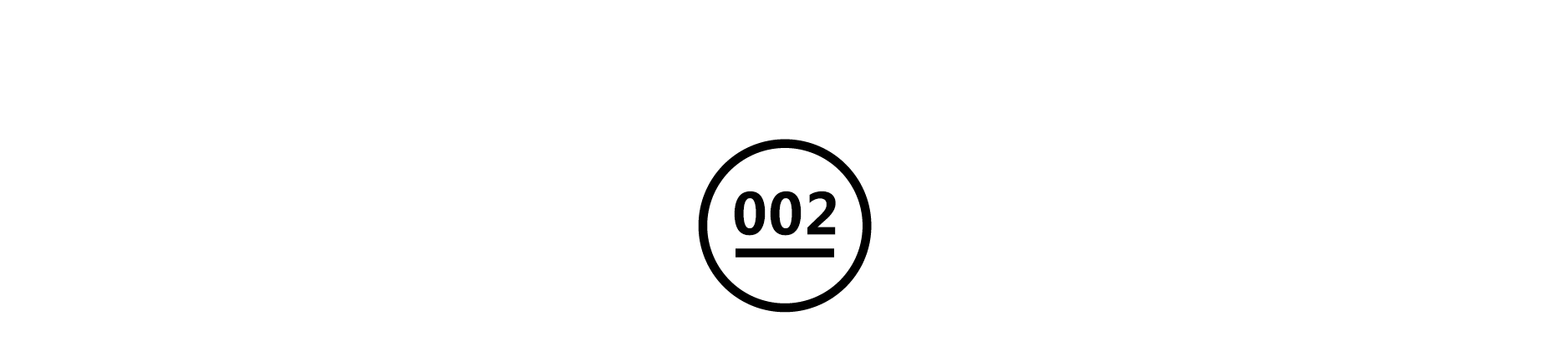
死亡是可以习得的,就像习得怎么去生活,怎么去繁衍一样
吴筱慧
大部分人对死亡的恐惧都源于未知,两位觉得“理解死亡”能让我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吗? 或者说这是可以克服的恐惧吗?
王兴
很多人会在这个家人的离世当中习得一种死亡,就像我们习得怎么去生活,怎么去繁衍一样,它是一种可以习得的,看别人的临终会推测自己的临终。所以像有一句话:父母是我们跟死亡之间的一道窗帘。每走一个至亲,我们就离死亡就更近了一步,或者就更清晰地看到了死亡的模样。那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有两个方向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个是我们认识死亡,接触死亡之后,慢慢地就会理解死亡,而不是说我们要克服恐惧。
第二就是不要去戏谑死亡,不要默认为自己就是一种心很大的状态,因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你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不要压抑自己,就是释放。
袁长庚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就谈到说我有这种死亡恐惧,那是不是通过学习知识的方式我就会降低这种恐惧。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种最大的误解,这个其实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很常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其实非常相信知识的力量,比如说是不是我学习理解死亡这门课,那我知识上一旦储备完整了,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击败它。
首先我觉得对死亡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在知识上完全地覆盖它,不管你从医学的角度,还是从哲学、历史、宗教的角度,因为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没有真正经历过死亡的经验,穿越死亡的经验。第二个,实际上知识本身在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就是非常无用的,你回顾自己的一生,你自己的重要的转变,重要的抉择,很多时候它不是知识完成的,很多时候就是你的价值上的偏执,甚至是你情绪上的冲动,帮助你完成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也成就了你的人生。
……比如说医生觉得这个人回天乏术了,经常让家人把他带走,就是回到家里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其实不太理解这句话的社会学的含义,在生死学上讲,只要这个人的生命体征没结束,他就是一个活人,他不是一个死人。实际上就是让他在最后的时间段里,尽可能地按照一个活人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告诉他你自己曾经对他的某些事情的开心或者是不满,或者问他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生命,我们把他当成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从医生的角度而言,他最后不适合吃冰淇淋,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他是个活着的人,他有权利吃他想吃的任何东西。因为最后这段时间那一点点的干预已经不对他的医学上的结果构成影响,但是会对他作为一个活人这件事情有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是通过学习知识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忧虑,死亡带来的痛苦永远不会解除,但是我们可以死亡为契机,重申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就是人的意义。
王兴
所以为什么我会鼓励很多医生也去读书,不是说非要去写书,我们要去读点书,比如像《乡土中国》这种书,就能够帮助很多医生理解病人深层次的诉求,它不是表面的说钱治好这个关系,而是我怎么给这个病人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出路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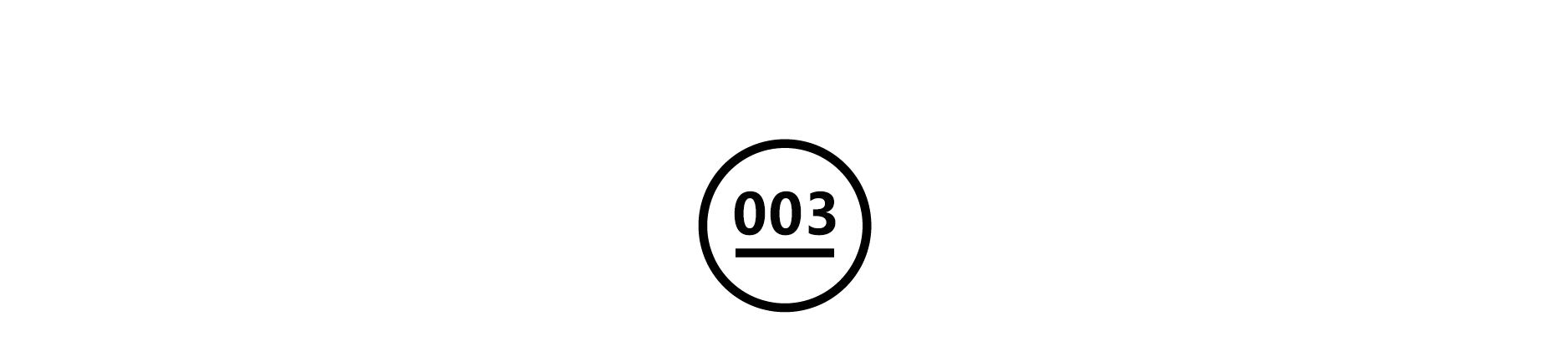
在死亡这件事情上,看到一个社会的基本底色
吴筱慧
袁老师您之前在南方科大每年都会开设“理解死亡”课程,您觉得中国的文化背景对我们如何看待死亡,有哪些影响?在我们国家谈死亡教育,您遇到过哪些的困境?
袁长庚
其实我们整个医学人类学里面研究过很多,比如中国语境里面讲,烧纸这些事情就很重要。我记得在广州听一个我们的医学人类学的前辈做研究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意思,他说广州一些很好的医生,都有一个经验,因为岭南的风俗是说必须要离他这个离世的地点近一点最好,比如说在病房里烧纸才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成熟的医生会给你很多方案,比如说医院的后门街角可能管得比较松——成熟的医生,会知道很多这样方面的建议。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医生比较冷漠,对我们家是天塌下来的事情,结果你们转手之后就又去下一台手术,我觉得这其实是医学的壮美所在,从医者的第一品质就是必须要勇敢,在目睹离世死亡之后,马上就要转变观念——我经历了死亡,但是我依然对救活下一个病人有信心。所以他是没有空间像我们一样坐下来去咀嚼具体死亡带来的悲喜。
其实在死亡这件事情上是最能看到一个社会的基本的底色,就是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在乎的是什么?重视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家属或者是身边的人,特别想寻求一个答案。我们人类的生命很多时候是由荒诞性构成的,我记得以前看葛文德写过说80岁以上离世的人,你如果给他做病理解剖的话,会发现他身上可能同时有十几种病,每一种病都比他最后离世的原因更危险,但是他却没有死在这些严重的病上,他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
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一是没有办法接受人的复杂性,第二就是对人生命底色里面的一些荒诞性的不确定,我们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做好准备的,这也是死亡教育或者死亡讨论在目前比较难以展开的原因,它触及到的是我们整个的认知和心理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缺的不是谈论这些东西的知识或者是技术储备,而是大家先尝试一下走进那个谈话的场域,这些现在相对而言都还比较奢侈。

豪斯医生 第七季 剧照
王兴
刚刚袁老师说有一种语境,一种氛围,我感受很深,像有的患者告诉他一个答案,你有三个肺结节,他会很焦虑,我下面怎么办呀?要不要切呀?怎么观察会不会长大呀?一系列问题全来了。然后你告诉他下一个答案,有10%的概率可能变成癌,90% 不会有问题,他又开始焦虑,那我会不会是那10%?那我会不会就是那个倒霉蛋?但是,如果你告诉他,外面前面那个病人有8个结节,再前面那个人有18个结节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舒服,会觉得自己是最轻的那一个,有一种共同处于某种环境的感觉,反而就没有那么的焦虑紧张,也不需要某种答案了。
吴筱慧
用他人的焦虑缓解自己的焦虑。那袁老师刚刚说,其实我们走进那样的语境、那样的场域以后,好多问题就能缓解。在乡村人们也有种习惯,早早把自己的棺木放在家里,大家都知道那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死亡也是一场众人参与的仪式,村里的人会围在一起谈论这个人生前的种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人和这个世界的关联,死亡不是突然的消逝。但在现代社会,死亡这个词似乎变得遥远了,一个生命的结束意味着被拉去殡仪馆火化以及一场小型的追悼会,这个过程让死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隐蔽,也让死亡离我们更遥远。记得您之前也说死亡课最初设想过要带学生去墓地、医院这样和死亡相关的场所,到场景中去实践。那这样亲临现场的实践,如果能实施的话,您觉得会给死亡教育带来什么?
袁长庚
这个不是我自己的独创,我看了很多国外生死教育的材料,我后来理解其实大家就是一个目的:不断创造场景,让大家练习。我以前上课的时候经常跟学生讲,对于你们而言,有一点是很好理解的,比如说人的理性思维和人的数理能力是需要通过锻炼的。你做数学题、物理题,就是为了锻炼自己。但是我说你们经常忘了一个事情,人的感性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比如说悲伤这种能力,比如说爱的能力,这是需要锻炼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死教育这件事情,不是说老师掌握了一个道理,要让学生知道这个道理,最成功的教育应该是不断地创设场景,你要让学生自主地走过去,要他明白这个走过去的过程是什么。以前有句话,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但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是因为那个道理你从来没有把它激活过。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很多的人是通过自己父母的死亡才开始理解这个事,因为你自己在操办的过程当中,亲身演练了一遍,有些东西就变成了你人生的素材。
王兴
像疫苗的原理一样,用灭活的病毒先给你来一套,产生了一种免疫,再去面对自己真实的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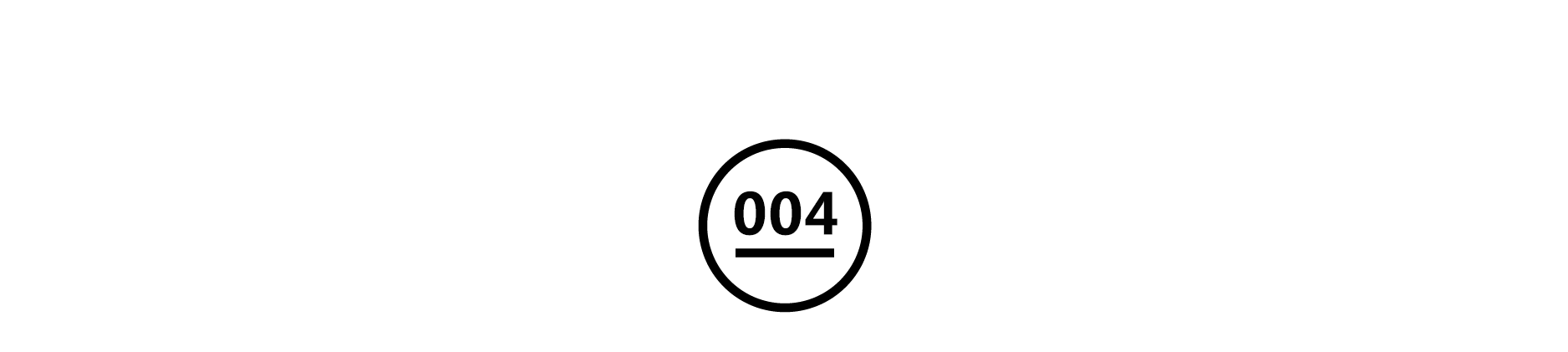
越是在压力的年代,我们越应该慢慢地张开自己
吴筱慧
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面对死亡的经历,王兴医生说我们是通过亲人的死亡、他人的死亡来习得怎么面对死亡。袁老师也说可能死亡教育也是需要激活的。那么习得之后、激活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其实压力都非常大,两位觉得在当下的环境里,死亡教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袁长庚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延展死亡的概念,死亡不是最后生命体征终结的那一刻。以前我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个比较直接的挑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的孩子,他从小接受的其实是优胜教育,就是我要在考试当中取得很好的成绩战胜其他人,我就在整个高考序列里面站在前排。那其实死亡教育有一点是重要的,你要告诉他,人生的挫败感,荒诞无意义,它就是一个不能祛除的东西。 我们人的所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其实是一体的,我们身上的很多创造力的部分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我们身上有很多脆弱的,甚至残缺的部分也很难解释。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整个社会的发展,包括普通人的梦想,一直都是过得更好,要战胜困难,要克服困难。但是可能我们慢慢要学会一个东西,就是你要跟困难共处,你要跟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共处,那其实这个共处的过程往往就打开人生另外一个可能性,你会接受另外一个自己,你会接受另外一种状态,其实这种平和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实际上就是要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面相联系起来,它非但不应该变成一个特殊教育,它应该变成一个长期谈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极限,我们所有人的困境在哪。
王兴
其实像袁老师刚刚讲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机会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年轻人这个场合谈论的,因为有一点好处是我们毕竟离得远,我们可以先了解习得、在氛围里感受,可以像数学刷题一样,我们去训练某种直觉、感知和感性的这样一个力量。如果最后告别的那个时刻,你才突然间开始拿一本《病人家属》开始去学习怎么叫做家属,其实有点狼狈。如果早接触一些,可能那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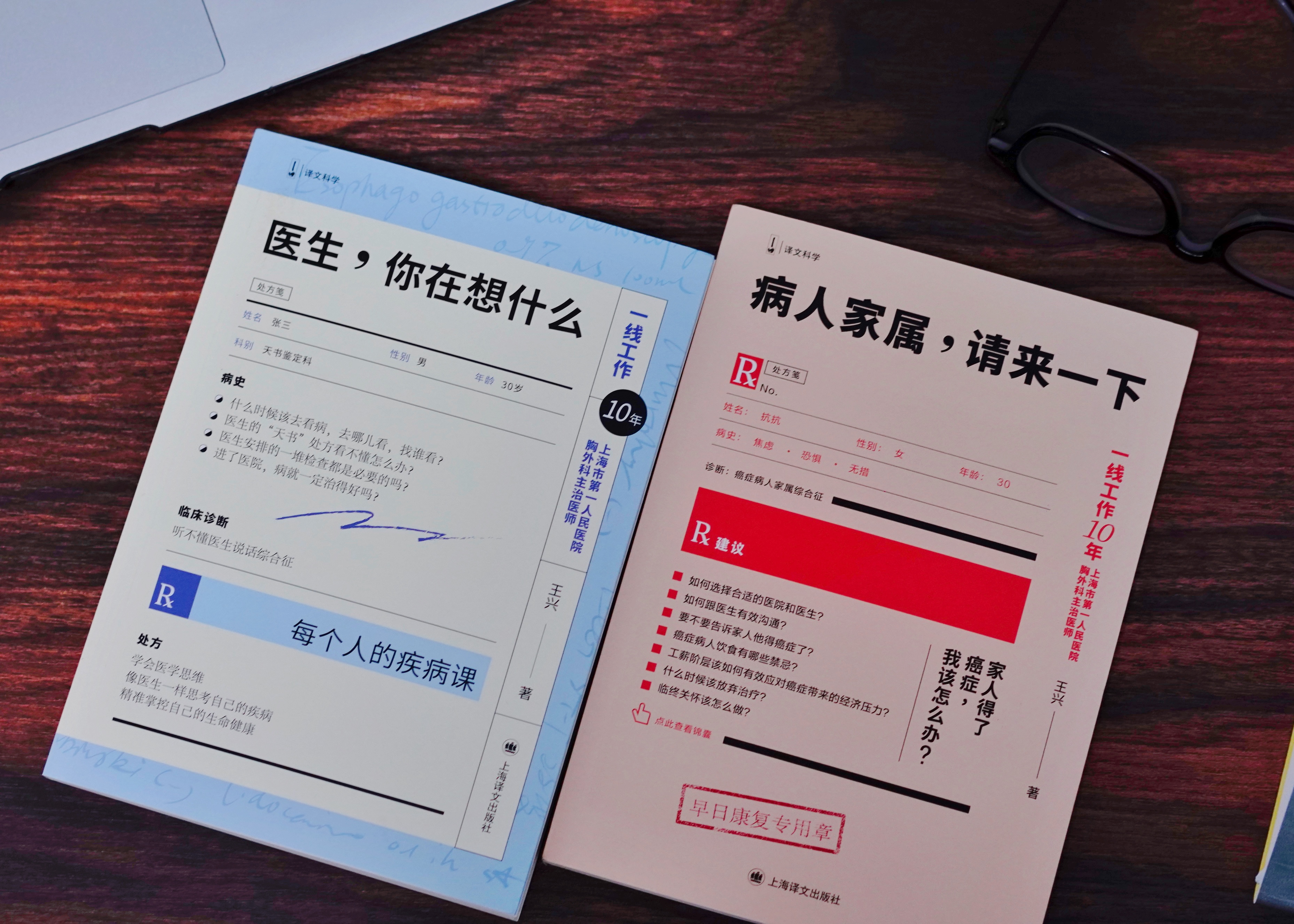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吴筱慧
之前我们在采访张秋子老师的时候,她提到说很多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可能从小到大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对于生活的操控感,然后他会觉得我怎么来控制我的人生,步步为营,走向下一步的人生巅峰。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聊过虚无或者死亡的话题,那么可能当这些孩子突然间接触到了这样的话题,他会发现和以前对人生的理解、生活的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会崩溃。袁老师之前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死亡课程的时候,觉得死亡教育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哪些影响?另外,两位怎么看待失控感这个问题?
袁长庚
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问题,我们最该感谢的是高考,但我们最该憎恨的也是高考。因为高考在很大一个程度上讲它既是一个保命仙丹,18岁之前人生有无比清晰的目标,而且它其实是有路径,有技术可以做到的,所以你其实在18岁之前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但是实际上高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你整个青春期里面积累的很多问题,家庭的、社会的,有些时候跟你的性别、所在地域有关的这些问题,全部都打包放在一起,然后等到你进入大学,自己面对一日三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是个成年人,以前那个包住问题的包袱就会散开。在散开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是个概率问题,有些人可能没那么严重,不会受到那么大冲击,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人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会突然一下面对很多问题同时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方法,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风犬少年的天空 剧照
王兴
关于失控感这个问题,其实刚刚这个袁老师讲的我能感同身受,我觉得像年轻人从上学到高考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做选择的机会不是很多,只有到了大学才会发现有这么多我可以做选择的点,那选什么可能都会错,所以这种失控感还是从大学开始逐渐显现的,工作之后就更暴露出来了,那像死亡也是一个无法掌控的事情,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就突然会面对死亡。像我们经常说中国人一生当中患癌的概率是30%,在年轻人到了30岁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他的父母一般是在60岁左右,进入了一个癌症高发的年龄段,所以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刚工作的时候有1/ 3的家庭突然间面临癌症的问题,另外1/ 3可能还有一些心梗、脑梗的问题。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从概率上讲是确定的,是确定有30% - 50%的人,在30岁这一年一切都很顺畅的时候,突然间遭遇家人或自己的离世或者重病。那这个确定性如果你知道的话,其实就应该早点去铺垫一种对死亡的理解、感知和想象。你不能作为一个侥幸心理说我不太可能碰到这些事情,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我们在主观上抛弃了很多明明确定的事情,而假想它不存在而已。
袁长庚
我以前在课上说过一个比较绝对的话,我说你看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都在处理死亡问题,人类是会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思考自己人生意义的延续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人越来越恐惧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切都是物质的,那我去世了以后真的就不存在了,那我怎么解决意义延续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能是需要重建一些东西,比如说横向延展,我们有其他的比如你跟这个社会的联系。
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当年轻人感觉到外部压力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会缩小自己的范围,这其实是心理学上一个很容易解释的问题,就是我缩小自己的范围,我专注于我眼下的生活,然后我甚至跟我的父母、跟我的亲人、跟我的朋友、同学之间都不会那么亲切,因为我暴露自己就有危险,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从长远来看是更危险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要自己解决你人生当中的所有问题,而这个问题,从人类经验的角度而言,100%是不会成立的,你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多么强,无论你到什么程度。
所以其实越是在所谓一个感觉到压力的年代,我们所有人越应该慢慢地张开自己,不是说让你去牺牲,或者是让你去无谓的奉献,而是你要更多地尝试建立跟这个世界的联系。看起来可能是会让你疲倦,但是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更安全的人生策略。 至少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能看到的相对比较成熟的人类经验都在告诉你说,不要怕把自己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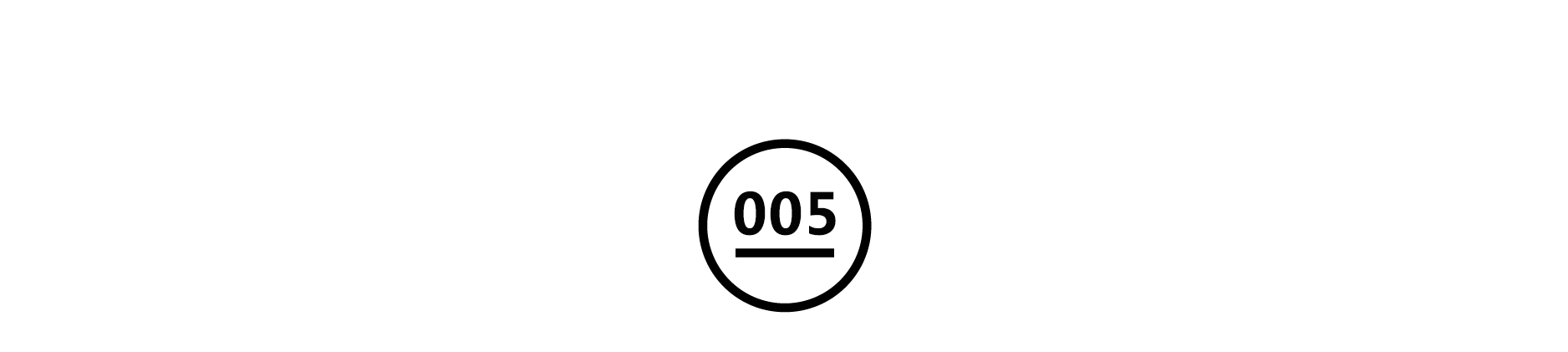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跟医学对话去理解自己的生命
吴筱慧
我在看《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的时候,里面你说曾经和一个人生赢家的大叔聊过,他当时50岁出头,晚期的结肠癌,在病床前陪伴他的妻子才 20 多岁,你就问他说现在最怕什么?他说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不是这辈子挣了钱没花完,也不是娶了个年轻的太太遭人指指点点,他最无奈的事情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记得他自己的原话是,“就好像我坐在一艘小船上,有人告诉我前面有瀑布,我想办法也不可能上岸,但我不知道这个瀑布到底有多远,如果还有10秒钟,我就抬头看看天空,如果还有10小时,我就先吃块面包,不要饿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也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会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遥远。两位老师觉得像这种尚未知道自己在哪里和考虑死亡这两件事情之间有冲突吗?
王兴
当时写那段话主要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想让你告诉一个答案,他才好更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医生有时候也没法给你一个大致的答案,你很有可能两年、三年、五年都活着,也有可能下周突然间就突然爆发一个肺炎,人就没了,这种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是让我们最难办的,也最难处理跟死亡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这也恰恰不是由医生能够解决的,像袁老师这样的人类学者才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心理上的小工具,让我们能够去理解,在任何一种状态下,无论是还要多久,我们都可以有一套心理的应对机制,或者通过感知氛围的办法去解决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感。人的死亡通常都是断崖式的、爆发式的,这种死亡非常难以去预测。所以你要理解这种无常性,才能把很多的准备提前给做好。

遗愿清单 剧照
袁长庚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其实谁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过了这一辈子里面的某一天,某一个月,或者是某一年,都不能让我坐下来静静地说我已经接受了这辈子还可以的话,那为什么它未来的那几天就会让这个局面发生扭转呢?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这样,你的生活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单位构成的,我们很少有人一辈子有机会做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真正意义上讲,对外交代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要求你把那个最基本的单位拿出来衡量一下这个单位是不是成立。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不是靠大的意义来填充的,是靠每个小的细节来填充的。我以前也觉得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这件事情有些太绝对了,但我后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释,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都讲不清楚,说不清楚你怎么去进入对死亡的讨论,怎么去进入对死亡的思辨?是不可能的。因为死亡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赋值,它来源于整个生命体、生命过程、生命意义的这种确立。
在这个问题上讲,你应该先问自己,人其实往回看看自己的一生,从小尺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你不可能指望医生给你这个答案。因为西方医学在今天有很多时候也是尝试性的、试探性的,没有哪个医生会过去说你这个,我们就直接开刀拿了就完了。很多时候是试探性的,要做检查,要做对话。不是说我们开刀这件事情就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有些时候你不体验你不经历是不能理解自己肉身的脆弱性的。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是说我们要通过西方医学去无谓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通过跟医学对话去理解自己的生命,否则的话你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真正感受到你这副肉身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没有单纯意义上的死亡教育,死亡教育一定是连通着生命教育,因为死亡只是最后的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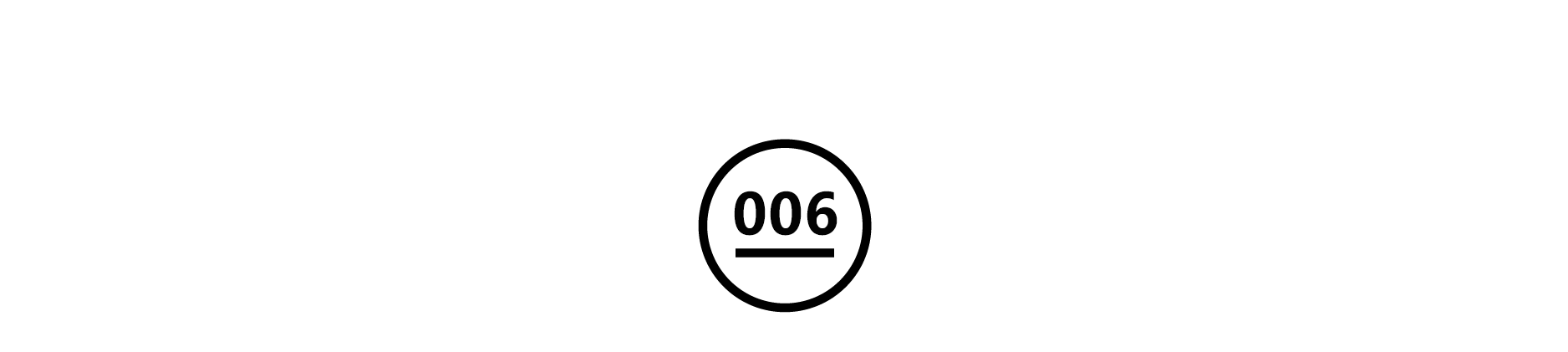
对大多数人而言,讲述自己是个很奢侈的机会
吴筱慧
袁老师您之前在理解死亡课程结束的时候布置过一份特别的作业,让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设计故事场景,大家一起表演一场葬礼,这种表演形式听起来很有意思。想问一下通过这样的表演形式,最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或者对学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袁长庚
我自己当时的一个感觉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的年代,社交媒体、移动终端都很方便,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大多数人而言,讲述自己是个很奢侈的机会。当时设计这个环节就想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拉近双方,要么你去主动走近一个人,要么你被别人这么主动地走近。实际上就是把教室变成追悼会的现场。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对很多同学而言,它非常非常有震撼性。有一个学生后来跟我讲,因为他是计算机系的,那几年正好又是深圳计算机专业最好就业、最舒服的时候。但是他实习完了回来非常难受,他当时有另外一个机会,可以去中学里面教计算机的课程,他一直觉得这个工作有意义,但是很难说服自己放弃这么大的一个诱惑。他扮演那个死去的同学,躺在教室中间,灯也黑了,大家在那纪念他,他说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的决定,躺在那的那一刻,就想一件事情,他说他也不能完全讲出来就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他突然有一个意识,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交代,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干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死亡诗社 剧照
吴筱慧
之前看过袁老师的一些采访,您在开这门理解死亡课之前,其实就开始了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而且您曾经形容过“无处讲述亲人逝去的悲伤,就像掐住脖子一样”。然后您读了人类学,开始关注和死亡相关的研究,那个时候您才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中,哀悼这件事情没有完成过。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亲人过世后其实都觉得没有完成哀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都有一种“脖子被掐住一样”悲伤无处讲述的感觉。那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您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完成了哀悼?
袁长庚
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其实是更困难的,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充分哀悼这个事情,它需要整个社会,留一些基本的口径。
我以前读过一个最极端的材料,马达加斯加的民族志的材料,里面讲马来加东海岸有一个族群,他们其实跟中国人很像,有一个家族墓地,尤其是那种从一个地方迁来的一家人,他们很注意所有的死去的亲人都葬在一起,墓地越大,越象征着你的祖先的繁盛,所以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习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很恶心的,就是他们每隔五年会把棺木起开,把尸体拿出来,而且他还不只是拿出来,因为他们下葬时候是用布裹着了,他们是要把这个布打开以后重新洗这个腐尸。有些时候那个几乎就是一摊泥了,但是他们每五年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这是个节日,他们在清洗的这个过程会把过去这五年我们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事像歌谣式的方式唱出来。就是我对你有个交代,你看你走了,但是你留下的那片橡胶林非常好,现在它今年这个收成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以前的很多的文化里面,它其实会安排一个特定的出口,让你跟死者之间定期的见面也好,讲述也好,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生前没讲出来的话,我们死后也很难讲。但是所谓哀悼这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说得极端一点,它可能会把一些真正的具有扰动性的话说出来,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哪怕是情感上非常激烈,或者说我真的非常想念你,类似这种东西。其实关于哀悼这个事情,这些年不只是在生死学内部,很多的哲学家认为它是一个根本的哲学性的问题,就是哀悼这件事情其实就象征着你跟这个世界失去的那个部分之间的,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你能不能说得通?我面对你的时候,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说得通?生死教育,其实最起码能够让大家意识到一点,就是你谈论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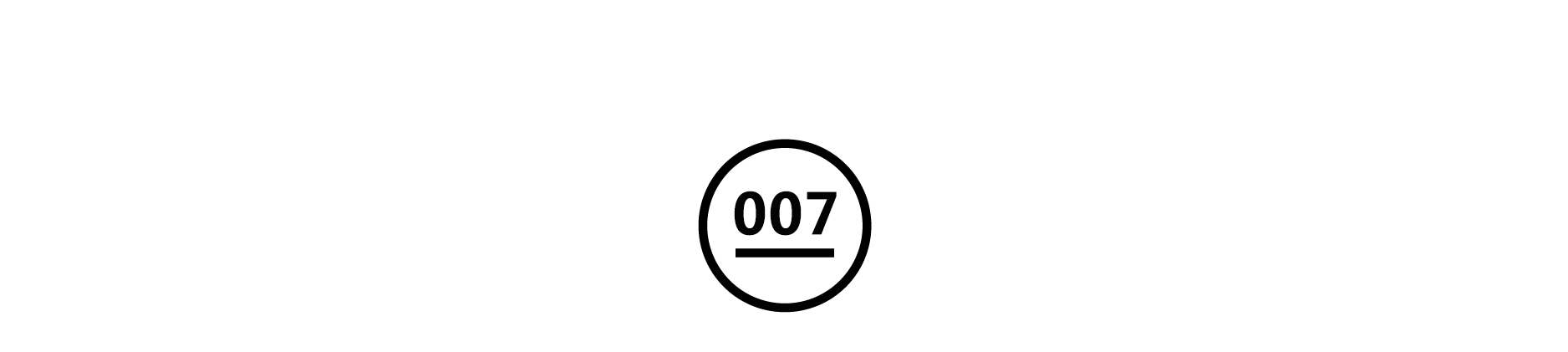
死亡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死亡方式带来的影响不是均质的
吴筱慧
之前袁老师说,“当下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价值体系已经不太匹配了,父母希望孩子实现的东西越来越难以得到落实。”所以您觉得50后和60后这一代走向衰老甚至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他们会非常的孤独,这也是为什么要我们要关注临终关怀这件事情,所以也想趁此机会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你们理解的临终关怀是什么,应该如何做好这件事。
袁长庚
这些年,包括学术界或者公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热衷。我觉得临终关怀从医学上讲就会很清楚,他有些基本指标,比如说身体疼痛的管理,比如说临终整个身体感受的舒适度之类的。那临终关怀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层面讲的知识环境,包括周围的情感的支撑,包括自己的人生意义得到确立之类。我反而觉得比较有信心的一点是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我们在硬件方面,甚至是我们在医学方面的跟进会相对而言非常及时。
但是我自己比较悲观的一点是说,我认为短时间之内能够实现临终关怀的整个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支撑,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我其实非常同意刚才王兴老师讲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有的时候正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抽烟的时候,我就会非常蛮横,就说你管的,这是老子的命,对吧?我想抽死那是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旦到他到了胸外科,确诊说是肺癌以后,他不光是马上戒烟,而且他要跟医生讲,你无论如何得把我救回来,无论如何你得让我活下去,所以前面的这种所谓的自我是假自我,后面的这种所谓的贪念或者是执念,也是真贪念、真执念。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临终关怀比较难的一点。
看了一些材料之后,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周围有一个系统性的团队的支持。因为人最后离开的时候,他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复杂,尤其是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很多事情在短时间内同时安排,他其实是对一个执行团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现在反倒觉得我们在物理条件和人力条件上,东、西的根上是很近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可能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性的共识,这种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合力。

漫长的告别 剧照
王兴
对,特别同意,硬件虽然目前在布局上还没有达到,但其实袁老师说的它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如果真的想做,立刻医院就来配备,我们社区跟上,其实很快就可以解决。止疼药又不是没有,医疗技术也不是没有。但其实从软件上到底该怎么去引导一个人,最后的临终,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时候不干什么,我觉得都很重要。像我自己会很有信心的是,如果我家有问题,不管从医疗上还是从理解上,我可以去帮助他,但这种帮助他不是所谓千人千面的。
我有一个流程,按流程走就完了,病人需要让你告诉他,这个时候也可以工作,或者需要告诉他,这个时候也可以带孩子,你有价值,你有意义。让别人跟他道个谢,道个别,或者他见一个什么人,很多事都是很细节的,很无法量化的,但又很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在小的事情上寻找生命的一些意义,不是说他这辈子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套房,然后现在得病之后有多少级别的领导过来看他?这些都是没法产生很大意义的。
我一直也在努力尝试做一些关于这部分的志愿工作和引导工作,帮助一些人做决策,告诉这个病人什么治疗还需要用,什么治疗就别用了,什么治疗可以有选择地用,如果出现什么事儿咱们就尽快结束。我们每个时刻都在做一些决策,最后在复盘的时候就会觉得,在每一个时刻都做了那个时刻最好的选择,咱们不后悔,不往回倒,不往回想,只要一个家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解决事情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都没有错,都没有说什么有遗憾啥的。其实在中国说姑息医治疗也好,缓和医疗也好等等词汇也好,其实在我内心看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个家庭要怎样帮助一个人优雅地走,或者说符合他的认知地走,这就算是好事,所以它不难,但是也不简单。
吴筱慧
之前袁老师的“理解死亡”课上会让学生在四种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中做选择:孤独终老;突发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袁老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几种死亡方式作为选项?我记得您说很多同学都选择了空难,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袁长庚
我们那时候研究医学人类学的时候,就是人的不同的疾病状态,其实不是只是病的问题,你会相应地进入到一个生存状态。比如说很多人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但是心血管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体认是非常微弱的,它并不会太困扰你日常生活。但是有些病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不会对你构成太大威胁,但是你每天都需要照顾它,每天都需要想办法,然后包括像艾滋病,它有社会污名在,大家觉得你得这种病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想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前面三个选项,它其实是在乎其中的某一个部分,就是这种死亡方式,它都保留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就看你想要的是哪个部分。
实话讲,我是觉得最后一项是最没有人选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都选最后一项,所以这个题其实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说的就是我不希望死后再麻烦别人,死了还留下一堆事儿特别麻烦。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事情,如果你用那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的离世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永远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因为它太惨烈,而且它太匆忙,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重新讲一个故事的可能性,他们可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残酷性,所以这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原则。
人类学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人是特别需要表述的,我们人生这一辈子的意义其实不取决于你真正做了什么事情,而取决于你到底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圆满的个人叙述把它讲出来。我们很多人生的遗憾就是,你其实没有坐下来谈过这个问题,可能它就需要一个晚上就够了,但是你就是一直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没有安排这一个晚上。其实我们讲死亡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死亡方式带来的影响不是均质的,不是因为最后我们都没有逃过这个结果,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这也是生死这个问题比较微妙的部分,它确实有些时候需要当事人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需要一个特别的在意或者特别的关注才可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