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女人的事》:谁能享受家庭之爱,又能逃避一切责任?
【编者按】在战地记者梅根·斯塔克(Megan K. Stack)在中国和印度生下两个儿子后,是当地保姆陪伴斯塔克走过了最艰难的五年。在与中国“阿姨”和印度保姆共度的上千个日夜中,她洞察到自己对她们依赖与支配、信任与疏离并存的微妙情感,也意识到,自己的解脱以一部分女性远离孩子、困守雇主家中为代价。本文节选自《女人的事》第一部分:如何消失。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女佣》剧照
事实上,小李和我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购物,为大人做饭,为婴儿提供食物,打扫,洗衣服,当然,照顾宝宝还需要付出无休止的时间。
如果汤姆和我愿意住在一个脏乱的公寓里,或者多吃点外卖,那么小李的加入可能意味着一条我回到书桌前的捷径。但我们都是洁癖狂,汤姆很挑食,而且自打小李开始为我们工作后,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忍受邋遢的家庭环境了。
是的,我失败了,但不是像汤姆想的那样。我失败在没能很好地和丈夫沟通我真实的日常生活上。现在我不得不试试,但已经晚了,而且一说起话来我就按捺不住火气。
“不是小李没做好她的工作,”我终于开口,用力拉住声音的缰绳,这声音稍一放松就可能变成尖声厉叫,“只是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她在打扫房间,那我肯定要负责照顾马克斯。”
“不能趁他午睡时打扫吗?”
“我有时也得做别的事情吧,比方说,我要洗澡。”仇恨的尖刺,句子的碎片:时间被打碎——我必须解释——他算老几,怎么能质问我?——他整天都在哪里?——如果他去公园散步了,如果他出去喝咖啡了——那他怎么还敢这样审问我——我永远不会......
我想用盘子砸他的头。
“你不明白,”我终于说,“你不是整天都在家里,你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
“是,我猜我确实不知道。”他刻薄地说。
现在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你应该相信我。”我爆发了,“因为我做过你的工作,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每天是怎么过的。但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而且我敢打赌你永远不会做。”
汤姆怒气冲冲地回到卧室,我坐在那里惊恐地审视着自己的处境。小李给了我一些至关重要的碎片时间,以及对我的事业来说十分宝贵的希望,但我为她的出现付出了金钱,我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一点。现在我意识到了,如果我强迫汤姆分担更多家务,他就会要求解雇小李。他与家务活的疏远变成我(身份是家里的经理人)或者小李(身份是全职女佣)的失败。

《女佣》剧照
他总是用那个词,女佣。这让我很不舒服。这个词暗示着富足,隐藏着指责。我是一个以穷人为食的剥削者。我已经变成了我们从来都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当然,汤姆仍然在外面的世界自由穿梭,他为弱者挺身而出。他已经为人父,却还能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没有做出任何降低身段的妥协。他不像我,绝望地数着自己的分分秒秒,就像一个乞丐在翻看口袋里越来越少的硬币。【……】
不知怎的,一切都出了问题。雇用小李是为了让我把注意力从孩子身上剥离下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种情形一度发生过,但只是昙花一现。我了解到,保姆不是托儿所。她不是一个村庄。她不是一个出现后就能简化生活,并且不会造成更多麻烦的工具。小李是一个人,她的问题也开始成为我的问题。也许,就像汤姆一直说的那样,这种纠缠表明我缺乏专业界限。但我想,除非我缺乏所有人类的情感,否则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
每个雇用另一个女人照顾孩子的女人一定都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挣扎。她们在各种关系中注入情感,而情感又在持续的、无意义的人员流动中从这些关系中移除。在雇主的心血来潮下,家庭情感先是被放大,然后被否认。过于积极维护正式雇佣关系权利的管家和保姆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我的脑海里回荡着朋友们的声音。这些谈话一直围绕着我。有和同栋楼里其他妈妈的谈话,有和宝宝群里其他女人的谈话,也有和朋友中的职场妈妈的谈话。
这对她们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你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她们,但你应该看看她们离开后会发生什么。突然之间,她们关心的就只剩下推荐信和钱了。
我以为她在乎我们。我是说,孩子们。他们哭了。而她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整张脸都不一样了。她走出门去,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让我想起一位俄罗斯同事过去常常讲的一个笑话:我以为这是爱,但她找我要了二十美元。
笑点是一样的:即使爱偶然出现,那也不是重点。重点是生存。但当涉及孩子时,很难冷静地看待。谁不想既享受家庭之爱带来的好处,同时又不用碰到各种不方便、不可逃避的责任呢?一个你可以雇用和解雇的家人?
我们在自欺欺人。
在和小李共度的最后几星期里,这些不舒服的想法折磨着我。“只要你准备好了,我这边随时欢迎你回来。”我向她保证。
“好啊。”她同意,“我也想回来。”
这番交谈裹上了一层糖衣。双方都没有协议、没有谈判、没有承诺。
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新生活的不便中。扫帚哗啦啦地落下,家具被推开,脚步声啪嗒啪嗒地穿过大厅。然后是关门的巨响,呕吐物飞溅。她仍然扭头趴在厨房的橱柜上睡觉,脖子像被踩扁的花茎一样弯着,但现在午睡的时间延长了。
看着她,我想起自己怀孕早期的样子。恶心感在血管里咆哮,每天都凝结成一种比前一天更顽固、更强烈的呕吐感。小口吞咽着尝起来一股铁锈味的水,像一只受伤的熊在地铁里慢吞吞地走着,悲惨地嗅到所有下水道、垃圾和烹调油的臭味。吐在交通隔离带里、建筑物后面、公共厕所里。
那时我还在工作,但我找到一些放松一下的小方法。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同事,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允许自己少做一点工作。
怀孕期间,我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女性生理真相:晨吐不是什么玩笑话或电影桥段,而是一种从发根到骨髓都让人痛苦的严重疾病。
我第一次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除了忍受呕吐不适、继续工作外,别无选择。农民和工厂工人,从事繁重手工劳动的妇女。即使是白领女性——她们至少每天多数时间可以坐下来——也仍然在暗自忍受着这种严重的疾病。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女人都对我的孕吐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这么过来的,但在怀孕早期没有就业保护。
我们必须在呕吐和隐秘中承担物种的基本繁衍。我想我不应该感到惊讶:还是孩子时,我们就已经学会掩饰月经的疼痛和流血。我们明白,否认物理外壳是获得承认的代价。只要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或者假装我们的身体和男人的一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他女性会对你抱以无声的同情,但你必须对男人隐瞒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在严肃而同情地点点头后,就会提醒你,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观点,然后他们会让你离开。生理差异会被拧成一根绳子,用来束缚你。
现在轮到我了。小李在孕吐,而我是她的雇主。
“你想躺一躺吗?”
“不用。”
“你还能继续工作吗?要不还是回家?”
“不用。”
“你确定吗?”
“我没事。”
我回到电脑前,没再管这事。我帮她分担家务,这样汤姆就不会意识到她在体力上已经不能再做这份工作了。我鼓励她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我向自己保证不给她施加压力,也不增加她的负担,我确实没有这么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对这样的情形,我能说的就是,我本可以做得更糟,而她并没有指望会有更好的安排。
与此同时,我为她的离开做了准备。
“小李不会每天都来了,”我告诉马克斯,“不过她有时还是会来的。”
“为什么?”马克斯问。
“她要有自己的宝宝了。”
“什么宝宝?”
“她的宝宝。她自己的孩子。”
“我也想要我自己的孩子。”马克斯回答。
“也许吧。”我说。
几个月其实就是几个星期。没什么,真的。时间慢慢过去,然后,在指定的那天,小李给了马克斯一个长长的拥抱,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她看着马克斯的眼睛说再见。
“再见。”他高兴地回答。
“我爱你。”她说。“我会再见到你的。”她说。“好吧。”她说。
我们已经达成一致,这次分手要迅速而冷静。我们不会向马克斯隐瞒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要避免戏剧化的场面。小李拿起包包,走出门,上了电梯。
然后她就走了。
我突然意识到,她带走了她工作时穿的人字拖。盯着门厅空荡荡的地板,我有一种被骗了的疯狂感觉。
我对自己说,她当然要把她的鞋子带走。那是她的鞋子,非常好的鞋子。
但她是偷偷拿走的。她等了一会儿,趁我没注意,把它们塞进包里。
看着空荡荡的地板,我明白小李真的走了。我知道这是最后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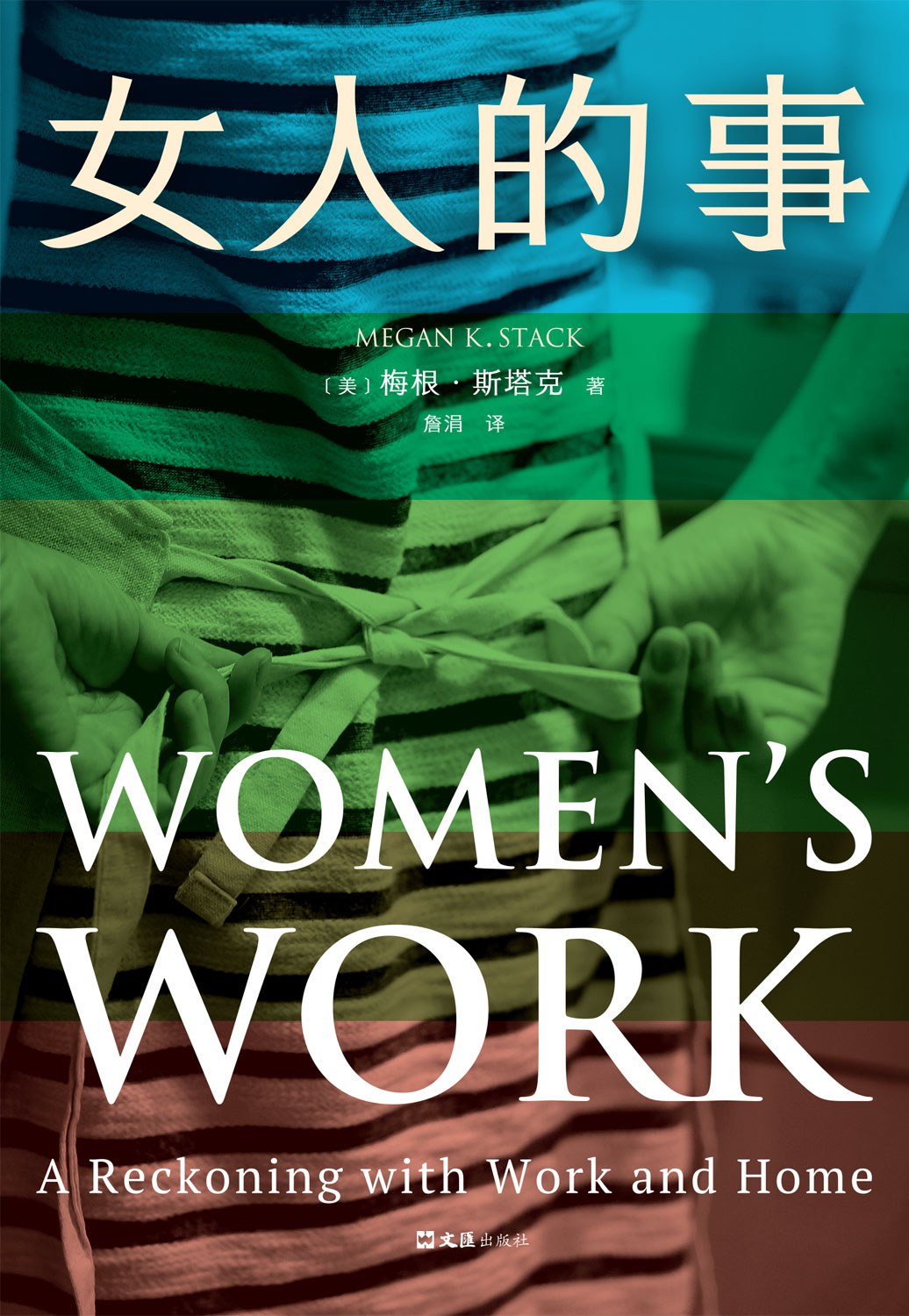
《女人的事》;作者:[美] 梅根·斯塔克 ;文汇出版社;2023年8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