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纪念︱学问何以养眼?
“学术史进程主要靠学人的纸上工夫来传薪,其成就高低大致依据著述多寡及其中的识见上下。这一点固然无可非议,但因此而忽略了轻于著述、重于事业的张元济,则显得有些不合理。”这是先师荣华教授所撰《张元济评传》一书起头的两句话。话极寻常。然于先生遽归道山以后读之,令人不禁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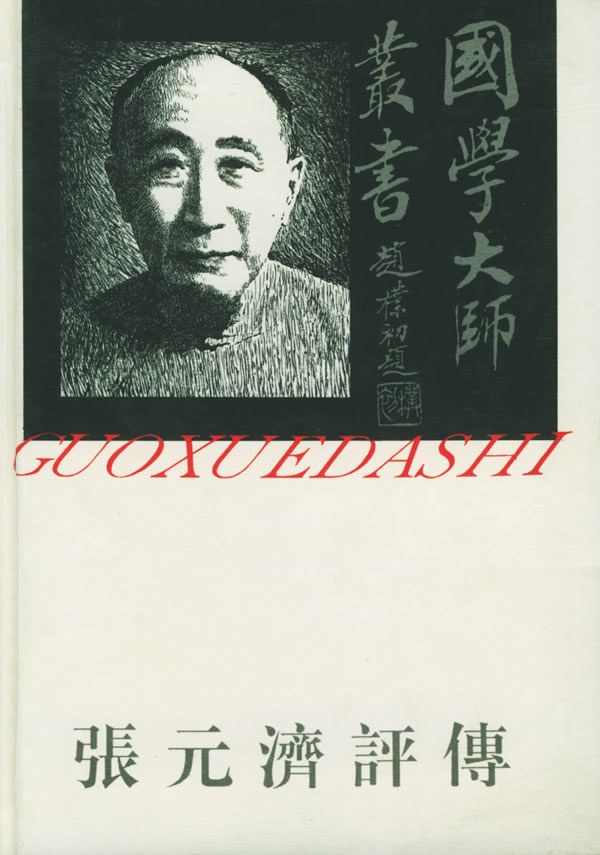
先生毕生阅读和教学的重心,正是学术史(当然,强分之下也含括史学史、文化史)。他对学术的理解,鲜有托诸空言者,往往于身体力行中透露出来。先生对学术史书写(及史学研究)中的遗忘、扭曲等现象多有观察与批判。如清末民国学人对儒之起源屡有讨论,其后学界在梳理此一议题时较注意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人的论述,往往不及其余。先生则特意撰文介绍乏人问津但可修正成见的许地山《原始的儒、儒家与儒教》一文,并谓“人微言轻的官场逻辑并不适用于学术研究领域”(此文近期从先生遗物中拣出,此前未公开发表)。后来在评议另一话题时,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万象中,有名无实的事物,往往因有名而被附会实之,有实而无名义则遭受忽视,虽有而若无”;并引述边沁创论的“语文能虚构实在或事实”,霍布斯揭示的“国家机器滥用词语、巧立名目使民众信虚为实的统治术”,以警示历史书写被扭曲之恶果。
这些教训化入先生本人的学问实践中,就是惜墨如金,不求文名,只问识见。或许在先生看来,学问之事,读过,想过,笑过,足矣。先生是一位独行冷静的学人,极少参加学术活动;但他并非与学术界绝缘,恰恰对世风学风甚为敏感,时于课堂上表出名家论著中值得商榷之处,亦时撰文批评粗疏之作。先生曾数次讲到,读书要多读老书,研究不要刻意追时髦,无不在提示弟子要将心力投注到基本文献和经典论著中,进而养成扎实的学问根基。
践行此种学术理想的典型方式之一,便是先生埋头苦读学人手稿。有时一天两天才能读通一篇,先生也乐此不疲。先生亦领着弟子阅读手稿,以达文字、文献、名物、义理等多层次的训练。某次课上,弟子不经意间说看钱锺书手稿“费眼”,先生即告当是“养眼”。
“养眼”,恰是先生学问品质之写照。先生不愿做学术生产流水线中的一员,只是安安静静地读书,然后养出养眼之作。秉元师借孔子语评价先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信然!
先生学术生涯早期,聚焦于文化研究,撰有《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等文。其中涉及文化学的思考及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多少都体现着那个年代特殊的学术风气。九十年代,先生参与多部文献集的整理,尤为《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康有为全集》贡献较多精力。这与复旦史学的学术资源和思想史研究传统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先生陆续发表关于严复、张元济、康有为等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先生唯一的一部专著《张元济评传》),进入学术的成熟期。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先生并无什么发表,数载后突然拿出《章太炎与章学诚》一文,深令读者赞服;随即,编校质量上乘的巨著《康有为全集》面世。先生在生命最后十余年里,继续留心康有为文献的搜辑,编成《康有为来往书信集》;多数时候则是在阅读钱玄同、钱锺书等名家的手稿。在学生辈的“动员”下,先生陆续于《书城》、“澎湃”等媒体中发表十余篇文字活泼而学养厚重的作品。其中对“事君欲谏不欲陈”、“中兴”、“伍子胥申包胥亡楚复楚”等文化现象的解读,可谓臻于谈艺管锥之境。

张荣华教授
先生遗留下来的文字不多,然可值三复。频现于先生文章中的三组关系,就是例证。
其一是文化研究中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在前揭讨论功利主义一文中,先生批驳了非功利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一似是而非的看法。先生立论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以往论者从少数思想家的重义贱利论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特征的做法。先生认为,讨论社会文化的整体特征,起码要注意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这两个主要构成因素的差异。社会心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经验,并通过情绪、风尚、习惯等表现出来,“撇开社会心理,就无法对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多重性取得切实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无从定义社会文化的总体特点”。四年后,先生给已创刊七年且对当时文化研究热潮起着推动作用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建言,应该重视“对上层文化(即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民间文化(即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这不是逢场作戏的一句口号,而是先生持续思考的一个话题。十余年后,先生发表《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传统关系论》一文。此文概述西方学术界关于大、小传统关系的若干重要研究,将其分别为支配说、隔阂说、挑战说、修正说、挪用说及源流说六类。先生认为,大小传统之间有着共享和妥协,但研究者不能走向另一极端而无视两者并列分立的历史存在,“特别是注意到在历史过程中,对小传统的改造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按照自身文化价值改造小传统,甚或要将小传统变为统治阶级的创造物,这无疑间接地映现出两种传统对立的轮廓”。大小传统在话语体系和史料留存上并不平衡,故先生更为关注的还是如何书写小传统的问题,即“辨识和表现小传统的本真性”。追问本真性不可忽视小传统自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尤应避免“着眼于大传统的价值标准或趣味范畴,对形形色色的小传统内容有选择地凸显、解释或建立模型,以论证大小传统之间的贯通性或一体化特征”的方法。先生还提醒要注意区分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前者是“从底层升起来的,它是民众声音的真实的表述”,后者则是“从上层降下来的,它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类型或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在先生多年前的文章中,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混而不分。
其二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对此一关系的论述,构成先生文章中或隐或显的一条主轴。九十年代,“公共领域”及其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中国学术界讨论甚为热烈的一个话题,学界对近世中国有无“公共领域”及能否引入这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议题未成定论。先生对此持肯定态度,在为张元济作传时,表彰张氏是“近代中国致力于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先生认为,张元济为学术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和介绍西学,而是通过经营商务印书馆,“孜孜不倦地为维护学术文化的自主理想和独立精神建立坚实的基础”。
先生为《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撰写的词条(1994年版中为38则,2019年合订本中复增写或改订若干则),没有受限于工具书的平实体例而着重从政治与史学的关系角度衡鉴一部史著的优长与缺陷。以研治明史的三部基本文献为例,先生对官修史书之弊有详细地揭示和明确地批评(类似评价亦出现于《清实录》《东华录》等词条中)。针对当朝官修史籍《明实录》,先生举《太祖实录》三修之例,指出其中掩非饰过之处。“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明成祖夺位后,以其中有于己不利之处而下令重修;后因监修官李景隆等人获罪,又有姚广孝、夏原吉等三修之举。其目的在于将‘其有碍于燕者悉裁革’。”即便如此,《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仍高于《明史》。《明史》因“众手成书、修纂日久”而颇多讹误,然其“真正缺陷在于有意掩蔽史实”。“如清之祖先女真部,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等活动甚多,均清代发祥后为明代之臣的明证。清统治者为表明祖先从未臣服过明代,不惜将自己祖先三百年间的历史全部删除。”“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的活动,也是书中着意淹没的史实。自弘光朝、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至鲁王监国的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皆予隐讳,不承认南明帝号,而将其事略述于诸王传中。”相较之下,先生对私家撰述《国榷》的评价要客气许多。“《国榷》以实录为本而并不盲从,对为明实录所隐没或为清统治者所讳言的史实,皆能具事直陈,不予掩饰。”“自《明史》行世后,有关明清之际及建州、南明的历史已形同禁区,故是书所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之史实,为他书所不及,史料价值甚高。”至于《国榷》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叙事过于简略,且有前后叙述不一,失于照应之处;书中的灾异迷信色彩也比较明显”,“但与全书的成就相比较,这些缺失毕竟是次要的”。
对这一关系的思考也贯穿在先生学术生涯后半期的学人个案研究中。《章太炎与章学诚》一文揭示,章太炎在1906年东渡日本后集中思考的学术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学术如何摆脱官方的制约而发展”,随后在《原经》一文中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大加挞伐。先生指出,“章学诚认为天下之道尽在先王政典中,六经作为政典的载体或载道之器,与‘史’异称而同实,从而将史学纳入官学的范围之内,并规定了史学负荷的使命是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事实。”章学诚对方志修撰的重视,亦被章太炎敏锐地看到是要实践“官师治教合一”的意图;章学诚对史德的阐述,更是教人树起尊君卫道之“心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一文续说前义。康有为与章太炎一样,对《文史通义》的“治教合一、官师无二”理想均持否定态度;但与章太炎“政学分途”论截然有别,康有为没有破除政教合一的观念。“《改制考》中对周公、孔子形象的褒贬抑扬,以及散布于各卷中的‘道尊于势’之论,明朗地显现出藐视政治威权的勇猛性格和进步精神;然而其思想的归宿点,依旧是回到儒家传统‘治教合一’的理想社会与政治结构。”先生无奈地写道,在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康有为“并驰”说的影响远甚于章太炎的“对境”论。在读钱玄同手稿的札记中,先生亦特撰一则谈“大学如何排课”,重点说明钱氏在课程取舍中“有意识地贯彻思想自由、推进文化革命和避免意识形态说教的教育理念”。
其三是学人交往中的师生关系。先生讨论学术史,注重从文人交往看学术思想之形成与嬗递。先生在课上讲五伦观念及其现代变迁时,尝言一部近世学术史大半牵涉师生关系。复谓诸多师友断交都值得细致考索,如黄宗羲-吕留良、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等等,由交友或绝交适可写出一部别样的学术思想史。惜乎,先生早逝而此一著作终不见于人间。不过,先生已刊文字中留下了数个精彩案例,足慰人心。
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对师生先后引领清末民初思想舆论界之风气,学界对两人分歧讨论甚夥,常以新旧更替、“凝质流质”加以解释。先生则从保皇会海外商业活动失败之关键事件振华公司内讧切入,考证康梁二人在事件及其前后的态度与作为,说明两人分歧之一大因素为对实业救国的不同看法。在振华公司内讧事件及保皇会的海外商业经营活动中,梁启超大体与康有为处于一种不合作的状态(甚至是“存在着严重分歧”)。促使振华公司内讧激化的广西振华公司筹建一事,本是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观点的一次具体实践。在康有为眼中,物质建设事业乃“救国至急之方”;但梁启超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振兴实业必以确立立宪政体、养成国民公德、整备所需机关、掖进国民企业能力为先,“四者有一不备,而哓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呓之言也”。先生进而认为,康梁之分歧,“本质问题是他们在中国改造问题上的不同思考和见解,及其对近代化道路的不同抉择”,“反映了投身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蜕变状况,体现出他们对于自身所肩荷的历史使命,所拥有的知识价值及所隶属的民族命运的不同理解”。
先生讨论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评价,亦注意到谭献章太炎师生对《文史通义》的不同理解实是影响两人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先生认为,谭献对章学诚崇仰之深和评价之高,晚清学人中无出其右者。“谭献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和阐发,主要是突显章氏命题的内在精神是标举‘官师治教合一’之旨,并尊奉此旨义为‘不磨之论’和‘师说’,认为此旨能‘洞然于著作之故’,能洞究‘六艺之本原’”。而这恰恰是章太炎《原经》一文着力驳斥的观点。就在写作《原经》不久前的《某人与某君论国粹学书》一文中,章太炎已公开批评谭献,并拒称后者为师而直呼其名。章氏此举引来钱锺书的痛斥,谓章太炎对昔日师弟之谊轻易勾销,是尊生畔死之奸人。在先生看来,章太炎对谭献的不满事关大节,钱锺书对章氏的批评有失允当。
对章太炎钱玄同关系的解读,是先生从师生关系讨论学术史的至为精微的一页(该文先以《钱玄同与章太炎北上讲学》为题,于2010年发表在《书城》杂志;2014年,改题为《钱玄同思想中的师承因素》,作为“代导言”收入先生选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玄同卷》一书,文首多出两段)。钱玄同早年追随章太炎习小学和经史之学,在新文化运动及其后同章太炎的政治见解与学术观点均有着显著的分歧。但钱氏未像周作人那样有“谢本师”之举,亦未有如鲁迅“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之类的表述,反而从章太炎北上讲学经历和两人晚年互动中“可见其敬师之情愈趋淳挚”。此前论者或从钱玄同接受章太炎“六经皆史”论中解释两人精神之相承,或从功利论角度臆测趋新弟子与守成师长为维系学术地位而相互支援之动机。先生对两说均予否定,从钱玄同日记手稿中细绎出一条维系章钱师生情谊近三十年的精神纽带。此一纽带即为两人多次探讨的“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章太炎曾告诫弟子,“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嵇、阮,不可嫖妓”。钱玄同对此深表认同,“章师固言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礼教必如颜、李,否则流于虚伪;放弃礼法必如嵇、阮,否则流于放僻邪侈矣”。师生两人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上终身抱持着一致的态度(至章氏离世前三个月仍以此告诫钱氏),章钱“能够葆有纯真的师生情谊并且善始善终,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树立的相同的人生观”。
清末民初以来,传统的负面化愈演愈烈,个体从传统中脱嵌(disembedding)后如何自处,个人道德修养走向何处,乃成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即如同为章门弟子的钱玄同、鲁迅,两人均极赞誉嵇康、阮籍等名士,对“在抉破世俗礼仪规训、反对一切人为束缚之后,在乱世之中如何培植个人道德修养以抵制放诞自肆的习气”这一问题却有着不同的选择。先生不惟呈现了一个“出语惊人、思想偏激”背后“自有其不肯逾越之界域”与对待师友“始终能笃厚唯谨,恪遵师训”的钱氏形象,更表出近代中国在步入世俗时代的过程中少数思想家对本真性伦理的深切体认。
前举三组关系只是先生文字中的一些小片段。这些片段和先生其他文字中的观点自然有待来者检验(先生自己对其先前的看法就常有更新),但先生学问之风格同样值得珍视。先生尽可能地减少社交(包括应酬式的学术活动),少了功利浮躁的侵染;与之相应地,沉浸于手稿古籍,“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进而目光高远,下笔谨慎。先生曾在一篇未刊稿首页的天头处摘录章太炎《说林》述治经之法,“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又曾以仲长统《昌言》谓天下士之“三俗”、“三可贱”、“三奸”告诫弟子。沉潜、切实,正先生治学育人之宗旨。惟其如此,可言养眼之学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