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瘦死的骆驼没马大:一战前夜军备废弛的沙皇俄国
俄国巨人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在军事计划的棋盘上面,俄国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视为庞然大物。尽管它在对日一战中丢脸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法国和英国就感到心宽胆壮;而德国人因害怕在他们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瘦死的骆驼
虽然俄国陆军积弊甚多,声名狼藉;虽然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是俄国的严冬而不是俄国的陆军;虽然在克里米亚之战中,俄国陆军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两国的败仗;虽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战(Siege of Plevna)中已经挫败俄军,只是后来因为众寡悬殊而告失利;虽然日本已在满洲打败了俄军;但是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仍然流传一时。哥萨克骑兵冲锋,杀声震天,凶悍残忍,在欧洲已深入人心,所以报刊的艺术家们在1914年8月能够置身俄国战线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细笔刻画出这样的画面。人们对俄国军队已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哥萨克加上不虞耗尽的数以百万计的身强力壮、驯服听命、视死如归的庄稼汉(mujiks)。俄国陆军为数之大,令人咋舌:平时兵力为142.3万人;一经动员征召,便可再增加311.5万人;此外还有一支200万人的地方军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备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员总额达650万人。
在人们的脑海中,俄国军队是个庞然大物,开始时不免臃肿迟钝,但是一旦充分动员起来投入行动,它一浪接一浪永无穷尽的人海波涛,不论伤亡多大,都会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滚滚向前。自从对日作战以来,军队里便开始进行整顿,肃清其颟顸无能、营私舞弊的现象,并且据信业已取得成效。法国政界,“对俄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具有非同寻常的印象”。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国人谈判海军协定时,便注意到这一点并抱有同感。他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总统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的。”
在法国人看来,第十七号计划能否胜利,向莱茵河进军能否所向披靡,将是他们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欧洲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为了保证他们能突破德军中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要俄国人牵制住一部分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问题在于要使俄国人在德、法两国各自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同时,在德军后方发动攻势,也就是说,尽可能在接近动员第十五天行动。法国人跟别人一样深知要俄国在十五天之内完成动员和集结部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要求它于动员第十五天以手头已有的力量开始作战。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叫德国人从一开头就得两面作战,以削弱他们所面临的德军优势兵力。
1911年,当时身任陆军部参谋长的迪巴伊将军奉派前往俄国,去给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思想。在一场欧洲大战中,一半的俄国军队得集中用于对付奥地利,而用于对德作战的部队,在动员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数可以准备就绪,尽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却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俄国人正因他们的军队蒙垢而急于重振军威,同时对计划的全部细节又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态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国人同时发动攻势,这自然是大胆有余而细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国人的承诺,一俟俄国的前线部队进入阵地,不等全军集结完毕,就在动员第十六天发动进攻,越过东普鲁士的边界。“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沙皇在双方签字的协议上声言,“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
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的协议经过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一年一度的会谈而愈形牢固加强,这种总参谋部之间的会谈正是法俄同盟的一个特色。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日林斯基(Jilinsky)来到巴黎; 1913年,霞飞将军前往俄国。到这时,俄国人已经完全受制于冲动的魔力。自从兵败满洲以来,他们确也需要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格朗迈松上校的演讲集译成了俄文,备受欢迎。俄国总参谋部因为领受了光华熠熠的“殊死进攻”的理论而神采飞扬,所以其诺言也就一再加码。1912年,日林斯基将军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80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全部送达,而不顾俄国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1913年,他又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两天,不顾俄国兵工厂的炮弹生产能力不到估计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枪子弹生产能力还不到一半。
盟国并不因俄国军事上的弱点而牵肠挂肚,虽然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早在满洲时就曾对这些弱点写过不留情面的报告。这些弱点表现为: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才。每周为《泰晤士报》撰文评论日俄战局的雷平顿上校,由于他在评论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专栏文章汇编成书献给了日本天皇。尽管如此,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却仍然认为,它们需要关心的只是促使俄罗斯巨人行动起来,而无须考虑他如何发挥作用。但这谈何容易。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700英里,为德国兵的4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作为防范入侵的国防措施,俄国的铁路轨距有心造得比德国为宽,法国人提供巨额贷款资助增建的铁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国人达到同样的动员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国人答应派往德国前线的80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只有半数能进入阵地向东普鲁士猛扑过去,不论其军事组织如何之糟,预计都会对战局造成极大的影响。
派出大军在敌国境内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危险而又万分复杂的行动,需要作一番呕心沥血的精心组织,在铁路轨距宽窄互异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国陆军的特点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并不显著。
由于耆龄老将过多,军官团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他们最锻炼脑力的工作是斗纸牌。不顾体力条件而让他们忝居现役军职,为的是要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或是有钱的靠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练的军人,但是那个制度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上最高层。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怠惰和不感兴趣”使得一位英国武官为之愕然。他访问过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一处俄国边防军的驻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连“一个网球场也没有”。经过日俄战争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将校不是呈请辞职便是被迫离职,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拂除凝聚在上层的陈年积垢。一年之间,因为不称职而退役的将官达341人,这个数目接近法国陆军的将官总额,而作同样处理的上校也有400人。尽管在俸金和晋升方面有所改进,但1913年军官缺员仍达3000名之多。日俄战争以后,虽然在清除陆军中的积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无奈俄国的政体还是那个政体。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其最精明能干的捍卫者,1903年至1906年间出任首相的维特(Witte)伯爵便是这样称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政体的统治者是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的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妥加维护,勿使缺损。此人一无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过负此重任的训练,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贵幸臣,他心血来潮,执拗成性,还有那轻率浮躁的专制君主的奇思异想。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Tsushima)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 !’”。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 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Stolypin)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 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Tchinovniki),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 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须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他们,宫廷里钩心斗角成风,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听从谗言,也就动辄罢官削职。大局如此,英彦俊硕都难以久安于位,有一个托词“体弱多病”而辞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兴叹,“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点,终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罗斯,国无宁日:灾祸频仍,屠戮不绝,出师屡败,民不聊生而相继举义,终致酿成1905年的革命。维特伯爵当时曾向沙皇进谏,若不俯顺民心,畀予宪法,就须厉行军事专政,以恢复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气吞声,采纳了前者,这纯粹是因为担任圣彼得堡军区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担军事专政的责任的缘故。大公这一次坐失机宜,从此便永远得不到那些极端保守的皇权主义分子的宽宥,同样得不到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具有德国血统和倾心德国的王公大人,那些黑色百人团—“右翼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作为专制政权顽固堡垒中坚的其他反动集团的宽宥。他们觉得,曾经一度结成三皇同盟的三个帝制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更其是俄国的当然盟国。许多德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俄国的反动派别把国内的自由派看成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宁要德皇而不要杜马,这种态度跟日后的法国右派如出一辙,他们宁要希特勒而不要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只是由于战前二十年间德国自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愈演愈烈,这才促使沙皇俄国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结盟。到了最后关头,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把它跟英国结成一伙,但就是这个英国,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达一个世纪之久。当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Vladimir Alexandrovich)大公曾于1898年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我每天向上帝热切祷告祈求的就是这个 !”
弗拉基米尔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主持的午后降神会(séances)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王子;自有其“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关于这个阶层,沙皇曾经说过,“我最讨厌这个词!我但愿下一道诏令,让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里删掉”;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为自己的灵魂,为社会主义,并且也为俄罗斯的土地,内心备受煎熬,此恨绵绵无尽期;自有其一批绝望的万尼亚舅舅;自有其独特气质,促使一位英国外交官得出结论,认为“在俄罗斯,人人都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就是这气质,一种叫做“斯拉夫魅力”(le charme slav)的气质,半是无所用心,半是无所事事,一种19世纪末的颓废气氛(fin de siècle),这种气氛有如一片薄雾笼罩着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樱桃园”。
弄臣当道
就备战的情况而言,只消举出一个人来便可以代表这个政权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对他有个评语:“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 可是要他说句老实话那就简直难如上青天。”1877年对土耳其的一仗中,苏霍姆利诺夫是一员骁勇的年轻骑兵军官,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战役中学到的军事知识都是永恒真理。
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参谋学院教官的集会,会上居然有人对诸如火力要素对马刀、长矛、刺刀冲锋的不利影响之类的“新花样”有兴趣,他对此斥责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说道,他听不得“现代战争”这个词儿。“过去的战争是这样,现在的战争也还是这样……这种种玩意儿都不过是邪门歪道的新花样。拿我本人来说,二十五年来我就没有看过一本军事手册。”1913年,他把参谋学院的五名教官撤职,为的是他们都坚持宣扬什么“射击的组织与实施”的异端邪说。
苏霍姆利诺夫的智慧,因其轻浮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他既要存心巴结沙皇那样的人物,这些人也就无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Paléologue)眼中,他的形象“使人一见便会产生不可信任的感觉”。内阁大臣的任免,全凭沙皇的一时兴致,苏霍姆利诺夫之所以能得宠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谄媚迎合和曲意承欢的功夫,说点儿凑趣讨好的故事,来几下滑稽逗趣的动作,小心不去议论正经大事或不快意的话题,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当时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缘故,事实表明,什么营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丑闻,甚至连轰动一时的间谍丑闻,也都对他的地位毫无影响,他仍好官我自为之。
1906年,苏霍姆利诺夫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二十三岁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来是个懒坯,从此以后便越来越把公事推给下属去办,用那位法国大使的话来说,“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专门用来跟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二岁的夫人尽享鱼水之欢”。苏霍姆利诺夫夫人喜欢向巴黎定购时装,出入豪华的酒楼饭馆,举行盛大的筵宴舞会。为了满足她挥霍浪费之需,苏霍姆利诺夫及早施展了虚报开支之术而财运亨通。他按每天24俄里骑马视察的费用向家报销旅费,实际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车。他的贪污所得,数字已属不小,加上他对股票市场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个财源,六年之间他在银行里存入了702737卢布,而他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270000卢布。他的生财之道还包括他的左右亲信给他的孝敬,只要他签发几张军事通行证,送几张参观演习的请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会借给他款予以报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名叫阿尔特席勒(Altschiller),苏霍姆利诺夫夫人离婚所需的证据便是此人供给的,他以挚友的身份出入陆军大臣的府邸和办公室,在这两处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乱摊的。1914年1月,此人离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来是奥地利派来俄国的间谍头子。还有一个更为声名狼藉的米亚索耶捷夫(Myasoedev)上校,盛传他是苏霍姆利诺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过是边境上一个铁路警务处长,居然拥有五枚德国勋章,并蒙德皇邀往离边界不远的罗明滕森林(Rominten)皇帝行猎别馆赴宴。毫不足奇,米亚索耶捷夫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审,但是由于苏霍姆利诺夫亲自干预而宣布无罪并得官复原职,直至战争开始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护人终于因俄国的屡战屡败而被罢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间谍罪被处绞刑。
苏霍姆利诺夫在1914年以后的运道颇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够与米亚索耶捷夫上校同时幸免被起诉判刑,纯系沙皇和皇后的庇护;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业已逊位,临时政府沦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堕入法网。在当时千疮百孔、一片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义上虽是叛国罪,而审讯的内容却大都是旧政权的种种罪恶。检察官概述案由,把这种种罪恶归纳成为一条:俄国老百姓被迫作战,既无枪炮又无弹药,对政府完全丧失信心,这种绝望心情散布蔓延,无异瘟疫,“后果极为严重”。经过一个月轰动一时的听证,他贪赃舞弊、荒淫纵欲的具体情节都真相大白,苏霍姆利诺夫的叛国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无可逭。
他被判处终身苦役,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布尔什维克党人释放,随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并题字献给德国的废帝。他在序言里声称,俄国和德国这两大君主政体由于在战争中互为仇敌而同归于尽,只有两国言归于好才能使两国的君主复位亲政。这个见解使那个流亡在外的霍亨索伦皇室的废帝感触至深,他便写了一个题献,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回敬给苏霍姆利诺夫,显然是由于受到劝阻,这个题献在公开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从1908年到1914年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便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代表了反动派别的意见,并得到反动派别的拥护,对德备战工作该是陆军部的主要任务,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开始的陆军改革运动,已经取得进展,他却立即把它草草收场。总参谋部本来已被授予独立建制,以开展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隶属于陆军大臣的管辖,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觐见沙皇。总参谋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权力,从此便得不到一个能有作为的领导人,甚至也没有一个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终地领导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间,一共换了六个总参谋长,影响所及,作战计划也就休想是系统周密的了。
苏霍姆利诺夫虽说把工作全部推诿给属下去办,却容不得别人有什么主张。死抱住那一套陈腐过时的理论,忘不掉年代久远的战功荣誉,他一口咬定俄国过去的失败,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错误,而不是由于训练、准备和供应各方面的不足。他顽固不化,坚信刺刀胜过子弹,所以根本不肯花费气力去兴建工厂,增产炮弹、步枪和子弹。没有一个国家在军需品上是准备充分的,这是各国军事批评家们毫无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结论。如英国的缺少炮弹后来竟成了一桩有损国家声誉的丑闻;法国从重炮直到军靴的不足,在战争开始前就已是丑闻。但是,在俄国,苏霍姆利诺夫甚至连政府专供生产军火的拨款也没有用完。俄国在开战时每门大炮只摊到850发炮弹,对比起来,西方国家每门大炮则有2000到3000发炮弹的储备,而苏霍姆利诺夫本人也曾在1912年同意过一个折中办法,给每门大炮储备1500发炮弹。俄国的一个步兵师有7 个野战炮连,德国的步兵师却有14个。整个俄国陆军有60个重炮连,而德国陆军则有381个。战争主要取决于双方火力的较量,而苏霍姆利诺夫对于这类告诫则一概嗤之以鼻。
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汉”
他厌恶“射击的组织与实施”,但他更为反感的,就是那位比他年轻八岁,又是代表军队中革新倾向的尼古拉大公了。大公身长1米98,体态挺秀,相貌英俊,山羊胡子,穿的一双靴子高及马的下腹,算得上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对日战争以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负责改组陆军。该委员会的宗旨和布尔战争之后的伊舍委员会一样,不过跟它的英国样板有不同之处,它问世不久便落入了官老爷们的手中,沦于死气沉沉的境地。反动派别对这位大公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插手了那篇宪政宣言,怕的是他深得人心,所以到1908年便把国防委员会撤销了事。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在日俄战争中曾任骑兵总监,全军现职军官,他几乎无不熟识,因为他身为圣彼得堡军区司令,他们奉命履新时都例须向他报到,他便成了军中最受钦佩的人。他之受钦佩,主要倒不是出于他的特殊勋绩,而是由于他的身材、仪表和风度,是这些唤起了士兵的信仰和敬畏,是这些在他的袍泽中赢得了倾心敬慕,但也引起了 嫉妒憎恨。
他对待部下,不假辞色,甚至粗暴,不论军官小兵,他都是这样,宫廷圈子外面的人都把他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汉”。从未见过他的农家出身的士兵,都津津乐道关于他的传闻轶事,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成了一个专与“德国帮”和朝廷里的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神圣俄罗斯的捍卫者。这种舆情,此响彼应,但丝毫无补于他在宫廷内的人缘,尤其是在皇后面前,她本来就因为他鄙视拉斯普京而恨透了“那个尼古拉”。“我对他绝不信任,”她写给沙皇的信中说,“我看穿了他根本不是聪明人,他连侍奉上帝的人都要反对,可见他做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他出的主意也好不了。”她还无休无止地数说他搞阴谋诡计,要迫使沙皇逊位,并且凭借他在军队方面的深得人心,由他自己登上皇位。
沙皇对他心怀疑惧,使他在对日作战期间未能成为总司令,因此也成全了他事后没有遭受谴责。今后再有战争,势必非要让他出马不可,战前制订的计划中就已内定由他出任对德作战的前线司令,沙皇本人预期将亲自担任总司令,而由一位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大公曾经数次前往法国参观演习,并且深受福煦的影响,他也跟福煦一样怀有必胜信念;他还受到盛宴款待,究其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他的仇德情绪之外,同样也是由于他的雍容豪迈的风度,使人一见就有此人是俄国威力的象征之感。法国人都津津乐道大公的随从科茨布(Kotzebue)伯爵的一番议论,这位伯爵说过,他的首长认为,只有把德国彻底粉碎,并把它重新分割为一个个小邦国,让它们各有一个小朝廷去快快活活过日子,才能使全世界有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大公的夫人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和嫁给大公的弟弟彼得的她的妹妹米莉姹(Militza),对法国的热忱也是毫不逊色。她们两位同是黑山国王尼基塔(Nikita)的公主,她们对法国的爱慕是和她们天生的对奥地利的仇恨成正比例的。1914年7月下旬,在一次皇室的野餐会上,帕莱奥洛格称之为“黑山的夜莺”的这两位大公夫人,过来与帕莱奥洛格聚在一起,絮叨起这场危机。“战争要打起来了……奥地利要输个精光……你们将收复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两国的军队要在柏林会师。”姊妹俩一个给大使看了一只镶宝石的小匣,里面盛的是洛林的泥土,另一个告诉大使她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上了洛林的大蓟花。

俄国总参谋部未雨绸缪,制订了两份作战计划,待最后视德国如何行动而择定使用。如果德国以主力攻打法国,俄国就要用主力攻打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用四个集团军投入奥地利战场,用两个集团军投入德国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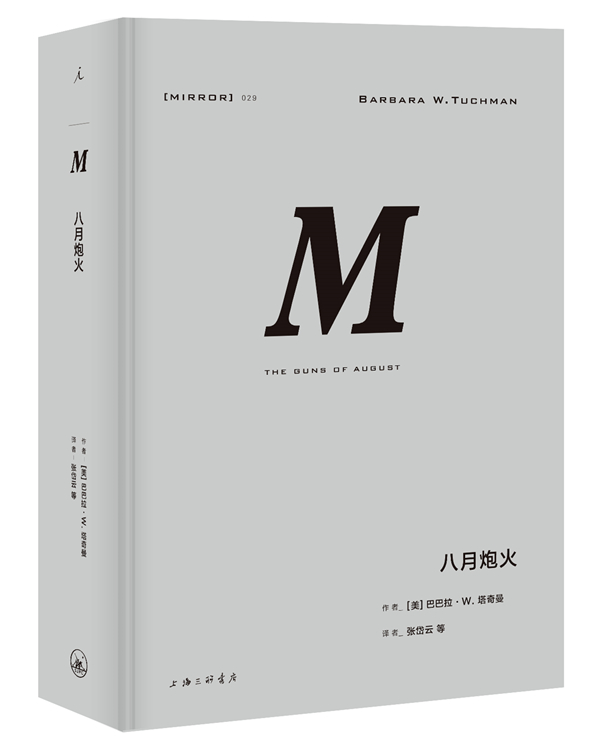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