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伟|“理法”融通:从古典戏剧《三哭殿》透视恢复性司法理论
原创 王伟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收录于合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文集 24个
王伟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目
一、秦英杀人案的争议
二、戏剧中大众情感倾向折射恢复性司法理论的特征
三、恢复性司法或为融“理”与“法”新路径

古典戏剧《三哭殿》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其中的浪漫主义想象蕴藏该时期的法律文化。从法律制度与浪漫主义想象的对比考察中可以管窥到大众情感倾向中对司法恢复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折射出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的诸多特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唯物史观重构寻“理”与“法”的融通路径。解构与重构之间发现古典文学作品对司法恢复性的追求实质是对“人治”的追求,恢复性司法则是现代化法治的产物,是融通“理”与“法”的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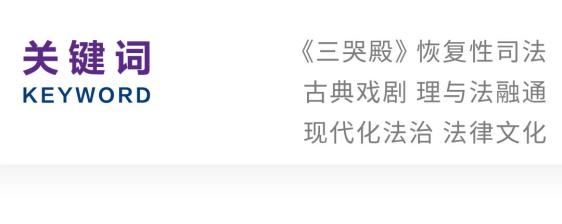
一、秦英杀人案的争议
《三哭殿》讲述的是大唐贞观年间秦怀玉之子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时失手打死詹太师,詹太师之女贵妃詹翠萍与银屏公主(晋阳公主)、长孙皇后为是否斩秦英偿命,哭闹于金殿的故事。詹贵妃要求斩秦英为父偿命,银屏公主与长孙皇后请求宽赦秦英,唐太宗杀赦难决,于是对詹贵妃百般相劝,提出修庙堂、顶礼焚香的条件,并命公主捧皇封酒跪请原谅。最终詹贵妃以国事为重谅解秦英,最后重归于好,戏剧圆满结束。
尽管《三哭殿》作为古典文学作品实为世人对秦琼后代的谬传与文学浪漫想象结合的产物。比如首先,故事发生在公元645年即唐朝贞观二十年,而历史上的长孙皇后三十六岁时即贞观十年“崩于立政殿”;其次,据史书记载“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晋阳公主从小被唐太宗亲自抚养,《新唐书》记载:“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薨年十二”。因此晋阳公主不可能与秦怀玉结婚生子;最后,《旧唐书》记载秦叔宝曾说过“况子女玉帛乎?”可见秦琼是有子嗣的,但并非后人谬传的秦怀玉而是秦怀道与秦某道,秦怀玉与秦英皆是民间杜撰的人物。但正如从1960年开始在饰演《三哭殿》中李世民一角的戏剧名家田占云所说,戏剧本身不过是借用了几个古代历史人物来演绎一段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而已。可见《三哭殿》并非真正的历史情况,也就不能透过它探究唐朝真正的法律制度,但是可以将故事作为案例梳理相关争议,以故事人物特征为背景,再以唐朝法律为工具作为唐朝法律裁判者进行一次“应当”的裁判。故事以迎合大众情感而流传,戏剧由故事演绎,将裁判结果与戏剧想象比对,便可管窥唐朝百姓对判决结果的情感倾向。
案件法律争议梳理
古代法律始终贯穿着“杀人偿命”的复仇观念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理念,对于唐朝百姓来说秦英似乎罪无可赦。然从唐朝法律出发,该案件仍有许多可能的争议。从主体身份上分析,根据故事出处《少西唐》记载,秦英杀詹太师时十二周岁,在唐喜成、李树建、贾延聚等各个豫剧名家不同版本的《三哭殿》戏剧中秦英也是孩童形象,由此对秦英就可能涉及唐朝对未成年人轻缓刑罚的考量,此为争议一;秦英乃驸马秦怀玉之子,秦琼之孙,唐太宗亲外孙,公主之子,属于皇亲国戚,将门之后,是否应该适用“八议”制度,此为争议二;詹佩贵为太师,其女詹翠萍坐西宫是唐太宗的宠妃,也有着皇亲国戚的身份,那么詹太师是否是秦英的长辈就关乎秦英杀詹太师是否属于“十恶”中“恶逆”的情形,此为争议三;从犯罪行为上分析,戏剧中的秦英为“过失杀”,推倒詹太师致使其当场死亡,是否适用唐朝关于“过失杀”减刑的情况,此为争议四。
法律争议分析
形成准确的裁判还需要适格的裁判者,因此在分析法律争议之前需要考察故事中的人物能否胜任裁判者的工作。历史上的唐太宗德才兼备,雄才大略,开创了大唐朝的“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长孙皇后乃名将之女,相传长孙皇后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旧唐书》中称赞其“贤哉长孙,母仪何伟”。周召在《双桥随笔》也写道“三代以来,皇后之有贤德者,唐长孙氏为最。”甚至据史书记载晋阳公主也是自幼孝顺,劝太宗礼遇大臣,左右莫不赞公主厚道贤惠。因此可以假定裁判者与辩护人都具备明辨是非、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
关于争议一,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矜老恤幼”的历史传统,《唐律疏议》中《名例律》“老小及有犯”条:“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但是秦英已经满了十岁,未成年的身份并不能为其偿命与否提供帮助。在争议二中,关于“八议”贵族特权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八议者,犯死罪者,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秦英拥有皇亲国戚的身份,属于“八议”中的“亲”,可以享受到“八议”的特权,由皇帝决定处理结果,一般“议”的结果可以不死,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不死。在争议三中,“十恶”是传统社会中的重罪,十恶犯人不得或限制适用议、请、减、赎等刑罚优待办法。而根据唐朝法律关于“十恶”中“恶逆”的规定“犯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此名恶逆。”詹太师虽然是詹贵妃父亲,但唐朝妻妾地位差距极大,妾不被认为具有正室的地位,皇室也不例外。因此西宫的詹贵妃并不算皇帝的妻子,只有长孙皇后才是皇帝的妻子,詹太师并非秦英长辈,秦英未犯“恶逆”之罪,不是必死之罪。争议四,《唐律疏议·斗讼》关于“过失杀”规定“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刘晓林教授认为结合《唐律疏议》的律文可以认为“过失杀”包括“非故意”与“未预见”两个方面含义。戏剧中秦英与詹太师的鸣锣队伍起冲突,詹太师呼“左右,拿下了”,秦英在与随从打斗时詹太师上前来被秦英一把推倒在地身亡。秦英在事发后十分惊慌逃离现场,后又多次与管事、母亲晋阳公主甚至唐太宗殿前说道“只是一推,他死可不能怪我”,其本人又是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后果缺乏判断力,因此可以认定具有“非故意”与“未预见”的主观条件,符合“过失杀”。《斗讼》规定了“过失杀”的处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可见,唐律中对包括过失杀人在内的过失犯罪予以宽宥的具体方式为以金赎刑而不科真刑。
综上,首先,秦英虽无法享受未成年人的宽宥措施,但属于“过失杀”,又因“过失杀”情节因素与其皇亲的地位,在适用“八议”制度时可能得到更大宽宥。其次,秦英不属于“恶逆”,不必“不得以赦原”。案件又有公正明智的裁判者辩护人参与,秦英不必偿命应是显而易见的结局。法律裁判结局是贵妃之父一品官员太师被杀,杀人者秦英不必偿命,但唐朝百姓情感上却难以接受。文学作品是法律与百姓情感之间的纽带。《三哭殿》在故事情节上的文学性想象一方面维护了百姓受“杀人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传统观念影响的情感倾向,也将大众喜闻乐见的儒家观念中“和”的理念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也维系了法律裁判的结果。
二、戏剧中大众情感倾向折射恢复性司法理论的特征
“和”的理念
戏剧的最后晋阳公主搀扶长孙皇后,秦英扶着姨娘詹贵妃,唐太宗坐于金座上哈哈大笑,三名女性角色哭于金殿的闹剧终于结束,秦英杀人一案也迎来“家和”的结局。大圆满的结局在民间得以流传正是基于其中的浪漫想象与大众情感中“以和为贵”兴趣相投。“和为贵”是与儒学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价值观,这恰恰与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关系恢复理念”相契合。加拿大学者苏珊·夏普(Susan Sharpe)提出了恢复性司法的五个要点,其中就有追求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以及双方共同地融入社区之中的内容。
“和”提高了涉案多方的接受度,使得大众情感上得以接受,《易·乾卦·彖传》中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要求百姓以“和”为做事的目标。尽管恢复性司法理论并非以儒家传统为基础,而是以刑事实证学派的目的刑思想、犯罪被害人学理论、犯罪标签理论与立足于并合主义的恢复性司法理论等多种理论为理论渊源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但二者都注重双方、多方之间的和解,解决双方矛盾并非诉诸冷冰冰的法律制度,法律的结果未必让人满意却以强制力使人接受,和解立足于双方达成一致,从多方自愿接受的“合意”中诞生强大生命力。“和”的理念映射出重归于好的情感倾向与恢复性司法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具有同样的价值指向。
有学者指出,传统法律文化中“和”的理念与恢复性司法理论具有实用主义的相似性,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存在较大的冲突。其认为二者理论渊源上存在不同,恢复性司法中的恢复是独立自愿的恢复,而儒家学说影响下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恢复是一种压迫性的恢复,强调“无讼”,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为双方同时接受即非“合意”。或许正是由于现实中的“和”仍是一种实为强制的“和”,大众才倾向逃离现实环境,在想象中抒发情感,将戏剧中的三名女性角色与唐太宗置于同等地位上演绎。
协商主体平等自愿
不同于真实历史中的“压迫的和”,《三哭殿》中唐太宗的调解也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的。《三哭殿》一方面将帝王一家平民化为普通家庭,另一方面家主唐太宗似乎失去了君、父、夫的地位,集三纲身份于一体的至高无上的唐太宗并不是争议的双方也非戏剧的主角,相反妻、妾、女却活跃在舞台之上,为秦英是否偿命大闹金殿,以至于唐太宗百般相劝许下诸多条件才得到其妾詹贵妃的谅解。戏剧中的詹贵妃拥有拒绝唐太宗,谅解秦英的选择权,自愿为了国家大义选择原谅秦英,这种选择权正是自愿性的体现,是詹贵妃发自内心的谅解。
文学作品中想象的自愿性恰是恢复性司法的重要原则。200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颁布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规定协商主体的自愿性是恢复性司法的一条重要原则。苏珊·夏普把自愿性作为恢复性司法五个要点中的第一个要点,即“恢复性司法鼓励充分的参与协商”,“鼓励”排斥了强制性的协商与恢复,如果当事人某方不具有“自愿性”,而是在国家、社会或是对方当事人、社区压制下强制协商或被动恢复,就无法对人际关系起到真正意义上的修补。被压制的一方或者多方不能有效参与到协商中来,不能形成利益相关者的“合意”,恢复性司法便失去了公正的价值。彭海青教授认为“自愿与明知”是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条件。自愿客观上要求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地位的平等,协商主持者中立,主观上要求各个当事人对协商过程结果的明知。
现代新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复杂的主体形式则对协商主体平等自愿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通过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达到“强国家—强社会”的目的。恢复性司法的运行是公共权力与私人交往的交叉地带,除国家权力、私人交往因素外,一些在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公共组织也参与其中。多因素的作用使协商过程十分复杂,各个参与主体之间有明显的力量差距,协商主体参与协商、进行协商以及协商结果都可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保障各参与主体的自愿性不仅是公正的要求,也是恢复性司法得以正常运转不被地方环境异化的必要条件。恢复性司法的自愿性以双方地位权利上的平等为基础,有必要赋予当事人知情权、咨询权、帮助权和撤回权等权利,尽可能地使每方参与人具备制衡其他力量差距方的能力,同时需要对协商过程进行监督并设置权利失灵时的救济制度。
积极补偿行为
文学赋予了同等地位的詹贵妃对抗不公正因素的能力,唐太宗不能下达“和”的指令命令两方,位高权重的长孙皇后与晋阳公主也无法依仗权势欺压詹贵妃。唐太宗就只得许下修庙堂、顶礼焚香的承诺,晋阳公主则捧御酒跪求原谅,犯罪人秦英也一改“不怨我”的说辞,先是知错后又搀扶贵妃。詹贵妃获得多种形式的补偿,终于了结心中怨恨,顽劣的秦英也真正被教育悔改。唐太宗提出赔偿时戏剧就从前半段的“闹”转向后半段的“商”,故事情节转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传统朴素正义观,“商”的目的就是为所受损害寻找相应公正对价;另一方面是积极补偿行为在修补犯罪损害、安抚被害人过程中独特的价值。
美国学者托尼·马歇尔将恢复性司法定义为“所有与特定刑事案件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一起共同参与处理犯罪结果的一种程序”。恢复性司法更改传统的“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模式为“犯罪人—受害人”模式,重视被害人的地位,强调对其遭受的损害进行恢复和补偿;犯罪人的责任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采取积极行动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鼓励悔过和重新回归社会。积极补偿是恢复性司法的实质性内容,是修补社会关系最主要的方式。
对于犯罪人来说,犯罪人对被害人负有债务,需要通过积极补偿向被害人清偿债务。一方面他必须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启动恢复性程序;另一方面犯罪人作为刑罚的承受者,需要积极赔偿,努力弥补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取得被害人以及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的谅解得到量刑上的优惠。对于处在“犯罪人—被害人”模式另一端的被害人来说,犯罪人承担责任的形式从以往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转变成承担对被害人具体现实的物质精神赔偿责任,被害人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而不再是刑事体系内“被遗忘的人”。正是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害的重视和补救,恢复性司法才发挥出着眼于未来、恢复现实具体的人际社会关系的效用。也因此刑事损害赔偿在恢复性司法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是恢复性司法的责任形式之一。不同的被害人在不同的刑事案件中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传统国家本位的刑事赔偿以惩罚犯罪人为出发点,忽略了被害人多样化的需求。在恢复性司法场域内,基于双方达成一致形成的“合意”具有契约的特点,契约的内容是多样的,根据契约双方主体独特的需求订立,从而满足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实际需要。比如犯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方式修补被害人被犯罪行为损害的财物;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赔礼道歉;未成年人必须通过自己劳动所得进行赔偿而不是由父母代为赔偿。同时损害恢复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个人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在尊重罪犯、培养其自尊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三、恢复性司法或为融“理”与“法”新路径
分析本土法治拆分出的“理”与“法”可以发现,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唐朝百姓“杀人偿命”的理念在唐朝法律甚至在现代中国法律中依旧存在,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适用范围越来越小;唐朝法律中“过失杀”不必偿命也是唐朝百姓完全可以接受的“理”。“理”与“法”是辩证统一、相互融通的关系,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必然的交叉地带,苏力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道路通向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本土法治,却忽略了即便在本土法治中同样有自上而下并不扎根于“理”的“法”,比如为维护贵族统治的“八议”制度就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不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哲学将并非发源于“理”的“法”解释为统治阶级将本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同时他们也关注被统治阶级的要求,但根本上是为统治阶级统治服务的。“理”与“法”的融通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或急或缓地发生着。同样对这种融通做出解释的还有自然法学派,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开始。《安提戈涅》将“理”视为“永恒不变的不成文神法”,而“法”则是“人定法的规定”。二者冲突时“神法”优先,强调自然和宇宙的理性。自然法与人定法分离,被以乔治·萨拜因等代表的学者们解释为一个步步为营的过程。海因里希·罗门称:“希腊人看来,所有的法律都盖有神的印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法学家夏蒙等人开始倡导“复兴自然法”,复兴自然法的一批学者被称为新自然法学派,与古典法学派明显不同的是新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是可变的”。
在法的讨论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自然法学派都是以“本土法治”为预设条件的。在面对“法律移植”时两种法哲学不同的观点导致的结论也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何种样态取决于统治阶级意志如何改变。当社会变革发生阶级变动时,新的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新法与原本与旧法相适应的“理”适应的范围就变得狭隘,而“法律移植”与本土法治的不适应,相对意义上就成为新法与旧“理”的不适应,与发生了一次社会变革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社会变革的结果与法律移植的结果同样是本土法治。而自然法学派认为“人定法”是以“自然法”为起源的,由于不同地域实质上的差异,这种“自然法”实际是本土意义上的自然法,然而无法回避的是法律移植时外来的“人定法”并不是从本土“自然法”中始发的,古代自然法思想无法解释这一突出矛盾,也无法解决法律教化作用对“理”的影响,“自然”范围的扩大,由此才出现自然法学派的妥协。
自然法学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唯物史观的观点,对各个法学流派优劣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本文旨趣。而是从自然法学派主张的流变以及不同法哲学的对比说明作为大众认可习惯的“理”与作为国家权利与意志体现的“法”是可融通的,具有可融通性,即使在自然法学派以“自然法”评判“人定法”正义与否的观点中,这种融通是始于自然法的,也因而是普遍的。“理”与“法”的可融通性在中华传统法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周礼》有“以礼乐合天地之化”。自周公制礼始,“礼”就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一条主线。“人而不仁,如礼何”居于古代王朝治国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也追求“礼”与人的情感的内在联系,因而古代法莫不表现出一种“融礼于法”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在社会变革、法律移植的过程中,融通仍然存在,只是融通范围变得狭隘、融合时间更加迅速,也具有融合时间上的可变性。在历史进程中这种融通又表现出宏观性、实质性的特征,它或表现为法律的修改或为大众价值观中“理”随法教化的转变,以一种“理”与“法”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相互转化变迁的形态出现,本文称其为“理”与“法”融合的第一条路径(以下简称第一条路径)。
“理”与“法”的可融通性与时间上的可变性为更加微观和非实质性的融通路径提供了可能。当融通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表现为即时性的融通;“法”或“理”体现在具体的个案中,而不是相对宏观的社会变革与法律移植;融通也并未导致某方实质性的改变,只是相互妥协从而达成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理”与“法”就具备了在具体个案中即时性妥协的融合路径,本文称其为“理”与“法”融合的第二条路径(以下简称第二条路径)。在《三哭殿》的戏剧结局“理”与“法”的冲突通过“和”要求司法过程具有恢复性予以调和,调和的过程也是“理”与“法”的融通,这种融通显然不同于以往融通的特征,首先不是“法”或者“理”实质性的妥协,普遍意义上的“法”与“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次这种融通并不是或急或缓的发生,而是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最后“法”与“理”普遍意义上的融通从法诞生时起就必然开始直至“法”与“理”再度融为一体,而即时性的融通只在个案中“情”与“理”发生冲突出现。是故文学想象中对司法恢复性的追求就具备了第二条融通路径的所有特点,也与恢复性司法的特征相同。
称恢复性司法为“理”与“法”融合的新路径并不是因为这种即时性的、短暂的个案融通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刑事诉讼产生的初期阶段,刑事诉讼被视为一种私人争端,诉讼程序的启动依赖于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控告,因此大多数的纠纷在私人领域内就已化解。比如中国周代的“调人”有“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的职责,而柏拉图则搭建了“哲学王”作为统治者的理想国。这种常见于古代刑事案件的调解同样具有融通性、即时性、个案性、非实质性的特点,似乎与恢复性司法具有第二条路径上的相同特征。因此有学者审慎地评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恢复性司法是古代司法模式更高层次的回归。
司法恢复性与恢复性司法的区别首先在于二者强调内容不同,司法恢复性强调恢复性,不以法律为必要规范;恢复性司法则落脚在司法过程中,现代司法在体现程序正义的法律规范下运作,依照法律进行司法活动的过程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过程。古代的调解作为司法恢复性的表现形式尽管具备“理”与“法”融合第二种路径的特点,但其背景是法制的,以“人治”为语境,以人的作用为依靠。“人治”是司法恢复性时代的背景,统摄“法”与“理”,因此即便《三哭殿》中的文学想象超越了三纲五常的“理”,脱离了贵族杀人不偿命的“法”,仍然无法超脱“人治”的枷锁,唐太宗是裁判者可以不依法,以人治为核心展开的司法恢复性是戏剧最深层的底色。
那么恢复性司法可以不依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活跃在古代社会的“人治”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法治被现代化文明社会奉为圭臬。恢复性司法作为现代化法治的产物不仅必须服从于其他法律,而且其内容也要被法律所规定,第二条路径的新旧之分就从“人治”与法治的区分上区别开来,人治与法治之别也是司法恢复性与恢复性司法的根本区别。法治背景下的恢复性司法作为融“法”与“理”的新路径有以下两个层次的构建。首先,它是第一条路径的产物,第二条路径虽有新旧之分,但它们都建立在“理”与“法”融通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第一条路径不具有“人治”与法治的区分,从法产生之始就不断运动融通。而第二条路径是以第一条路径的融通性为背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最终产生了“人治”背景下追求司法恢复性的调解与法治背景下的恢复性司法。从这个层次来说,第二条路径是“理”入“法”的体现,恢复的“理”影响呼吁“法”对其确认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次,它具有独特的能动性。这种独特的能动性首先与第一条路径的历史必然性相区别,具有即时性、个案性、非实质性的特征;其次与旧的第二条路径相区别,是以法治为背景的,能动性必须限缩在法律的范围内而不得超越法;能动的内容条件必须被法律有所规定。
原标题:《王伟|“理法”融通:从古典戏剧《三哭殿》透视恢复性司法理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