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要轻易靠近苔藓,那是时间留在地球皱褶的诗句

《苔藓森林》
苔藓常常被人忽略。作为最古老的陆生植物,苔藓早在四亿多年前就成功征服了原始的“不毛之地”。作为北美波塔瓦特米族原住民,作者对自然万物皆怀有敬畏之心,她将每种苔藓都看作自己的老朋友,去体悟如此微小生命所蕴含的深刻启迪。
今天夜读,是一篇令人容易迷上苔藓的文章,和作者共同感受“苔藓生于石上的辩证——一种巨大与微小、过去与现在、柔软与坚硬、沉静与波动、阴与阳的交汇”。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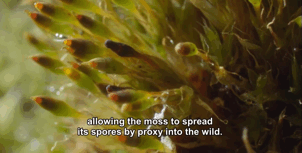
▲ 纪录片《苔藓的奇妙世界》
夜晚,赤脚走在这条小路上,柔软的泥土贴合着足弓。我差不多这样走了20年了,这20年就好像我人生的大半。我通常不打手电筒,任凭小路指引,在阿迪朗达克荒野的黑暗中,走回我的小屋。脚触土地,就像手抚钢琴,响起一支来自记忆深处、带着松针和沙土气息的美丽的歌。我太熟悉这里了,我知道怎样小心地越过那棵糖槭的粗大树根,带蛇每天清早都会在那里晒太阳。我曾在树根上重重地磕过脚趾,所以印象深刻。山脚下,雨水冲刷着小路,我绕道走进路旁的蕨类植物丛,好避开路上尖利的碎石。小路攀升,伸向光滑的花岗石,越过岩脊。岩石里还储藏着阳光的温暖,从我的脚底蔓延至全身。剩下的路就很好走了,沙地、草地,再就是我女儿拉金6岁时踩过大黄蜂蜂巢的地方,以及茂密的条纹槭树丛——在这里,我们遇到过角鸮一家,当时角鸮宝宝们在树枝上站成一排,正香甜地睡觉。再走下去,就要到我的小木屋了。在那里,我能听到春雨的涓滴,我能闻到春天的潮润,我能感受到渐渐增大的湿度在脚趾间弥漫。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个本科生,在克兰伯里湖生物研究站忙着完成野外生物学课程的结业研究。就是在这里,我头一回认识了苔藓。我脖子上挂着标准配置的“沃尔兹”科学实验用手持放大镜,每天跟着凯奇博士在树林里穿梭。放大镜是我从研究站储藏室借来的,挂绳已经蹭得黑乎乎的。这门课程结束后,我从自己大学期间攒下的本就不多的积蓄里拿出一部分钱,买了一个凯奇博士用的那种博士伦牌专业级手持放大镜。那时我便知道,我迷上苔藓了。
毕业后,我回到克兰伯里湖,做了一名教师,并最终成为生物研究站的主任。直到现在,我带领学生在克兰伯里湖周围小径做野外观察时,依然戴着这个放大镜,用一根红绳穿着。这么多年过去,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变化,这里的苔藓也像我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凯奇博士当年带领我们走“塔楼小径”观察到的小金发藓斑块还在那里生长着。每年夏天我都要停下来仔细观察一番,感叹它的生生不息。

过去的几个夏天,我都在研究石头,观察苔藓如何在巨石(指冰川漂砾)上聚集,想试着发现苔藓群落形成的秘密。每一块巨石都像一座荒凉的孤岛,静静地停泊在挤挤挨挨的森林中。只有苔藓以它们为家。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想知道,为什么在一块巨石上有10种甚至更多种苔藓共生,而在旁边另一块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巨石上,却只有一种苔藓独自生存。
冰河时期的巨石遍布阿迪朗达克山脉,这些巨石是一万年前冰川留下的磨得浑圆光滑的花岗岩。巨石上布满苔藓,让森林看起来更具野性,我也由此意识到周遭的景观发生过多么大的变化。这些巨石曾经搁浅在冰川冲蚀沉积而成的荒芜平原上,如今它们周围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槭树林。
大部分巨石高度只到我肩膀,但有的很高,我得爬梯子上去才能做全面的观察。我和学生们用卷尺测量巨石的周长,记录光照和酸碱度,统计巨石上的裂缝数量,量出表层薄薄的腐殖土的厚度。我们仔细地记录所有生长于此的苔藓的位置和名字:曲尾藓、棉藓。学生们忙不迭地记下一长串名字,嘴上喊着为什么没有短些的名字。然而苔藓大多都没有俗名,因为关注它们的人实在太少。它们只有学名,伟大的植物分类学家卡尔·林奈早已为植物订立了一套国际通行的学术命名体系。出于对科学的浓烈兴趣,甚至林奈自己的本名、他的瑞典母亲为他取的名字CarlLinne,也被拉丁化了。
这里的很多巨石都有名字,人们把它们作为湖边区域的地标:椅子石、海鸥石、火焦石、大象石、滑梯石……每一个名字都能引出一个故事。每当我们叫出它们的名字,都会与这里的过去和当下产生联结。我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她们天然地认为所有的石头都有名字,还自己发明了好些名字:面包石、奶酪石、鲸鱼石、读书石、潜水石……
为石头或其他事物取什么样的名字取决于我们的视角:站在圈里或是圈外。我们嘴上念着的名字,反映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有多少,所以我们总会用充满爱意的私密称呼来呼唤自己爱的人。而我们给自己取的名字,则是一种强有力的自我宣示,是对自我独立性的声明。站在圈外,苔藓拥有学名也许已经足够;但是站在圈内,它们会怎么称呼自己呢?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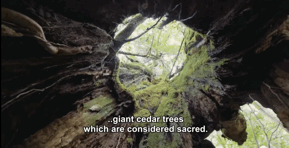
克兰伯里湖生物研究站的一个优势是,它每一年的夏天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好比我们每年六月都穿上同一件衣服,比如一件褪色的法兰绒衬衫,上面还带着上一个夏天木头燃烧的烟火气息。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基调,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是这个世界诸多变化之中的一个常数。每个夏天,森莺都会在餐厅旁的云杉上筑巢。每到七月中旬,蓝莓成熟之前的时节,一头熊总会在营地附近晃悠,饥肠辘辘地找东西吃。海狸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总在日落前20分钟游过研究站前面的码头。早晨,雾气总是散得很慢,依依不舍地在熊山南边缭绕。当然,也会有些小插曲。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冰有时候会悄悄带走岸上搁浅的木头。……我的身体和这片土地亲密无间,从中我找到了力量和安慰。这是一种知道每一块石头的名字的感觉,是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栖居何处的安心。在这片荒野,在克兰伯里湖岸,我内心的风景就是这片土地的完美映像。
所以,今天看到的一切让我很惊讶。这里原本有一条熟悉的小路,它从我的小屋门前延伸出来,顺着湖岸一直往下,大概有几英里长。可是眼下,路被挡住了。我迷失了方向。我深吸一口气,四下张望,好确定自己仍然在那条曾经的小路上,而没有走到晦暗不明、难以看真切的陌生地带。这条小路我走过无数次,然而直到今天我才把它看清楚:这里有五块巨石,每一块都有校车大小;它们靠在一起,棱角相嵌,好像多年的夫妻温情相拥。一定是冰川将它们推到一处,形成了这样充满爱意的造型。我绕着它们静静地走,手指触摸着它们身上的苔藓。

在东边,岩石间的暗影里有一处洞穴一样的开口。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它在那里。很奇怪,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扇“门”,但此刻它看起来非常熟悉。我们家是波塔瓦托米部落熊族的后裔。熊掌握着对人类至关重要的药学知识,它们与植物有着特别的关系,能叫出所有植物的名字,知道每一棵植物的故事。人们会向熊求取预言,以找到自己应当去履行的使命。我想,我在追寻的,就是一头熊。
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已经警觉起来,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侦察外来者的踪迹。我身处一个安静得有些异常的小岛,时间仿佛岩石一般滞重。不过,当我摇了摇头,眼前变得清晰时,我便又听到了熟悉的浪花拍打湖岸的声音,还有橙尾鸲莺在上空叽叽喳喳的鸣唱。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洞穴,然后手脚并用地爬进那片黑暗,在我上方,就是数吨重的岩石。我想象着发现一头熊的巢穴。我往前爬,胳膊擦过粗糙的岩石。转过弯,身后的光亮就彻底不见了。洞穴里的空气凉凉的,没有熊的气味,只有松软的地面和花岗岩的味道。我用手摸索着继续向前,但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向前。前面的路向下倾斜,地面上是干燥的沙子,好像雨水从未抵达过这里。再往前,转过一个拐角,洞穴开始向上延伸。前方有穿过森林的绿光透进来,于是我继续前进。我猜自己是爬过了这片巨石下的一条隧道,马上要来到另一头了。我从隧道里挤出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置身于森林。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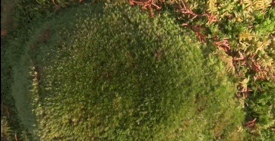
我来到了一小片草地上,环绕四周的是坚固的石壁。这是一间石室,光从上方打进来,使得这间石室就像一只望向蓝天深处的眼睛。火焰草正在盛开,草香碗蕨沿着石壁底部长成一圈。我处在一个环形的空间里。除了我来时的通道,再没有任何开口,而且就连刚才的入口似乎也在我身后闭合了。我再望向四周,竟然看不到任何出口了。一开始,我很害怕,但脚下的草在阳光下散发着暖暖的香气,石壁上的苔藓间滴落着水珠。奇怪的是,我还能听到外面树林间橙尾鸲莺的叫声,我仿佛身处一个海市蜃楼般正在消散的平行宇宙,只有这片布满苔藓的石壁围绕着我。
在巨石的环抱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为何游离在思维和感觉之外。这些岩石充满了意图性,是一种吸引着生命的深沉的存在。这是一个力量之所,通过一种很长的波段振动进行能量交换。在岩石的注视之下,我的存在得以被认可。
这些岩石已经不知道在这里挺立了多长时间,也没有必要再用坚固来形容它们,但它们却不得不臣服于那柔软的绿色之息——苔藓销蚀着它们的表面,一点一点地让岩石重归于土,这些绿色的生命像冰川一样强大。苔藓和岩石之间进行着一场远古的对话,这对话一定是诗,关于光亮,关于暗影,关于大陆的漂移。就是这样的诗,被称为“苔藓生于石上的辩证——一种巨大与微小、过去与现在、柔软与坚硬、沉静与波动、阴与阳的交汇”。在这里,物质与精神共生。

对科学家来说,苔藓群落或许仍然是神秘的存在,但苔藓自身却彼此了解。作为亲密的伙伴,苔藓熟知岩石的轮廓。它们记得水流过裂隙的路线,就像我记得回到小木屋的路一样。站在这个圆圈里,我知道,在林奈双名法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苔藓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时间啊,流逝不停。
我不知道自己出神了多久,是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那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存在没有了感知。只有岩石和苔藓,苔藓和岩石。仿佛有一只手温柔地放在我的肩上,让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感知当中,向四周望去。我回过神来。我又能听到橙尾鸲莺在上方歌唱了。环绕四周的岩石上有各种各样的苔藓,石壁光彩照人,我再次看到它们,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此时此地,绿色的、灰色的苔藓,新的、老的苔藓,仿佛在冰川之间栖居一处。我的祖先知道,岩石记录着地球的故事,有一瞬间我听到了它们的讲述。
这时,我脑子里的想法吵闹起来,烦人地嗡嗡叫,扰乱了石头之间安静缓慢的谈话。石壁上的门又出现了,时间也开始流动。进入这石头的入口被创造之时,便给予来者一份馈赠——我能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了,既从圈内,也从圈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使命。我完全无意于命名这里的苔藓,给它们冠以“林奈式名称”。我想我从这里得到的使命是,告诉人们苔藓拥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不能只用数据来描述苔藓的生命与存在。它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秘密不是量尺能够测量的,提出问题、找出答案的逻辑在岩石和苔藓的内在真实面前无足轻重。
出来的时候,隧道似乎没那么难走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回头看看巨石,然后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回家的小路。我知道,我正在追寻一头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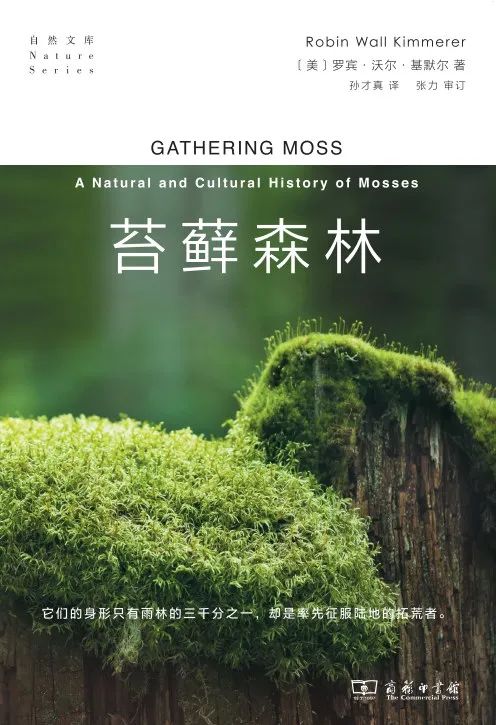
《苔藓森林》
罗宾·沃尔·基默尔/著
孙才真/译
张力/审订
商务印书馆
原标题:《不要轻易靠近苔藓,那是时间留在地球皱褶的诗句|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