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朔《动物凶猛》③|一个人成熟的恋爱观是什么?
10天共读一部经典好书,满足你的知识渴求。
「经典共读精华领读」栏目开启4年了,未来我们会在持续提炼人物传记精华内容的同时,新增心理、影视原著、社科、现代文学等多领域共读书目,为你带来更加新颖、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激发你对人生的深度思考。
这一次,我们读的是著名京派作家王朔的代表作《动物凶猛》,本书是豆瓣高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原著,讲述20世纪70年代一群大院少年五味混杂的青春期生活。让我们共同阅读这本书,回忆青春里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阅读,既是一种陪伴,也是为了更好的成长。
领读|辛峰
十点人物志原创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动物凶猛》。
昨天我们读到了《动物凶猛》里故事的主人公“我”在米兰的家里看到米兰的照片引起相思继而守候,以及后来在大院里偶遇狐狸脸女孩的故事。
换句话说,青春期里那个在后来看起来可有可无的细节,在当时的主人公的生命里却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么,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下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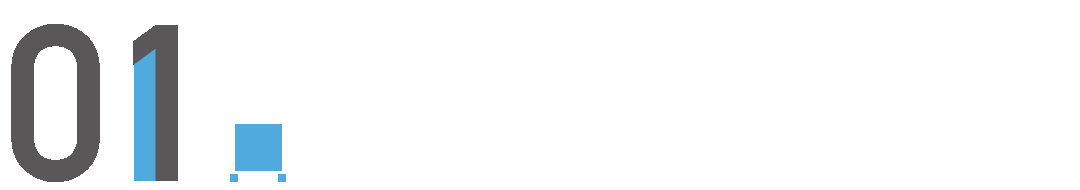
熟识于北蓓
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
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
类似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
父亲进来视察时,我已经睡了。当他放心地回房后,我便重新穿上衣服,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潮湿柔软的土地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的天空还未受到严重的污染,比现在透明度好,月光更有穿透力,星星也比如今繁密璀璨。
我沿着一扇扇窗前的杨树林走。银光闪闪的杨树叶在我头顶倾泻小雨般地沙沙响,透出朦胧灯光的窗内人语呢喃,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猫蹑手蹑脚地走过。
我穿过一个个跨院、夹道、小广场和花园,路过八角香楼时,从装着铁栅栏亮着灯的地下室窗户,看到我们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卫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

我来到后院墙杂草丛生的废弃游泳池边,远远看到黑黝黝的假山上,中间的那个亭子里有几颗晃动的忽明忽暗的烟头。
果然,他们都在这里,那个狐狸脸的女孩坐在高洋身边,笑吟吟地从容应付他们厚着脸皮开的玩笑,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烟。
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
于北蓓比我们中的哪一个都大,当时十八岁,应该算大姑娘了,可智力水平并不比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更高。
她比我们要有些阅历,称呼起我们来一口一个“小孩”,提到不在场的人,也总说“那小孩那小孩”的。

她对我说话很随便,态度很亲热,一见我就和我开玩笑,说我长得很乖像个女孩儿。这使我又喜欢又窘,一向伶牙俐齿的我当时却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脸也一定红了。
除了哥们儿,从来还没一个人这么亲昵地对待我,更别说是个姑娘了,她那种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态度一下就把我迷住了。
因为只有她一个女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说过分的话。
大家问她愿意跟我们中谁,她觉得我们中哪个更漂亮。当时奶油小生还不是贬义词,很受少女青睐,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漂亮、健康的男孩子,后来我再也没交过这么一致漂亮的男性朋友。
她胡乱指,甚至还指了我。虽然是戏言,可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宽容地把她列入可以配得上我的那一档。
她向一边挤挤,挪出一个空位,招手叫我坐到她身边,这在她并非有意引诱和挑逗,仅仅是为了使玩笑更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令气氛更加活跃。
我坐了过去,充满自豪。她用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令我立刻透不过气来,这时我发现她原来就是和高洋勾肩搭背坐在一起。
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打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
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
说完好汉说侠女,谁最近又转入谁的手中“带”着,哪次有名的斗殴其实是哪个女的引起和召集的,后来又开始聊起本市哪个大院的女孩漂亮多情,哪条街上时常会出现一个绝佳少女而且目前不属于任何人。
这时,高晋提到了米兰的名字,她显然是于北蓓的女友,他们见过她。高晋请求于北蓓下次把她带来“认识一下”。
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

高晋表示他是真喜欢米兰,务必请于北蓓帮个忙。
于北蓓说米兰挺正经的,她和她说过好几次她都不肯来。
她搭在我肩上的手夹着烟,不时歪头凑手吸上一口,这时她就把我搂紧了,脸几乎挨上我的脸,我甚至能感到她眨动的睫毛在我面颊上引起的柳絮扑面般的茸茸感觉。
夜色中浮动着假山上栽种的丁香树、香椿树和其他草木的馥郁芳香,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
后来,夜深了天也凉了,山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
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
当夜,我和汪若海结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待了两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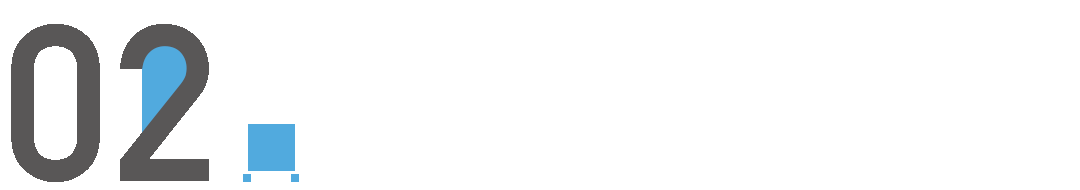
去看于北蓓
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的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
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
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
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坐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在游逛。
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
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问他怎么没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
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开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
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
我怀着忐忑不安和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望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
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
他家的偏院内十分静谧,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
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再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
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

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
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
我点着一根烟,坐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
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了,撂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不净骂着脏话。
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
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
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
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嘴里说:“这帮土匪。”
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屋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

“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吗?”
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
“没有。”我当即否认。
“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
“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
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谬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我变得快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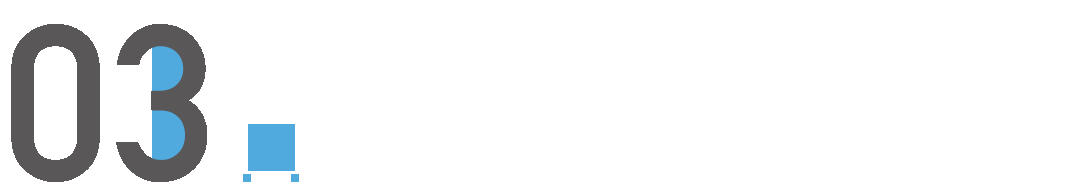
与于北蓓厮混
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
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可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下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
“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吧?”她把脸凑上来盯着我问,一口烟喷到我脸上。
“根本不是。”我挥手赶散烟,又向她脸上吐了口烟,“我是我们家挨打次数最多的。”
她在烟雾中睁着眼睛笑,鼓足腮帮子用一个手指敲腮帮子侧,吐出一连串的小烟圈,“真看不出你像坏孩子。”
她一张嘴说话,烟就全吐了出来,她又吸足了一口,全神贯注地制造烟圈。
我真想用两指使劲一捏她圆鼓鼓的腮帮子,来个一气尽吹的效果,想得心里直痒痒,就是不敢真伸手去捏。
“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我对她解释,“学校老师也都刚见我挺喜欢,后来没一个不讨厌我的。”
“你会吐大烟圈吗?”她忽然过来,扒着我肩膀,一嘴烟气地问。
“不会。”我说,吐了一个,果然不成形。
“我会。”她说,在我耳边接连吐了几口烟,但无一成功。

“前两天我还吐出一个特大的呢。”她说,很有耐心地坚持吐。她嫌这儿靠近窗户有风,坐到墙角的藤沙发上面朝墙吐。
我问她上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她回头告诉我她早就工作了,初中毕业便去郊区一个果园农场当农工,每个月挣十六块钱工资。
“我现在是学徒,出师后就能挣三十多块钱了。”她补充说。
“那你够富裕的。”我表示对她已经挣工资的羡慕。
接着我问她老在外边“飘”,她爸爸不生气吗?每天和男的混在一起。
“他都气死了,可又没办法。”于北蓓笑着说,“好几次都说不认我这女儿。”
“打过你吗?”
“怎么不打?捆起来打。”于北蓓做了个手脚被束缚的样子。
我抓紧时间教育她,“其实你没必要每天不回家,在男的这儿住。我们都挺坏的,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多不好……”
“他想打我,可打不着,一打我就跑。”于北蓓听清了我的话,好笑地望着我,“会出什么事?我早出事了,还等到你们这儿再出事?”
她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烟蒂扔到地板上用脚碾灭,抬头又白了我一眼。
我惭愧地低下头。
她忽然怒容满面。
吃饭的时候,她对我很冷淡,不停地和别人说笑,玩笑开得比昨天晚上更加露骨,使得一屋人兴奋异常,开心的哄笑声几乎掀翻屋顶。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一边用筷子把菜盘里的肥肉挑拣出来,扔进我盘里,我把那些肥肉又一片片夹到桌上,很快便堆起了白花花、油汪汪的一坨。
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
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
大家呼啦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
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

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
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分量。
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
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谈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吗?
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怂恿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拧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龇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太没轻重。
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
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他一开口我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
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
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眷恋。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动物凶猛》里故事的主人公与狐狸脸女孩于北蓓从相识到打闹继而厮混在一起的日子。
换句话说,青春期里的暧昧似乎都是甜的,但这甜中带酸。对于主人公来说,却是懵懂人生中对情感的初体验。那么,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原标题:《王朔《动物凶猛》③|一个人成熟的恋爱观是什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