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落马村官出狱后:60岁,他从零开始学做工丨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丨杨海滨
编辑丨柳逸
编者按:
四年前,杨海滨曾记录了豫北村官马国力(化名)政治生涯的极速下跌路(详见:镜相 | 村官马国力的急速下跌路)。他曾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享受着村支书的特权与荣耀,落马后,五年的牢狱磨平了他的骄傲,也磨损了他的基本生存。落马村官出狱了,如今,他在街心公园流浪、像老鼠一样溜回村庄,又企图重新直起腰杆,希望“归来又是一条好汉”,他进工厂学做工、跟师傅卖烧饼,战战兢兢,渴望再次走回正常生活的人行横道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封面图出自《大江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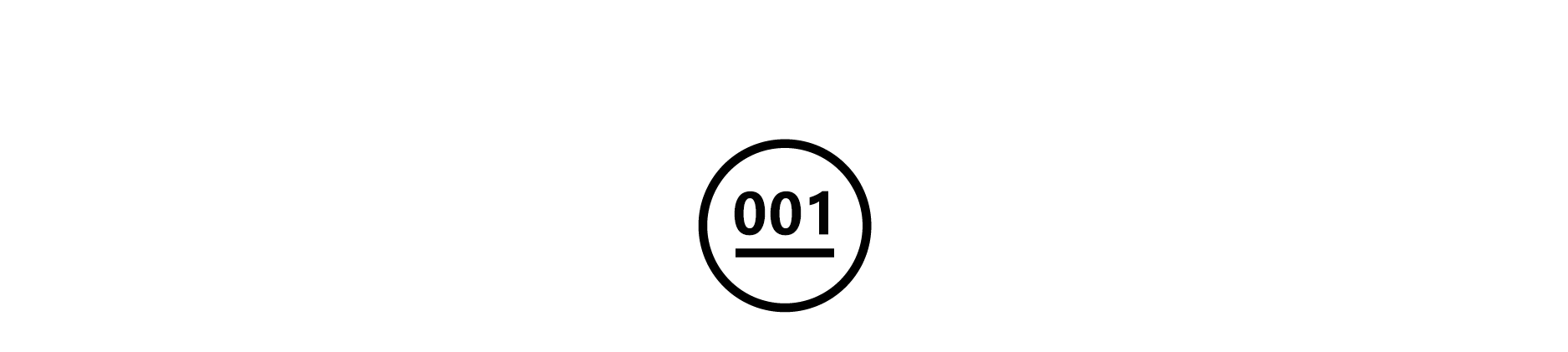
2017年10月8日上午8点,马国力在新乡监狱,穿着印有白灰条纹的监服,正努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办完最后一道手续,进入最后一道大门——会见室,他看到了老婆提前送进来的便服,一时间竟感到眩晕,如同1995年在厦门第一次看见大海时涌起的波涛让他眩晕。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快速脱光全部衣服,准备迎接自由人的生活。
五年后,2022年的深秋,天气渐冷,郑州街头公园的长条椅已不容他再躺在上面夜宿了,他忽然决心“从哪摔倒就从哪爬起来”,结束流浪般的生活。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他犹如梦游者,偷偷摸摸回到了W县老家的村里。
街道上没有一个人,他如老鼠“哧溜”一下就闪进自家杂草茂盛的荒院,看见自己当年旧生活的痕印,如今被五年半的岁月抹掉了颜色,只留下惨白,他若有所思地愣在了原地。数行眼泪被微风刮干后,他去邻居家借来铁锹,清除杂草。那个他叫叔的老男人看到他,愣了,不确定地说“你真是马国力?”,到了傍晚,他从监狱回来的消息如狂风掠过原野,不时有人来他院里看热闹似的跟他打招呼。

马国力在农村住着的那条街(作者供图)
马国力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才有空坐下给发小邹海伦打去电话,说自己已回村。邹海伦早年在县城开饭店,马国力每次去县里办事,都不时带着村委几人去他饭店吃喝,从来没结过账。那年邹海伦儿子初中毕业后想当兵,可条件不够,邹海伦找到马国力,让他想办法,马国力利用自己的关系,硬是把他儿子送到部队当了消防兵。后来邹海伦有了外遇,和发妻离婚,原配死活不再嫁人,也不愿离家,他对马国力下命令说:“赶快划个宅基地,不然就得住大街了!”马国力顶着镇政府的压力,在出事前一年,把村里的耕地划给他了一座。按规定每户要给村委会缴纳5千元费用,可他对几个村委说:“邹海伦的钱就不收了,咱们过去几年在他那吃饭喝酒的钱,早超5千了。”后来邹海伦生意倒闭,回村组了个建筑工程队,自己当老板,专门承建农村别墅楼房,一年能挣不少钱。马国力打电话给他就是冲着这点。
邹海伦扔下电话,带着两根黄瓜、三个西红柿、一瓶“仰韶彩陶坊”到了他家。俩人刚坐定,马国力故技重施,说:“你还记得你儿子咋当上兵的?你那院子是咋到手的?”每当他说起这些事,总习惯性地仰着头往上点几下,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邹海伦瞬间接住了他的话,并往高处推了推,说:“这辈子是忘不了了。这不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立即到你这报到来了。”马国力如三九天泡在热水澡堂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喝酒时,邹海伦问他,“这几年过得还行吧?”,这一问让他瞬间想起处于人生分水岭的那个时刻——2017年10月8日上午9点20分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那时他站在门外,并没有看到家人来接,一个人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人喊“马国力!”。他习惯性站直身子,身体向前倾斜30度,应了声“到!”,须臾才醒悟自己已出了狱,立刻放松身体,转过头,看见老婆正从远处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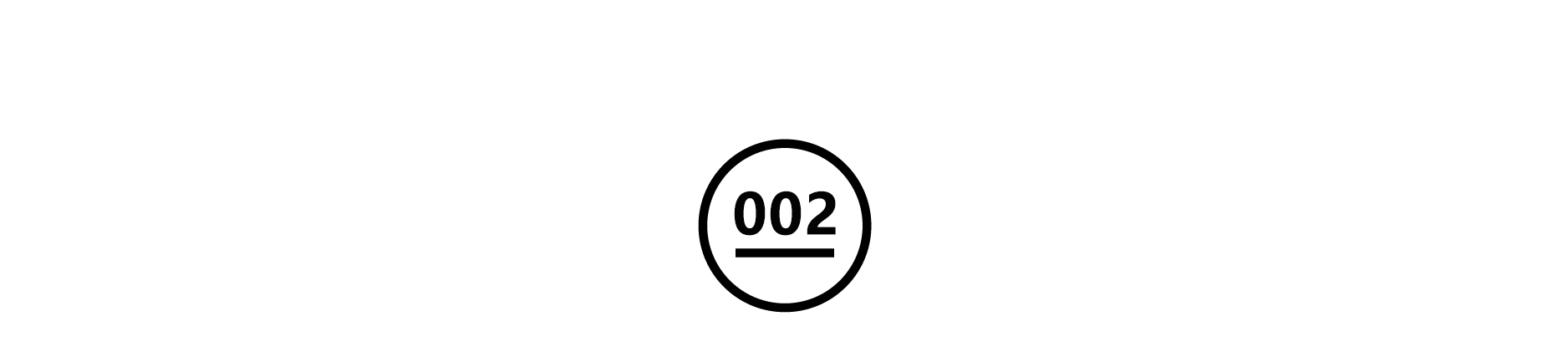
往事历历在目,这几年的新生活就是从这场景开始的。当时他急切地问老婆:“就你一个人?”老婆充满火药味地反问:“难道还要举行欢迎仪式?”他听了将嘴边的话咽回肚里,跟着老婆上了公交车,晃悠好久才在市里“丹尼斯”站下了车。老婆走进超市直奔男装专卖店,又买了一套衣服鞋袜。他说:“身上这套不是你刚才送进监狱里的,又买?”她回道:“彻底去去你身上的晦气。”出了超市,他终于在门口看到了期盼已久的儿子。
其实儿子见他时并没说话,他却听到他喊他“爸”,还突兀地高声应了一声,这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娘俩狐疑地相互看了一眼。儿子说:“我陪你去洗浴中心洗洗澡,也算为你洗晦气。”
儿子以前在新乡市当消防兵,复员后就在新乡定居,当年买房时他还没出事,
还是他做主选择了靠郊区的小区,没想到房子刚买过,他就在W县被判刑,并被送到新乡监狱服刑,注定和儿子咫尺天涯、同住一城。现在他跨越咫尺,回到了儿子家,可明显感到了陌生。吃晚饭时,儿子像在看他,其实是把目光射向他头顶上空,用漠然的口气说“把饭吃饱”,却把“爸”字省略。四岁的孙子也带着小心翼翼的神态注视他,只要他伸手,孩子就做哭泣状。他知道儿子家没自己的位置,五年半来的缺席让他成了多余的人。
晚上他躺在宽大的床上,听不到呼噜声,放屁声,磨牙声,竟失眠起来。他心想还是回老家休养比较好,可一想到自己在村里14年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得罪过不少人,现在以劳改释放犯的身份回家,不是让那些人嘲笑自己吗,脸面没地方搁。但不回老家住,在儿子这又格格不入,他就在回与不回间反复踟蹰,想到天亮。吃早饭时,儿子还是连声“爸”都没叫,这让他坚定了回老家的决心。
到达W县的长途汽车站时已是下午3点,就在距离村头两公里时,昨晚上的犹豫又重新开始了,他感到脊梁发凉,正好看见旁边有个凉皮店,便进去要了份凉皮,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天黑后才匆忙回到老宅,幸好一路没碰到人。但院里早已荒芜成了草原,因家里常年无人居住,欠着电费,线路早被电工掐了,他只能就着朦胧的光走进屋,可立刻就被飘出的陈年腐味刺得连打了四五个喷嚏。
他坐在屋里摸着黑给现任村长来福打去电话,问他父亲来耀先的电话号码。来耀先在他当最后两届村支书时是村长,俩人搭班,关系密切。来福在电话里说,他父亲在他出事后的第二年,就在换届时落选了,随后就和陕西户县的战友在那开了家面食加工厂。他一阵窃喜,当即给来耀先打电话说自己回了村,但村里的气氛诡异不适合居住,来耀先说:“那你明天就来西安吧,这边的工厂需要人。”
马国力躺在五年半没睡过的落满灰尘的沙发上,似睡非睡地熬到四点半就起了床,也不洗漱,直接往镇上方向走去。在村口,他碰到七十多岁的老支书在散步,当年就是他让他先当了民兵营长,然后一路提携他干到支书,他是他的引路人。按理说,在他回村后理应先去看看老支书的,可他眼下的身份让他丧失了自尊心,也就不讲情面地谁也不见了。不料在逃离村子前还是碰到了他,马国力故意装作咳嗽,捂着脸快速走过,走出老远后回身一看,见他仍在审视他的背影,便加快脚步如丧家之犬般落荒而逃。
他坐头班车到了洛阳,然后坐火车去了西安,来耀先早在出站口等他,接上他直接到了户县工业园区的一家饭店,他说:“专门为你接风洗尘,咱俩好好喝顿酒。”同时从塑料袋里掏出两瓶“国花瓷10年西凤酒”,和他推杯换盏。红烧肉、清蒸鱼、海鲜,各种硬菜轮番上了桌。来耀先不停地说:“今天非把这五年缺的酒给补上,这肉也给吃上。”
约二十分钟后,马国力的胃开始翻腾起来,呕吐不止。来耀先困惑地说:“以前你是两斤的量,就是几年没喝这一斤应该也没问题啊。”马国力吐出一股鲜血,满脸痛苦地说:“我五年半没喝过一口酒,这么高档的酒都没见过,也没吃过这一桌的肉菜,脾胃早已不适。”说完又吐出一股鲜血。
来耀先赶忙把他扶上车,直接送到户县人民医院,医生一检查,说:“基本可以断定是十二指肠溃疡导致的吐血。”来耀先对医生说,“他刚从监狱出来还没过三天,今天给他洗尘喝了‘西风’酒就吐血了。”医生把正看片子的头转过来,用白眼斜视他:“不用说了,因情绪激动造成肠胃不适才胃出血,赶紧住院。”
十天后他出院来到食品厂,来耀先说:“厂里工人多,我给你特意安排一间人少的屋住。你的具体工作在运输部,每天上午和下午往市内各超市送成品,你自己负责装卸。”来耀先看着他意外的神情又说,“咱这是私企,一人得抵两人用,你要理解。”
他想起那些年在村里都是自己特别关照了他,连电话费这样的小事,都在年底奖金中悄悄给他多发600元,而别的几个委员一分钱也没有,更不用说别的小事了。现在自己落难来投奔他,想图个轻松高薪的工作,他却让他干体力活。他倒不怕体力活,在监狱里干了五年早已适应,就是觉得和他想象的相差太远,不像同村搭过班的老朋友。马国力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感叹,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人情就像当年患难时共同吃的那个馍,经历五年半都发馊了,而且馊味只有他独自品尝。
第二天上班,第一趟去市里送食品,路上司机接到电话,得知他母亲突发心梗,便把车停到路边打车去医院了。马国力没出事前,在村里是第一个有轿车的人,车技很好,只是五年半没摸过车,也不熟悉交通道路了,在该拐弯时他却走了直行道,坐在身后的女工大喊“走错了!”,吓得他猛踩刹车,结果让后面紧跟着的轿车一头撞了上来。
交警问他要驾照,他说自己没驾照,交警说没照你都敢上路?他理直气壮地脱口而出:“我刚从监狱出来,请你原谅。”交警对他的直率感到惊讶,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当听到警察准备对他罚款200元拘留15天时,脸色瞬间惨白起来,浑身颤抖着被警察带走。
那个女工回到厂里,把马国力在街上出的事,给来耀先汇报了一遍,不等她说完,来耀先便一拍大腿,骂道,“他妈的真是个信球(河南方言:傻瓜)货,住监狱住傻了,主动交待住过监狱,还无照开车?他还以为这是他一手遮天当支书的那个村咧!”来耀先骂完却又叹了口气,还是替他交了200块罚款,半个月后马国力出了拘留所,回到食品厂。
马国力觉得食堂的伙食费太高,便在一个调休日到二手市场买了个煤气罐,又买了天然气灶和一个铁锅,准备自己开伙,本还想买个碗的,又觉得锅可代碗。食品厂附近没有天然气站,他又用了数天时间在下班后四处转悠,终在十公里外的一条街道找到一家天然气站,他骑着借来的三轮把那个空罐灌满气,运回厂里,在三人共住的房间做起饭来。
开始时那俩室友还同情他,时间一长,他又是炒菜又是煮汤,把整个房间弄得乌烟瘴气,让室友最不能接受的是,轮到上夜班、白天睡觉时,他在那炒菜的鼎沸声让他们睡不成觉。室友要求他调换宿舍。来耀先找到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休息不好就会影响工作质量。你要是真想自己做饭,那你搬出宿舍,自己去租屋……”
他琢磨着他的意思,明白再这样下去就得走人,以往那种伤感再次如雾弥漫开来,他想说“去你的,老子不干了!”,可转眼又用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来自我安慰,叹自己只会当支书,还真没啥手艺活,遂停止在宿舍做饭,回去吃食堂。
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要靠食品厂挣钱生活后,从此踏实工作,只要接到通知,即使正在食堂吃饭也会放下碗筷,第一时间出现在仓库装车,一个人押车到各个超市卸车。冬天的时候,户县很冷,即使再冷,一天也要跑数趟送货。那天他又去某超市送货,当他搬着一筐馒头走到超市前,不料地面冻着的一层冰让他滑倒,正好冲出一个中年妇女骑着电动车,朝他的胳膊上轧了过去。到医院一拍片,果然骨折了,他打了石膏,将胳臂包扎好吊在胸前,继续押运送货,也没休过病假,厂里规定,一旦休假了就没工资。
有天他跟老婆通话时说起这事,发牢骚地说来耀先不念旧情,也不照顾他。他老婆略微停顿,说:“儿子住的这个小区太靠近郊区,买个烧饼都得走半小时到城内,我早想让你回来卖烧饼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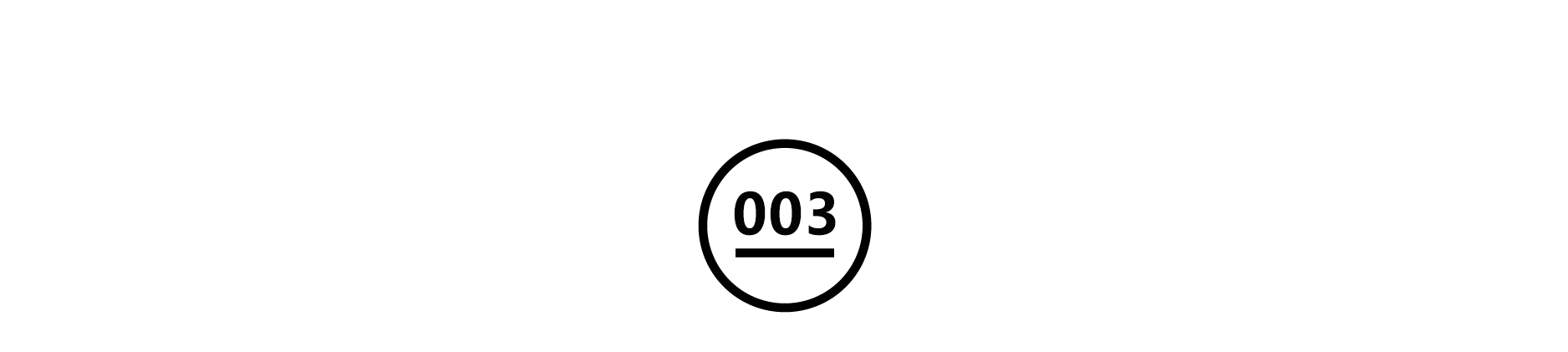
马国力从陕西户县回到新乡的那几天,天天和老婆在街上寻哪家烧饼做的好,最后在市内看到“登封五香烧饼”店前常有人排队,老婆对他说:“看见没?只要排队,就说明烧饼好吃,咱们去跟师傅套套近乎,你跟他学手艺。”
老板听她说眼前的男人想跟他学做烧饼,用怀疑的口气说:“咦,没出息的人才干这行。”他老婆一听人家不教,带着讨好的口气说:“他就是没出息的人,让他给你学费,你就教教他吧。”老板又说:“不用开玩笑,恁整齐的人咋会学做烧饼?我不信。”直到他老婆用微信转了500元学费,老板才相信,盯着没有说话的马国力看,心里还在想着他为啥要学做烧饼。
第二天上午8点,马国力跟着师傅先学识别什么样的面粉适合做烧饼,然后学和面时开水和冷水的比例,需要多长时间省面,省到什么程度,揉面的顺序和方向,还学五香调料的配制。他这才知道五香并不是五种香料,而是十二种香料,当然还有几种秘籍。
人过50不学艺,这是古话,马国力没想到都60岁了还要学做烧饼,不仅要学,还得好好学。白天师傅讲的技术他记不牢,五年半的监狱生活让他的脑子变得很迟钝,他专门买了个日记本,把师傅说的那些技术,如五香配料等等记得清清楚楚,关键处还画上画,尽管那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他知道这些秘籍是他将来的生存法宝。
马国力学成出师时,师傅特地送给他一口崭新的老式铁鏊,这东西做起烧饼来特别能散出小麦原味香气,也是师傅的秘籍之一。他背着铁鏊回到儿子住的小区,租下了药店与蔬菜店中间的半间门面房,也做了个“登封五香烧饼”门头。他戴起白圆帽,围着长白围裙,严格按师傅说的步骤做,很自信地把烧饼一个个放进白色泡沫箱里,置在店面前最显眼的位置。但小区的人还是习惯到几公里的市内买,起初他以为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烧饼店,就印了几百张A4纸广告,写了地址,特别注明1块钱1个,5元钱6个来吸引顾客,可一天也卖不出去20个,只好让他老婆把剩下的烧饼拿回家自己吃了。
有天中午,他闲时打开微信收款,查看今天挣了多少钱,突然发现一笔1万元钱的转账。他吓了一跳,这不是飞来之财吗。一回想,确实有个男青年在早上买过一个烧饼付了1块钱,但他的微信没设提示音,当时没在意,现在一想可能是那人把密码当金额了。他犹豫了好久,想把钱昧了,可又怕出事,就给老婆打电话说了这事,老婆说:“鉴于你的身份,赶紧报警,以免人家找上门来,脸上不好看。”他这才报了警,直到第三天,那个男青年和派出所的人来找他。男青年要给他五百元感谢他,被他拒绝,结果那人把当天所有烧饼都买走以示谢意。

马国力夹在两店中逼仄的“登封”烧饼店(作者供图)
但那之后,他的生意依然十分冷清,他咬牙坚持着,想着只要能熬过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他的烧饼店了,就能像师傅那样有人排队买他的烧饼。直到半年后,不要说挣钱了,反倒贴了5千元的房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认定是他租的房子风水不好,得换地点。
于是他选择了在小区大门口的一间房子,尽管房租比原先高了近百元,可位置显眼,进出小区的人都能看到,而河南人的传统是晚饭都得喝汤吃馍,不可能离开烧饼,他便重复以前的那个广告,并将优惠的5元6个烧饼换成只要一次买10个烧饼另送3个,同时将海带、鸡蛋、豆腐皮在卤汤里卤上一天一夜,放在烧饼箱边的火炉上,提供烧饼夹菜。数月后,卖出的数量还不如没搬家时多,光房租就用完了他在陕西户县挣来的全部工资,他最终在“自己不是经商的料”的哀叹中收了摊。
晚上在儿子家,儿子儿媳看他的神情仍有十万八千里,这再度让他尴尬。老婆晚上躺在床上对他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你就算是杀人犯,被政府判死刑,尸体也得拉回老家,那才是你的家。我觉得你从监狱出来以后,像在盲道上摸索着找不到人行道的盲人,只要你回到家,就能睁开眼看清路,那才是你正常生活的道路。”老婆见他不吭声,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又说:“面子值多少钱?你得面对现实!当年你出事后,村里有多少人等着看我笑话,我戴个口罩、帽子,出门时低着头不给他们机会,不是挺到你回来了!你回去后把自己打扮得精神些,在村里来回走上十趟八趟,故意让大伙看,谁想说就让他们说呗。”
他信心满满地回到了郑州,却像急速奔驶在高速路上的车,突然来个急刹车,又不敢也不愿回老家了。不过他倒是早有准备,在户县食品厂时,就打听到发小颜寿祥在郑州富士康上班,还是车间主任,想着可以帮自己,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颜寿祥约他下午7点在中牟县富士康正门外见。俩人一起来到一家烩面馆,要了两个凉菜,喝起啤酒。
马国力举起酒杯,用炫耀和提醒的口气说“你家院子是咋来的没忘记吧?”他又把头仰起朝天点了点,有点意味深长的意思。颜寿祥笑说:“吃水不记挖井人,当年要不是你帮助,我能在村里划到这么好的院地?几年前就准备等你回村好好请你喝场酒,没想到今天你来中牟了。”他如喝了蜂蜜水,笑着说:“你在厂里具体干啥?”“在车间流水线上打螺丝,到年底就不干了。”马国力知道他混得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根本帮不到自己,就低头专心喝酒,不再提要他帮忙的事。
颜寿祥却说:“听说你在陕西当老板,还想给你去打工呢。”他顿时自豪地说:“我在厂里入了个最小的股,来耀先是大老板。你知道当年在村里我一直罩着他,要不是我,他哪有今天,所以我出来后,他就叫我去厂里管理工人,别忘了我以前是支书,管理是我的老本行,那一百多号人都听咱的,只是工作很辛苦,年龄大了,在监狱那几年把身体熬出了毛病,现在回老家休养身体,路过郑州顺便看看你。”颜寿祥恭维道,“你的钱花不完,不像我五六十岁了还得打工。”他就哈哈地笑起来,说:“我全国各地都有关系,无论到哪,进了工厂起码都是个管理人员。”
吃完烩面喝完啤酒,得知颜寿祥住集体宿舍不便借宿后,马国力就坐上最后一趟公交车回了郑州,路上一直为晚上住哪犯嘀咕。直到在终点站下车,看到不远处的街心公园有人影晃动,他的心里才有了底。进去一看,果然有数人盖着上衣睡在条椅上,他于是也找了个僻静角落躺下身来。
睡到半夜,有个人来到他身边悄无声息地翻他的口袋,一下把他惊醒,颤抖着说:“干什么?”那人见他很警觉,也不吭声就离开了。他半天没睡着,等他朦朦胧胧再次想睡时,公园里已有人在吊嗓子,还有人在吹萨克斯,他只能起身沿着金水河离开。
他在郑州晃荡了三天,也连着三个晚上都在这个街头公园长条椅上过夜,甚至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将自己的双肩包压在头下,把上衣脱下盖到胸口,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他轮番给以前的朋友打电话,有的不在郑州,有的在南方打工,都没有稳定工作,不可能帮到自己。就在打算离开郑州的前一天,颜寿祥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中牟厂边喝酒。当天下午去的早了点,见厂区外路边有几个人正在做绿化,便过去随意问起他们需不需要人手,那个年龄较大的人看着他说:“看你这装扮就是个老板,怎么还找活干?”他说:“衣服穿得整齐点就是老板的话,全中国的人都能当老板。”那人笑了,说:“有道理。最近俺老板有个工程正找人呢,但不管吃不管住,你愿干吗?”
就这样,他白天跟着这几个人到苗圃裁树苗,到西郊刨树,再运回苗圃,晚上回金水路上的那个街心公园睡觉,一个月后,拿到了3千的工资。这时,时节早已入深秋,天气已冷,公园里也没人再在那过夜了。他决定,回到那个曾经带给他荣耀和耻辱的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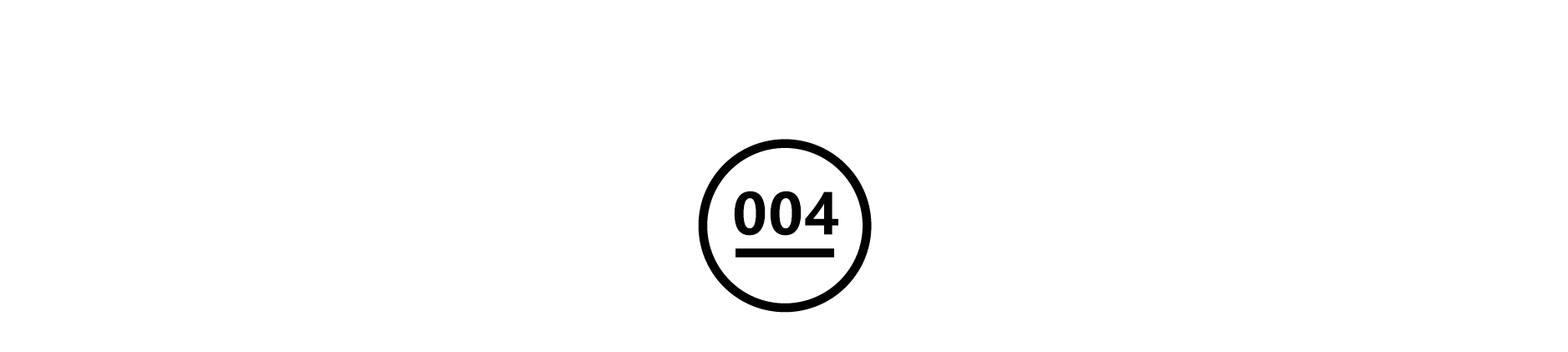
眼下,邹海伦正拿着黄瓜西红柿和一瓶 “仰韶彩陶坊”为他洗尘,马国力渐渐从过往的屈辱和迷醉中清醒过来。他说:“出来了恁长时间才回来,就是不想让那帮人看我的笑话。”邹海伦骂了一声,说:“你明天就专门在村里来回走一趟,用行动告诉大伙你‘胡汉三’又回来了!一年后又是条好汉!”马国力笑了,把话转入正题,“回是回来了,你现在是老板,我这劳改犯……”邹海伦立即打断他,“只要有工程,你领着人干,挣了钱平均分。”马国力举起大姆指朝空中一摁,说:“我摁手印签合同了!”“不用摁,这些年的朋友你还信不过我?”
很快,一瓶喝完,还没喝尽兴,俩人又到邹海伦家开了瓶“鹿邑大曲”,喝到四点,俩人迷迷糊糊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此后,马国力随邹海伦在农村干起工程来,有时半年接不到活,他就做日结工,到山药地里刨山药,一天能挣120元,或是和那些妇女们在菊花地里拔草,一天也能挣60元。每当排队等着领工钱时,他都会想,当年的支书竟然混到了与妇女为伍的地步,但内心的羞耻很快会被麻木的表情掩盖。
冬季时,邹海伦连续接到三四座楼房的工程。这时,邹海伦让他领着工人在工地吃住,自己却消失不见。有次偶然聊起此事,发小淦小东告诉他:“他常去‘大浪淘沙’泡澡泡美女。”马国力反问:“你咋知道?”淦小东说:“我在‘大浪淘金’当保安当然知道。”他心里即刻有了不平衡感,可又一想自己的处境,也就没了怨言。

马国力带领建筑队在农村盖房打成的地基(作者供图)
某天他偶尔看到邻居大爷把一头肥壮的花牛拉到家里喂料,便惊奇地问他是从哪弄来的牛。大爷说,他在黄河滩养有20头母牛两头公牛,已有多年。母牛可挤奶卖,公牛可刺激母牛发情,产更多的奶。另外,公牛一岁半就可当肉牛卖,价格也高,也能挣钱,不过可不像给人盖房来钱快。
马国力突然顿悟,觉得这是件实在事,便问起投资规模、如何养牛、得了病咋解决、牛奶的销售等问题。大爷说,“刚起步养个五六头也就十来万,如牛有病,镇上的兽医随叫随到能解决,牛奶销售你可先卖给我,跟着我慢慢熟悉门道再单干。”
马国力想,我可是前支书,是有魄力的人,几天后便决定不再跟邹海伦干了。他找到村长来福,租了五亩黄河滩地,买了五头花花奶牛,还计划之后视情况增加数量。至于这笔投资的来源,大约和他坐牢的原因脱不开干系。
这是2023年春天,至此,马国力像个中风患者,正颤颤巍巍地努力步入离他仅一步之遥的生活的人行道上,只是眼下还不知那所剩的最后一步到底还要迈多宽。

马国力买回的“花花奶牛”(作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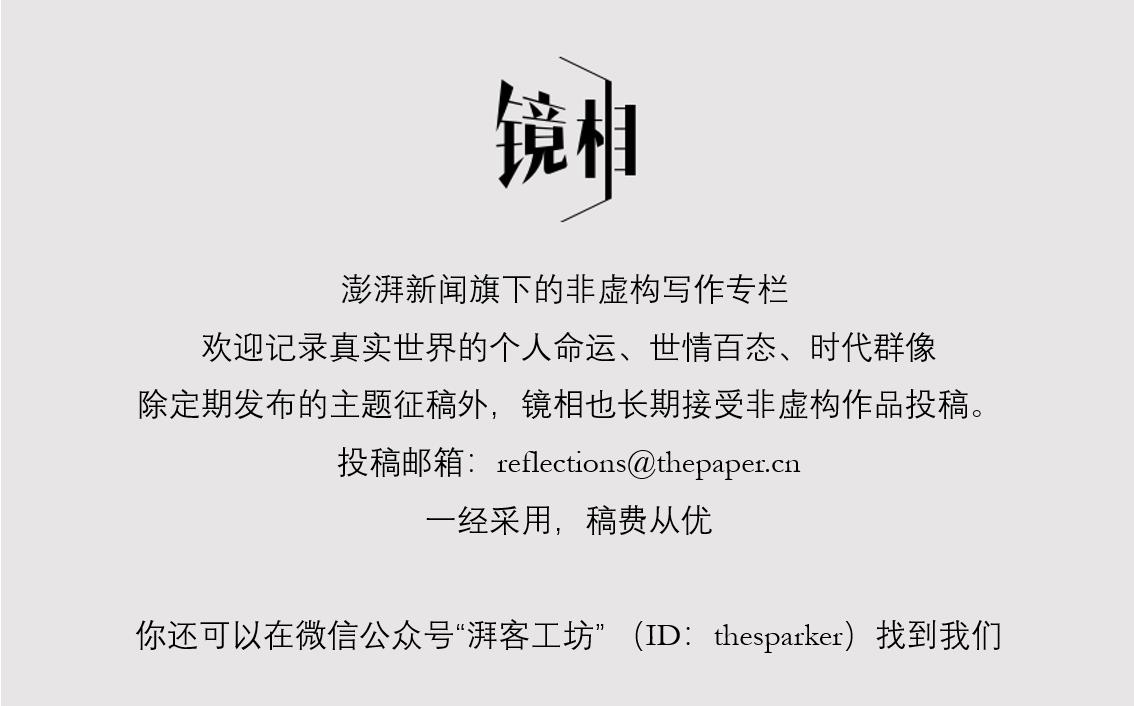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