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永远无法摆脱爱 | 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
即使不关注摇滚乐的人,也多少听过约翰·列侬的名字,更熟悉点的会知道这首叫《Imagine》的歌。
1960年,约翰·列侬组建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段神话。1970年,乐队解散。1980年,这位传奇艺术家在纽约寓所前被枪杀,年仅40岁。
列侬和小野洋子是世界上最知名、同时又最受争议的艺术伉俪。列侬遇刺前,《花花公子》编辑部对列侬和洋子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达3周的采访,这也成为两人最后的公开谈话。在这场“最大规模”的谈话中,他们真诚而犀利地谈论婚姻与家庭、音乐与创造,也谈到了在今天似乎已成为口号的“爱与和平”。两位传奇艺术家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离完美相去甚远,但绝非虚幻。
我们摘取了这场对谈的片段,从中可以窥见“披头士”解散背后的故事,可以看出既是艺术家、又是富豪的二人的金钱观、艺术观,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理想主义光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赤裸地、诚恳地邀请我们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邀请我们庆祝生命、让爱常驻。
下文摘编自《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经出品方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1.所有的音乐都是老调重弹
《花花公子》:对那种坚持说没有“ 披头士” 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谓的摇滚乐的人, 你怎么看?
列侬:没有摇滚乐就不会有“披头士”。这都是推测。没有埃尔维斯就不会有“披头士 ”。没有约翰尼·雷(美国歌手,被评价家认为是摇滚乐发展的先驱)就不会有埃尔维斯。没有约翰尼·雷之前那些人,就不会有约翰尼·雷。没完没了,无休无止。60 年代属于“披头士”, 所以这音乐对他们很重要,至死方休。

△ “披头士”乐队成员。左起依次为主音吉他手乔治·哈里森、贝斯手保罗·麦卡特尼、鼓手林戈·斯塔尔和约翰·列侬。
但是对于 40 年代,那是格伦·米勒(其舞曲风格的爵士音乐风靡1940 年代)的时代,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们的父母听格伦·米勒时,他们经历同样的事。不过,也许他们并没像我们这代人,没有把额外的所有东西都放在那上面。你知道,这些玄乎的东西。
《花花公子》:对那些坚持说自“披头士”出现以来,所有摇滚乐都是“披头士”翻版的人,你有什么话说?
列侬:所有的音乐都是老调重弹。就几个音符。就一个主题的变化。请告诉 70 年代对“比吉斯”尖叫的那些孩子,“比吉斯”的音乐只是“披头士”的翻版。“比吉斯” 没问题。他们干得真棒。那段时间除了他们没什么别的。
《花花公子》:至少“披头士”更聪明,不是吗?
列侬:“披头士”更有智慧,所以他们在那个层面也很有吸引力。但是“ 披头士” 最基本的吸引力不是他们的智慧,是他们的音乐。只是当《伦敦时报》上有人说《不会太久》(“It Won’t Be Long”)用“爱奥尼亚调式作为终止式”之后,中产阶级才开始听——因为有人在那上面贴了个标签。
《花花公子》:你有没有在《不会太久》中放进爱奥尼亚终止式?
列侬:直到今天我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它听起来像一种外国的鸟。
《花花公子》:你现在做的歌很难被曲解。
列侬:我现在不想制造幻觉。“塑料小野乐队”简单直接。这就是我要做的。我一直都想这么做。我只想直接说出我想说的话。我对所有“大写的诗歌”都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最好的诗歌是俳句。所有最好的画都是禅。

△ 1970年,Paul McCartney宣布甲壳虫乐队解散。同年,John Lennon发行了第一张真正的个人专辑,图为专辑封面。
话越少越好。我想不用歌词就能说出来,可我不能。我只好——只好用语言表达。总之我所追求的就是清晰,表达的清晰。画壁纸或做米尤扎克音乐,都不是我想干的,虽然我并不反对。我只想在画布上画一个清晰的瞬间。
假如人们不喜欢,那么……那就跟想要“披头士”回来一样。你想从我这里得到音乐,你就会得到。但不要告诉我该做哪种音乐或建议我该怎么做。否则,你就自己去做。人人都有可能。别的人可以去做那件事。
2.我们并不是来拯救这该死的世界的
《花花公子》:为了引出话题,让我们继续坚持这种说法:除了“披头士”,没有别的艺术团体以如此深刻的方式感动了这许多人。
列侬:但是,是什么感动了“披头士”?
《花花公子》:你告诉我。
列侬:好吧。不管那时的风怎么吹,那风也吹动了“披头士”。我不是说我们不是船桅的旗子。但整艘船都在动。可能“披头士”在桅杆瞭望台里叫着“陆地到了!”之类的话,但我们都在同一艘该死的船上。你不能一辈子都盯着看那瞭望台。总得有人扬帆和落帆。
《花花公子》:就说“披头士”仅仅是桅杆瞭望台。这样, 人们又一次仰望它是有理由的。
洋子:但是“披头士”本身是一个社会现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某种程度上……
列侬(喘着气):这个“披头士”的谈话要闷死我了。
洋子:我敢肯定有些人会因为听到了印度音乐、莫扎特或巴赫而受到了影响。最重要的是“披头士”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里确实发生了些什么。一种化学反应。好像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一个鬼魂出现了。就是那种交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媒介。

△ 披头士成员与印度冥想师玛哈士。1968 年,乐队曾到印度隐修,期间创作了《The Beatles》与《Abbey Road》等专辑中的多首名曲。
他们之间曾有一种东西, 一种强烈的彼此联系,一种在一起的感觉,而不只是四个人。现在不一样了。这不是你能强求的东西。那是人物、时代,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就像我说的,他们就像是媒介。他们对他们所说的没有意识,但是那些话通过他们说出来了。
《花花公子》:为什么?
列侬:我们接收到了那个讯息。就这样。我不是有意贬低“披头士”,当我说他们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我只是不想夸大他们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重要性。我不认为他们比格伦·米勒、伍迪·赫尔曼(深刻影响了摇摆乐和冷爵士时代)或贝茜·史密斯 (早期爵士乐和蓝调唱片中第一位现象级女歌手)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仅此而已,这就是60 年代音乐。
洋子:而人们还想要更多?记住,你读到《圣经》的时候, 基督传教差不多快五年。五年他就上了十字架,说,我将再一次显现,但是“披头士”已经做了十年了——够久了, 不是吗?
列侬:你不觉得“披头士”已做得够多了?这用掉了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整个青春;当其他人都在傻乎乎地玩耍,我们却在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没法停下。电梯服务生在你回酒店房间的路上想要一点你,女招待在你回酒店时想要一点你——我不是指性, 我是说你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我突然明白了:我要再回到那儿吗?我们真要做的话,就得把“披头士”拯救世界这件事搞搞清楚。如果你看不清,那么没人能看清。把我们重组筹集的钱献出去,只是给人提供治头痛的阿司匹林。头痛的原因是无法解决的。
《花花公子》:也许你不用给阿司匹林。也许你筹集钱,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比如实现某些社会事业什么的。
列侬: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你为什么不马上开始,让自己像“披头士”一样出名?如果你想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一直微笑、跳舞,搞它十到十五年,这很容易。那么你就可以做到。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我说我要做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上帝知道我们创造了多少福利。我们提供了“披头士”能提供的一切。我们并不是来拯救这该死的世界的。

△ 狂热的披头士粉丝
洋子:同样地,这样产生出来的钱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税收是个大问题,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钱并不会流向你想要它去的恰当地方。而有这么一种想法,这四个男性人物,或者说这四个男性人物的延伸物,做了些好事,一场音乐会可能在象征层面上奏效,但在实际意义上, 在金钱层面上,它却通常不起作用。他们对此有经验,请相信我。
3.为了生存和改变世界,首先你必须照顾好自己
《花花公子》:在你自己的财富问题上,《纽约邮报》最近说,你们承认有一亿五千万。
列侬:我们没承认过任何事。
《花花公子》:《邮报》说你们承认了。
列侬:《邮报》说——好吧,我们有钱,所以怎样?
《花花公子》:哦,问题是,这和你的政治理念吻合吗?
列侬:在英国,只有两件事情可做,基本上是:你要么拥护劳工运动,要么拥护资本主义运动。如果你处在我的阶级,你要么成为右翼的阿尔奇·邦克,要么变得像我这样,成为一个本能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人们的假牙、健康之类的该被照顾好。
而除此以外,我为钱工作,我想发财。那又怎么着?如果这是自相矛盾,那么我就不做社会主义者。怎么着?而我什么都不是。我本能地拥护工人,因为我以前和工人一起生活,虽然很多工人是右翼。我以前对钱有罪恶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失去了它,要么送出去, 要么允许自己被所谓的经理(随你叫他们什么)骗去。但潜意识里是,因为我对有钱这事有罪恶感。
《花花公子》:因为?
列侬:因为过去我以为,金钱等同于罪恶。我不知道。我想我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我要么去干要么闭嘴,你知道。如果我要做一个一文不名的修道士,那就做吧。相反,如果我要努力赚钱,那就赚吧。金钱本身并不是邪恶的根源。金钱只是一个概念,也只是一种能量。所以现在你可以说, 我已经与金钱达成妥协并且在赚钱。
我总是忽略钱。所以现在,洋子管生意,把钱投入到奶牛和房地产之类的事情上。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钱在那里,而我总是避开。反正我也太艺术了,处理不好金钱。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有了这些钱。每当我忽略它,总是会带来问题。我很难解释这事。我现在变得有些迟缓, 因为我累了。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绪。

△ 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
《花花公子》:我们可以以后再谈这个。
列侬:没事,没关系。如果一直谈下去,我们就能把这事搞明白。
不是我凌驾于政治之上,而是我做的事就不是政治。政治与社会是分开的,而我不是。政治是包容性的,就像艺术、饮食和生孩子;它不仅仅是你四年做一次的事情。正如戈尔·维达尔常说的:“不要给他们投票,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
我从来不给任何人投票,任何时候都没有。即使是在我所谓的最热心政治的时候。我从来没登记为选民过,永远也不会。这么说会让很多人心烦,这可太糟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大多数人都不投票。哦,他们更明智一点。
洋子:无可否认,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而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我们有些朋友可以说是 1920 年代的社会主义者,生来就有钱,总是说他们不在乎钱。这么做很容易。
但我认为,为了生存和改变世界,首先你必须照顾好自己。你得靠自己活下来。要改变社会,你必须得与这个社会周旋……
现在 60 年代的许多人去了地下,想着要炸掉白宫之类。那是暴力做法,我觉得负面影响太大,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这不是个办法,对我来说绝对不是。
如果你不使用暴力,你也不要钱,你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改变体制,你就要变成体制的一部分, 有个改变它的地位。所以你需要钱。纵使你想当市长还是什么。
可悲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你不考虑钱,你就会成为寄生虫。在有些社会,即使不考虑钱,如果你是艺术家或者你有技能,你就不需要什么了——这并不是指苏联, 因为他们的体制也有缺陷。我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就有一个社会那样地存在着。
每个人都有这个理想,认为社会中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来保护人们不必真正地依赖于金钱系统。但是这个社会依赖于金钱体系。所以我们必须玩这个游戏。
列侬:“任何来自虚伪政治家的消息对我都不起作用。” 我早先说过这话,现在仍然属实,仍然奏效。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我涉足所谓的政治,更多的是出于负罪感。内疚于变得富有,内疚于想到爱与和平也许是不够的,你必须去挨枪子儿,或者脸上挨顿揍,以证明我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违背了我的本心。

△ 列侬、洋子和儿子肖恩在日本
洋子(朗诵道):“现在,我是这儿唯一的社会主义者。”
(她笑了)我一分钱都没有。都是约翰的,所以没关系。我以前真的玩过这个游戏。但是钱,当然,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也在用这些钱,不得不面对它。所以,是的,你必须玩金钱的游戏。
《花花公子》:你能在何种程度上玩这个游戏而不被卷入其中——换句话说,不为钱而赚钱?
洋子:有个限度。可能与我们感到多安全正相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情感上的安全水平。
《花花公子》:达到那个水平了吗?
洋子(笑):没有,还没有。我不知道。可能达到了,但我们觉得要达到那样的水平才会更舒服。
4.大多数人被他们随身携带的概念窒息而死
《花花公子》:就一个艺术家而言,你的商业感觉似乎很突出。
洋子:我只是在做类似下棋的游戏。我喜欢下象棋。我做这件事、每件事都像是在下象棋。不是像“地产大亨”那种游戏——那更现实一点。象棋更具概念性。
《花花公子》:约翰,你真的需要遍布全国的所有这些房子,让你有地方可以逃离吗?
列侬:它们是很好的生意,但我们确实喜欢它们,在使用它们。
《花花公子》:为什么有人需要一亿五千万美元?难道你不能满足于一个亿?或者是一百万?
列侬:你想建议我什么?把一切送出去,以街头为生?过去没钱时我不满足,有一百万时我不满足,现在有一个亿, 我也不满足。满足感不在于金钱。
《花花公子》:那为什么要投身于获取更多金钱的游戏?
列侬:因为做我在做的事,需要钱来达成。
《花花公子》:一亿五千万吗?
列侬:都是相对的,不是吗?
《花花公子》:那些要超越财产的话题呢?
列侬:不用穿着长袍走来走去也能超越财产。财产可能存在于头脑中。一个洞穴里的僧侣,梦想着食、色、性,比我这所谓的背后口袋里有钱的人,情况要糟得多。我已经摆脱了不能又清醒又有钱的那种冲突。那绝对是胡说八道。

△ 列侬和儿子在家中
当基督说,“富有的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从字面上理解—— 一个人必须抛掉财产才能进入涅槃,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
但是一个知识分子比我更不可能穿过针眼。他们拥有想法。一个没钱的知识分子,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没有电视之类东西——嗯,他们拥有想法,关于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不再拥有想法了。因此,那些才是我要抛弃的,而不是物质上的所有物。
洋子:一个人不能通过压抑来抛弃事物。为了要“抛弃”, 你必须先得“得到”,明白吗?
列侬:我的不安是我有太多衣服。这是我不安的一种生理表现——我有一柜子不可能去穿的衣服。但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还是有衣服,会每年把它们扔在救世军的柜台上。但我明白了那种焦虑恐惧。但是有很多钱对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会要获取更多。小野没这个问题,因为她生来富有,她这辈子一直很富有。她无法理解我对金钱的态度。不管我们钱多钱少,似乎都与她不相干。
所以所有物不仅仅是物质财产。思想也是所有物。大多数人被他们随身携带的概念和思想窒息而死,通常那些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属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阶层的。那是你穿过针眼时必须要抛弃掉的所有物。这完全与物质财产无关。
《花花公子》:你穿过针眼了吗?
列侬:我想我已经穿过去又穿回来好几回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这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金子的问题。有许多觉醒了的非常富有的人,也有许多觉醒的不拥有任何物质的人。一个碗,一个杯子。那是什么?禅宗吗?一个碗,一条斗篷。

△ 1969年“屋顶演唱会”(The Beatles Rooftop Concert)现场。这场演出是披头士乐队的最后一场演出,亦对流行音乐史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来说,那样做相当疯狂——离开所有一切。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所有物,包括你的家庭、纽带和一切。就这么极端。但是走开就是逃避责任。就像“披头士”。我不可能离开“披头士”。那是一个还依附在我身上的所有物,对吧?不管我自己怎么说。如果我要远离真正的自己,不管是两栋房子还是四百栋房子,我都逃不掉。
《花花公子》:那要怎么逃呢?
列侬:把我身上的那些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垃圾扔掉,要花很多时间。这与洋子有很大关系,她让我意识到我仍背负很多。当我和洋子相爱时,我就从肉体上放下了,但在精神上我挣扎了有十年。我从她那里学会了一切。
5.如果你不那么怕,爱就会常驻
《花花公子》:就像汤姆·罗宾斯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半真半假地问:“如何让爱长驻?”
列侬:试图占有它会让它消失。试图占有一个人会让他离开。每次你想搞明白一件事,它就会溜走。每次你打开显微镜的光,事物就会改变,因而你永远看不见它是什么。
一旦你问出问题,它就消失了。这都是周边视觉。不能直接盯着它看。试着看太阳。你会变瞎,对吧?虽然如此, 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专注于它。爱是一枝花,你必须给它浇水。
洋子:是的。我认为爱永远不会消逝。一旦你认识了某个人,你就再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人。而相知就是爱。所以你永远无法摆脱爱。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会有误解和分离,但爱总在那里。
在一起只是爱的一种形式。也许那是一种强烈的爱和爱的表达。但爱是灵魂的东西。它总是在那里。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对失恋感到不安。如果他们不害怕去爱, 那么他们总是会爱。

△ 1969年,洋子和列侬发起“床上和平”行动,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整整七天,房间里贴满了反越战标语。世界各地媒体接连报道这场行为艺术。
人人都有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想弄明白如何才能让爱持续。每个人都真的关心爱。这是最大的主题。爱让万物运转。它使万物生长。
爱也很难。有时候我们有占有欲,这没什么。我们不应该为有这种感觉感到羞愧。没事的。我们因嫉妒而感到羞愧,因占有欲而感到羞愧。我们如此害怕有仇恨之类的感情。这都不必要。
所有这些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能量。能量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我们拥有的东西没有哪一样是丑的。出自我们的一切都是美的。我们被教导说唱歌是美的, 但如果你唱走了调就不美了。我们被教导说你要以一种特定方式唱。但是我认为,出自我们的一切都是美的,因为我们是人。
我为人类感到惊叹。他们多有韧性啊!他们生来就没有保证可以存活。他们的保证只有父母,而父母也如此不安,他们自己也像孩子一样。而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在“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你不该这么做”中活下来了。
一个人若没有这些成长中的不安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将是个有趣的设想,但即使有这些不安,我们还是活下来了。
想象一下,我们真的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微笑着摇头) 无论如何,人生是如此艰难。走下去需要极大勇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好活着。(笑)我认为人生是美好的, 我很享受人生。我正在享受。

△ 洋子、列侬和儿子
也许直到最后,我都是一个无止境的乐观主义者。我有时会想到那些人的想法:啊,好吧,世界很快就要完蛋了,所以我不要孩子。哦,如果你害怕失去,你就会失去的。看看那些人。我们在谈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美——这是真的。
列侬:嗯,今天它是。昨天它糟透了。所以管它呢。(他和洋子笑了)
洋子:就是那样。没关系。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不会那么怕了。如果你不那么怕,爱就会长驻。
本文摘编自

《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
作者: [美]大卫·谢夫
译者: 李皖
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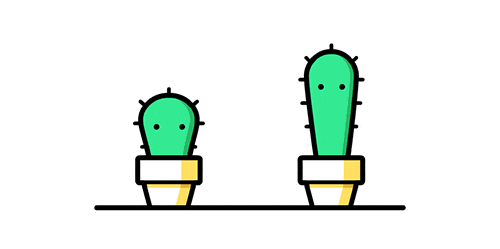
编辑 | 蚂蚁
主编|魏冰心
原标题:《你永远无法摆脱爱 | 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