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社科院成立60周年,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在沪颁奖
2018年9月7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60周年大会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于信汇书记主持颁奖仪式,并宣读获奖人名单。
经过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通讯评议专家委员会评选,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斯特林讲座荣誉退休教授史景迁,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荣誉教授白吉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梅津采夫,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东南亚研究院主席、澳洲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王赓武荣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梅津采夫、王赓武出席颁奖仪式并发表获奖感言,白吉尔、史景迁因身体原因未能与会,白吉尔在会前寄来感谢函,史景迁由其夫人金安平女士代表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张道根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同志分别为获奖者及其代表颁奖。
梅津采夫是俄罗斯著名中国通,曾先后担任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主席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秘书长,并于2016年6月起当选为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他为增进中俄友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获得俄罗斯四级“祖国贡献奖”、 “促进俄中友谊”奖等多项荣誉。

史景迁是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汉学家,与魏斐德、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的著作《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王氏之死》《天安门》《大汗之国》等无不词章华美,义理深邃,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因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卓著贡献,获得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等多项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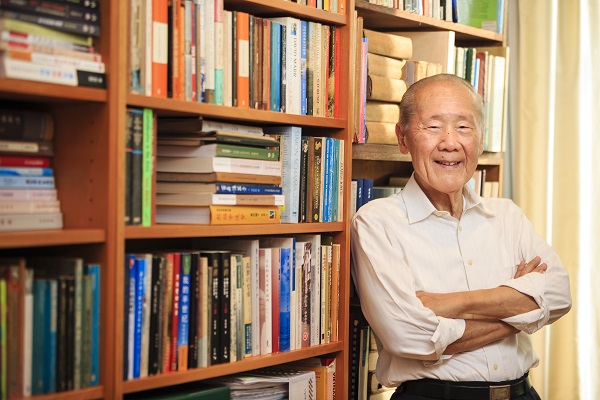
王赓武是澳大利亚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他厚植中西学术根基,尤擅于从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众多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被新加坡前总统纳丹称为“新加坡国宝级学者”。他的著作如《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南洋贸易与南洋华人》《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移民及兴起的中国》《建立新国家:五个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历史》等皆根底深厚、识见卓特,在国际学术界深具影响力。

白吉尔是国际公认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和上海史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5次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她多次来华访问,并受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白吉尔夫人出版专著、编著20余部,代表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孙逸仙》《上海史》等被译为多种语言,受到国际学界推重。
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承办,自2004年创设以来,已成为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2010年起,论坛设立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2年起,增设海外华人中国学贡献奖,以表彰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中国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迄今已有15人获奖。(本文撰稿:潘玮琳)
【附录】
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获奖者感言(中文版全文)

梅津采夫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对我个人而言,今天能够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是莫大的荣幸,我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上海社科院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同时,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作为一名俄罗斯公民,我既能饱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成果——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俄罗斯人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在此,我衷心感谢世界中国学论坛组织委员会,给予我个人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殊荣。我也要衷心感谢以下几位在中国和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名师,这些人包括尊敬的蔡昉先生、周慧琳先生、张道根先生、燕爽先生和于信汇先生。
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所有伟大成就,中国在自身发展上获得的这些成就,也使俄罗斯联邦受益。今天我们都看到,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获得的长足而蓬勃的发展,这也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两位领导人持续而密切的关注。我想强调的是,当前在两国元首的关怀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展开,在政治、经贸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不仅是两国间的关系,还影响了国际和地区合作的方方面面。201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此后,“一带一路”倡议立即获得了来自中亚和俄罗斯的支持。去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首要贵宾出席。在这次论坛上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伙伴关系”倡议进行了对接。两国提出的倡议不仅关涉双方,同时也为在欧亚地区的全方位合作和发展奠定基础。
我曾在上海合作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的三年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上合组织不仅是地区和国际性组织,同时,由于它被冠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的组织。今天,上合组织不仅关注欧亚地区的安全发展,也在欧亚经济、人文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上合组织也与联合国的相关机构不断合作。在此,作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一员,我也想讲一下中俄方面的合作。在不久前中俄两国的议会合作也开始了。在双方代表团的会晤中,我们都决定要加强中俄议会之间的务实合作,来自中方的议会代表也支持俄罗斯议会合作委员会代表的建议,希望能在中俄两国双边议会合作机制下,引入上合组织的合作理念。
今天,正值上海社科院成立60周年,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衷心祝愿上海社科院在科学培养方面更上一个台阶。在座各位都是幸福的人,因为你们可以亲眼见证和经历中国的发展。我想请各位注意“60”这个数字,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符号,还意味着一个年份。60年不是短暂的,它代表着所有在座的和没有参加本次大会的上海社科学界人士,为了自己的学术目标长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我希望以上海为平台,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官员等志同道合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到中俄各项倡议的对接和合作中来。我知道今天出席会议的有很多来自中国和上海各个方面的权威人士。我个人非常想提到一个名字,就是来自上海的王战教授。他为中国的发展和中俄合作做出了不少贡献。同时,我还要感谢一位长期默默地为促进中俄友好合作的奉献的人,他就是来自上海社科院的潘大渭教授。我还要再次感谢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先生。我衷心祝愿上海社科院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获得成功,也衷心祝愿上海作为全中国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不断地走向辉煌!
最后,我诚挚地感谢主办方为我颁发的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除了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中俄合作和中国学在全世界的推广奉献良多,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中俄关系,研究中国学。再次祝愿上海社科院60周年的纪念大会圆满成功!谢谢!(潘玮琳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王赓武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上海社科院的同仁、同学: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感谢你们鼓励和奖励我几十年来对中国的了解和教学。我是海外华人背景的代表。我生长在海外。在海外要懂得中国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海外,总是在想,中国跟海外华人的关系应如何解读?我们也很难得真正的了解,因为几百年来,不管是海外华人在外面的经历,还是中国之内的情况,都变化无穷,因此,坦白说,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疑问。
现在谈起“世界中国学”,过去没有这个词。什么是中国学?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但是我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是中国?”因为从海外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中国的同胞们所认同的中国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在海外看中国,因为角度不同,观察、了解的背景也不同,所以有很多地方搞不清楚。因此。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
我有很多朋友在海外出生、成长,有些是明清时已经去海外居留的人的后裔。他们是华裔——当时没有华侨这个词——当时他们怎么看中国?明朝的中国、清朝的中国也是中国,但是经过19世纪的大变动,明清中国变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共和国是什么?他们就更不懂了。坦白说,一般的海外华人认同的是他们的家乡,并不一定认同明朝或者清朝。那些王朝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有限。海外华人基本上是出于贸易、商业和劳工方面的需要,到外国去重新生活,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那么简单,他们了解的是他们的家乡,认同的也是他们的家乡。我最初关心这个问题时就注意到,几百年前海外华人的墓碑上,根本没有提到国家,甚至也没有省县,只有某某村、镇、城。他们认同的是他们的家乡,根本没有国家概念。所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他的同事们到海外去谈革命,谈民族、谈国家、谈共和国,这些都是新概念。海外华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仅是家乡的还有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国家的还有民族的认同,这些概念是比较新的。最后,他们也接受了中国。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海外办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主旨就是希望海外华人认同新的共和国: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当时,海外华人的生活环境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下,他们没有国家概念,后来才有了中华民国、民族国家的概念,才开始自认为是“华侨”。海外侨居的人怎么看中国?在华侨学校里,不停地在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一切被灌输给他们。他们懂了一点,但事情又开始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影响之下,在东南亚的华人更加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世界的看法又变得不同。
我在那个年代长大,开始注意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但当时,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方便谈。所以,我开始认识中国学的时候,还是念的历史,而且是世界史,尤其是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世界史。同时,我对中国的了解还是非常浅,懂得一点古文,看了一些中国的书,但是因为冷战的关系,有关近代、现代的中国书根本看不懂。因此我没有关注自己特别喜欢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因为当时没法研究。所以我回头研究古代史。
因为我是海外华人,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变化。中国在近代经历了数次大革命,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感同身受。海外华人要如何跟从中国的变革?这个问题在海外来看是不容易的,尤其因为当时海外各地也同样受到变革的冲击,帝国主义垮台之后建立的新兴国家,都在谈民族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要求,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是最主流的方向。因此,海外华人在其所居国家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又受到很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海外华人对“什么是中国”的新的思考:中国是几千年历史上的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华民国的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抑或是只讲文化民族而不讲国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这都是大家在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不得不考虑近代史的问题。
虽然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出身,而且对我来说,中国近代史本来是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学习的,但是在海外长大的华人,面对如何认同将来的世界、如何看待将来的中国等问题,不得不重新学习近代史。因此我又回到近代史。对我转向近代史影响最深的两位学者,是上海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张仲礼先生,和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萧公权先生。张先生的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我有机会到上海社科院见张仲礼院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是引领我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人物。我对他非常感激。因为生活在海外的关系,我当时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还非常浅。我在对中国、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等问题上都受张先生的很大影响。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回去的不仅是近代史。我回到新加坡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所以我走了很长的路,从汉唐时期的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再到当代中国。每段路程都经历了不少的挑战。我自认为,对于中国的了解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浅,但是我很感激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者、中国本地的中国学研究者,以及两者在各方面的互相交往。这些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最近,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的研究,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葛兆光先生也问“什么是中国?”我年轻时问的问题,现在他也在问。但是有意思的是,他问的深度和我当时幼稚的提问相去甚远,可见几十年来对中国学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
“什么是中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传统的史学、国史传统对现代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海外华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今天到上海社科院参加贵院60周年建院的纪念,心里充满了感激。我非常希望了解,上海社科院是如何把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前途的研究连通起来的?你们对从古代到现代到将来的中国的互通是怎样解读的?从而使我们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
谢谢大家!(潘玮琳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史景迁为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撰写的获奖感言
我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给予我此项荣誉,同时很抱歉不能亲自出席在上海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海这座城市,是中西文化创造性交融的光辉典范,她历经往昔的战乱劫难,依旧傲然挺立。只要提到上海,我便会想起魏婓德先生(1937-2006年),他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着力颇深、成就斐然。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座诸位一定与我一样,对他怀抱着深切的追思之情。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妻子金安平女士今天将代表我接受这个奖项。
我在很久以前便与中国及其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上了几堂现代汉语课之后,便深感中国历史、艺术史和文学的浩瀚无垠,可供我上下求索。于是,在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如今,经过半个世纪在中国学领域的教学、写作和研究,我退休了,终于有了闲暇时间。在退休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阅读,阅读任何我想读的东西——历史、小说和诗歌;我也一直在看电影和电视剧,有时一次连续观看4个小时。生活很惬意。然而,有时我也会想念课堂,想念学生的脸孔(和他们脸上渴望学习的表情),想念图书馆里发黄的旧书和霉味,我甚至想念工作和工作中经历的挣扎——无论是为了理解某个文言文段落,还是为了用字遣词上表达自己的意图。除了偶尔引发的怀旧情绪之外,也有艳羡的成分。我实在羡慕那些如今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学者和学生。他们接受的语言训练时间更长、更完善,因此,他们能够更自如地说汉语、读汉语,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时在资源上能够与中国同行优势互补,当他们彼此产生分歧或在研究中碰壁时,也能够共同探讨、互相启发。像上海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中心鼓励的正是这样的活动——大家对学问和智识求索怀抱共同的热爱,对学术研究追求共通的方法。我为他们喝彩。我多么希望自己当年在学习中国历史时能有个不同的环境,但往事毕竟已不可追。今天,我本着学术追求的精神和对历史的热爱,以最由衷的感激之情接受你们授予我的奖项。(潘玮琳译,金安平审定)

白吉尔为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颁奖仪式撰写的获奖感言
尊敬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先生,尊敬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评选委员会各位评委,尊敬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们,亲爱的同仁们,朋友们:
获得2018年度的中国学贡献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给予我和我的家人的极大荣誉,也是法国汉学家和我的同事们的荣耀。在此,我衷心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世界中国学论坛评委,授予我这项奖励。鉴于健康原因,我不能亲临现场参加授奖仪式和上海社科院建院六十周年大庆,深感遗憾。然而,值此时机,请允许我与各位分享一些我的有感而发。
在我看来,对我的奖励具有三重意义。就个人而言,是对我与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历时长久的友好工作关系的认可;对年轻一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能够看到一种迹象,即他们的中国同仁们与当前受人类学和社会学影响的西方历史编纂学趋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能够从这一实例中得到启发;从更广泛的效应来看,世界中国学论坛倡导邀请中外专家进行跨文化对话,通过比较、对照、商榷和最终的综合创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学科,适宜于全球化的需要。
我与上海社科院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1979年,时值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作为前往中国协商发展中法文化交流的法国正式代表团的成员,我受到了社科院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接待。尽管当时他们受着认识上的约束,这些研究员还是亲切友好带着知识分子的好奇倾听向他们提出的观点。当然,他们没有像我这样,说20世纪上半叶编织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演变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和控制的范围;也没说,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或者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结果,而且也是中西实践相遇相交之际出现的现代化的原始模式。
我们认识上的分歧明显存在,这些同仁仍然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让我发掘新的资料,并从他们对中国和上海的经济、历史的深入了解中获益。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我曾多次前往上海社科院做研究之旅,他们的慷慨相助从未停止。这段时期内结下了太多的友谊,我无法在此逐一述说。但我至少想向杰出的近现代历史学家张仲礼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是位出色的管理者,善于在国际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引导社科院对外开放,他和蔼可亲,充满力量,稳重节制。在十七世纪的法国,人们会称他为“一个正派人”,即一个能将道德和社会承诺融为一体的人。而在我的眼中,这位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是“好官”的化身。
今天授予我的奖项唤起了这些记忆和以往的友谊,她还证实了六十周岁的上海社科院永葆青春,仍然忠于其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传统。 多年来,社科院把某些外国专家发起探索的主题深入化多样化,令其面目一新,使国际历史编纂学有关近现代当代中国的部分取得了重大进展。
以中法合作为例。直到20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学派的声誉完全基于对传统中国研究的资质。 仅仅是在1950年之后,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历史才缓慢地艰难地被接受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摆脱当时着重致力于共产党发展的中国史学模式,避开美国学者开辟的注重研究机构、宗教团体或外交关系的途径,法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波高潮是投入探索一个当时被相对忽视的领域:即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思维方式的启发,这些历史学家对各阶级的分析感兴趣:工人、农民、资产阶级,阐明他们的经济行为,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与权力的关系。我个人研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发展的成果是,出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11-1937》(1986年),其后又出版了《上海史》(2002年)。
社会历史学家的第一波浪潮很快就被接纳,中美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员还经常超越其研究范围。 所有这些专家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近现代当代中国历史的认知有了很大的进展。
在这些进步得到肯定之际,新一代法国研究人员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他们前辈所开设的项目。受美国史学影响,他们专注于分析社会阶级和这些阶级的实践,撇开了与这些阶级及其实践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这种新方法最初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但成为主导后,很快就颠覆了原先的形式: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取代历史学家。就像所有的过激行为一样,这种现象需要纠正。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回归一种比我个人愿望更具历史意义的方法。这样的演变在法国只能以中国近现代当代史史学家目前的作品作为榜样来促进:硕果累累,质量优秀,立足于越来越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认识上的束缚。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向认真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王菊博士致意。长期以来,她向法国研究人员提供了她的中国同事们不断更新的资料及其他们更多更详尽的出版物的大量信息,而她的中文翻译,尤其是«上海史»中文版,使中国公众了解了法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
中法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是全球化导致的广泛的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层面,因此社科院和中国学论坛倡议邀请我们参与。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继续交流的人都清楚,这种对话有时很困难,充满了含糊不清和误解。这类对话的主要框架的构成取决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多样化的社会人物的相遇,他们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和阅历。在这些社会人物中,知识分子起了特殊作用,因为受学科给予他们的类似约束,他们有着共同的概念和语言,即便跨越大陆和海洋,即便词语有时会改变意义和内容概念。
在我撰写有关孙中山的专著时(1994年出版),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事实上,西方指责孙中山未能真正理解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和东亚传播的西方学说和理念,他经常表现出混乱的思维或虚假的雄心。他在1912年创立的共和国与法国或美国模式相距甚远,而他说是从这两个国家得到的启发。同样,他于1923年至1925年在广州推动的革命运动,经常偏离他所依靠的苏维埃先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表象上。跨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输入,不是一种模式的再现,也不是服从主导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而是以各种形式的新颖方式为起点的创造,通过融合的过程,开辟新的途径。该过程的效果不应通过与原有模式的比较来判断,它们是否符合这些模式或者它们相似的程度有多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明了这种融合产生的结果是否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演变所产生的具体问题,以及激发特定历史情况所需的特定政策和学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标准,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思想和工作之伟大。在借用西方文字和观念—民主、自由、社会进步—的名义下,他尽力通过演讲和著作引导中国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不是引进国外模式、而是建立适应当时中国需求和能力的新制度的道路。
即使有时在曾经的殖民背景下发生的这类融合只是优势文化的副产品,缺乏价值,但大多数情况下融合的原创性和效用使它们成为演变和发展的引擎,进而能够建立适合自己的模式,就像21世纪的“中国模式”。当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融合的转化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学论坛邀请我们参与国际合作,提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责任。
我衷心祝愿中国世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真诚期待各国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在此,我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王菊译,白吉尔审定)
【本文图片由上海社科院、获奖者本人提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