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钱一栋︱朱迪丝·施克莱与恐惧的自由主义

朱迪丝·施克莱
熟悉的陌生人
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1928-1992)也许是上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英美学界,施克莱享有崇高地位。她是哈佛政府学系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首位女主席;沃尔泽(Michael Walser)、卡维尔(Stanley Cavell)、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同辈巨匠和她是知交好友,桑德尔、阿克曼等后辈学人对她恭敬有加;罗尔斯、罗蒂都坦承,施克莱对自己的政治思想有过关键性影响。此外,虽然她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辩护士,但尚古且傲娇的施特劳斯学派却对她颇为尊崇;斯金纳、波考克、邓恩等剑桥派思想史家也将其视为重要的对话者。
虽然在学界内部,施克莱几乎可以与罗尔斯分庭抗礼,但如果以文章引用率、社会知名度为衡量标准,她则完全无法与罗尔斯、伯林乃至诺齐克、桑德尔等人相提并论。以施克莱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本就不多,安德烈亚斯·赫斯认为,其中仅有三部博士论文值得一提(Andreas Hes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udith N. Shkla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3-4)。在学术工业空前发达的今天,这个数据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在她去世时,《纽约时报》也只作了简要报道。这些悖谬现象大概与施克莱的学术风格有关。她是蒙田的信徒,拒绝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她的论述很难归入某一学术脉络,人们无法在熟悉的智识版图上将其准确定位。因此,虽然人们常能从她那里得到启发,但这些思想种子很少会出现在文献综述或注释里。

甘阳:《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李猛写于1997年的书评《我们如何理解现代性?——评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社会理论论坛》,北大社会学系,1997年第一期)是国内最早提及施克莱的文献之一,文章简要交代了施克莱对罗蒂的影响。甘阳那封著名的信件(《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一封信》,2001年;该文后以“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为题,收入渠敬东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对施克莱的学术地位及其在法学领域的基本观点作了凝练晓畅的介绍,由此引发了我国学界对施克莱的关注。但施克莱从没大红大紫过,其作品尚未系统翻译进来,相关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只有刘擎指导的一篇硕士论文(姚瑶:《面对残忍与恐惧——史珂拉政治思想初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其思想作过相对全面的梳理。也许对施克莱,我们还缺乏基本的了解,虽然她的名字早已不再让人陌生。
边缘人与美法传统
施克莱出生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父亲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经营的企业最终附属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并且还拥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在半个世纪后,继承了父亲财富的施克莱依然是其中一家公司的主要股份持有者(Andreas Hess, 2014, pp. 26-27)。与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等最终在美国大放异彩的犹太裔学者一样,施克莱也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但她走了一条独特的逃亡路线:横穿西伯利亚,经日本、跨太平洋、到美国,最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落脚。途径美国时,她们一家还因证件失效被长时间扣留。
施克莱没有犹太教背景,也不是德国文化的子嗣,她从小接受的是一种法国风格的世俗教育(Bernard Yack ed., 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 1996, p. 264)。因此,她在美国犹太裔流亡知识分子群体中显得极为独特。优越的物质条件也使她不同于一般的欧洲难民。这种疏离于各种群体的边缘身份在施克莱的学术工作中有明显反映:她对共同体边界、公民身份、排斥与接纳等问题多有关注,并一直以边缘人的视角思考政治问题。

施克莱对法国和美国的政治思想传统有深入且独到的理解,这离不开她的几位老师。施克莱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她在那儿遇到了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一位卢梭专家。施克莱的硕士论文即以卢梭为主题。
沃特金斯推荐她去哈佛读博。她在哈佛的导师是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后者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对极权主义、现代意识形态很有研究,施克莱在这些方面受他和阿伦特影响颇深。但此时的施克莱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者了,学术上不再亦步亦趋追随自己的导师。对弗里德里希的一些做法,她也颇有微词;事实上,她一直像索尔·贝娄那样冷眼旁观学院中人的种种做派,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院氛围尤其厌恶。此外,在罗伯特·麦克罗斯基(Robert McCloskey)、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课堂上,施克莱深入了解了美国政法传统,虽然她后来对哈茨那种洛克中心主义的美国史叙事不无批评。她也参加过阿伦特、伯林等人在哈佛主持的研讨班(Andreas Hess, 2014, pp. 2, 48-49)。渐渐地,施克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家,并顺利留校任教。

由今入古,鉴欧知美
施克莱生前出版过八部作品,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她最早的两本著作名为《乌托邦之后:政治信仰的衰退》(After Utopia: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Faith , 1957)和《守法主义:法律、道德与政治审判》(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 1964)。乍看之下,这两本书风马牛不相及:前一本侧重历史维度,对启蒙理想、基督教思想和浪漫主义传统的恩怨情仇作了细致分析;后一本以法理学领域的哈特-富勒之争和纽伦堡审判为背景,讨论法律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但它们其实是同一时代氛围的产物,关注的都是政治哲学在当代世界的命运:提供理想社会蓝图的政治理论为何不再可能?自认为超然于诸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守法主义为何依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施克莱认为,以理性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启蒙信念不可避免地消退了,浪漫主义等对立思潮同样无法对这个时代作出回应;她还向冷战时代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自由民主派泼了一盆冷水,指出他们那种价值无涉、理性客观中立的自我期许只是一场幻梦。这两本书与弗里德里希、阿伦特的相关研究关系密切,还展现了施克莱在法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的深厚学养,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她在博士阶段及职业生涯早期吸收的庞杂思想资源。

《守法主义:法律、道德与政治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守法主义》一书在法学界恶评如潮。施克莱认为,法律与道德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法律更没有高踞于各种价值体系之上,相反,法律处于特定价值体系之内,法律理论只有作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恰切理解。这些本是常识,但晚近的意识形态氛围尤其是法律职业群体内部的意识形态氛围却使这些常识观点显得荒谬且危险。当代最重要的法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与施克莱观点类似,也因此,他的立场在法学界并不占主流,最近半个世纪的法哲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德沃金一人与哈特及其徒子徒孙的漫长论战。
德沃金直到晚年才真正点破这一点:法律是政治道德的一个枝杈,法律权利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权利。在早期作品中,他同样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规范体系,试图在此前提下说明两者如何互动(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02,405)。于是,既在法律体系之内又具有道德属性的原则就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但德沃金很快意识到,围绕原则进行阐述多少有些词不达意。在写于1972年的文章《规则模式II》中,他已明确指出,关键不在法律是否包含原则;他真正想说的是,法律识别过程无法独立于政治道德因素,完全形式化;他之所以关注原则,只是因为原则为法律命题提供了道德证成。但在此文发表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法律实证主义者依然乐此不疲地讨论分类学意义上的法律和道德究竟有什么区别、道德原则能否纳入法律范畴之内,完全没领会到德沃金关心的是规范性问题。德沃金事后感慨,时间都被浪费在这种无聊争吵中了。而回过头来看,早在写于1986年的《守法主义》再版序言中,施克莱已经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德沃金尚未挑明的理论要义:法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规范性问题具有论辩特征。不无夸张地说,她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了作者的观点。当然公平而论,与德沃金、拉兹(Joseph Raz,拉兹也主张法律是道德的特殊部分、法律的规范性最终来自价值,但认为法律规则无需解释它所要求的行动有何种价值就能成为行动理由,其证成是内容独立的,因此法律又表现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规范体系)等人相比,施克莱的相关论证要粗疏很多。客观来看,《守法主义》展现了施克莱的敏锐洞察力,但仅此还不足以使它成为里程碑式的法学著作,观点同样深刻而论证远为精细的《法律帝国》当然是更伟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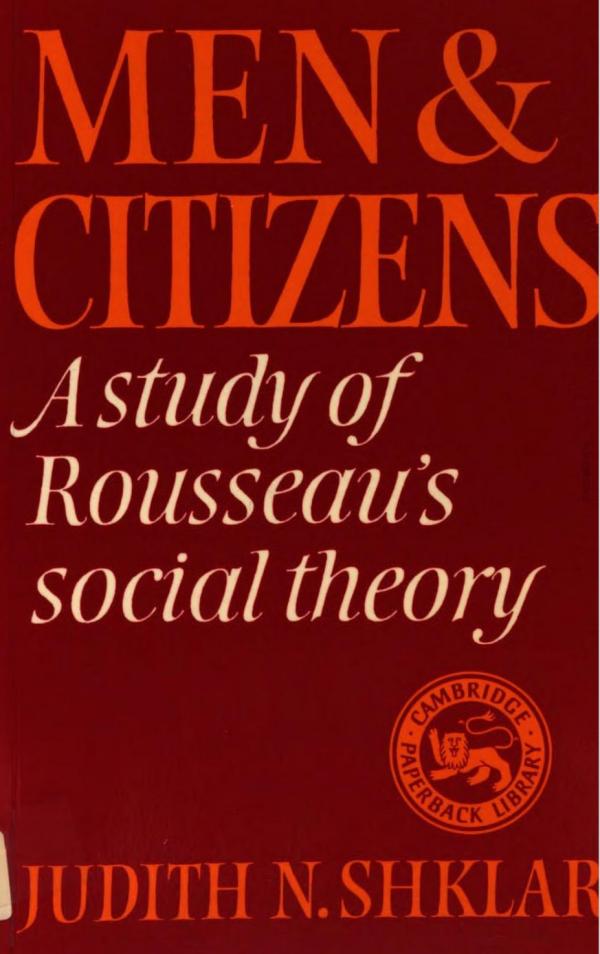

施克莱只在五十年代开设过法学课程,后来长时间讲授欧洲政治思想。除了教学需要,从自身研究脉络来看,在对当代问题作了初步诊断后,她也有必要返回现代思想的初生年代,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下思想模式的来龙去脉。因此她转入了对卢梭和黑格尔的研究,最终产物是《人与公民:卢梭社会理论研究》(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1969)和《自由与独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政治观念研究》(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 1976)这两部作品。解读卢梭和黑格尔的文献早已浩若烟海,但施克莱这两本书却别出心裁,揭示了两人作为道德心理学家的一面。此外,她还写过一本讲孟德斯鸠的小册子(Montesquieu, 1987)。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施克莱开始深入研究美国本土政治传统,她的阅读重心转移到了美国文学和智识史。出版于1984年的《平常的恶》(Ordinary Vices)是施克莱第一部拥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作品。同属于这一创作阶段的还有两部作品:《不正义的诸张面孔》(The Faces of Injustice, 1990)《美国公民身份》(American Citizenship, 1991)。相比后两本书,《平常的恶》依然留有一些思想史色彩,不少研究者会把这本书放到卢梭、黑格尔、蒙田、孟德斯鸠这样一个人物研究序列中来把握。不过我认为,此书与那篇纲领性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 1989)显然是施克莱式政治理论的核心文本,施克莱自己而非蒙田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可以说,以此书出版为标志,施克莱进入了学术生涯成熟期,开始以自己的声音阐发独特的政治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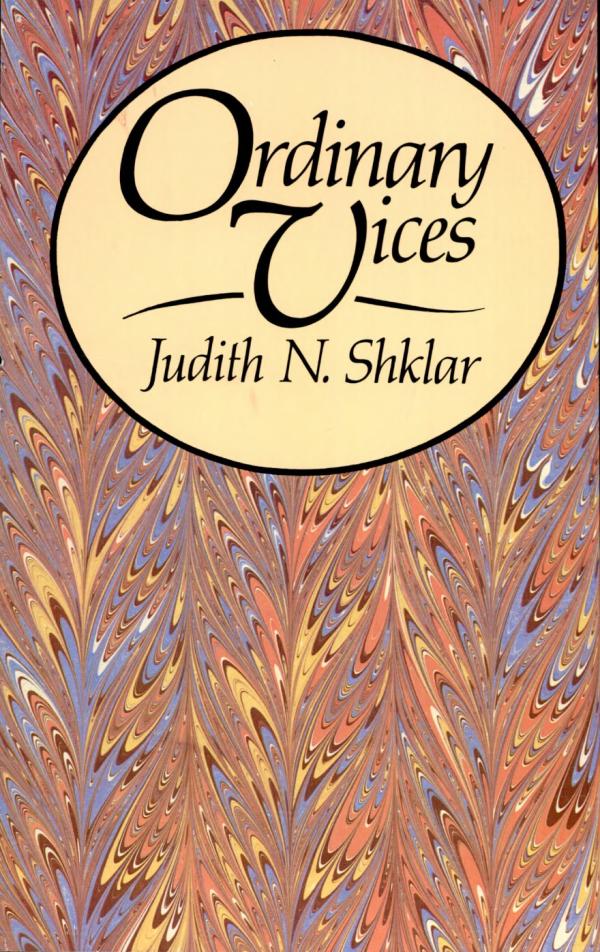


文史交融、欧美互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例如《平常的恶》乍看之下几乎是一部文学评论集,而实质内容则是“与蒙田一起思考美国问题”;《不正义的诸张面孔》上来就讲了《匹克威克外传》中著名的巴德尔诉匹克威克案,并从许多地方、不同时代选取例子,“但这整本书写的其实是美国”(Judith Shklar, The Faces of Injusti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施克莱并不赞同那种流俗看法:欧洲提供政治思想,美国将之付诸实践。她不仅认为美国的政治实践值得老欧洲学习,还呼吁“找回美国的政治思想”。与那些在欧洲完成学术训练,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多有不满的流亡学者相比,施克莱的立场显然更现代、更美国。
1992年,正处于学术巅峰期的施克莱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生命,她的诸多思考尚未付诸笔端。施克莱去世后,斯坦利·霍夫曼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将她的零散文章汇编成了两册文集:《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1998)与《找回美国政治思想》(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1998)。此外,在1996年,伯纳德·雅克(Bernard Yack)编辑出版了一部极为重要的文集,《不抱幻想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里面收录了诸多与施克莱有过交集的重量级学者对她思想的评述,并附上了施克莱的思想自传《一生问学》(A Life of Lear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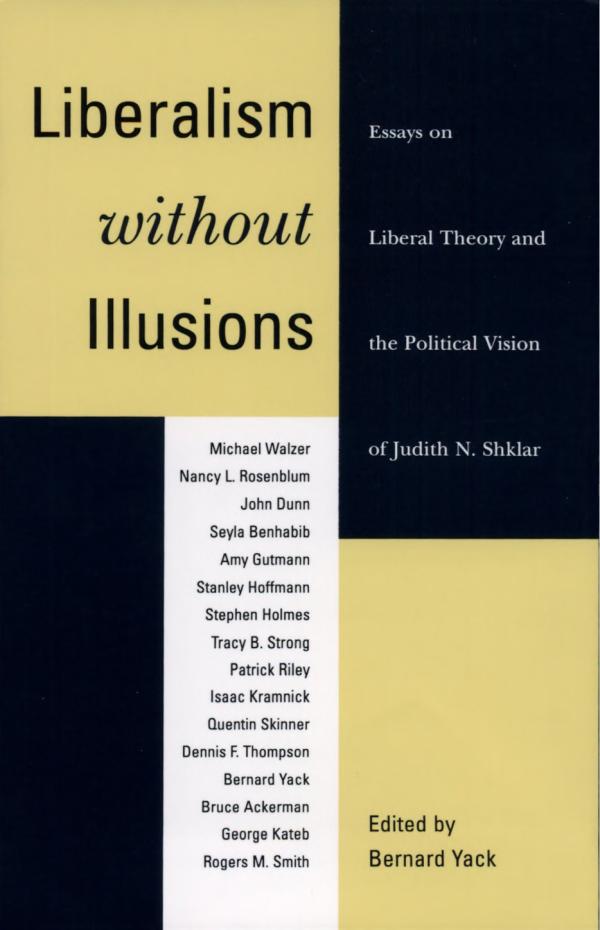
沉重的思想与轻逸的思考
政治思想家一般以善或正义为核心概念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施克莱关注的却是恶与不正义。在前述第三个创作阶段,她发展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想,其最早表述则可追溯到《守法主义》一书(Judith Shklar, 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
施克莱的政治思想被贴上了诸多标签,如前面提到的不抱幻想的自由主义,此外还有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少数派的自由主义、骨感自由主义(barebones liberalism),以及最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恐惧的自由主义。每个标签都提示了施克莱政治思想的某一侧面。大体来说,施克莱式自由主义以道德心理学为基础,关注自由的制度保障和自由社会成员的品格问题(施克莱意义上的道德心理学,以及道德心理学与政治理论的关系问题参见Stanley Hoffmann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xi)。

施克莱并不认同洛克那种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她认为,在科学昌明的年代,再谈自然权利未免有些装神弄鬼。她更不会接受小密尔式的至善论自由主义。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她着眼于沉重的历史记忆,认为自由主义不是一项追求至善的筹划,而只是避免至恶的良方,并且是以牺牲柏拉图式至高美德、接受庸碌者之恶为代价,来避免至恶(Bernard Yack ed., 1996, p. 56. Judith Shklar, Ordinary V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
伯林认为,标准的自由主义心理学——受理性约束的自利和正义感——很不充分,忽视了情感和无意识层面,尤其是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此外还低估了人类的邪恶和破坏性动机。与伯林类似,施克莱虽然持自由主义立场,但也认为大部分自由主义思想所预设的心理学乐观且肤浅。她将自由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组阴暗的假定之上:人的残忍性情根深蒂固,而残忍是首要之恶,残忍行为使人恐惧,恐惧则会败坏人格、使人陷入悲惨低劣的状态。可见,施克莱关注的是弱者免于强者伤害、免于恐惧的自由;她将对残忍行为的恐惧设定为自由主义的情感基础。因此,恐惧的自由主义并不以权利为起点。施克莱追随孟德斯鸠,认为法治、权利是为了使人免于恐惧而创设的一系列制度。她还强调,孟德斯鸠对美国政法传统的影响并不逊色于“伟大的洛克先生”。
施克莱的这些观点也许会让人想起霍布斯。不过,虽然她和霍布斯都认为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使人免于恐惧,但她更关注利维坦带来的恐惧,而非人们彼此之间的恐惧。在她看来,像施特劳斯那样将霍布斯视为自由主义之父是一种粗疏的误读,因为《利维坦》的作者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公共权威不能侵犯个人自由(Stanley Hoffmann ed., 1998, p. 6)。于是乍看之下,施克莱的观点很接近哈耶克等主张最小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非如此。她认为哈耶克之流对私人企业的信仰是无根无据的,后者同样会威胁人们的自由与安全。更糟糕的是,哈耶克们还会把人们有能力控制的不正义之事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不幸之事,而对于不幸之事,我们只能默默忍受,无法责备他人、要求补偿(Bernard Yack ed., 1996, pp. 2-4)。

残忍是首要之恶,这也许是自由主义者唯一的道德确信。自由派丧失了古人那种整全的道德信念,自由主义是诸文化的文化、无体系之体系,多元主义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不过,人们不会因为多元主义现实而径直拥抱宽容。面对多元现实,人们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压制“异端”。但冲突的残酷性使人认识到,相比于为至善而斗争,避免至恶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出现恰恰以基督教道德对基督教实践的否定为中介,“这是一种在残忍的宗教内战中诞生的自由主义,这种战争使基督教的仁爱主张永远地变成了对所有宗教机构和派系的责难”(Judith Shklar, 1984, p. 5)。对教义一致性的要求因其残酷后果而遭到仁爱道德的谴责,后者演变为了宽容。不过,“视残忍为首恶”这一信念虽然有基督教道德根源,但残忍的至恶地位最终却使上帝统治的道德宇宙坍塌了: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残忍没什么区别,宗教理由并不能为残忍辩护。宽容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宗教信仰,而扩展到了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为了避免残忍、保卫自由,孟德斯鸠们构想出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多元团体制衡的手段,于是自由主义的形象变得丰满了。
可见,自由主义与多元性之间关系极为复杂。自由主义诞生于宗教内战这一多元语境之中,自由主义制度为多元性提供了庇护,而多元性最终也成了抵御政治横暴、维护自由的坚实后盾。当然,我们也要为多元性付出代价,因为宽容是一种沉重的道德负担。我们必须持续一贯地自我克制,容忍那些很令自己厌恶但不触及原则的性观念、道德立场、宗教信仰……
我们甚至还得在一定程度上拥抱虚伪。在公共言谈中,我们必须对不同种族、性别平等相待,哪怕内心并不真正认同这些群体。施克莱说,这种道貌岸然恰恰是道德努力而非道德失败的证明。在多元社会,势利也是不可避免之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都在排斥他人,也被别人排斥。背叛则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有权拥有多种多样的忠诚对象。此外还有厌世。对人性缺陷的厌恶也许会把我们引向一种不抱幻想的政治生活,但也可能使人变得像尼采那样,希望庸人早点灭绝,好为超人腾出历史舞台。在此,恶的排序变得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厌恶虚伪、背叛胜过残忍,那么我们也许会因愤世嫉俗作出残忍举动。
残忍、虚伪、势利、背叛、厌世……这些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恶。它们出现在私人领域中,但也会产生公共影响。这就是作为政治理论家的施克莱思考平常之恶的原因(她本人对政治理论的理解参见Judith Shklar, 1984, p. 228. 以及1990, p. 16)。在残忍为首恶这一确信的指引下,施克莱细致考察了这些恶对自由民主政制的利弊,以此揭示我们要与哪些举止做派作斗争。也因此,自由主义并非如一般人理解的那样,不会对人提出什么高要求,放任自流即可。自由主义施加于人的心理负担特别是自控要求表明,它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品格理论,这意味着,自由派要过一种平凡而艰巨的道德生活。

除了实质观点,在论述风格上,施克莱同样独树一帜。她不喜欢凭空雕琢概念、构造论证的哲学式论述,而着迷于揭示尚未获得概念结构的人类经验(Judith Shklar, 1984, pp. 6, 228-230)。她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家,虽然她对诸种观念体系的历史浮沉作了大量分析。了解历史是为了返回自身;施克莱相信,认清我们精神上的先祖有助于理解当下的思想模式,正所谓今乃古之变,由古入今,乃真得今者(Judith Shklar, After Utopia: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ix)。因此不同于剑桥学派,施克莱并不劳心费力于考察特定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她无意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问题——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准确性无关紧要。她更不会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认为过去时代的思想巨人已经对恒常问题作了透彻思考,侏儒般的现代人只应俯首聆听其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施克莱认为,过去与现在显然不同,但也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和复杂的历史联系:现在由诸种历史传统层累而成。可以邀请先哲加入我们对此时此地之事所作的讨论,借助他们的智慧来思考我们的问题,但千万别认为他们无所不知。
施克莱将自己定位为政治理论家、道德心理学家。她的论述既没有哲学那样抽象,也不似史学那般缺乏分析色彩。她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历史上、生活中,以及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她希望那些难以被理论话语捕捉的微妙感受在故事中显形,从而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自身,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