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托妮·莫里森《他者的起源》:世上没有外来者,只有不同版本的我们自己


本期封面人物
托妮·莫里森
郭天容/绘
1993年,托妮·莫里森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非洲裔女性作家。瑞典文学院赞誉她的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激活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她的诺奖演说中,莫里森讲述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手中之鸟”的故事:当眼盲的老妇人面对年轻人关于手中之鸟是死是活的提问时,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手中的鸟儿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就在你们手中。掌握在你们手中”。莫里森将语言比作“手中之鸟”,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更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她相信,尽管语言会被权力利用、操纵,但语言也是自由的,它能保护我们免于无名之物的恐惧。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描绘叙述者、读者和作者真实的、想象中的和可能的生活。尽管有时语言以抽离经验的姿态出现,但它不是经验的替代品。它以弧线趋向意义可能的所在。
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尽可能地靠近无法言说之物。
莫里森在演讲中告诉所有人,我们会死。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创造了语言。这也许就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
由此,莫里森的写作常常以多声部的复调,引入不同文化角色、真实与虚幻的声音,读者常常迷惑于她笔下的神话、魔法乃至迷信与现实产生了极为贴合的效果,以至于一部分评论者将她归于类似马尔克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一类的作家。
但在她眼里,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许多同类的黑人作家一样,莫里森会在作品里呈现主流文化对少数族群文化的破坏。对此采取的反思体现了莫里森的特殊之处,她呼吁少数族群里的知识分子能够返身内部,重建自身文化的传统,她也注重在作品里体现传统的语言习惯,不随意使用主流文化的那套词汇,她以作品引导读者如何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的独特身份而不被主流文化轻易吞没,这个过程里有牺牲,但更有可能在平凡人中间诞生英雄般的人格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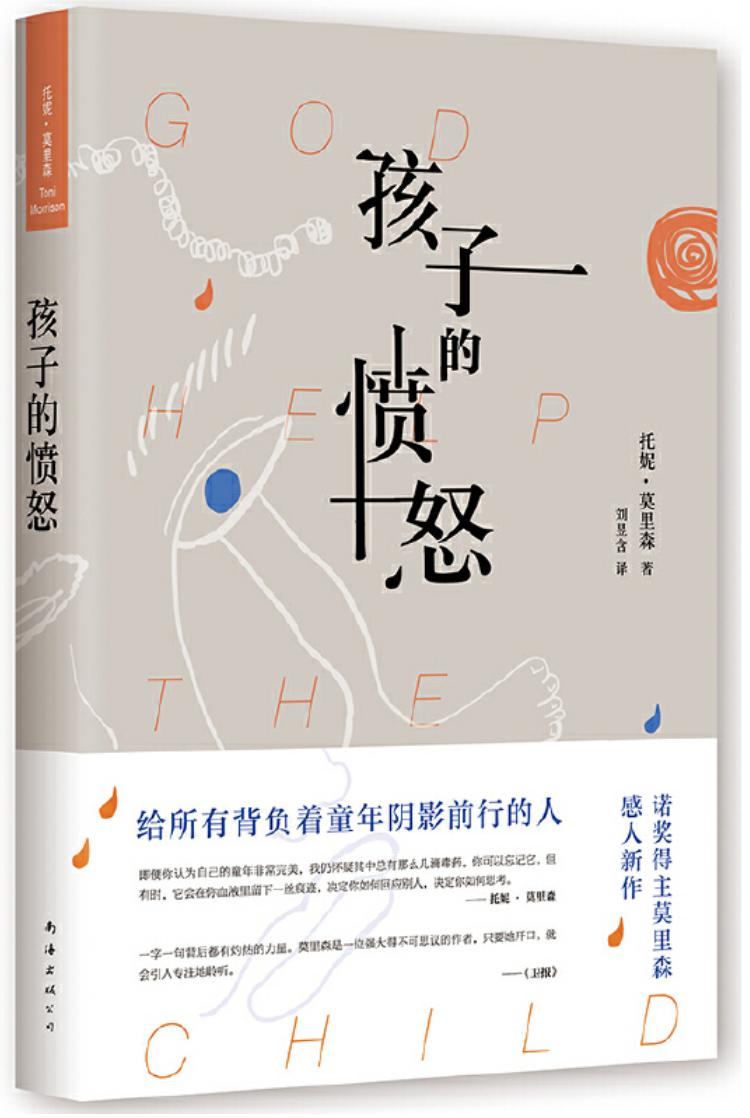
托妮·莫里森部分作品
写作生涯中,莫里森一直践行着她的理念。随着我们对多元文化的深入感受,也终将会意识到她带来的前瞻思考:每一种文化都应保护自己的传统和自信,在世界文化里彼此平等。
近期由新经典推出的《他者的起源》中收录了托妮·莫里森的诺奖演讲全文,以及她在哈佛大学发表的两次系列讲座《在黑暗中游戏》与《他者的起源》,作家唯一的短篇小说《宣叙调》也纳入其中。《宣叙调》讲述了两个女孩从孤儿院到成人的经历和友谊的故事。她的作品用诗性的文字指引读者越过修辞的藩篱与故事的屏风,指向语言本身最难言明的美,揭示掩藏在权力背后的历史潜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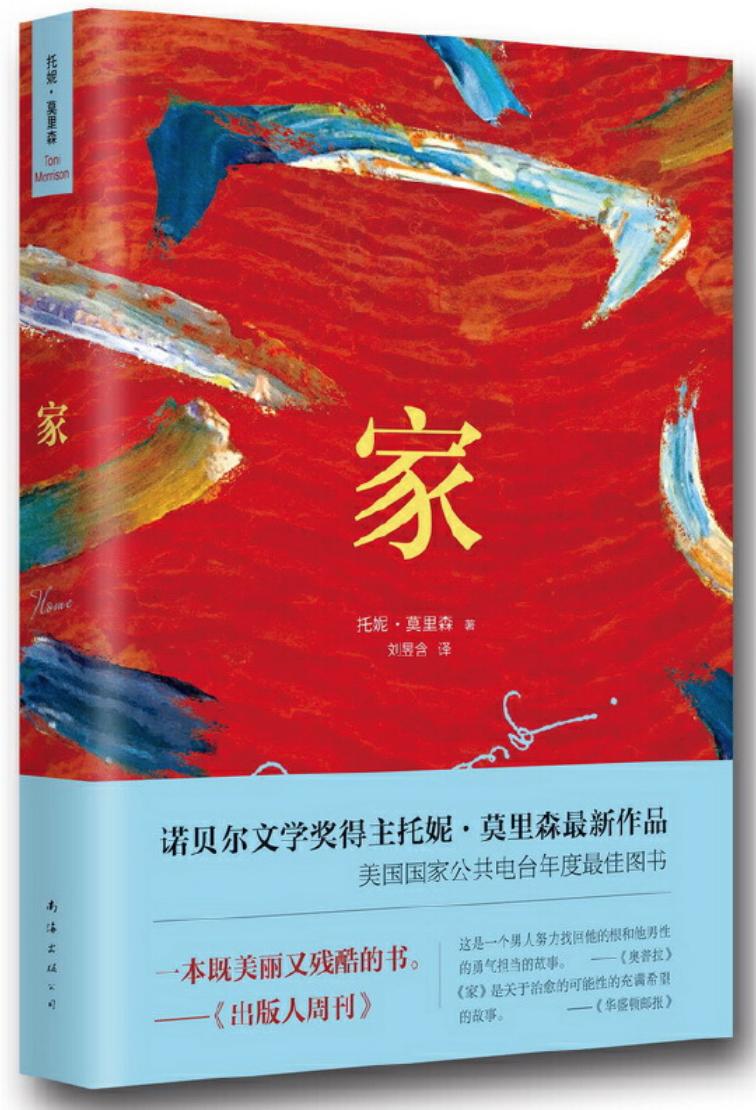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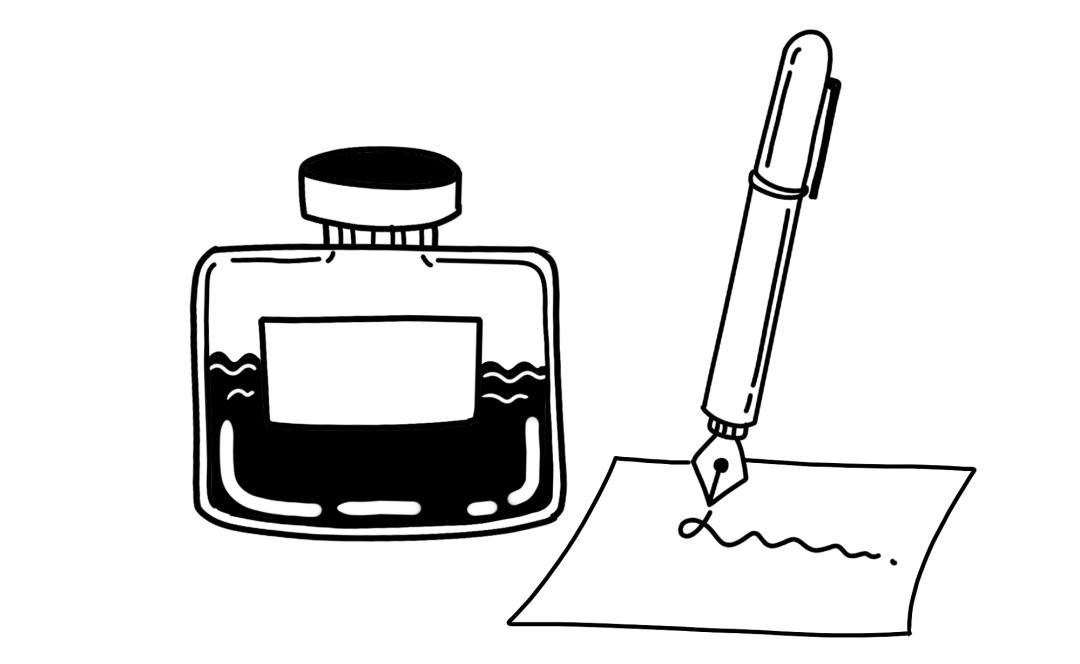
宣叙调(作品节选)
我的妈妈整夜跳舞,罗伯塔的妈妈病了。这就是我们被带去圣伯尼的原因。当你告诉人们你住在收容所时,大家总想伸出手臂拥抱你,但情况其实没那么糟。那儿没有贝尔维尤收容所里那种摆着一百张床的长长的大房间。一个房间四张床,当我和罗伯塔到那儿的时候,从州里来的孩子不多,所以只有我们被分到了406号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从一个床位换到另一个。而我们也正想这么做。我们每晚都换床,在那儿的整整四个月里,我们都没有选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床位。
一开始事情并不是这样。从我走进房间、那个“大笨蛋”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胃里一阵恶心。大清早从自己的床上被叫起来是一回事,和完全不同种族的女孩一起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则是另一回事。玛丽,也就是我的妈妈,她说的是对的。她时不时会停下舞步,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他们从不洗头,身上有股怪味。罗伯塔的确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她闻起来怪怪的。所以当“大笨蛋”(从来没人叫她伊特金太太,就像没人管这里叫圣伯纳文彻一样)说“特薇拉,这是罗伯塔。罗伯塔,这是特薇拉。你们要好好相处”时,我回答道:“你把我安排在这儿,我妈妈是不会乐意的。”
“那样也好,”“笨蛋”说,“说不定她就会来接你回家了。”
那是什么意思?如果当时罗伯塔笑了,我会杀掉她,但她没有。她只是走到窗前,背对我们站着。“转过来,”“笨蛋”说,“别那么不讲礼貌。听好了,特薇拉、罗伯塔。当你们听到一声响亮的嗡鸣,那就是晚饭的铃声。听见后就下到一楼。谁打架谁就不能看电影。”接着,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错过什么,她说:“《绿野仙踪》。”
罗伯塔一定以为我的意思是,我妈妈会因为我住进了收容所而生气,而不是因为我要和她住一个房间,因为“笨蛋”一走,她就朝我走过来,问:“你妈妈也生病了吗?”“没有,”我说,“她只是喜欢整夜跳舞。”
“哦。”她点了点头,我喜欢她一点就通。所以尽管我们站在一起看起来就像盐和胡椒,有时其他孩子会这么取笑我们,但现在,这都无关紧要。那时我们八岁,考试总是不及格。因为我不记得我读过什么、老师讲了什么。而罗伯塔根本不识字,也从不听讲。她什么都不擅长,却是个抓子儿游戏的能手:抛接抛接抛接。
一开始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对方,但其他人都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因为我们俩都不是真正的孤儿,天上没有我们已故的慈爱父母。我们是被抛弃的。连从纽约市区来的波多黎各人和纽约上州来的印第安人也不理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孩子,黑人,白人,甚至还有两个韩国人。但这里的伙食还不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罗伯塔讨厌这儿的食物,把整块食物剩在盘子里:午餐肉、索尔兹伯里汉堡牛肉饼,甚至是加了什锦水果的果冻,她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吃了那些她不想吃的东西。玛丽的晚餐理念是爆米花和一罐优糊。对我来说,热土豆泥加双份香肠就像是过感恩节了。
圣伯尼真的没有那么糟。住在二楼的年纪大些的女孩们会时不时地推搡我们。但也不过如此。她们涂口红,画眉毛,看电视的时候会晃动膝盖。她们十五六岁,有些人年龄甚至更大。这些女孩大多是出于害怕而离家出走的。这些竭力从她们的叔叔手中逃脱的可怜姑娘在我们看来又凶又刻薄。天哪,她们看起来真的很凶。管理员试图将她们与年纪小的孩子们分开,但有时我们偷看她们在果园放着收音机一起跳舞,会被逮个正着。
她们会追上我们,扯我们的头发,扭我们的胳膊。我们害怕她们,无论是我还是罗伯塔,但我们都不想让对方知道。于是我们想出了一长串脏话,从果园逃跑时,我们可以喊出来回骂。我以前经常做梦,几乎总会梦见这座果园。面积两英亩,也可能有四英亩,园里种着这些小苹果树。几百棵。我刚来圣伯尼的时候,苹果树空荡荡的,像乞讨的女人一样弯着身子,而当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枝头开满了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梦到这座果园。那里无事发生。我是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只有那些年长一些的女孩会播放着收音机跳舞。我和罗伯塔看着。玛吉有一次在那儿摔倒了。就是那个腿弯得像括号一样的厨娘。大女孩们都在嘲笑她。我知道我们当时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我们害怕那些涂着口红、画着眉毛的女孩。玛吉不能说话。孩子们说她的舌头被割掉了,但我觉得她只是生来如此:哑巴。她的年纪很大,皮肤呈沙色,在厨房工作。我不知道她人好不好。我只记得她的腿弯得像括号,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她从清晨一直工作到两点钟,如果她迟到了,或是需要清理的东西太多,那么直到两点十五分左右她才会离开。她会穿过果园抄近路,免得错过公交车,否则她就要再等上一个小时。她戴着一顶很蠢的小帽子——一顶带有耳罩的儿童帽——而她也并不比我们这些孩子高多少。真是一顶糟透了的小帽子。即使对一个哑巴来说,这也够蠢的——穿得像个孩子,一句话也不说。
“可是如果有人想杀了她怎么办?”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她想哭呢?她会哭吗?”
“当然,”罗伯塔说,“但只有眼泪,没有声音。”
“她也无法尖叫?”
“对,她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她能听见吗?”
“有可能。”
“我们试试看。”我说。于是我们这么做了。
“哑巴!哑巴!”她没有回过头。“罗圈腿!罗圈腿!”她依旧没有反应,只是摇摇晃晃地继续走着,儿童帽的绑带左右飘荡。我认为我们做错了。我觉得她能听得到,只是假装没听见。直到现在,一想到当时毕竟有人听到我们那么叫她却又不能告发我们,我就感到羞愧。

我和罗伯塔相处得很愉快。我们每晚换床睡,公民教育、沟通技巧和体育课都不及格。“大笨蛋”说她对我们很失望。在我们这一百三十个从州里来的孩子中,有九十个不满十二岁。几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孤儿,他们死去的慈爱父母在天有灵。只有我们俩是被抛弃的,也只有我们体育在内的三门课都不及格。所以我们关系不错——她把不吃的食物完整地留在盘子里,也出于友善不对我问东问西。
我想那应该是玛吉摔倒的前一天,我们得知我们的妈妈会在同一个星期天来探望我们。我们已经在收容所里待了二十八天(罗伯塔待了二十八天半),这是她们第一次来看望我们。她们会在十点钟来,正好赶上我们做礼拜,然后会和我们一起在教师休息室里吃午饭。我想如果我那跳舞的妈妈与她那生病的妈妈碰面,也许对我的妈妈来说是好事。而罗伯塔觉得她那生病的妈妈见到我那跳舞的妈妈会激动不已。我们越想越兴奋,还为对方卷了头发。吃过早饭后,我们坐在床上,透过窗户盯着马路。
节选自《他者的起源》托妮·莫里森/著,黄琨/译
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7月版
原标题:《托妮·莫里森《他者的起源》:世上没有外来者,只有不同版本的我们自己》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