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写作与凝视:成为文学记者需要哪些自我修养?
“凝视是一种
穿越时空的努力。”

对文学读者而言,似乎成为一名文学记者是很幸福的事,这意味着直接深入文学现场,时常收到作家的签名新作,与作家们面对面交流,意味着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多面。与此同时,这份职业也并非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轻松,它更意味着记者需要保持学习的能量,保持追踪作家新作的毅力与热情,随时关注读者和评论家的反馈。
近期来自《文艺报》青年评论家、记者行超的新书《爱与尊严的时刻: 当代作家访谈录》正好为读者打开了这样一个观察窗口。在这本书里,她集纳了10年间对王蒙、莫言、王安忆、阿来、贾平凹、梁鸿、徐则臣、鲁敏等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采访对话,这些作家分享了自己对文学和现实的洞察,也在表达如何怀着善意、体谅和爱去看待他人与生活。
在下面这篇序言中,她坦言面对一些作家时对话的艰难时刻、从作家身上学习到的思考与自省的能力,以及凝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最终我们都还原到了“读者”的身份,“阅读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它让我们可以与所有伟大的灵魂相遇、对望,最终也指引我们真诚勇敢地面对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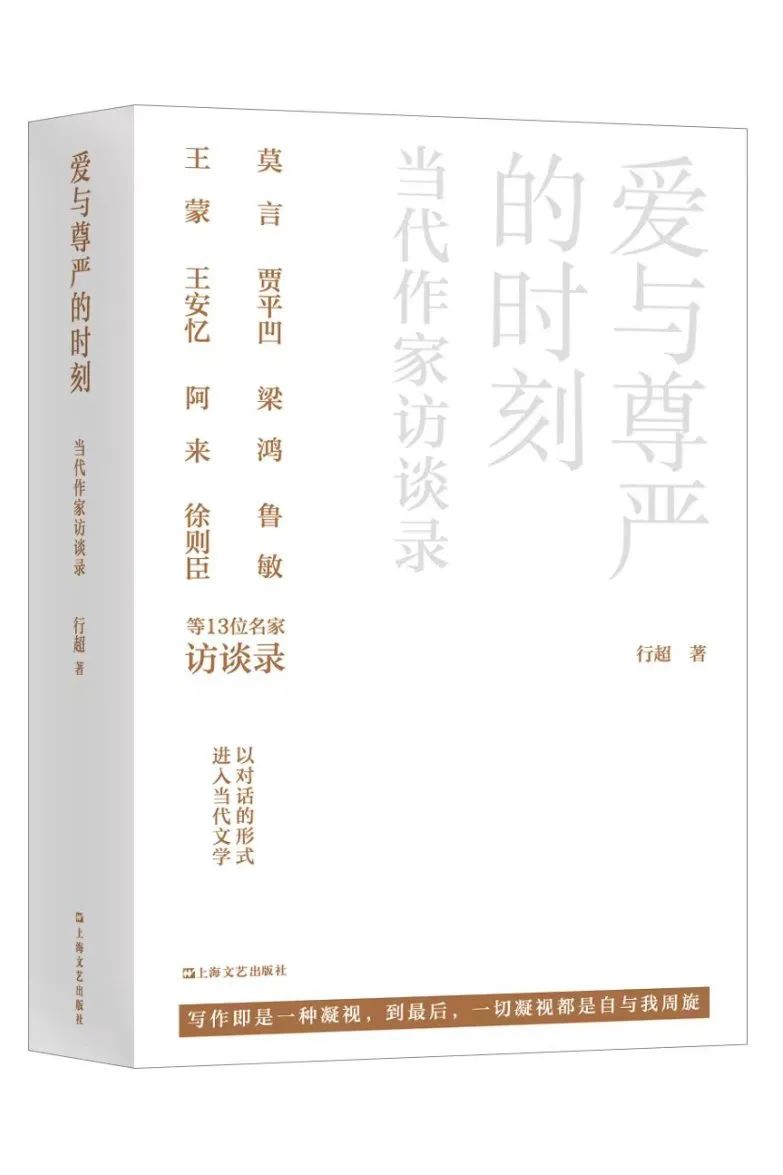
《爱与尊严的时刻:
当代作家访谈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写作与凝视
文 / 行超
在一次与梁鸿老师的对谈中,我忽然意识到,写作即是一种凝视。
那次对谈中,梁鸿忆起她儿时常常凝视天空中缓慢移动的云彩,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文学想象。我想我们都有过类似的时刻,凝视一棵树,凝视一条河,凝视一些仿佛转瞬即逝却最终令人终生难忘的场景。与单纯的观看或观察不同,凝视包含更多的主体意识。对于作家而言,“凝视”时的“看”,几乎是一切写作的起点,而它所隐含的、随着时间的前行而不断深入的思考与自省,更是所有写作共同追求的意义。
有时候,凝视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努力。
2013年,我受命采访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王蒙老师。这是一部尘封多年的旧作,从1974年完稿,到2012年的重新发现和修改,再到最终出版,其间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岁月沧桑。四十年,足以将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蹉跎成洞若观火的耄耋老人,也足以翻越一段段历史,足以遗忘许多的人和事。在文字中与四十年前的自己相遇,该是何等的心境?我想对王蒙而言,凝视一部四十年前的书稿,就如同凝视这浩荡的人生。小说《这边风景》的艰难面世,恰如用四十年的时间赶赴一场漫长的约定,如其所说,“唯有生活不可摧毁”,也唯有文学最难放弃。


作为一个四川人,面对“5·12”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时刻,阿来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行情绪的抒发。他一边克制着书写的冲动,警惕于肤浅的文字呈现,一边目睹着以天为单位迅速蔓延的集体遗忘。十年之后,一个特殊的形象在他脑中出现,于是才有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用十年凝视一场灾难,阿来思考的是,既然人力不可阻挡,那么劫后余生的人们该如何在废墟中寻求希望。在这种长久的、冷静而理性的凝视中,一个作家重新认识了自然,也重新评估了命运和死亡。
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凝视故土,是认识自我、建构自我的开始。
2018年秋天,当我踏进贾平凹的书房,我便理解了,为何他的写作始终凝视着秦岭,凝视着商洛地带。那不仅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滋养,更是令一个人成为今天的自我的根本性塑造。长篇小说《老生》写到,“我有使命不敢怠”。书写是作家的根本使命。《秦腔》《古炉》《老生》《山本》《秦岭记》,贾平凹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自己的使命,他早已与自己笔下的土地生死与共,他的双脚扎根在这里,他的双眼凝视着这里,他的笔于是也长久地留驻在这里。


从《中国在梁庄》开始,梁鸿花了十年时间凝视自己的故乡。虽然早已走出梁庄,但这个梁庄的女儿,她的目光始终牢牢地牵绊于此。无论是此后的《出梁庄记》,还是小说《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四象》,梁庄几乎成为她所有作品的种子。不久前出版的《梁庄十年》更见证了她与梁庄的共同成长。与十年前的矛盾、挣扎不同,如今,梁鸿的文字与她笔下的梁庄一样,逐渐松弛、温暖、泰然自若。从年少时的凝视一朵云彩开始,梁鸿的写作得益于这样专注而坚韧的凝视能力,她从梁庄看中国,也在梁庄和梁庄人身上重新认识自己。
凝视也是一种对镜自照。
阿甘本曾提出著名的“同时代人”,指的是那些对自己所处时代具有审视能力的人,他们不过分契合时代,而是“死死地凝视它”。徐则臣所推崇的“中年写作”,即是一种对时代与自我的凝视。《耶路撒冷》《北上》,他的写作仿佛沿着一条开阔而深邃的长河,朝向更加复杂的他者与世界。这样的写作路径,或许也昭示着许多当代人的人生轨迹,我们一边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毅然前行,一边不断地自我怀疑,深陷于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挣扎。在业已中年或迎向中年的时刻,用写作与时代对话,其实也是一种感知和应对时间的方式。


作为80后的代表,张悦然的写作过程折射着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与蜕变。长篇小说《茧》的出现,让文学界看到了80后作家直面历史的努力。从世纪之交的出道到现在,这些曾被视为叛逆者的“新新人类”,亲历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的巨大变革,一步步由玩世不恭的少年成长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笔下,多年前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已经逐渐被真实、复杂乃至沉重的生命经验所取代。青春期转瞬即逝,真正牢固而长久的,是现实生活的坚不可摧。凝视这样一个同龄人的写作,对我更像是再次踏上一段时光的旅程。
到最后,一切凝视都是与自我周旋。
与王安忆的对谈,在本书中篇幅最小,却最让我感到艰难。自八十年代开始,王安忆时刻立于当代文学的潮头,但她并不是追逐潮流的写作者,以任何思潮或理论去阐释她的小说,都是一种遗憾与局限。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凝视着上海,凝视着历史,更凝视着那些日常生活深处的温情与残酷。许多年来,王安忆的写作一直在与自我周旋,仿若一次次将自己推向深渊。她的文字从细腻敏感、旖旎风姿,一点点转向抽象的哲学思考,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干涩、硬朗,但这并不意味着枯燥,而是一字千金的铿锵与力量。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同为女性,这样的改变令我深深感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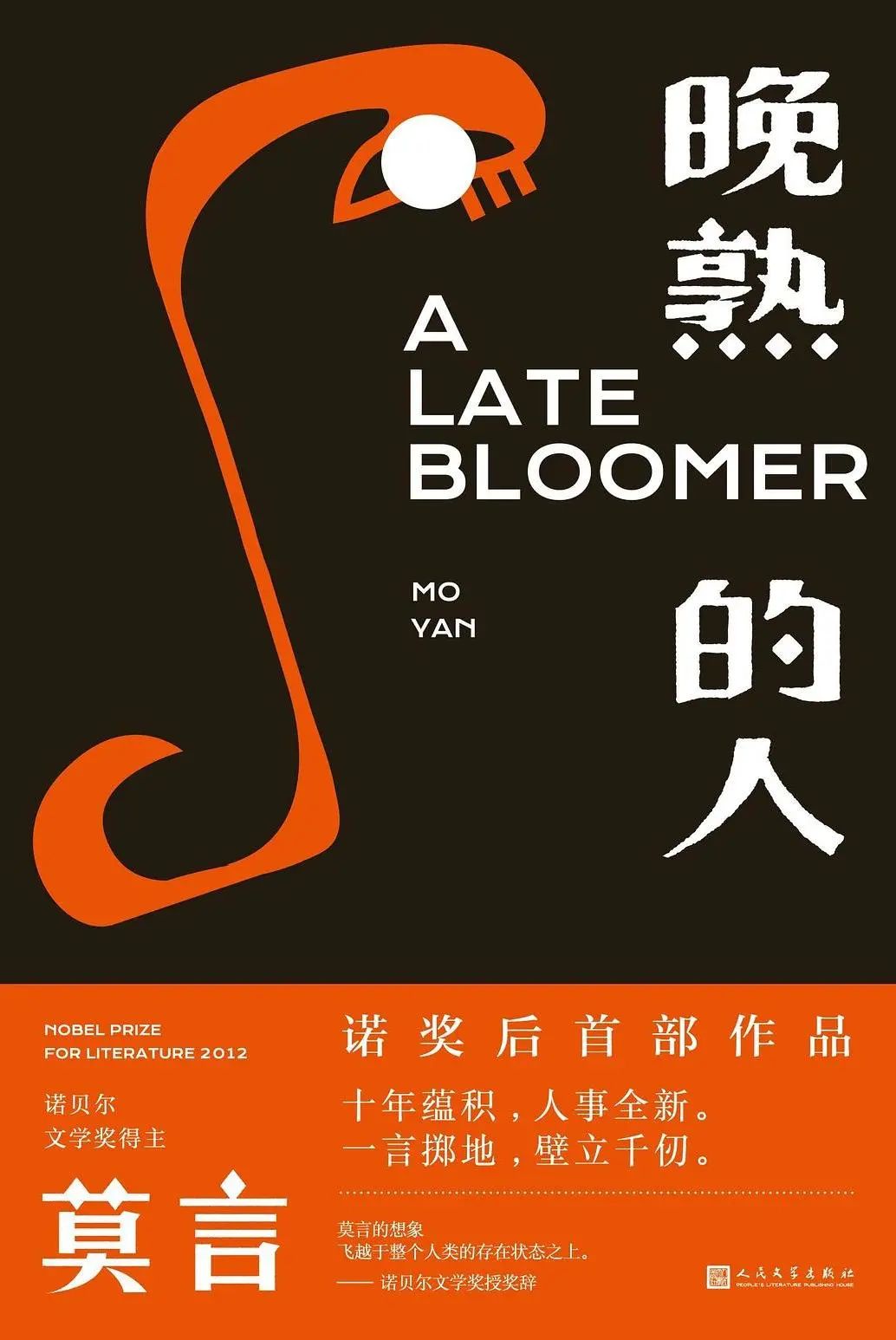
莫言的写作体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晚年风格”。从凝视高密东北乡开始,“讲故事的人”如今已被整个世界认识。在最新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中,《透明的红萝卜》时期的那种奇想当然还在,《红高粱家族》里的野性与生命力也并未衰减,但却分明多了一些宽宥和圆融。这或许是作家多年写作所收获的豁达,更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与自我相处之后所达成的和解。
还有曹文轩、周梅森、周晓枫、鲁敏、葛亮等各位老师,我无法一一尽数他们的写作。正是通过凝视他们,凝视他们多样的文字与时间洪流中微妙的改变,才有了这本小书。收录其中的十三篇访谈,来源于近十年的工作与学习。这些访谈有的进行在报社旁边的咖啡馆里,有的进行在作家的住所、书房、办公室里,还有的通过遥远而神秘的网络通讯得以达成。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报社旁边的那家咖啡厅早就几易其主。十年来的每次访谈于我都是一次深长的凝视。福柯认为,“凝视”当中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我想作为读者,阅读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它让我们可以与所有伟大的灵魂相遇、对望,最终也指引我们真诚勇敢地面对自我。
(节选)王安忆:
弃“文”归“朴”

Q
《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姐妹篇。虽然同样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一段上海历史,但是,《长恨歌》中浓烈的抒情色彩在您此后的作品再少见到,到《考工记》时已经接近于白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几个男人所改变的,而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孑然一身,他的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你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王安忆:评论作品的事,还是交给评论者,自己只能说写作时候的具体处境。《长恨歌》写于1994年,距《考工记》写成的2018年相隔整整二十四年时间,无论对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二十四年前写《考工记》,篇幅一定不会在十五万字结束,《长恨歌》在今天写,也不会写到二十七万字。然而,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呢,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
Q
《匿名》之后,陈思和老师说“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而《考工记》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小说读起来有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力量,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您来说,简直信手拈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像它看起来一样轻松吗?
王安忆: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似乎交替上演,比如,《流水三十章》之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记得那时候,陈思和谈到《纪实与虚构》,也说到“抽象”的问题,我说,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正在写,那就是《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终至写到《启蒙时代》,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天香》,再回到具象;然后,《匿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陈思和的激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举托马斯·曼《魔山》的例子,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读的……我觉得这样的激将是很有好处的,它扩充了“小说”这种文类,让我尝试叙事的边界,我和陈思和,可以说是作者和批评者之间最良性的关系,也是八十年代流传下来的遗韵,对于一个作者的写作生涯,足够用了。
Q
您好像对方言很有热情?比如沪语,似乎一直是您小说存在的背景、依托,还有《红豆生南国》里的广东话、《乡关处处》里的绍兴话……在今天,普通话的通行,让方言变成了某种语言“化石”。但您又好像对类似《繁花》那种方言写作并不感兴趣?在您看来,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王安忆:我从来不用沪语写作,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服从书面语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沪语的评价不高,我也不觉得《繁花》是用沪语写作的,方言是个博大精深的词库,可惜我们不得不接受书面语的现实,但是,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打开一个新天地。语言既来自看世界的方式,又反过来创造看世界的方式,方言可提供资源,但如何与现代汉语变通,是费思量的事情。
Q
因为对上海以及上海人生活的深入书写,您被认为是当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不过,与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相比,除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外,您的小说其实更追求的是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表达,用张新颖老师的话说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
王安忆:我觉得“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根源上说,“海派”相对于“京派”,是以批评的方式提出,“新感觉派”则是一个极狭义的概念,到今天,则变成时尚,从哪一点论,我都不属于其中,似乎也看不到“海派”有什么切实的内容,所以,我既不承认我是“海派作家”,也不认为有“海派文学”这一门类。
原标题:《写作与凝视:成为文学记者需要哪些自我修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