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非行纪①︱南非和平过渡前后的斯泰伦博斯大学
7月1日下午,经过长达18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位于非洲南端的开普敦机场。这一刻,百感交集,因为访学南非是我35年前做的梦,现在终于梦想成真。35年前的夏天大学毕业,虽然已经通过考试要读研,但还是填写了若干就业意向。令同学们吃惊又好笑的是,我的所有意向单位都与非洲有关。由此可见当时自己对非洲的痴迷。那时就已经萌生了去非洲看一看的强烈愿望。读研后,因为主攻南非史,尤其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探讨南非采矿业中阶级结构与种族主义的关系,契合了当时在英国和南非兴盛的激进社会史潮流,感到很兴奋,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乐观。但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原始资料,没有切身感受,基本上是从理论出发,在别人的研究中披捡自己需要的史料,在消化吸收先行研究基础上进行概括和综合,进而提出一点自己的不成熟见解。显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很成问题的,但这就是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现实。其中最令人焦心的是没有机会出国考察,去南非进行实地研究成为我的最大愿望,但当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只有中国官方的代表团以民间身份才可以去访问,这样的机会不可能给研究生。后来虽然获得去德国进修非洲史的机会,也学到了做实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依然没有机会像我的德国导师那样自由去非洲做实地研究或避寒避暑休养。2001年去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从Nancy Jacobs那里学到了如何进行档案研究,还了解了把社会学的方法(RRA)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历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回国后,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到非洲考察,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如愿。这时的自己就像武侠小说中身怀绝技但没有施展机会的侠客,其中的失落和不甘刻骨铭心。更为令人不甘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学科结构逐渐调整,向实用学科倾斜,历史学这种长线学科被压缩,世界史首当其冲,变成八个二级学科之一。非洲史的命运可想而知。去南非进行实地研究的梦想一搁就是35年。今年是北大的“国际战略年”,学校也希望教师们在疫情停摆之后能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走出国门,把中断的国际学术交流恢复起来。利用这个机会,在南非同行的帮助下,终于踏上了南非国土。这是何等令人高兴和值得纪念的事情!
这次访学的第一站是斯泰伦博斯大学。斯大号称“南非的牛津”,不仅因为它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声誉,还因为它与牛津一样,是个离开普敦大约50公里的大学城。斯泰伦博斯是白人殖民者在南非建立的第二个农业定居点(1679年),仅次于开普敦(1652年)。最早在这里进行拓殖的是荷兰人和法国人,他们利用这里冬暖夏凉、土质优良、水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发展了水果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为来往两洋航线的船只和开普殖民地的欧洲人提供优质农产品。现在的斯泰伦博斯不但是享誉国内外的大学城,也是享誉世界的南非葡萄酒生产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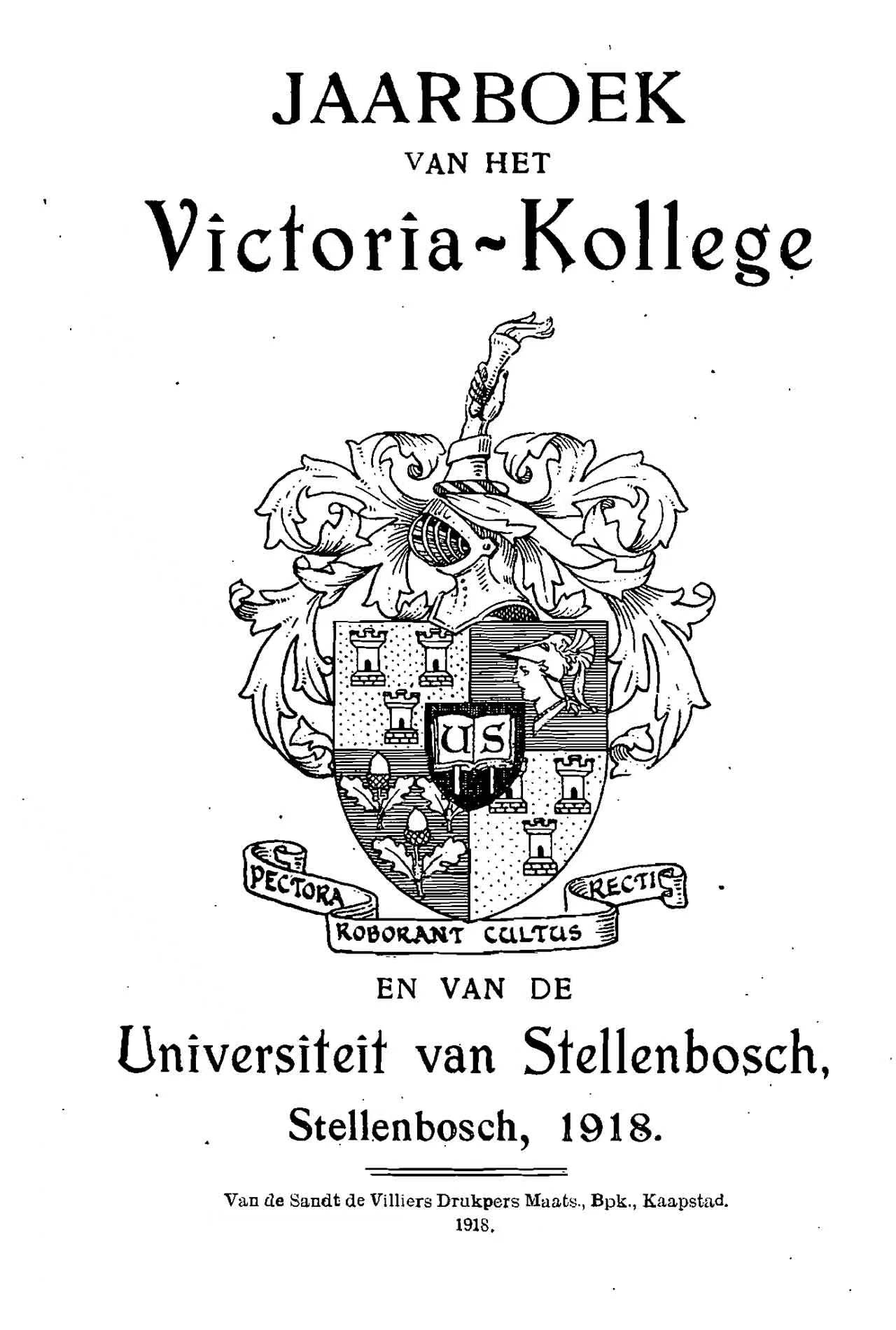
从维多利亚学院到斯泰伦博斯大学

现在法学院大楼就坐落在维多利亚学院旧址上
在斯泰伦博斯垦殖的荷兰和法国殖民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和子女教育的需要,于1859年建立了隶属于教会的神学学校,1866年建立斯泰伦博斯高中。1879年,为了纪念先辈在斯泰伦博斯建立农业定居点200年,建立了斯泰伦博斯学院。1886年11月6日,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位50周年,把斯泰伦博斯学院改名为维多利亚学院。1915年,本地慈善家马雷斯捐赠10万英镑,为维多利亚学院转型为大学提供了充足的财力,1916年,南非联邦议会通过当年第13号法案(即斯泰伦博斯大学法),准许维多利亚学院升级为斯泰伦博斯大学。1918年4月2日,由四个学院组成的斯泰伦博斯大学正式成立。现在,斯大有5个校区,10个学院(农学,经济和管理学,医疗和健康学,工学、军事科学,艺术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学,法学和神学),3万多学生,是一所学科齐全、“影响力非凡”的大学。
之所以说它影响力非凡,在于它与南非政治关系密切,在种族主义统治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泰伦博斯是南非种族主义的渊薮。在斯泰伦博斯从事种植业的荷兰加尔文教徒和法国胡格诺教徒虽然都在母国受到挤压,但在南非都变成了自由农民。然而,他们并没有以己及人,知恩图报,相反却形成了种族主义思想和作为。由于白人数量太少,要供应两洋航线上船只和殖民地的需要力不从心,因而大量使用科伊桑人、马来人和黑人奴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种族歧视思想形成了。英国殖民者夺取开普殖民地后,实行相对比较人道的政策,这让完全依赖奴隶劳动的阿非利卡一方面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把种族歧视思想逐渐发展成种族隔离思想。在这里成立的教会学校、高中和学院,毫无疑问都是崇尚白人优越和血统高贵的白人学校,学生都会受到种族主义的熏陶,原有的种族歧视意识都会得到强化。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20世纪,南非7位总理或总统都与斯大有关。其中斯末资、赫尔佐格、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沃斯特都是斯大校友,维沃尔德还曾担任斯大教授,马兰、沃斯特和博塔都曾经担任斯大校监。历届内阁中的许多部长和国会议员都出身于斯大。斯大是名副其实的、分别发展意识形态的知识渊薮,是把阿非利卡语变成学术语言、进而培育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摇篮,其神学系、政治学系等就是培养执行分别发展政策人才的基地。斯大培养的政治家不仅是种族隔离制度的设计师,也是政策的执行者。
如果说阿非利卡人的特兰斯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1910年建立的南非联邦主要实行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和种族隔离政策(Racial Segregation),那么1948年之后的南非主要实行“分别发展”政策(Apartheid)。与主要由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不同,阿非利卡人统治的特兰斯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表面上看是共和国和自由邦,但对非洲黑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英布战争之后,南非联邦在1910年建立,阿非利卡人全面掌权,在全国推广种族歧视政策,并强化为种族隔离政策。1881-1889年在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的赫尔佐格在1924-1939年担任联邦总理。在维多利亚学院期间,形成了反对英国人和土著人的思想。担任总理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种族主义法律,建立了种族隔离的制度框架。1887-1891年在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的斯末资在1919-1924年和1939-1948年担任联邦总理。在维多利亚学院,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与赫尔佐格相同的是,他对土著形成了种族主义观点,不同的是他的认识基础主要来自宗教,是宗教种族主义,另外,他接受了后来成为开普殖民地总理的塞西尔·罗德斯的南部非洲联合的思想,逐渐形成阿非利卡人和英国殖民者联合对付数量庞大的土著的主张。在他担任总理时期,通过严厉镇压1922年的兰德罢工等,进一步强化了职业和城市的种族隔离制度。
马兰1883-1890年在维多利亚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作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裔和荷兰归正会的牧师,马兰主张要保持纯正的白人血统。从政之后,他在南非国民党内组建了纯正国民党派系。1948-1954年担任总理期间,提出并实施了“分别发展”政策,并把种族隔离制度系统化。1941-1959年还兼任斯大校监。1910-1914年在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的斯揣敦1954-1958年担任总理。他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重点关注如何保持作为少数的阿非利卡人的权益,执政后进一步强化了马兰的分别发展政策,通过取消开普有色人的选举权来强化对白人优先地位和纯净血统的保障。维沃尔德在斯大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7年在游学德国、英国和美国之后回到母校任教,30多岁晋升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他认为,黑人天生就是、也适合劈柴挑水做苦工。他甚至说,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结婚只能陷入贫困。离开学校后,先是担任土著事务部长,在斯揣敦去世后担任总理。他依据“独立而平等”的理论设计了“黑人家园”政策,从而最终把黑人变成白人统治的南非的外国人。显然,维沃尔德的政策比马兰和斯揣敦的维持阿非利卡人家长式统治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维沃尔德因此而在全世界臭名昭著,虽然在1961年的暗杀中逃过一劫,但最终没能在1966年的刺杀中侥幸保命。沃斯特1934-1938年在斯大学习。在学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除了担任辩论俱乐部主席和学生会副主席之外,还是国民党在斯大的青年组织负责人。也就是说,他在成长时期就已经完全服膺国民党的理想和政策。在1966-1978年担任总理、1978-1979年担任总统的任职期间,不但通过了一些完善和强化种族隔离的法律,还判处曼德拉终身监禁、制造了索维托惨案。从1969到1983年,兼任斯大校监。1964-1970年,斯大利用集团住区法,把多年来一直住在武拉科特地区的有色人种和黑人强行迁走,修建了以沃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和社会科学大楼。1978-1984担任总理、1984-1989担任总统的博塔虽然没有在斯大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在1985-1988年担任斯大校监。
虽然这些政治人物的作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和时势的左右,但学校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国内在说到校友与大学的关系时常有一句话,“今日,你为某大而骄傲,明日,某大因你而自豪”。斯大也不例外。他们的做法是用著名校友的名字命名建筑物或竖立雕像。在斯大校园里,会计学与统计学大楼在1963年4月3日被命名为维沃尔德大楼,楼内挂着纪念维沃尔德的画像,学校体育中心被命名为马兰纪念中心。在这里,除了进行室内体育活动之外,还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然而,世间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正所谓“世易时移,人亦异矣”。

曼德拉在斯大演讲
1994年,南非实现和平过渡,少数人统治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终结,代表大多数人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台执政。种族隔离从法律和政治上似乎得到解决,非洲人扬眉吐气,当家作主。曾经是种族隔离思想大本营的斯大也揭开了新的一页。1991年,出狱后的曼德拉第一次访问了斯大。1996年10月25日,斯大打破不再授予政治人物荣誉学位的规定,授予已经担任南非总统的曼德拉荣誉博士学位。曼德拉接受斯大的学位被认为是和解的标志。曼德拉在毕业典礼上用流利的阿非利卡语发表演说。他说:“虽然我们已经相互融合,但我们还将继续在这块辽阔的国土上融合,这仍是我的愿望。阿非利卡学校和阿非利卡人将不再漠视和孤立于我们正在创建的新国家之外,相反,他们将是这个新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曼德拉最后说,“大家知道,大学在把愿望变成现实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就是我接受斯大荣誉学位的原因”,从曼德拉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对大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重视,他也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和教师,彩虹之国需要不同民族和文化共同参与建设。曼德拉的名言也成了“曼德拉日”的主题之一。那就是:“我们不必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因为我们能让苦难过去,然后我们都能收获伟大的未来。”2004年,斯大还授予曼德拉的继任者、南非总统姆贝基名誉博士学位。
曼德拉不仅是这么想、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面对历史积怨和政治经济现实,曼德拉政府成立由德高望重的图图主教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毫无疑问,这个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它并不能解决历史上形成的极度不平等的现实问题。于是,学生先后发起“必须打倒罗德斯运动”“必须废除学费运动”等。前者要求罗德斯大学改名,推到罗德斯雕像;后者要求降低学费,解决教学大纲和教学用语中存在的非正义问题。显然,这些运动虽然针对的是提高学费等现实问题,但反映的是非洲人生活水平没有根本改善或不如预期的现实,深层含义是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得到清算的不满。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新南非的突出表现是白人主导的标准、取向等及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结构依然存在。2015年9月1日,斯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共同发起游行抗议,要求学校对所有族群开放,不但要清除分别发展的恶劣影响,还要改变语言政策,让所有族群的学生都能通过公平竞争进入斯大学习。抗议运动中展露出来的对现状的不满促使学生运动不断深化,后来竟然发展到提出“我们被曼德拉出卖了”这样的口号。这是对和解政策的怀疑,是对执政者的抱怨,是对曼德拉等解放者为了获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让步而做出的让步的不解。换言之,不满现状的学生希望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具体到斯大,学生们要求消除学校的不公平政策,去除学校残留的种族主义痕迹。

十字路口和马雷斯雕像
顺应时势变化和学生的正义要求,斯大在2000年3月20日采用新战略框架,承诺开启开放的、广泛的自我审查和自我更新进程,也承认在历史上对不公正所做的贡献,并承诺推进适当的纠错和发展议程。南非和平过渡18年后,沃斯特大楼改名,并设立永久图片展,纪念这个不幸的事件;20年后,马兰纪念中心改名;21年后维沃尔德大楼改名,维沃尔德画像被移走,代之以南非国旗。学生还想把矗立在校园中心位置的马雷斯雕像移走,因为他捐款建校是为了提升阿非利卡人的民族利益,但没有成功。不过,学校通过在马雷斯雕像前方竖立另一个由学生和教师创作的、名为十字路口的雕塑来实现与马雷斯的对话,通过场景的改变实现了对马雷斯雕像的新认识。确实,历史不容遗忘,但这些“种族隔离之父”应该放置在种族隔离博物馆中供后人评说,而不是置于公立大学勾起学生和老师的不愉快回忆。饶有趣味的是,在移走维沃尔德画像时,维沃尔德的两个孙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而且都表示,他们欢迎这一行动。其中29岁的威廉不但已经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且公开为自己祖父的罪恶忏悔,同时在教会做义工为穷人服务。他说:“分别发展不仅是一个善意实验的失败,还是一个道德失败,是非正义。”32岁的博斯霍夫承认分别发展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但依然认可它的道德基础,甚至身体力行,要在奥拉尼亚建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州。与其祖父的政策不同的是,他要建立的州不剥夺任何人的选举权和公民权,也不强迫任何人迁徙。兄弟俩的不同认识和作为反映出南非白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多元认识。而这些不同认识和做法的存在说明,彩虹之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新阶段。
然而,仅仅改名和移走雕像还远远不够,学生们要求学习的语言和内容都要去殖民化,进而解构校园里根深蒂固的白人性,从而增强学校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虽然早在1977年斯大就声明接收有色人种、黑人和亚裔人学生(当年14100注册学生中,只有100黑人学生和550混血人学生),但因为仍然使用阿非利卡语作为唯一教学语言,学生来源多样化政策事实上并没有落实。2015年的学生运动要求学校把教学用语由阿非利卡语改为英语,因为英语是每个南非人从小学就学习的语言,而阿非利卡语与种族隔离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是一种具有压迫性和排外性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教学和研究对已经占到总学生数40%的黑人学生既不公平,又容易勾起伤心的回忆(1976年,索维托黑人高中学生抗议政府把阿非利卡语作为教学用语,遭到残酷镇压。)。2016年,学校发布了斯大语言政策,同意以英语为主要教学用语,同时准备投资7000万兰特使教师队伍多族群化。2021年,学校修订了语言政策,宣布学校执行多语种政策,平等使用阿非利卡语、英语和科萨语,尤其鼓励在课堂和学术会议中使用科萨语。为此在教室和会议室安装了同声传译设备,帮助学生和学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多语种的使用昭示了多元文化的平等地位,也为不同族裔的学生进入斯大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更有助于不同族裔的学生形成对斯大和南非的认同。
就研究和教学内容而言,以历史学为例,斯大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两句话完全适用和平过渡前后斯大历史学的变化。在斯大历史上,其历史系绝大部分时间都坚持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研究和教授阿非利卡人的苦难和英雄历史,强化作为阿非利卡人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天选之民的优越性。广大黑人、混血人和亚裔人最多只能作为陪衬或“他者”来彰显阿非利卡人的伟大。不能客观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阿非利卡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剥削和压迫他们,类似于通过去其史而灭其国,使其失去在南非生存的合法性,为实行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但是,南非和平过渡之后,原来的被统治者翻身做主,与此相适应的是需要赋予非阿非利卡人适当的历史地位,需要积极开展研究,并为其在世界历史中合理定位。于是,历史系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白人一统天下变成白人、黑人、混血人、亚裔人应有尽有。教师来源族群的改变带动了研究和教学内容的改变。教授们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除了研究社会史之外,还开拓了环境史、性别史等新领域,除了研究南非历史之外,还关注南部非洲、整个非洲、金砖国家集团等不同区域的历史。显然,这改变了先前只讲授阿非利卡人历史、对阿非利卡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盲目自信甚至迷信的状况。教学内容的变化使学生对南非史、非洲史以及世界史都产生了新认识,使南非不同族群的学生都能对斯大产生归属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历史学家在揭露阿非利卡人把黑人和科伊桑人看作类人猿或狒狒的虚假叙述的基础上,重新从长时段界定了南非不同族群的关系,以及不同族群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学生开阔了视野,有助于树立多元共生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对培养处于人类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南非公民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克柔托娅

以克柔托娅命名的大楼
饶有趣味的是,历史系所在的大楼在失火重修之后,并未沿用先前的命名,而是用曾经给布尔人当向导、在科伊人和荷兰殖民者之间担任翻译或代言人的克柔托娅(1642-1674)的名字来命名。荷兰殖民者曾经赋予她爱称“夏娃”或“天使”。显然,以她的名字命名建筑物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以彰显她在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发挥的沟通和桥梁作用,进而引导现在的学生和学者要做民族团结和融合的纽带,在尊重多元族群和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建设美丽新南非,即彩虹之国。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国家、任何大学都应该克服短期主义造成的局限,否则,走了弯路再纠正起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有些代价是无法弥补的,会成为刻在历史上的一道伤疤。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