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消费有机食品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和社交货币吗?| 三明治
原创 套子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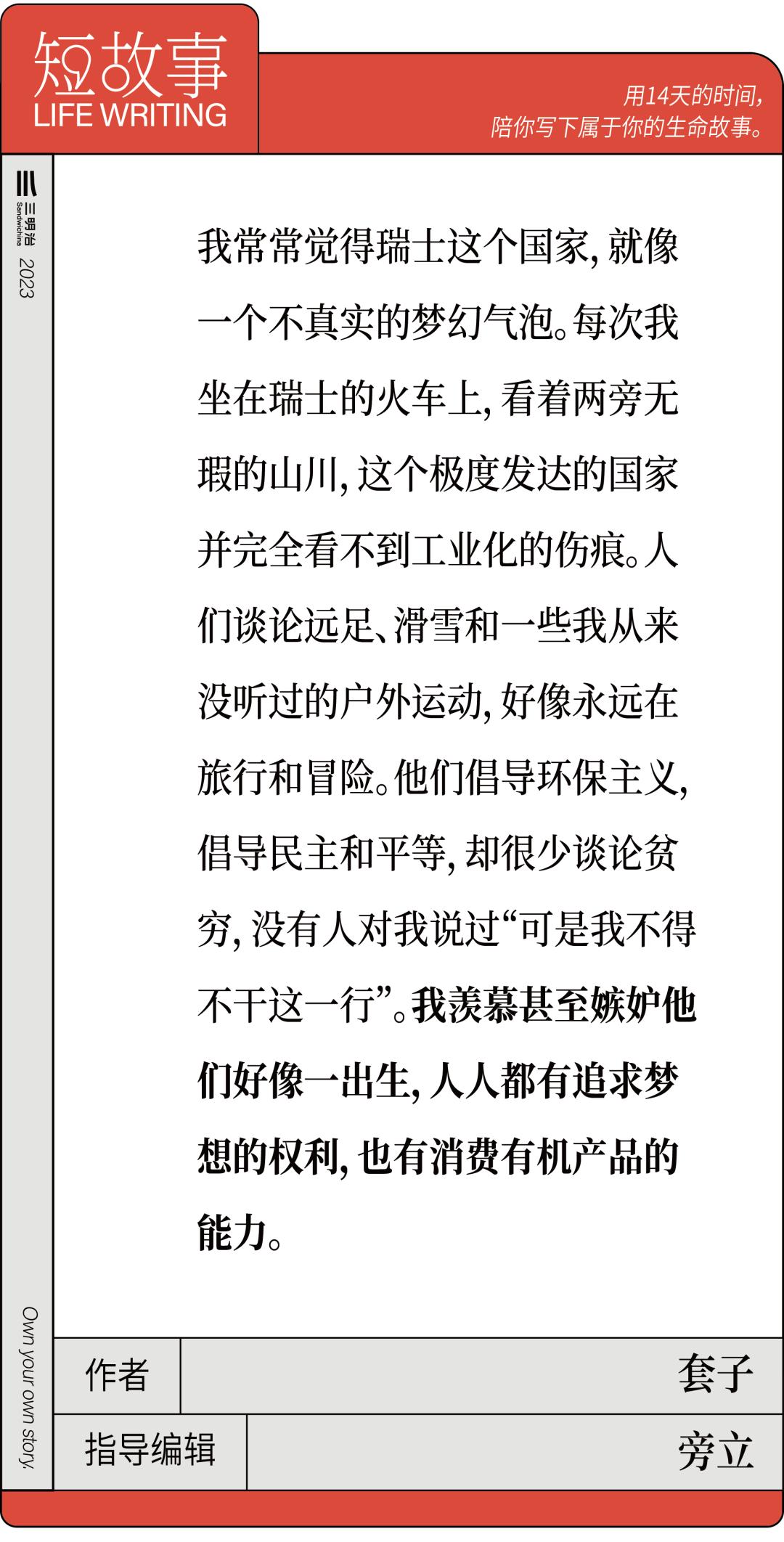

2019年的春天,我在瑞典的超市里,第一次看到贴在食品上明明白白的有机标签。那时候我在读大四,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在瑞典交换学习。这些有机食物打着“Eco”的标签,在瑞典语里用来指示“有机的”(Organic)。相比于我印象中的“洋鸡蛋”和“土鸡蛋”,瑞典鸡蛋的货架更是令我大开眼界:鸡蛋全部被装在纸盒里,鸡蛋壳干干净净,除了有机的标签之外,还有“大、中、小”的标记;另外,盒子上鸡的活动范围从只能在笼子里活动到完全散养,分出了五六种鸡蛋的等级。当然,越自由的鸡生的鸡蛋越贵。那时候,我和同行的同学像观光客一样给那一面鸡蛋货架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们最喜欢的鸡蛋是,在价格便宜的中东超市里没有任何标记、甚至没有盒子只是拿塑料绳捆好的一大板的“洋鸡蛋”。我们为自己找到省钱的妙招而沾沾自喜。
我在小城长大。方言的椒盐味儿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像吵架,走进小城清晨的菜市场,像淌进沸腾的火锅里。奶奶是我印象中最会买菜的人,她会一些讲价讲不通,就假装离开的经略战术;也有一些神秘的土方去鉴别蔬菜和水果的可口程度,比如要挑“肚脐眼”小的橙子,橙子才会甜美多汁。但她从来没问过这些橙子是怎么种的,用了多少农药和肥料。我成长在一个如果一顿饭没有荤菜,大家都会觉得这餐吃得很差的家庭,在我前20年的人生里,我从没听过“有机食品”这个概念。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家庭里最接近对有机食品的崇拜,是大人们对土鸡和土鸡蛋的宝贝。乡下的亲戚来拜访,总是会拎来被稻谷茎秆捆住脚的两只活鸡,以及用塑料桶整齐装好的一些土鸡蛋作为礼物。他们把超市里买的鸡蛋叫做“洋鸡蛋”,他们说“洋鸡蛋”是吃的是人工合成的饲料,养在养鸡场的笼子里的鸡生的鸡蛋,远比不上乡下的鸡,漫山遍野地跑,吃的都是实打实的粮食长大的,生下的鸡蛋个头大、营养好。于是大补的土鸡和土鸡蛋也往往只在庆祝或重要的场合出现——过年过节的家宴、高考生的营养餐、坐月子的补汤......

2022年我在瑞士苏黎世访学时,同住的室友是一位瑞士人,她是严格的有机支持者、素食和环保主义者。她告诉我,她在多份租房申请中选中我的原因是因为看到我的专业是生态学,觉得我们肯定有很多聊得来的地方。
我们的厨房门上贴满了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标签和贴纸,还有一份不同水果蔬菜自然成熟的时节日历。做饭的时候,她常常像个夸张的广告演员对着她锅里的蔬菜说,“我的蔬菜看上去真美味,而且他们还全是有机的!”我在心里默默翻个白眼,然后趁她不注意把我刚买的非有机的肉和菜偷偷塞进冰箱里。
有天在学校食堂吃饭,收到室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她说她把我没有有机商标的苹果拿出了厨房的果盘,不然会污染到她的有机苹果,还在文字的末尾加了一个俏皮的笑脸。我感到我和我的苹果都有了阶级,我想把她的笑脸撕得稀巴烂。
我没回复她,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给我发了大段的农药对人体和环境伤害的文字教育,并告诉我,如果我有兴趣,她可以发给我相关科学研究的论文。
羞耻像火一样烧上来。从大学以来,我上过的专业课,看过的专业书,都在告诉我集约化农业对土地和环境的伤害,我可以毫无波澜地在我专业课的报告绪论里写下这句话。但那又怎么样呢,课堂是课堂,生活是生活,课堂的标语是说给社会上那些该负责的人说的,我只是被动地卷入生活的一条小鱼。我周围的人,包括那些授课的教授,没有人在消费有机产品,如果那时提起消费“有机”产品,我可能依然想到的不是环保,而是奢侈。
在我的苹果没有资格被放在果盘里后,我开始注意到苏黎世的两个最大的超市连锁店里,有机的产品几乎占了货架的一半,它们常常被放在货架上最显眼的位置。这些有机产品看起来和其他产品并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还会因为使用农药和肥料的限制,卖相更歪瓜裂枣一些。但是它们常常按个数或重量被精美的盒子封装好,盒子上有来自欧盟或瑞士本地的认证标签。新鲜的有机产品通常比非有机产品贵三分之一,但是遇到临期打折时,有机产品也可能比非有机的还便宜。我走在超市里,仔细地对比价格,如果有机产品和非有机产品差不多,或是稍贵一点,我会首先选择具有有机认证的产品。
有机的种子在我的意识里发芽,我才发现,在苏黎世,有机的藤曼可以爬满生活的方方面面。精致的餐厅里,应季和有机认证的食材是轰隆隆响亮的广告标语。不仅是食物,洗护产品,化妆品,甚至是一个帆布袋或者搓澡球,也都是存在有机认证的,也会因为这个有机的标签而身价倍增。但也需要小心,有时候包装用了代表自然的绿色,还写着一个大大的“Nature”,买回家后,我瑞士的室友瞥了一眼,看似不经意地说,虽然这个写着“Nature”,但是和有机可没什么关系。
我的室友就像环保意识测试时站在我背后转悠的监考老师,我看到她对我的作答失望地摇摇头。

在日内瓦的国际生态学大会组织的法国山区牧地考察时,我认识了凯瑟琳。那天,穿志愿者服的年轻女孩儿清点好车上的人数之后,大巴掉头,沿着牧场边的公路往山下开。放牧的季节已经结束,从车窗远远望去,还停留在草原上和我们一样的城市观光客形成稀稀拉拉的小点,像是吃草的牛羊。渐渐地,大巴抛下平铺直叙的草原,驶入藏在山林里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下。到了山脚,森林被光亮划开一道豁口,顺着这豁口出去,阳光和车流的喧嚣又充斥了我们的耳目。车穿过法国边境,把我们带回到瑞士日内瓦境内。
凯瑟琳坐在和我隔了一个过道的座位上。短头发,中年,身体很富态,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和紧身的裤子。即使是在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考察团里,直到她插入我和一位德国学者的对话,我才注意到她的存在。
“考察向导告诉我们为了牧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每年人工砍树,不然牧地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森林。而对于像我们这样研究森林多样性的研究者来说,把全天下都变得物种丰富、结构多样的森林真是天大的好事。”
凯瑟琳听到我和一位德国学者的对话,突然转过头来,兴奋地问我森林生物多样性怎么研究,也许因为刚刚爬完山,她说话还有些大喘气。
凯瑟琳自称是为对生态学一无所知的经济学家,我惊讶地问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来参加这个生态学大会。她哈哈地笑着说她在瑞士一家有机农业研究所工作,老板让她来参会,她就来了,而且还叫她做一个报告,但是她现在还没有做完报告展示的幻灯片。
“有机农业”的研究让我眼睛一亮,欣然答应了凯瑟琳晚上去日内瓦湖一起吃晚饭的邀请。
日内瓦湖很大,蓝色的湖水像水彩一样和天边的夕阳交融晕染。一条石头堆成的小道从湖边延申到湖中央,湖水轻轻地冲刷小道底部,像夏天老爷爷手上的扇子悠哉游哉。凯瑟琳坐在小道边上,背对着正在落山的太阳,脚泡在水里,远远地跟我挥手。她下水游了泳,头发还挂着闪亮的水珠。
凯瑟琳说你跟我遇到的中国女孩儿都不一样,你太开放了,第一次见面就来和我一起吃饭。我说你也跟我遇到的瑞士人都不一样,你也太开放了,第一次见面就邀请我一起吃饭。说完我们两个人放声大笑。
“我虽然是个瑞士人,但我在国外生活了快20年了。今年当我重新回到瑞士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瑞士人我真的感觉到很多文化冲击。比如我回瑞士的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我震惊地发现食堂的水龙头是可以直接出来气泡水的!你敢相信吗,水龙头!直接出来气泡水!”凯瑟琳喝了一口啤酒,像话剧演员一样眉飞色舞。看得出来,这么久了,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我在非洲工作了10年,从一个喝上纯净水都成问题的地方来到一个水龙头出气泡水的地方,我震惊得像个傻子,而我的瑞士同事们也的确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这里真他妈是个‘天堂’!”她边说边摇头叹息,好像一个第一次来瑞士的外国人。
凯瑟琳在瑞士的法语区长大,然后去荷兰念了硕士和博士,结束学业之后,她就去了非洲工作了,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她大多时候在NGO(非政府组织)做农业经济相关的工作,辗转于不同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之间。我佩服她有勇气走这个梦幻气泡。

回到苏黎世之后的某天,突然想起在会场和凯瑟琳说再见时,凯瑟琳让我记得随时邀请自己去她工作的有机研究所参观。于是,在一个秋天的周末,我不请自来,到了凯瑟琳工作的小镇。凯瑟琳在公交站接我,然后我们步行去她家里,骑了两辆自行车到研究所。
研究所位于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两栋不高的楼房是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楼房的楼顶和墙壁都布置了植物,看起来很现代也很亲近。研究所在四十年前由一群农民成立,曾经主要的资助来源是瑞士的一家有机认证机构Bio Suisse。近年来,随着有机产品在市场的兴起,研究所开始和瑞士政府以及欧盟合作。
研究所的研究内容比我想象中脚踏实地得多,相比于科研机构研究农作物时去破译遗传密码,这个研究所则是会通过实验,科学地验证一些传统耕作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同时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这里大多做实验的场地是和当地农民合作的,研究所提供种植和管理的技术支持,农民为研究所提供监测数据,最后的产品会直接流入市场。
凯瑟琳带我经过一片已经收获后的实验田,地光秃秃的。她向我解释,这是一块属于研究所的长期实验田,她不在这个部门工作,但是她听说她的同事在这片实验田里曾经验证过根据月亮的周期来确定播种、除草的管理时机会让土地的产量有显著的提高。凯瑟琳摇摇头:“但我觉得只是这个月亮的周期让人更加频繁地去关注自己的菜地,让产量更高了,月亮什么的还是挺不靠谱的。”
但我在心里更愿意保留月亮和土地之间的这份神秘联系。我想我们永远在自然之下。
《人类简史》里说农业革命后,小麦的分布范围以惊人的趋势增加,每天还有一群群人类为其从早到晚忙碌养护,也许是小麦驯化了人类,而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工业化和化肥的出现似乎让人们发现了加速生产的秘密,可以用很少的劳动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现代的有机农业尝试从工业化之前的自然之法去耕种土地,但是人们这一次更大义凛然了——除了产量,我们还需要兼顾土地、昆虫和牛羊的快乐。
我问凯瑟琳地里这些收获后的作物,是不是作为员工可以免费拿回家吃?凯瑟琳说,每次收获季结束之后,研究所里面就会有两大篮子放着蔬菜,大家可以随意拿,一篮子写是实验组,一篮子是对照组。“没施农药的篮子总是早早被抢光,我常常开开心心地抱一大篮子的对照组蔬菜回来。”凯瑟琳说,“我前半生都没有吃过“有机”的食物,这点农药,害不死我!“
有机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农药,只是对农药的使用有很严格的限制。有机认证的具体细则根据不同的认证机构而不尽相同,我下载了一份Bio Suisse对于颁发有机证书的细则,密密麻麻写满了条款。总结起来,有机认证机构会从农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评估,包括对农场里的拥有者和工作人员。比如有机农场的管理者不允许在其他的非有机农场担任管理的角色,种子的来源必须是通过有机化的生产得到的,有机化生产过的土地需要被用有机的标准耕种24个月之后种植的作物才能被Bio Suisse认可,农场里至少有7%的土地是专门用来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以及生产的产品只能通过陆运和海运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参观研究所的农场,让我想到了电影《大大的小小农场》里面农场,那是一个通过生态学家的帮助,原本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来靠自然本身维持的美丽桃源。但是电影里的生态农场建立也经历了很多次令人沮丧的失败,农场的主人付出了很多心血,而到最后,这场美丽也许并不是那么容易在另一个拥有不同作物、不同土壤类型以及不同气候的地方复制。如果说工业化的农业是生产线上的一件冷漠模具,有机农业就像是一件色彩鲜艳的艺术品,或者说是一种哲学思想。
参观完有机研究所,凯瑟琳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饭。他们家住在一个披萨店隔壁,是一个很旧的房子的一楼。凯瑟琳的丈夫在门口迎接了我们,看我在门口犹豫不决,凯瑟琳的丈夫说不用脱鞋子,那太瑞士了,直接进来吧。他们好像很厌恶“瑞士”那一套精致的风格。
凯瑟琳说她中午炖了一些肉,然后拉开冰箱门,让我看看我还想吃什么。凯瑟琳的冰箱很乱,有很多超市塑料盒装好的肉,也有一些完全没有包装的水果和蔬菜一股脑塞在夹层里。她拿出一盒虾饺,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个!那是瑞士超市Coop的方便食物区常能买到的虾饺半成品,只需要沸水煮三分钟。我发现虾饺的盒子上有一张绿色的贴纸,那是Coop临期产品的打折标志,通常是半折及以下的折扣,同时上面写着如果这件商品不被购买,超市将会把它当废物处理掉。凯瑟琳告诉我,他们为了减少碳排放,消费肉类产品时只消费这样已经被生产出来的冗余产品,尽量不去鼓励更多的肉类生产。而水果和蔬菜,她都会直接从附近的农场购买,快捷又新鲜。
那天晚上,我们毫不愧疚地吃了一大盘炖肉和一大盘虾饺,甜点是凯瑟琳自己用研究所产的葡萄做的冰淇淋。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一场生态农业的专场报告。在午餐的时候,我端着盘子追上一个与中国有合作的英国教授,问他,“‘有机’那么好,那它是不是全世界农业的答案?如果在全中国实行有机农业,能养得起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吗?”
他说,我们永远在探索,“有机”是其中一条路,但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同一个问题,也有多种答案。

我在新闻里读到瑞士对有机食品的人均消费值是全球第一,瑞士政府2022年的报告显示,有机农业的耕种面积已经占总耕种面积的18%。我常常觉得瑞士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幻气泡。每次我坐在瑞士的火车上,看着两旁无瑕的山川,这个极度发达的国家并完全看不到工业化的伤痕。人们谈论远足、滑雪和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户外运动,好像永远在旅行和冒险。他们倡导环保主义,倡导民主和平等,却很少谈论贫穷,没有人对我说过“可是我不得不干这一行”。我羡慕甚至嫉妒他们好像一出生,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也有消费有机产品的能力。
一位不会刻意消费有机产品的瑞士本地朋友就在聚会上,被他的好朋友指责对他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也没有社会责任感。他的朋友让我想到了我的室友。好像在这座梦幻气泡里生活,消费有机有时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和社交货币。
“我太想吃韭菜盒子了,我去超市里找,发现像韭菜、香菜这样的东西都被根根分明地装在塑料袋里,一小袋就只有几棵,还卖这么贵。这么多钱,我在国内能买一大把韭菜!天天追求什么有机环保,也不看看他们这样的包装用了多少不必要的塑料。”最近刚从国内同一个所来访问的师姐,一边从冰箱里拿出她做得不是很成功的韭菜盒子,一边跟我吐槽瑞士超市的“伪善”。
在瑞士学习的时候,瑞士的老师补助了一部分工资给我,让工资总额对等了瑞士的博士工资水平,数量和一位在饭店上班的全职服务员差不多。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让我我没有感到时而消费有机产品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压力。而师姐并没有我幸运,她没有瑞士老师的补助,光租房就用掉了奖学金的一半,剩下的钱在昂贵的苏黎世,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她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搜集在瑞士省钱的秘籍,几乎不去瑞士本土的超市消费,而是选择更便宜的德国超市,更别说有机产品这样的“奢侈品”了。
我仍然认同有机概念中对土地的尊重和对生命的关怀,我感激那些推动有机农业发展的人们为这个世界提供了这个美好的选择。但是在收入有限的留学生活中,我不再为自己谨慎计算有机和无机的差价而愧疚,我自觉地把我的无机水果和我室友的有机水果分开放,我敬佩她能坚持消费有机产品,但这也许并不代表了任何阶级。那把架在我脖子上逼我消费有机产品的道德刀子消失了。
后来,我去超市挑选带去朋友家做客的礼物。Coop超市门口的水果货架上摆满了鲜艳欲滴的草莓。上两层放着有机草莓四瑞郎一小盒装在塑料盒里面,外面又套了一层塑料袋,塑料袋上印着Coop自己的绿色有机标志,草莓尖尖还有些青涩。下两层摆放着大纸盒装的没有有机标志的草莓,草莓只铺了一层,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纸盒里,上面只盖了一层薄薄的塑料纸膜,正在打七折,一盒五瑞郎。因为是礼物,从前的我大概会好面子地毫无犹豫买下两盒有机标签的草莓。但那天我把两种草莓都从货架上拿下来,左看看右看看,最后抱走一盒打折的没有有机标志的草莓。没有有机标签的草莓也有浓郁的春天的香味,拌在酸奶里,再放进冰箱冷冻,朋友说她很喜欢这道甜点。
回到北京之后,我在宿舍外面流动的便民水果摊买日常的水果和蔬菜。水果蔬菜都是当天老板开着大卡车拉过来的,很新鲜。它们散装在案板和塑料大框里,没有任何标签,就连价格也得现场问老板,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和奶奶一起逛的菜市场。我熟练地回到了没有有机标签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负担。

在写下这篇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有机消费”像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一样,永远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当我意识到它的复杂多面性之后,这件事又反而变得简单和轻松。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原标题:《消费有机食品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和社交货币吗?|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