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托宾用禁忌爱欲和艺术的联系暗示了托马斯·曼创作的源泉
阅读科尔姆·托宾的新作《魔术师》(2021)之时,我常常想到小说主角托马斯·曼早年的两部自传性作品:1903年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和1903年开始构思、190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陛下》。前者是28岁的青年托马斯·曼对自己艺术家生涯的反思,里面有整整一章是关于艺术和生活对立的思辨性论述,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篇理论性散文;后者则是一个有譬喻色彩的“童话”,在《托尼奥·克勒格尔》中,曼就用艺术家和国君进行类比:艺术家生来具有超凡的认知,从精神境界上高于大众,国君则具有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两类人都不可能彻底放弃天生的高贵,尽情享受蒙昧平凡的人生。所以,如果说《托尼奥·克勒格尔》是曼对精神/生活对立进行的思想论述,《陛下》则将这些反思用童话故事的形式重新讲了一遍。

不同于大量书写托马斯·曼的学术性传记,小说《魔术师》娓娓叙述曼的一生,两者叙述内容之间的巨大差异类似《托尼奥·克勒格尔》和《陛下》间的互补。托宾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托马斯·曼80年漫长人生中思想发展之路的回溯,甚至舍弃了大量历史背景铺垫,几乎把镜头贴在作家一人身上,仿佛一切的答案都只存在于人物的灵魂之中,命运会让曼走进属于自己的故事中。作为一部人物传记性质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做法。即便现实中的托马斯·曼大量阅读,不断吸收各种哲学、历史和美学理论,其作品的思想底蕴丰富且深邃,托宾还是会省去一般读者不感兴趣的理论性论述,将其转化为故事情节,以及“托马斯·曼”这一小说人物的主观感受。他不会如学者一样,穿过重峦叠嶂般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文献,小心翼翼地接近生于19世纪的托马斯·曼,而似乎凭借某种同类的直觉,直接点出那些在幽暗之中主导曼人生和创作的隐晦细节:死亡赋予父亲躯体的庄严和陌生、初恋阿尔明·马滕斯的微笑和拒绝、海因里希和卡提亚这两个“异类”同伴洞察的目光……显然,阅读过数本托马斯·曼传记和研究性专著后,托宾无意再从理论角度重构托马斯·曼的人生。他“要让生活,而不是某种生活理论,统摄他的书”——这是小说中的曼对《魔山》的构思,尽管实际上,《魔山》恰好是一本由各种理念和思潮交织而成的思想实验。托宾不打算在小说中重现一个过分真实、背负着19至20世纪厚重历史的德国作家,而要创作一位他“私人的”托马斯·曼,透过后者的眼睛,书写自己眼中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魔术师》仿佛托宾以某种观念(Idee)为核心创作出来的精致譬喻。而这个观念正是作为“魔术师”的托马斯·曼。
“魔术师”是家人对托马斯·曼的昵称,颇有几分一本正经的揶揄之意。在托宾的《魔术师》之前,还有数部托马斯·曼及曼家族传记作品以此为题(如彼得·德·门德尔松德的《魔术师》和玛丽安娜·克吕尔德的《在魔术师的网中》)。在托宾的书里,“魔术师”这个昵称第一次出现,是在“一战”时期。1914至1918年间,托马斯·曼出于对德国文化的同情,以及证明自我的意愿,创作了不少支持战争、批判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散文,但随着他的政治观点慢慢动摇,他逐渐对这些创作不再满意。在这段自我怀疑的时间里,有次他哄骗年幼的孩子,称自己具有驱鬼的强大力量,让子女钦佩不已。战争结束后,他放弃了自己战时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魏玛共和国,创作了《魔山》、“约瑟夫”四部曲等呼唤民主和人性的不朽名作,名满天下。再后来,“魔术师”这个昵称在成年的孩子们口中,多了几分戏谑嘲讽的意味:文坛君主托马斯·曼总能够让自己从复杂的社会性事务中抽身出来,把一切琐碎庸俗之事丢给妻子和子女,独自回到不许他人涉足的书房。用他那架著名的望远镜从自家窗户里观察楼下的人,借用他人的形象和经历,书写自己的故事,在别人为进入一部不朽之作倍感荣幸之时,冷酷地告诉他们,这写的是我,只关于我自己。托宾写道,这位伟大的作家得到了全世界的欣赏和赞誉,但他的孩子们不感激他,无法分享他的荣耀。尤其克劳斯在戛纳轻生后,“魔术师两三天后要做讲座”,即便同样身在欧洲,也没去参加长子葬礼,让其余的子女寒心不已。

卡提娅·曼与托马斯·曼,1930,柏林
这是一个和人性、生活隔阂的人文主义大师,一个呼唤博爱,却不能热忱对待身边人的孤独者——《魔术师》一书页页都指向这一折磨托马斯·曼一生的秘密:如他花了大半生构思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标题所述,“魔术师”就是技艺高超的骗子,擅长无中生有,骗取他人的感情。“一战”期间这些甚至不能让曼自己满意的政治性创作,只是“魔术师”一生中最失败的几次表演。托宾把“魔术师”线索埋在曼人生的最初。少年托马斯·曼惯于扮演一个优秀的吕贝克市民、未来的正派商人,骗取父亲和旁人的赞赏,同时自知是个“谎言师、欺诈者,不能被信任”,因为这种自知之明而内心不安。他的艺术同样如骗术般“道德败坏”。托宾设置了一个暧昧的情节:14岁的托马斯·曼一边注视哥哥和母亲演奏音乐,一边欣赏哥哥漂亮的身体,感觉被同样即将成为艺术家的哥哥海因里希看穿。在小说中,这个经历让托马斯·曼把艺术和堕落——“不正常”的爱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将表现出堕落。堕落是他拉小提琴时发出的每一个音符,是他读书时念过的每一个字。”
无法满足甚至无法言说的欲望是灵魂的饥渴,这种爱欲不同于丰饶守序的婚姻,近乎放纵的审美,冰冷寂寞,让人在恐惧和孤独中发现自己与众不同。托宾用禁忌爱欲和艺术的联系暗示,饥渴的匮乏即托马斯·曼艺术的源泉。正如他的每一段爱情都不是生活之树上结果的枝杈,而是一次次无果的“冒险”,曼的创作也不是生活之河充盈后自然而然的迸发,只是对灵魂匮乏的一种补偿和辩解。托宾虚构了一位满足了曼对同性欲望的许纳曼先生,用这个隐秘的小故事取代了托马斯·曼阅读叔本华轮回学说后的理论性认知:渴望的满足只会带来厌倦,直到新的渴望出现;生活就是一个在渴望和厌倦之间往返的钟摆,清醒的认知者托马斯·曼不愿卷进这场盲目的永恒轮回,因此选择断念,停留在欲望满足前的那一刻。他的小说——包括直接表现同性恋情节的《威尼斯之死》——总会用优雅华美的文字描述欲望的焦灼,但到了“确信此事将会发生之时,贪欲涌动的一刻”,魔术师一挥魔杖,一场即将降临的海市蜃楼化为乌有,而这幻象之所以耀眼,“正因为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艺术源自对生活并不真诚的仰慕,那它是否等同于对生活撒谎?从《托尼奥·克勒格尔》中的大段论述可以看出,这个问题长久地折磨着托马斯·曼。确实,直到《浮士德博士》和《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曼仍然在探索艺术超越表象和游戏的范畴、成为一种认知的可能性,为这个折磨他市民良心的问题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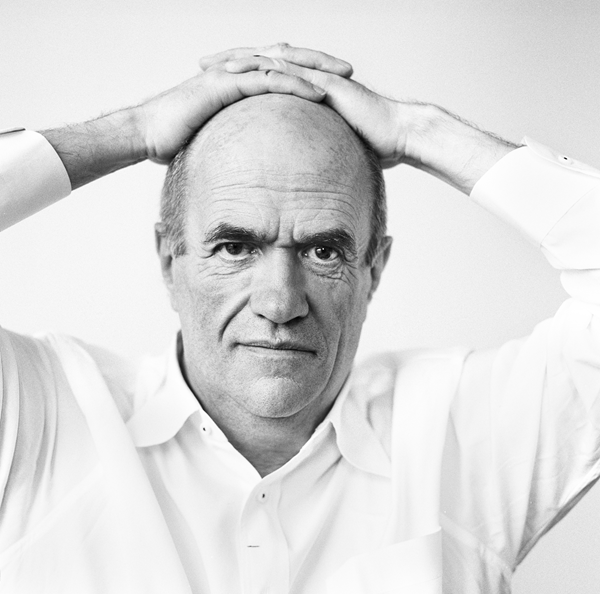
科尔姆·托宾
托宾也注意到曼心灵中的这份撕裂感:即便打扮成市民,过着市民的平凡生活,源自欲望的艺术还是让曼的异类特质显露无余,这是对生活的诱惑和损害,理应被举报,近乎疾病,近乎犯罪,甚至近乎死亡,令曼这样悬浮于生活和精神之间的人无法自拔。尤其是脱离了物质媒介的音乐艺术。音乐对托马斯·曼的意义毋庸赘述,这种“上升、变化的、令人震撼的”艺术格律规整,超越凡俗,只有死亡才有这样严格的线条和形式,欣赏音乐相当于在永恒的形而上世界体验短暂的安眠;另一方面,这个秩序的形而上世界之下暗藏着无数混沌的情感,即音乐创作者的灵魂泥沼。这个野蛮的世界被掩饰在工整的韵律之下,向听者的情感和灵魂直接发出召唤,威胁着要毁坏被驯化的理性。音乐包容着庄严有序的形式和野蛮浑噩的情感,两者时刻彼此抗衡,仿佛现实世界中理想主义和蒙昧主义间的冲撞。难怪托马斯·曼把音乐称为最能代表德国的艺术。
从“一战”爆发开始,托马斯·曼一直在思考德国文化和民族性。仿佛为了给自己不安的灵魂寻找庇护,曼选择依附德意志文化,把可疑的自我隐藏在族群之中。即便作为书写德意志心灵史诗的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仍然是个制造幻象的魔术师。他从德国的语言中体验文化的凝聚力,在德国“不安定的、非理性的、充满内在斗争的”精神中体会到某种亲切的认同感,为那千百万沉默地和他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立言,为这些蕴藉在音乐和诗歌中的珍宝辩护。可实际上呢,当他和妻子衣冠楚楚地走进慕尼黑歌剧院欣赏瓦格纳音乐,真正的德国大众正候在歌剧院门口仰望着他,无数阴郁的欲望正在向一场毁天灭地的爆发汇集;当他在五十年代再度踏上德国的土地,期待与“有着纤敏的灵魂和高雅的社会肌理的慕尼黑”重逢,面对的却是“巴伐利亚乡村的粗俗”,文明秩序被打散后剩下的赤裸现实。“德国文化的代表”托马斯·曼并不真正理解自己代表的德国。即便他可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用自己心中携带的德国文化重建“德国”——一个优雅深邃、属于歌德、尼采和叔本华的文化德国,这样的文化想象却只能满足美国读者对“好德国”的期待,得不到饱受战火摧残的故乡同伴的认可,甚至无法在同样流亡国外的大多数文化界同行那里找到共鸣。这个包容内在矛盾的德国兼具浪漫派对死亡的庄严倾慕,和原始的野蛮愚昧,与其说是对同时代纳粹德国的精准剖析,不如说是托马斯·曼把自己心灵中精神和生活的对立提升到民族层面。说到底,托马斯·曼是一个19世纪之子,沉浸在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汪洋中,把万物视作自我的投射,“等待世界自己走到他身边来”。

在托宾的小说里,“魔术”指的是艺术家投射自我的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隔阂。如果以此为评判标准,几乎所有现代艺术都属于魔术。将内心的匮乏投射进创作的托马斯·曼只是魔术师中最典型的一位,却对托宾有着更加微妙的意义。托宾曾说,除了《大师》的主角亨利·詹姆斯之外,托马斯·曼是他最想写进小说的作家,或者用《魔术师》中的话说,是那个让自己不再孤独的人,“那个他要对之讲出秘密的人”。科尔姆·托宾作为同性恋者成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主教爱尔兰,移居美国后不断书写故乡,被压抑的爱欲和与文化土壤失联的经历,让他在“魔术师”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纽约客》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如果身处七十年代,又是个同性恋者,“你并不会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而是生活在一种沉默的气氛中。我们所有人都学会了生活在自己的小隔间里”;甚至托马斯·曼在小说中用其他异类形式影射自身同性恋倾向的加密写作方法,也让托宾感到似曾相识:他发现,即便在当今社会,经历了同性恋去罪化、逐渐被世界接受的漫长过程,人们仍然“用‘酷儿’(Queer)来描述一切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为这些异类灵魂盖上章印的,终究是他们压抑的欲望。
于是,托宾让他笔下暮年的托马斯·曼在魏玛和驻守东德的苏联将军共同朗诵了一首歌德的诗歌,来自不同文化的灵魂在艺术中产生共鸣,歌德的魏玛再度作为德国文化之都熠熠生辉。然而一页之后,托宾把这全书最动人的一幕揭露为又一个艺术制造的美好幻影: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布痕瓦尔德距离魏玛咫尺之遥,如今是这位苏联将军关押囚犯的监狱,“没有一首关于爱情、自然、人类的诗能把这地方从诅咒中解救出来”。艺术家——“魔术师”们创作虚幻的美,无力阻挡现实的洪流,只能给人间带来短暂的奇观,引发一阵欢呼喝彩。那么,艺术是否只是泡影和虚空,并无意义?
不。仿佛为了回应自己对“魔术师”的最后一次拆台,仿佛给自己的故事留下一些光亮,也仿佛用另一个具有譬喻色彩的小故事代替曼或叙述者的反思,托宾在小说最后几页,借托马斯·曼母亲之口讲述了布克斯特胡德和巴赫的相遇。哪怕只是瞬间的奇观,美是那个驱动人在困顿中不断前行,让人眼中有光的秘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