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倪玉平:晚清中国的“变”与“不变”
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运河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哈佛燕京、UCLA访问学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代表性中文著作有《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英文著作有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主编《中国运河志·通运卷》等。本访谈谈及倪玉平教授的学术经历、嘉道时期政局、晚清漕运与财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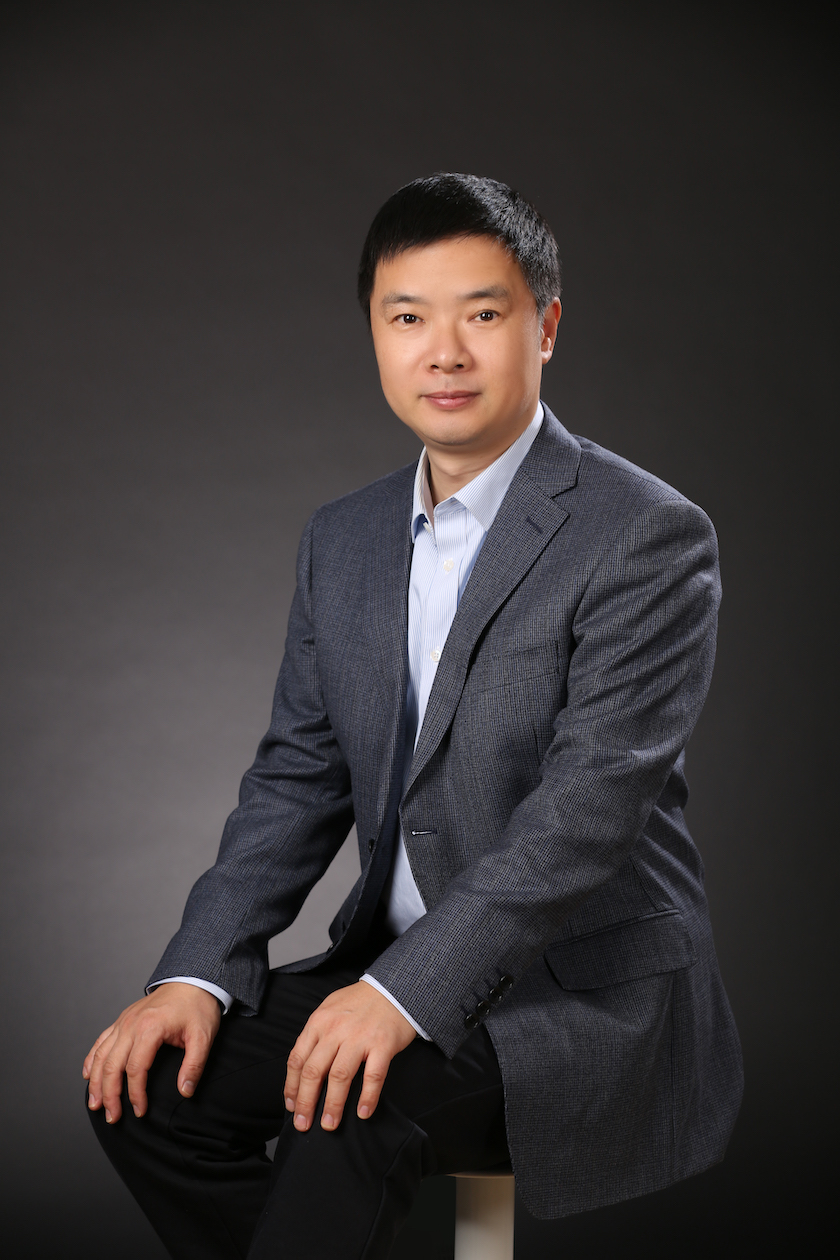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研究经济史呢?
倪玉平: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打算做经济史研究,也没打算学晚清史,我觉得做政治史有意思,所以最初想做政治史。读研究生时,专业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史。清史学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比较繁荣了,学者很多。当时大家或是集中于研究清入关之前的历史,但需要阅读大量的满文史料;或是集中研究康雍乾盛世。我看了嘉庆、道光两朝实录,模糊觉得政治改革很有意思,不过作为一个刚刚接触史料的硕士生,还不知道学问的深浅,想做大题目,先是想做嘉道政局研究,后来发现题目太大做不下去,就改做嘉道初政,后来又改成道光初政,最终才集中到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我把它作为政治史事件分析,主要研究河运派、海运派的斗争以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读博士的时候,我接着研究漕粮海运,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了晚清。漕粮海运确实是政治活动,但是要把政治活动解释清楚,就不得不涉及一些具体的史实,比如每年收了多少粮食、运了多少粮食、损失了多少粮食、取得了多少利润,不停地接触这些数字,石、斗、升、合,两、钱、分、厘,小数点后面蕴含着细微的计数技术。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些史料之后,我就体会出中国人“既精确又不精确”的特性,所谓精确是指史料中总有很多极其准确的数字,但是一看就是假的,因为不可能如此精确;所谓的不精确是指总有非常模棱两可的数字,类似于人山人海这样的模糊表达。我觉得无论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治国理政,还是日常老百姓的行为,都隐含着这种特点。
在研究漕粮海运过程中,我对经济史的不喜欢慢慢被消解掉,日益觉得政治固然重要,经济也很重要。我从经济史里抽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包括嘉道时期的财政、盐政改革、清代关税等。最初觉得经济史很意思,后来发现其实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样的,最终追寻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太大的区别,都要研究我们国家究竟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无非是聚焦的同各有不同而已。
您的很多研究是探讨清朝嘉道时期的经济和政局,您如何看待嘉道时期清朝的变与不变呢?
倪玉平:嘉道时期的经济,如关税收入、财政收入的变化、国家治理能力等,跟乾隆时期相比,表面上看不到下降的趋势,比如关税收入还是稳定在500万两,田赋和盐课合在一起每年也能够保证3000万两的收入。但是如果我们用购买力进行比较与折算,就会发现从乾隆到嘉道年间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再折算,我们会发现嘉道时期的关税与财政收入都下降了。
一般认为,造成嘉道或者道光财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财政收入没有与物价水平同步增长,而是支出方面极大膨胀,换言之,国家的开支越来越多,收入已经跟不上支出的节奏了。以前减缓支出膨胀的方式是靠报效、捐纳与国库的积累,所以乾隆后期还能够维持,可是到嘉道时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捐纳收不上钱,户部银库里的钱一年比一年变少。
变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账面数字变少,另一方面是实际数字变少。账面数字由乾隆时期的8000万两库存,下降到嘉道时期的2000万两。道光年间发生户部银库案,最后彻查发现实际上户部只有1200万两银子,900万两银子被偷出去了。除此之外,河工、战争、天灾人祸、蠲免等都造成财政的收缩。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表面上架子很大,但是里面已经被慢慢掏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光时期的萧条或者嘉道萧条确实存在,国家治理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如果不改革就很难应付下去。
您是否认为道光及其以后的对外战争与内部动乱加剧了清代的萧条?
倪玉平:实际上,嘉庆初年应对白莲教起义花了一亿两白银,如果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最开始让市场上的货币流通起来,使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短期刺激不可能持续下去,当然外部的影响也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嘉道时期的情况,我感觉是中国王朝历史周期规律性变化的结果,王朝建立初期比较凋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国家变化繁荣,进入所谓的盛世,进入盛世后,官员腐败享受,皇帝好大喜功,各种各样的开支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最后官逼民反。白莲教起义是开端,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其实也是我们本土农民起义的翻版,只是受到一点西化的影响。外因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还是内部的因素导致自我的变化。
您认为道光萧条的出口在哪里呢?
倪玉平: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出口无非是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如果当时国际环境允许,清王朝被推翻,重新走上自我更替的道路,也就是王朝的自我更新。二是用新的技术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比如人口危机,农民食物不够,怎么用新的技术提高亩产量,资源得到更好地开发,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思维体系,从而导致社会发生转型。
明末实际上已经出现转型的迹象,如四大名著中的三部和《金瓶梅》在当时已经出现,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其流变,明末思想解放等,都反映了市民文化的兴起,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状态,加之明朝皇帝并不足够有为,基层社会处于半失控状态,社会活力得到极大释放。不过清军入关之后,重新走上程朱理学道路,管控思想,加强中央集权,加之清朝的几位皇帝特别勤政,扭转了明末转型的道路。
您认为商税在晚清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您的一些文章里提到晚清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转变,但是诸多学者对财政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请问您是在何种意义上认为晚清存在向财政国家的转型呢?
倪玉平:先说商税。商税是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征税,我最初研究财政时就和商税发生了关系,因为关税、盐课、厘金都在研究范围内。晚清时期上面所说的这些商税都有极大的增长,而此前传统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丁钱粮,即以田赋为主,田赋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政府缺钱,需要广开财源,这一时期财政来源主要是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和本土创造出的厘金。厘金从1853年横空出世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迅速扩大,逐渐跟田赋齐平。此外,盐税和盐厘收入也在增加。清前期几乎没有地方财政,清后期地方财政迅速膨胀,膨胀的基础是厘金和杂税杂捐。杂税杂捐定义有几千种,但主体还是来自对商人、商业和商品的征税。
研究晚清财政时可以看到商税急剧膨胀,改变了田赋一家独大的格局。这种巨大的变化让我思考晚清时期国家向近代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由农业税向工商业税的转变,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晚清的商税做一个总体性的分析,也希望能够在资料建设方面做一些贡献,所以申请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我希望把我自己平时收集的很多档案、原始的材料全部放到网上,方便大家利用。
我后来又将晚清与西方做比较研究,发现西方财政结构在17、18世纪也发生了从农业税向工商业税的转型。当然西方的道路跟我们不大一样,西方最初是重商主义,国家在战争过程中为了筹钱,通过借贷的方式转让了一些自治权利,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民主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一般认为西方的财政国家的转型可以和军事财政国家画等号。而将军事财政国家概念运用到中国比较生硬,所以采取了财政国家的概念。像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魏文享教授等人,也在使用财政国家的概念,当然我们对财政国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
我对财政国家的理解是,以前国家财政就是财政的收和支,以维系国家正常运转,可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更多地获取财源,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了敛财而运转,不择手段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最终表现之一就是晚清商税的极大膨胀。中央政府在自己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放任地方督抚获得制度外的增收。晚清的杂税杂捐显然是制度外的收税方式,后来逐渐被纳入到制度内。从这个角度看,财政国家发生的第一个变化是财政结构由农业为主转向工商业为主。第二个变化是财政指导思想的转变,由传统量入为出的保守的、内敛的财政政策变成量出为入的激进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第三个变化是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野。清前期几乎没有地方财政,只有田赋的20%左右才会截留作为地方日常开支,并且日常的开支每一项都有严格规定。除田赋之外,关税、盐课、杂税都要上交到中央,地方不能染指,所以前期不存在地方财政。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地方财政开始出现。
总之,国家目的、收支结构、指导思想,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野等这几方面都跟晚清之前的国家财政状况表现出很大的区别,不能再用国家财政概括。用财政国家来界定,主要是想突出它的变化。
您认为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受西方的影响更多,还是内部的因素造成的呢?
倪玉平:从量出为入到量入为出的转变是我们本土的思想。中国历史上就有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两种财政指导思想的斗争,而且斗争很激烈。古代中国接受正统儒家观念为指导,皇帝不能与民争利,也不能太爱财,所以量出为入的激进扩张型财政为正统儒家所鄙视。
中国历史上有量出为入的实践,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南宋偏安一隅之后,土地减少,财政难以为继,于是开始大规模刺激商业,南宋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税收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外贸。但这些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不是常例,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也不高。清政府也知道这种做法不符合大家的期望,与传统的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的观念相违背,所以清政府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但是晚清时候没有办法,为延续政权,只能抛弃量入为出的做法。最初清政府也一直在上谕中说要量入为出,不能量出为入,但是实际上天天打仗,如果真的要量入为出,国家早就崩溃了。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出了一本新书《清代财政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分析晚清坚持不加赋的理念,我稍微有些不同意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虽然晚清时期朝廷一直在发布不加赋的政令,基本延续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不加赋政策,可是实践中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拿了这顶虚幻的高帽子作为指导,偷偷摸摸地搞各种加赋,比如按粮津贴、厘金等等,赋税早就加上去了,所以不能把不加赋太当真。我认为所谓的不加赋和量入为出,只是宣传的口号,百姓不相信,清政府自己也不会当真。
您如何看待晚清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化?
倪玉平:晚清发生的主要变化是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当然现代化有很多的定义,是否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标准走上西方所设定的道路存在很多的争论。我们今天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感觉有两个点: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我们今天开创的道路,就从传统文化与历史实践里面吸收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是有水之木、有根之源。所以,明清以来的发展演变,一定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根基,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内容。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一定不是只有中国才可以实践的现代化,而是能够对其他国家有指导意义和可借鉴意义的现代化,所以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西方式现代化也能够为我们中国所用,但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实践,探索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吸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一定能够对西方式的现代化产生对照意义,同时对亚非拉还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产生借鉴意义。
研究晚清走向近代的道路时,我主要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一直在揭示中国走向近代化,包括财政走向近代化的本土价值与内生性的因素,比如强调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它披着宗教外衣,其实是本土起义,而且导致了清代财政体制的巨大变化,包括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转型,这是一种本土因素的推动,转型的结果是农业性财政向工商业性财政的转变。第二,不能忽视晚清时期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对中国近代化的冲击基本上是负面的,它带来了技术,可是也掏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资金支持。晚清时期,政府的税收和借款主要用于赔款,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国家财政崩盘,紧接就是义和团运动。所以,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作用只是展示给我们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但同时又堵死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途径,因为没有资金,国家主权得不到保证,中国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识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晚清时期政府和老百姓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而且有些方面进展还很快,但是为什么最后中国没有很顺利发展?这与当时晚清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有关。中国跟西方有着代际差异的竞争,中国的技术比较落后,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候西方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同时它又不停地打压、欺凌中国,最终造成中国现代化道路面临资金干涸、环境不利的挑战。
这是否启示我们关于晚清的变化和现代化转型失败的原因要往前追溯?
倪玉平:是的。如果在中国跟西方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和学者能够早些认识到自身的差距,并且有意识地加以弥补,后面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这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表现。明清鼎革时期,是哈佛大学建立的时候,而且经过血腥的改朝换代,新王朝马上就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当牛顿研究苹果为什么落地的时候,乾嘉学派却埋头在故纸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有时也不禁希望,当康熙皇帝认识到西方火药技术的发达时,能够奋起急追,该有多好。又比如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虽然马戛尔尼提出很多苛刻的要求,但是乾隆皇帝如果也能认识到中西方科技上的差距,并且主动加以吸收借鉴术,而不是非常自我地、心虚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自己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中国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然历史无法改变,只是我们需要知道,闭关锁国并不能真正保护好自己,只会遭到更加惨痛的毒打。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现在的经济格局,但是您最近的文章提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重心的东移。清朝经济重心的东移和此前经济重心的南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当下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倪玉平:在读初、高中历史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句民谣的变化,最初叫“苏湖熟,天下足”,后来变成“湖广熟,天下足”,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定论。隋唐以来中国南方越来越发达,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人口重心,南方的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多。二是南方的经济水平和耕作技术等各方面都超过北方。三是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战争频繁以及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北方经济慢慢萧条,南方得到发展。
宋元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在南方,但南移之后重心其实还在变化之中,如果经济停滞不前是不可想象的,总会有所调整。我最开始还没有往东移的方向去考虑,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区域史研究有所进展,以前大家的重心是研究江南或者是华南,这些年明显感觉到华北区域的研究增多。比如阅读许檀教授等学者的论著,就会发现华北城镇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最近大家经常讨论的黄河夺淮入海问题,明朝黄河夺淮入海之后,把黄河的灾害“输送”到了淮北地区,这也是马俊亚教授的《被牺牲的局部》所涉及的内容。虽然从马老师的角度来说,他对这样的变化很愤慨,可是除非中国没有黄河,只要有黄河,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祸患,这个祸患不是由华北平原就会由淮北地区的老百姓来承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屡屡能看到“被牺牲的局部”,只是在明清时期,“被牺牲的局部”变成了淮北平原。黄河夺淮入海之后,华北平原的黄患减轻,华北平原经济有所复苏,城镇与人口都得到提升。此外还有外贸的影响。五口通商之后,中国沿海开埠的城市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南方的瓷器、茶叶通过运河运到北方,从北方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出国;北方的一些物产通过运河,或者通过沿海地区向南方运输,走向海外。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还不像晚清时期密切。1855年黄河改道,北方受黄河侵害的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华北地区的拉动特别是对华北沿海地区的拉动更加迅猛。通过研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出,烟台、青岛、天津等港口在晚清时期迅速扩张,天津直接变成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人口、商业、对外贸易都非常繁荣发达。明清时期中国的外贸主要是在广东粤海关,沿海城市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晚清开埠解放了这一约束。
我认为从明朝开始,经济重心发生了新的变化,并不是说江南与珠江三角洲不发展了,而是说同时期华北地区也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以南方为基点进一步向北扩张,所有沿海城市的发展都越来越快,我把这一现象归纳为清代经济重心的东向移动,也就是经济重心集中到沿海整体这一条线上。我把沿海分成三段,以山东、河北为北部沿海,江苏、浙江为中部沿海,江浙以南是南部沿海,这三个区域在人口增长、田赋征收、关税征收、厘金收入、杂税征收上各有优势,沿海整体的发展恰好又与内地整体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这个变化对今天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就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能够迅速发展,恰恰也是在明清时期打下的基础。
您如何看待大运河在清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大运河的兴衰与漕粮海运之间的关系?
倪玉平: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隋唐以前,中央王朝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西北方,隋唐以后外部压力从西北向北方转移,元明清时期为了支撑北部重心,修建了京杭大运河,保证了以北京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存在,恰恰是由于这条运河的存在,我们国家才没有分裂。如果没有北部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抵御外部压力,南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当时通讯条件手段有限,如果首都在南京,北方战事骤起,把信息传到南方,可能两三个月都过去了,战局瞬息万变,因此天子戍边很有必要。
从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大运河也具有很多特点。第一,大运河本身的治理体系与督抚体制平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由中央垂直管理。第二,为了保持运道通畅,朝廷每年都在维护运道。当然大运河牵涉到很多利益纠缠,所以清朝官场所有的贪污、腐败、低效率问题在大运河中也得到体现。国家治理比较廉洁、清明的时候,大运河运输也会比较高效。官场比较腐败的时候,大运河与漕粮也无法幸免。所以我觉得漕运也好,大运河也罢,都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第三,政令通过大运河上传下达,大运河上修建了很多的水驿站,南方的奏折、粮饷通过运河往北走。第四,康熙、乾隆十二次下江南巡视河工,召见知识分子,举行考试,给江浙增加了5600多个秀才名额。典型的例子是钱大昕,他通过给乾隆皇帝献赋,被赏给举人,后来考中进士,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第五,皇帝南方巡游期间每次都要整顿军务、接见官员,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第六,对儒家文化的宣传。康熙沿着运河到曲阜,对孔子行叩头礼,到南京拜祭明太祖朱元璋,都能收买人心。大运河不仅是南北经济的大动脉,也是宣扬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

1900年,苏州吴门桥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及清洗东西的妇女
您认为大运河兴衰与近代中国兴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倪玉平:可以说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说有关系,是因为当国家衰落之后,国家没有能力维护运河,运河没有办法通航,南北物资交流受到影响,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几个王朝,兴盛的时候都是漕运比较便捷的时候,比如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时,通过运河运物资,隋唐帝国也是如此。凡是运河运行良好的时候,都是国家强盛、物资交流通畅、文化发达昌盛的时候。
说没有关系,是因为运河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体制下最高效的运输方式,而近代已经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技术更加先进,已经有了铁路和轮船,这时候谁还会愿意坐三个月的木船,从杭州到北京呢?老百姓一定会放弃这种传统的运输方式而选择坐火车或轮船,大运河的功用就自然而然会衰退,以致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大运河的衰败既有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因素,同时也是时代的选择,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有新的东西来接替它。今天我们恢复大运河全线通水,在历史记忆传承方面的意义更为重要。

清朝漕运
我们知道您出版了英文著作,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的呢?您如何看待中外学者的交流?
倪玉平:现在学术界用英语写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很多高校的年轻老师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肯定得用英文写。其实以前也有很多学者用英文写论文,比如说最早研究经济重心南移的冀朝鼎。
我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在国外任教的时候写的,因为要跟外国人交流,总要让人家听懂。在那种环境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因为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是有误解的,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这与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让人家了解你,最好用别人的语言来让他了解。我们不要非常狭隘地以为,人家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先学习汉语,其实把中国历史介绍出去也是很好的途径。我当时正好也碰到了一些好朋友,他们帮我润色语言,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也得到提升。后来我又写英文书,主要是为了研究中西比较。总之,这是工作的需要,没有非要把自己限定在中文表达或者英文表达上,直接用英文写还是中文翻译成英文都可以,因情况而定。
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多语种交流的人越来越多的,以后用英语写作的人也会越来越普遍。用英语写作能够直观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也能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