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作为行动者的维特根斯坦是所有角色中最具体、也最抽象的一个
【编者按】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写道:“凡是不可说的,就该保持沉默。”这句被无数次引用的哲学箴言成为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钥匙。《维特根斯坦:从沉默到沉默》一书以“沉默”为主线,从语言、行动、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解读。作者认为具有浓烈伦理色彩的“沉默”是贯穿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关键。本文摘自该书第四章《灰烬或沉默》,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啊,有多好,没人知道,我是一个侏儒妖。(《格林童话》)
如果言说成为行动,那么行动的终结是否意味着沉默的到来?如果言说本就是沉默的一种方式(仅就维特根斯坦而言),那么紧随沉默的仍然是沉默吗?抑或是另一种言说的开端?如果以真正诗的手法展开行动,那么对行动的记录是否就是诗的练习?如果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哲学(尤其是后期)视为对话的结集,那么对于展开于对话中的行动来说,沉默的文本究竟是无声的指引,还是骄傲、误导甚或耻辱的证词?不仅如此,对一种间接行动(就宗教或伦理而言),尤其对这种行动可能具备的危险来说,行动中最后的行动不应是中止对行动的回忆吗?对行动者来说,除了行动,还能拥有什么?所有的这一切莫不与伦理,尤其宗教息息相关,有关宗教与伦理的一切又莫不与维特根斯坦变幻的角色紧密相连。其中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作为行动者的维特根斯坦,因为这是所有角色中最具体,也是最抽象的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哲学贯穿始终的宗教与伦理特性是对其处境的反应(《逻辑哲学论》写于战壕之中,后期哲学亦被战争打断。“这个时代的黑暗”始终影响着维特根斯坦),这种反应自然而然,但他的反应方式堪称异乎寻常:维特根斯坦成为行动者,并作为行动者进入哲学,从而使哲学成为行动。这两者的关系时而冲突,时而平行,并最终融为一体。
维特根斯坦在人与逻辑的优先性上选择了前者(如果不首先是个人,何以是个逻辑学家?),这与他对哲学的改造刚好一致(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行动。作为信条贯穿始终)。贯穿始终的这一信条无异于选择了困难。如果行动者为哲学的行动取代,那么这种行动将会呈现出何种形态?又如何呈现?一种反理论的努力肯定不是理论,也不应被看作理论,后者强化了困难。维特根斯坦不出意外地选择了间接表达;不是表达宗教或伦理,而是将其呈现;就行动者而言,不是提供个人的观点,而是将个人性体现于行动之中。正因为如此,在他出版和准备出版的著作之中,维特根斯坦要么以沉默来实施言说,要么细心地将任何直接的表达悉数祛除干净。
一种建立在间接表达之上的论断难以构成围绕中心并自成一体的系统。维特根斯坦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但也只能迈出第一步:为了进一步抵御其聚合的能力,还要强化它的自我消解。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的表达成为否定表达。“疑问与戏谑”既是其哲学的形式又是其行动的轨迹:问号为了解答而描画,同时笑声消解着追问的迷狂。在一切之后,所留存的仍然是问号。此外,维特根斯坦的计谋成功的可能有赖于使哲学成为对话,因为只有性质上堪称对话的思想才意味着真正行动的可能。同样,对话的可能有赖于真正对话者的可能。这一点将在某些时刻使其对话的性质发生逆转。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全由断片构成。它们或长或短,就像对话的笔录。就对话而言,构成对话特征的正是其开放、无限、具体,以及自发,它们使对话像生活本身那样具体可感,又同样长远而不可测度。在此意义上,对话最为可感的特征归结为对话的“在场”。在场构成对话未完成性的基础,同时亦为对话的内容所保证。
但是,对话是否会因行动者的退出而结束?能否在没有对话者的时候继续保持其“在场”?或者相反,对话被中断或被沉默取代,对话的笔录成为灰烬?甚至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思想成为“尸首”?在此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文本”成为问题的核心。如果言词只是灰烬,或者只是行动者的废墟,那出版其作品无异于一种背叛。反过来,如果他将著作留诸身后(正像维特根斯坦所做的那样),那么行动者得以始终一贯,但行动的轨迹却无从追寻。
维特根斯坦说,他的思想要等上一百年才能被真正理解。难道这是在意指他身后的喧嚣不过是持续不断的误解?意指一度与这些断片相伴随的、曾经沸腾的内心,伴随着作者的离去,言词也将归于沉寂?这是否还意味着等待与未来?也许在未来,或无限的时间之中,有人能在这些破碎的音符之上弹出一个曲调?就像巴赫尘封的乐谱为古尔德的天才照亮?那样的话,我们能否看到隐含于这些断片中的韵脚,听到沉默的吟唱?一句话,我们能否把维特根斯坦看作诗人?
“我认为,我对哲学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哲学其实只应是创诗。”(VB 19331934)他的自白并非没有道理。当我们阅读后期维特根斯坦时,我们会不断地为他跳跃的节奏和同样跳跃的想象力所倾倒,但同样也为之迷惑:每一次靠近都是一次退远,同时所有的努力无不被先期击碎。似乎那是些咒语的片段,正有效地抵御着任何企图强加于它的异质性,同时又时刻准备着接纳外来者。那些片言只语不啻散落的火种(“为特定的目的收集回忆物”),但拒绝成为火焰,因为后者总会熄灭。相反,火种始终留存为熊熊之势的可能性。所以,你尽可以将其看作诗篇,事实上却不是。
正因为如此,视维特根斯坦为诗人将遭遇巨大的困难。对他来说,袭用诗的手法既是计谋又是必然性。如果诗的手法是为了消解理论,尤其为了抵御科学理论的入侵而被引入,那么这种手法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借助跳跃将其连成一体,就如同珠玉之线,这条线本身却时隐时现。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示出宽容的姿态,其实却毋庸置辩。试图从维特根斯坦描述的“空当”处着手论证以击倒维特根斯坦肯定是徒劳的,因为他只会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描述而已。另一方面,描述只能是自我描述,他所做的只是“收集”,从而反过来强化了那种视其为诗人的困难。如果说诗的手法起于某种计谋,现在它成了保护自身免受侵袭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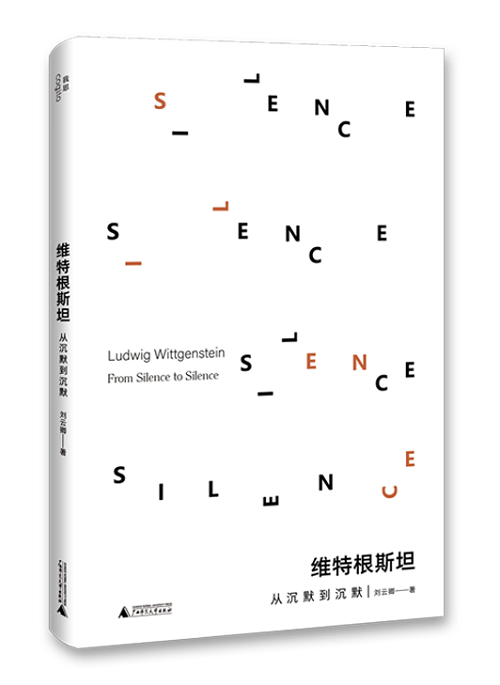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从沉默到沉默》,刘云卿著,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