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生存精神, 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邀请读者进入身后文学世界的唯一指南
近期,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首版于1972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本书是了解加拿大文学的最佳指南,也是阿特伍德早期奠定自己文学界地位的代表作品。在阿特伍德看来,代表美国文学中心象征的是它的拓荒精神;代表英国文学的是它的岛屿精神;而代表加拿大的则是其生存精神;此后“生存”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关键词之一。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生存”或许不再是一个独属于哪个国家的关键词,而是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关注的话题。在作家本人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更是从未停止过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和开拓。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赵庆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想写的是一本简短、易用的加拿大文学指南,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以及中学、社区学院和大学的老师,他们蓦然发现要教授一门自己从没学过的课程:“加拿大文学”。我也为同样的棘手问题纠结过,我知道可用的材料为数不少,却都是些包罗万象的历史报告、个人传略,还有艰深的学术论著,探讨的往往是绝了版的书籍。加拿大有很多作家,作品也多,然而,显而易见的经典寥寥无几。结果,编选、授课就要从长之又长的作家和作品清单开始,无论是读者,还是老师,都必须从中剔抉爬梳,挑出各自心目中的最佳作品。然后,问题迟早一定会冒出来,问法也许各式各样,内容不外乎是:“我们为什么研究他(而不是福克纳)?”“我们为什么得读这位作家(而不是赫尔曼·黑塞)?”要么,打破砂锅问到底:“加拿大文学到底有什么加拿大性?我们为什么折腾它呢?”
回答这些问题前,我先说说,这本书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本书不是穷尽一切、面面俱到的加拿大文学论著。那样的大部头已有几本,全面详实,已列在本前言之末。

我的这本小书,因篇幅有限,肯定会略掉不少重要的珠玑之作。我无意使自己的选录“均衡地”展现加拿大文学,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是一名作家,而非学者、专业人士。我挑选的例子并非研究所得,而是来自我个人的阅读经历。第二,这是一本关于作品分类的书,不是深究作家或某些作品,其意图不在于让每段选录都在书中占有等长的篇幅,而在于尽可能清晰地呈现把我们的文学凝聚在一起的主题、意象和态度的模式。如果那些模式确实存在,它们的各种变体就会体现在我可能未选的作品中。之所以有遗珠,要么是因为被选作品对模式的体现更加显明,要么是那些未入选的作品,我从没听说过。觉得我这种途径可取的读者,就不会止步于我所举出的例证,它们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
这本书不是加拿大文学发展史。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加拿大出现的第一本书写起,一路写到现在。更有帮助的做法是,先认清你现处的环境,且不管它如何,然后回顾一下你是怎样到达这里的。因此,在这本书中,你不会读到围绕加拿大联邦诗人或加拿大早年皮草商日记的长篇大论,我不否认其重要性,只是觉得它们并非走近加拿大文学的最佳途径。我给出的例子,大多选自二十世纪的作品,有很多是最近几十年的创作。
这本书不是评鉴集。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做颁发奖章之举。读者对于自己仰慕欣赏的作家,不应喜其入选,也不应悲其未列。我尽量不选自己觉得味同嚼蜡的作品,但是,这本书无涉“佳作”“风格卓越”或“在文学上出类拔萃”之类的讨论。
这本书不是传记。在这里,你不会找到无疑会令人着迷的作家私生活的任何信息。我对待他们的书的态度,就好像作者不是他们,而是加拿大。我希望你能暂时适应这个虚构,它纠正了一个偏颇的做法:众所周知,作家有私生活,但是直到最近,我们的作家都被当成只有私生活的人,而实际上他们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这本书不是完全的原创之作。它所借鉴的若干想法,浮游八方,散落于多年来的学术杂志和私人谈话。它们的出处,有一些已列在本前言的末尾。和它们相比,拙著犹如一粒维生素片,而它们仿佛是珍馐大餐。维生素虽然好在价格便宜,容易迅速消化,但不具备层出不穷的回味和精致。拙作也没有尽收颇值采撷的累累果实,而将采撷之趣留给了或许以追寻为乐的人们。

你或许要问:既然我这本书不概述,不评鉴,不提供历史和生平信息,不具备独创的灵心妙运,那么它能做什么?它企图做一件简单的事情:介绍一些重点模式。我希望它们能发挥鸟类图鉴中的地标功能,帮助你把这种鸟和其他鸟区分开来,把加拿大文学和其他经常与之相比较或相混淆的国别文学区分开来。每个模式必须在整个加拿大文学中频频出现,从而凸显出其重要性。这些重点模式,汇拢在一起,就构成了加拿大文学的独特形貌,折射出加拿大的民族思维习惯。
这本模式大全有多种用法。你可以用这些模式去考察未入选的书籍,看两者是否吻合。或者,你会发现所有的模式可能在一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有所体现。另外,你也可以就一两个模式深入学习。(有些老师生活在忌讳四个字母脏话的地区,我建议他们选用本书的第三章,这一章写的是动物,它们幸运地不会讲英语、法语,也不会讲神圣或渎神的话。)还有一个提示:请阅读章首的引文,它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以下是我意图所写的:它能让学者、专家以外的人士了解加拿大文学之所以为加拿大文学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把其视为加拿大境内写成的作品,并且它要写得通俗、易懂、实用。然而,我也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还不止于此。它介于一己之见和政治宣言之间,而大多数书被默认为二者必居其一。由于学校不教加拿大文学,也不做这方面的要求,加拿大文学在公众场合甚至不被提起(除非是以揶揄的口气),所以,一直到近来,我和其他同好都是出于个人兴趣来阅读加拿大文学。和以前,也就是一九六五年前接触加拿大文学的许多人一样,我是作为作家,而不是作为学生或老师,和加拿大文学打起了交道。我发现,我首先是通过自己的作品留意到加拿大文学中的几个模式—当然不包括所有模式。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拙作的关注点,也为其他作家所分享,而我仿佛和他们加入了一个从未被定义的文化社团。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多谈自己的作品,总觉得自写自评,最为吊诡。但是,我从作家的视角,处理了许多种模式及其相关问题,鉴于作家们本身也如此处理,这也许就是最佳的视角了。回答“在这个国家,读者要读什么?”,实质上就是要回答“在这个国家,作家都写了什么?”

加拿大文学创作历来是相当私人的行为,甚至没有读者的参与——长久以来根本就没有读者。而教授加拿大文学,却属于一种政治行为。做砸了,大家会比以往更觉本国乏味;做好了,或许会引发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被教得厌烦自己的国家,这种厌烦对谁有利。
阅读加拿大文学还有另一个原因,和读者是否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无关,而和读者的公民身份相关。一件艺术品,创造出来不仅是为了让人欣赏,也(如日曼尼.·.沃肯丁所提议)可被视作一面镜子。读者从镜中看到的不是作家,而是自己,在自己的影像背后,是所生活世界的投射。没有如此镜子的国家和文化,就无从知道自己的样子,就会盲目前行。像在加拿大这个国家,长期提供给观看者的镜中影像,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却被告知他看到的影像是他自己,那么,他对自己真正的容貌就会产生极其扭曲的认识。他也会曲解他人的样子:不自知,难知人。自我认识当然是痛苦的。加拿大文学在本土备受忽视,首先就表明了加拿大人害怕发现自己的真面目。加拿大文学中存在大量镜子和投射的意象,说明整个社会在徒劳地寻找一个有效的意象或投射,宛如亚.·.摩.·.克莱恩1笔下的疯子诗人,“整天盯着镜子,好像/为了认识自己。”
当然,在加拿大文学之外,也能找到我们的影像。在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有淳朴乐天的“加拿大人”,伐木,以土拨鼠为食。埃德蒙.·.威尔逊曾说:“我年轻时,也就是十九世纪早期,我们会把加拿大想象成为美国提供便利的辽阔的狩猎场。”(对极了,埃德蒙。)在马尔科姆.·.劳里的《火山脚下》,加拿大是主人公幻想的清凉世外桃源,只要能离开蒸汽蒙蒙的墨西哥,到了加拿大,一切都会好起来。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里的昆丁有一个舍友,叫施里夫,是个粉棕色皮肤的加拿大人,健康,爱运动,在昆丁的《古舟子》演出中扮演婚礼嘉宾。还有一个搞笑的:雷德克利芙·霍尔2的《孤独之井》是首部女同性恋小说,里面有一名加拿大男子,掳走了主角的女友,他强健,能干,刻板,是异性恋。这些多少呈现出“国际”文学中的加拿大形象:想象中的逃离“文明”之地、未被污染腐化的旷野,或是居住着欢快古朴的农夫、基督教青年会教员,他们要么奇特,要么乏味,要么二者兼具。看到加拿大啤酒广告和旅游文字,你常会感觉不自在,制作者把他们的形象建立在这些投射物之上,因为那是大家想要相信的样子,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如此。然而,加拿大文学本身述说的,则是迥异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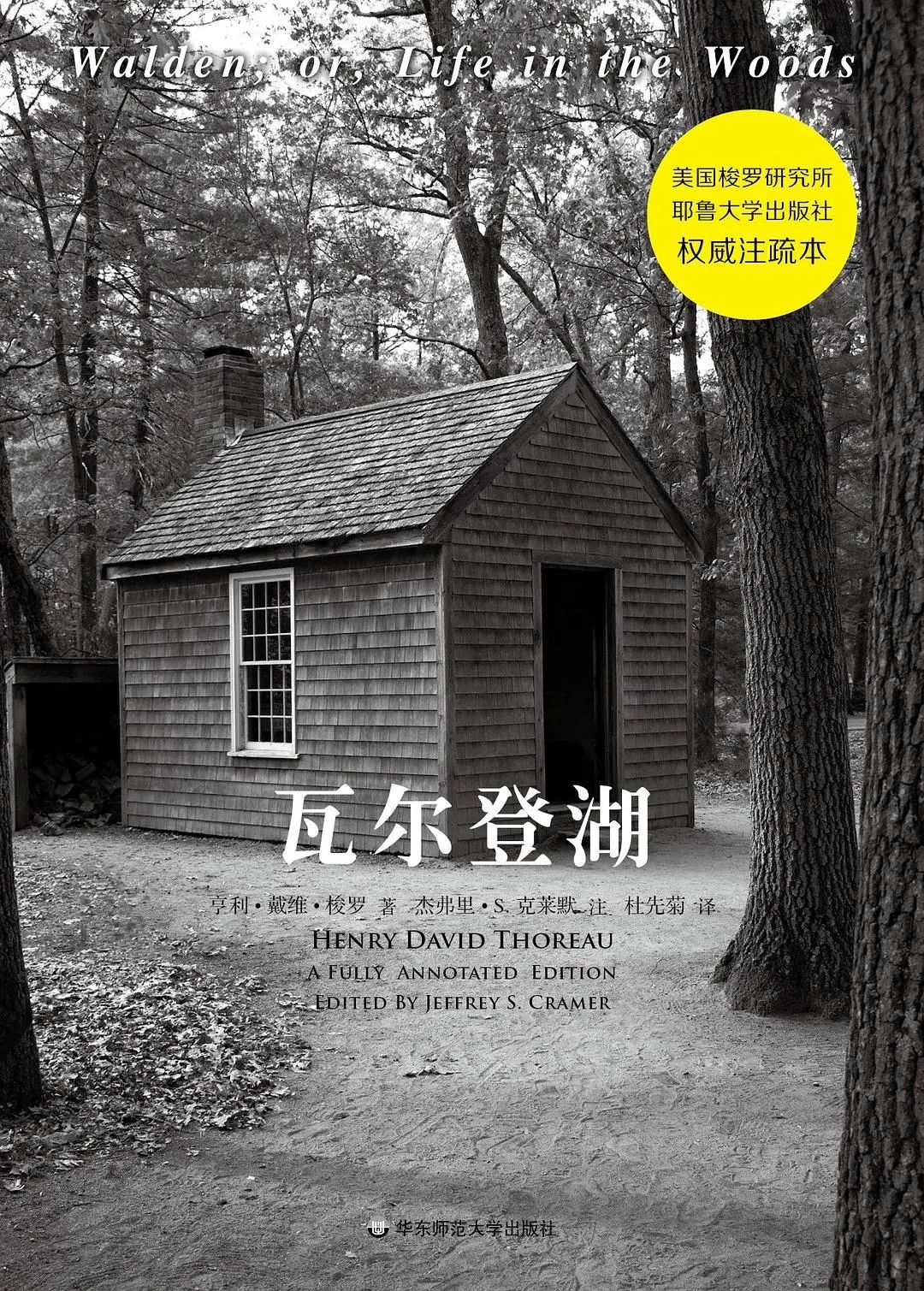
必须阅读本国文学,以便自知,以免沦为文化白痴,不等于说其他什么都不要读,尽管“国际主义者”或“加拿大第一者”有时持此论调。读者不能光读加拿大文学,这不利于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设想一个太空人落在荒岛上,只给他提供加拿大文学书,他将没有能力对加拿大文学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演绎,因为他没有可比较物,而把加拿大文学当成了人类文学的全部。对加拿大文学应该做比较研究,对其他文学亦应如此。通过对比,鲜明的模式即可脱颖而出。认识自己,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学;认清自己,则需要既将自己的文学视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要将之视作一个整体。
然而,弗莱建议道,在加拿大,“我是谁?”的答案,至少和另一个问题“这里是哪儿?”的回答部分重合。在有些国家,“我是谁?”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问题。这些国家对环境概念和“这里”定义明确,明确到甚至会给个体带来压垮身心的威胁。在众生万物各归其位的社会,一个人可能必须超脱其社会背景,才能避免沦为机制的功能性用具。
“这里是哪儿?”是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人到了陌生地,才会如此发问。它隐含着另外几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的什么方位?怎么找到路?要是一个人真的迷路了,他或许首先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原道返回,兴许能有找到对路或出路的希望。如果找不到路,他就必须利用“这里”为人类生存提供的条件,决定该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他能否生存下来,部分取决于“这里”的情况—是否太热、太冷、太湿、太干,部分取决于他自己的欲望和技能—会不会利用已有的资源,适应自己无法改变的环境,保持理智。“这里”可能已经住有其他人,比如土著,他们或合作,或冷漠,或敌对。“这里”也可能有动物,或被驯服,或被屠食,或要躲避它们。如果主人公的期待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可能会产生文化休克,乃至自寻短见。

卡罗尔·波尔特的戏剧《野牛跳崖》中,有一个精彩的场面:三十来岁的中学老师要求学生背诵亨利八世所有妻子的名字,与此同时,一支抗议队伍正从窗口经过。他告诉学生,上学可不是来看游行的。这恰恰代表了盛行多年的加拿大历史和文化观,即历史和文化发生在他处,若你刚刚在窗外看到二者,你就不该看。
亨利八世的太太们,不妨被视作代表着外来的、从“那里”——美国、英国或法国——涌进而泛滥的价值和老古董。它们的象征比比皆是,漫画书、女王像、埃德.·.沙利文秀、渥太华的反越战游行……这些价值和老古董的隐含义是:“那里”总比“这里”重要,“这里”不过为“那里”的低级版本,“这里”真正的价值和宝贝可以视而不见,结果,人们对“这里”熟视无睹,或将之误作其他什么东西。身在“这里”而宁可逃往他处,此人是流亡者或罪犯;身在这里而自认为身在他处,此人就是疯子了。
当你在这里,却因错误地标或定位而不知身在何处,你未必会变成流亡者或疯子,你就是迷路了。于是又回到这个问题:人在陌生之地,我们会觉得他是什么形象?对于加拿大居民而言,加拿大就是一块陌生的地域。我不是说,你没去过北冰洋或纽芬兰岛,没探索过旅行手册上赞美的“我们的伟大土地”。我是说加拿大的精神,因为加拿大不仅是你的身之居所,也是你的心之托寄。正是在这个精神空间,我们迷失了自我。
迷路的人需要地图,图上标出他的位置,对照其他地方,他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文学不仅是一面镜子,也是一张地图,一本心灵的地理书。我们的文学就是这样一张地图。我们是谁?我们去过哪里?我们的文学,就在解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诞生了。我们亟需这张地图,需要了解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对于一个国家和文化的成员而言,分享其居处和这里的知识,不是奢求,而是必须。没有那样的知识,我们就无法生存下来。
原标题:《生存精神, 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邀请读者进入身后文学世界的唯一指南|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