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然与自由:它们互相渗透,也可说是一体两面
【编者按】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变得稀有,会生出被“束缚”的感觉。这种自然和自由交织的感觉,东晋诗人陶渊明也曾有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业余是一位植物爱好者和博物学推动者,他在个人文集《自然以自由》中讨论了“自然”和“自由”的关系。本文节选自《自然以自由》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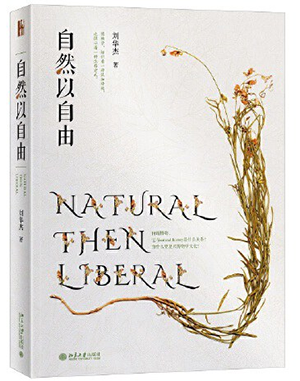
《自然以自由》书封
书名《自然以自由》包含两个大词“自然”和“自由”,以及一个非常含糊的连接词“以”。无论怎样的自由观,都没法脱离自然问题得以讨论。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也被讨论过无数次。
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自由问题看似单纯的政治哲学问题,其实也有自然的一面。当生命(不限于人类)自身能力低下时,面对大自然的束缚,活动余地有限。当生命自觉意识到局面需要改变并有可能改变时,自由问题就出现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再造新的自然等等,一路走来,部分打着“争取自由”的旗号。早期朴素的想法可能是(少有人公开讲出来),自由处在自然权威的对立面,降伏自然的“暴政”将获得更多人的自由。争取政治自由,不过是换个对手。突出人类个体之主体性,将一举两得,两种自由都解决了!真的如此吗?
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西方,当时的对手是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为何启蒙?是让处于蒙昧状态之人意识到不足、不自由,改变还在其后。启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让人意识到问题,又没办法改变,痛苦增加了,这恰好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到了康德那时,启蒙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84 年康德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生活在一个已启蒙的时代吗?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却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意思是启蒙没完成,还在进行中。到了 1884 年,启蒙任务完成了吗?没有。到了 1984 年呢?还没有。从康德讲那段话时算起又“启”了两百多年,还遥遥无期。对手已部分更换,却没有消除。有时老对手、新对手叠加在一起,任务愈发艰巨,几乎无法完成!以启蒙自居者,其人生大多染上悲剧色彩。
启蒙的目标是使民众能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理性又是什么?以前好像很清楚,现在则不得不思考一番。理性不等于当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不等于“现代性”的理性。当然,这不意味着几百年来无数前辈完全白费功夫,人们的确获得许多。许多什么?许多自由!席勒 1795 年说:“人类粉碎了枷锁。幸福者!恐怖的枷锁 / 断了,可别也扯断羞耻的缰绳! / 理性要自由,无限的欲望也高呼要自由,/ 他们放纵地挣脱神圣的自然。”不仅仅人类在持续争自由。也有人说,疫情的泛起实质就是日益边缘化的病毒为争取自由的绝地反击。人类不能就此而简单地服输,立即承认“地位低下”之新冠病毒的自由权利,但疫病泛滥的生态学解释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自由必然受到约束。从更大的范围看,启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启蒙也要反思,但措辞要十分小心。
在康德的时代,自然、目的性、自由就难以协调,康德哲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把三者的复杂关系理顺。通常,人类主体面对来自人为和来自大自然两方面力量的夹击,与前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政治自由(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在此有点用途),与后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生存自由(也关联着道德自由)。应当说,政治自由确实已争取到一些,而后者战绩不明显,有时战争进入了消耗战,矛盾愈加不可调和。比如现在“零零后”的年轻人,有些人不想生孩子。他们有这个自由,但是细想一下,是无奈的自由,还是不自由。“决定不生孩子”也是形势所迫,是精细“算计”的一种决策。人口多了是个问题,不生孩子更是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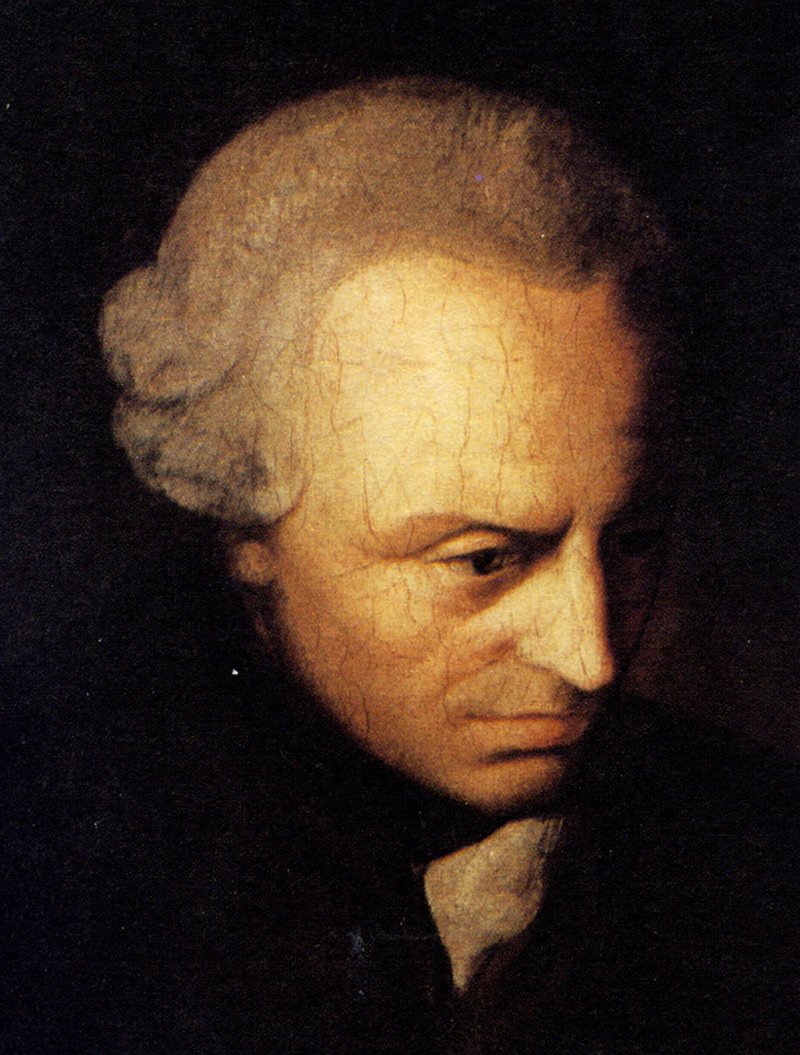
康德
回想一下笛卡儿、康德的二分法,人虽然根本上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却被“隔离”开来。人走出人之专制而导致的受监护状态(涉及人为法,称法律、规章、制度)被认为是自由的表现,人“征服”大自然(涉及自然法,称自然定律、规律)也同样是自由的表现,虽然康德早就暗示对两者的态度要有所区别。但康德哲学极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妨碍了对后者的发挥。“合目的性”是康德反复启用的一个说辞,为此他还构造了“自然意图”等不合时代潮流的概念。行为或思想合目的性,则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不自由的,这是心理层面的解释。但目的性本身也是时代建构出来的,由此解释堕入循环。对于具体的主体,自由有多少,更是难以度量。
康德从年轻时就在考虑,如果不借用宗教,如何表达、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法则(自然律)的关系。康德的写作多少还有点宗教禁忌,从那时至今,西方自然科学在功能上已经完全取代西方基督教,形势发生了大反转。康德对开普勒、牛顿、布丰都表示尊重,自己也考虑了贯穿大自然所有层面,一揽子给出世界存在与演化的图景(涉及他的“万有博物学”);后来基本放弃了这个艰巨任务,但晚年又试图拾起来。康德对新兴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极为敬重,所补充的只是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构思了“先天综合判断”等完全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就知识的生产而言,康德未提供任何新手法;就知识的性质而言,康德有惊人的领悟,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肯定人之认知与规范世界的能力。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讨论自由问题,对话方主要不再是康德的先验论,而是自然科学的有限经验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1987年我从地质学系准备考哲学系研究生时,首次接触到这段话,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后亦经常琢磨它的现实意蕴。当下,在非科学主义的意义上理解“自然规律”,这段话便显示了强烈的批判性。再进一步,单纯认识了“自然规律”,可能也不足以增加总体的自由(“总自由”)。但无论如何,认知对于获取自由、个体生存总是重要的。
现在重启博物之学,并非在逃避现实,是想借用科技的一个类似物(一个更有传统、经过了检验的东西)来平衡科技,反思科学主义以及与之相黏着的意识形态。
科技不应当垄断人们的自然观念。自然科学对于刻画自然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吗?自然与人为、人造是什么关系?怎么做才叫顺应了自然?现代科技发明了一些自由“项目”,也埋葬了若干,两者能进行会计核算吗?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争取自由的过程会附带产生什么后果?自由与自然、必然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始终考验着每一位学人。
……
简化来看,“自然”与“自由”分属两界,哪个高?有人说显然“自由”更高,本书名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其实不一定,两界的划分本身就有诸多预设,就排除了许多严肃的思考方向。自然、自由、自在、自我是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也应当联系起来讨论,那将用到更大的分析框架(博物学文化实际都涉及了)。人们可以讲“自然以自由”也可以讲“自由以自然”,它们两者还应当构成一个循环,互相推动,所谓“道之反(返)也”。其中任一环节,比如“自然以自由”,作为一个命题,表达了一种不常见的看法、非主流的哲学观点。它是我多年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博物学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心得。在我内心里“自然”与“自由”同样神圣,它们互相渗透,也可说是一体两面。做到自然了,也就自由了;有自由了,也就自然了。现实场景太复杂,通常“访问”不到纯然的、理想化的自然、自由,它们永远是学人憧憬、追求的状态。吉狄马加曾写道:
我曾问过真正的智者
什么是自由
智者的回答总是来自典籍
我以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
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
傍晚时分
我看见一匹马
悠闲地走着,没有目的
一个喝醉了酒的
哈萨克骑手
在马背上酣睡
是的,智者解释的是自由的含义
但谁能告诉我,在那拉提草原
这匹马和它的骑手
谁更自由呢

在这里,诗人没有论证“自由”是什么,但不等于他没有表达看法。相反,诗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宣布了“自由”的部分含义。席勒说过,“要提防挣脱锁链的奴隶”,“智者的理智所不能看到,/ 有童心的人会简单做到”。我的想法与此相关,若要讲明,那就是“自然以自由”。这个论点之强弱,要由实践来判定。演化有时间指向,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自然”,包含着合理性,也不意味“不变”,而是“自然地变”。自然地变,是指与环境协调一致地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