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智力和教育成功比其他人类表型都更多地被用于人的优劣评判
【编者按】
《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一书是一部与基因科学有关的科普著作。第一部分介绍了基因科学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成果及其广泛应用,包括解释人们在身高和体重方面的差异、预测疾病和学业的成功等。第二部分则致力于为遗传学建立一个新的道德框架。作者结合自己身为人母的经历,论证了为什么我们拒绝承认基因的力量,就会延续精英管理的神话,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就必须承认基因运气的作用。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智力(以标准化的智商测试来衡量)和教育成功也许比任何其他人类表型都更多地被从优劣等级的角度来看待,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一种被刻意设计和传播的想法。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凯弗斯总结的:“[20世纪初的]优生学家用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优生学家假定自己拥有的那些品质……即那种有利于完成中小学、大学和专业培训的品质。”而这种观念在智力测试的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第一批智力测试是由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和泰奥多尔·西蒙共创的,他们受法国政府委托,开发一种方法来识别在学业中有困难并需要额外帮助的儿童。由此产生的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要求儿童做一系列典型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任务和学习任务。例如,一个8岁的孩子被要求数钱,说出四种颜色,倒数和听写。
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的关键进步并不在于他们向儿童提出了哪些具体任务,而在于两项创新。首先,向每个人都布置相同的任务(标准化)。第二,向大量儿童布置相同的任务,从而了解某一年龄段处于平均水平的儿童的表现,以及任何一个儿童的表现与该年龄段的平均表现相比如何(规范化)。
任何一位家长,如果曾经查阅过成长图(growth chart)以了解自己孩子的体重增加是否足够,或者曾经问过老师,孩子的阅读量是否跟得上班上其他同学,就能立即领会到规范化(norming)的力量。你可以看看你朋友的孩子,或者试着回忆一下你的年纪较大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但你并不真正知道——18个月大的孩子的典型体重是多少?6岁的孩子平均能认识多少个单词?一套适当的规范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一个孩子的体重没有增加或为什么他在阅读上有困难。一套任务规范不会告诉你,是否有其他受社会看重的技能没有得到测量。但是,规范会给你一些比较数据,这些数据的基础不是人们对儿童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主观直觉。
可悲的是,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几乎立即被当作一种量化指标,对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特征的不平等主义进行正当化。关于测量,心理学家有一些发现:如果你要求儿童完成有限数量的任务,年长的儿童可以比年幼的儿童做得更多;儿童在这些任务中表现的改善速度不同;在少量任务上的表现差异,可以说明哪些儿童在他们一生中面临的更广泛的学习任务上会有困难。然后心理学家发明了另一个想法:这些任务的表现可以说明哪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秀。
1908年,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将比奈—西蒙智力测试从法国引进到美国,将其翻译成英文,用于测试成千上万的儿童。戈达德在1914年出版的《弱智症:其原因和后果》一书中发表了这些结果。在书中,戈达德声称,所谓的“弱智者”在生理上是与正常人不同的:“他们的动作不协调,外貌有某种粗糙的特征,这使他们缺乏吸引力,而且在许多方面显示出野蛮人的特征。”
更糟糕的是,在早期智力测试中得分低的人被指责在道德上有缺陷。根据戈达德的说法,这些人缺乏“对道德生活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非观的理解,也缺乏自制力”。同时,不道德行为的“愚蠢、粗野”,包括所有形式的“不节制和……社会罪恶”,都被认为是“智力低下的表现”。结合智力、身体和道德方面的缺陷,戈达德对“弱智”的总体描述是一种令人震惊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弱智”的男人或女人在他眼中是“更原始的人类形态”,是“人类有机体的原始和粗糙的形式”,是“有活力的动物”。
这样一来,戈达德和他同时代的人就把智力测试的分数定位为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判。得分低的人是“原始”人类,像动物一样野蛮,缺乏道德责任感。正如历史学家纳撒尼尔·康福特总结的,“智商不是衡量你做了什么,而是衡量你是什么——一个人作为人的内在价值的分数”。正是这种看法——不是“你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做对了多少道题?”而是“你的人性有多原始?”——被附加到关于遗传和遗传差异的思想之上。
作为监督过数千次智商测试的临床心理学家,我觉得阅读戈达德的书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体验。戈达德是美国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些创始人将该领域转变为一门实验科学,而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强制要求在公立学校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的法律。2002 年,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智障人士不应该被判处死刑。戈达德九泉之下一定会为之欢呼,因为他是第一个提供正式证词来主张智力低下人士的刑事罪责应当减少的人。今天,任何从事法医或临床或学校心理学工作的人都是在戈达德参与创建的领域里工作的,就像任何从事统计分析的人都必然要感谢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但是,戈达德刻意地提出了一种我认为可憎的想法:智力测试分数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一个世纪之后,可以用智力测试分数来衡量人性的想法,仍然困扰着关于智力测试的所有讨论。例如,2014年,作家塔那西斯·科茨对人们“探讨”是否存在遗传造成的种族差异感到愤怒,并明确表示,他认为关于一个人的智力的问题与关于一个人的人性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人生苦短。有太多比‘你的人性比我少吗?’更紧迫,实际上也更有趣的问题。”其他一些作家对科茨的声明感到不解,例如安德鲁·沙利文写道:“这真的让我很难过。”但这种困惑掩盖了对智力测试历史的刻意的无知。科茨的“你的人性比我少吗?”这一反问,正是智力测试的早期支持者认真提出的问题。
对智力和教育成功做任何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忽视这段历史。鉴于这段历史,许多学者主张干脆彻底放弃标准化测试和“智力”的概念。根据这种观点,即使是在单一种族群体内,也没有正当的手段来研究智力,因为智力的概念本身就是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历史学家伊布拉姆·X.肯迪在《如何成为反种族主义者》一书中对这种担忧作了精辟的表述:“使用标准化测试来衡量能力和智力,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种族主义政策之一,它贬低了黑人的头脑,在法律上排斥了黑人的身体。”
因此,即使关于智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欧洲血统人群内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是毒树之果。
但其他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的作家认为,不管智商测试的初衷是什么,它仍然是了解歧视性政策之影响的宝贵工具。正如肯迪本人所描述的,识别种族不平等对反抗他所说的“转移性种族主义”(metastatic racism)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识别种族不平等,那么我们就不能识别种族主义政策。如果我们不能识别种族主义政策,那么我们就不能挑战种族主义政策。如果我们不能挑战种族主义政策,那么种族主义势力的最终解决方案就会实现:一个我们都看不到,更不用说抵抗的不公的世界。
显而易见,记录诸如寿命、肥胖症和产妇死亡率等健康结果的种族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无法衡量这些差异,我们如何能消除这些差异,如何能调查政策对其的影响?例如,我们至少需要能够对婴儿死亡率进行量化,才会知道美国南方的医院取消种族隔离后缩小了黑人和白人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差距, 并在1965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拯救了成千上万黑人婴儿的生命。
记录健康方面的种族不平等,意味着记录每个身体系统的种族不平等,包括大脑。某些种族主义政策损害儿童健康的方式,恰恰是剥夺他们获得大脑最佳发育所需的社会和物理环境条件,或使他们暴露在神经毒素的影响之下。
铅就是一个例子。2014年,当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将其饮用水源从休伦湖改为弗林特河时,弗林特市民(大多是黑人)立即对这一转变提出了抗议:CBS新闻的一篇早期报道的标题是“我甚至不让我的狗喝这种水”。新水源的水具有腐蚀性,当它流经城市供水系统的陈旧铅管时,铅会渗入饮用水中。在该市饮用水铅含量特别高的地区,血液中铅含量升高的儿童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超过10%。铅暴露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黑人儿童最集中的地区。对这些儿童造成伤害的各种因素让密歇根州民权委员会得出结论,铅中毒危机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那么,我们用什么工具来衡量铅的神经毒性作用?智商测试。铅暴露导致的智商缺陷,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无法将铅的影响轻描淡写为暂时性的或微不足道的。这只是例子之一。哈丽雅特·华盛顿在《可怕的浪费》一书中表明,有色人种更有可能接触到有毒废物和空气污染等环境危害。她还认为,智商测试为儿童的抽象推理能力提供了一个数字指标,因此智商测试目前是量化她所称的“环境种族主义”之恶劣程度的不可替代的工具:“在今天的技术社会中,由智商 [测试]衡量的智力,被认为是与成功最相关的东西……智商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忽视它,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华盛顿说得对。虽然智商测试测量的技能肯定只能代表人类所有技能和才能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些技能不重要。在美国和英国等高收入的西方国家,标准化认知测试(包括经典的智商测试分数,以及用于教育选择的测试分数,如SAT或ACT,这些测试的分数与智商测试分数高度相关)的分数能够从统计学层面预测我们关心的事情,包括人的寿命。11岁时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孩子更有可能活到76岁,并且这种联系不能用孩子家庭的社会阶层来解释。拥有较高SAT分数(与智商的相关系数高达0.8)的学生在大学里会获得更好的成绩(特别是在考虑了优秀学生往往会选择更难的专业这一事实之后)。SAT分数特别高的早熟学生也更可能获得理工科的博士学位,更可能拥有专利,更可能在美国前五十名的大学获得终身教职,更可能获得高收入。
华盛顿希望恢复智力测试的正当性,并将其用作打击环境种族主义的工具。其他一些有色人种学者和女权主义学者也在做这样的努力。这些学者主张,可以用定量研究工具来挑战多种形式的不公正现象。例如,女权主义者安·奥克利认为,放弃定量方法的“女权主义立场”“说到底无助于解放性的社会科学(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的目标”。类似地,我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同事凯文·柯克利和杰敏·阿瓦德指出:“心理学历史上一些最丑陋的时刻,是研究者使用量化措施将当时的偏见正当化和法典化(codify)的结果。”不过,他们继续争辩说,“定量方法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事实上,“如果定量方法被有多元文化能力的研究者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学者兼活动家使用,完全可以是解放性的”。
智力测试被优生主义者定位为衡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的工具,由此产生的人类优劣等级制度方便地“批准”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社会的一些最丑陋的假设。智力测试衡量的是认知功能 的个体差异。在当前社会中,这些差异与人们在学校和职场的表现,甚至与他们的寿命长短,都有很大关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否认智力差异的遗传原因的前提下拒绝人类优劣等级制度。就像衡量一个孩子的语言障碍一样,智力测试并不能告诉你一个人是否有价值,但它们确实能告诉你,一个人是否能做(一些)受看重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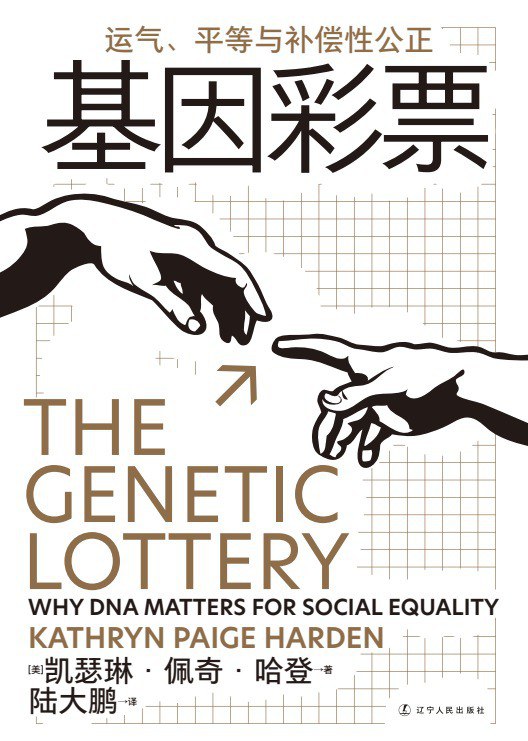
《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美]凯瑟琳·佩奇·哈登著,陆大鹏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