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持续不断损耗我,让我按部就班地成为螺丝 |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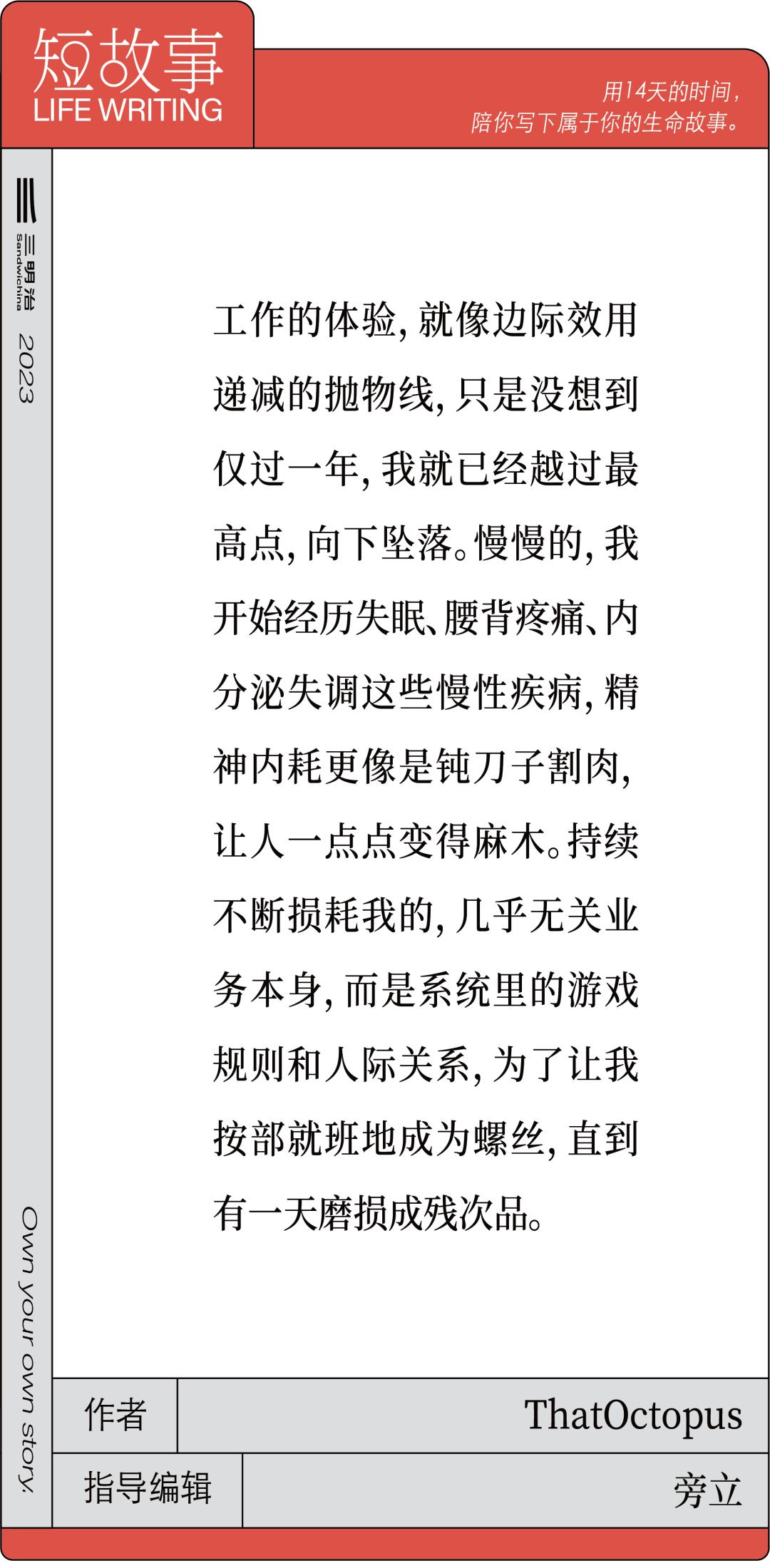

那个六月的晚上,家人们捧出一瓶藏了好些年的茅台,庆祝我成功拿下这家业内顶尖公司的offer。
一两白酒下肚后,醉意不断升温,烧得我的意识沸腾宕机,也烧断了内心深处充满怀疑和恐惧的保险丝:这份工作可能是我的牢笼,而至我于此境地的正是我自己。是我长久的逃避和内心深处的恐惧合谋,让接受这份工作“顺利”地发生了。
明白过来的那一瞬间,怀疑和恐惧合为痛苦烧到顶点,倒灌进内心的裂缝。我对着电话另一端为我揪心的朋友,不可抑制地嚎啕大哭:
“我好难受啊。”
“我好绝望。”
“我完蛋了。”
现在,我已经在这家媒体工作一年半了。这些日子,关于工作的思索,我记完了两根拇指宽的本子。笔记本的第一页,记录着上班第一天,前上司给我的几条建议,几个月后,他就跳槽去了离钱更近的地方。离职那天他清理工位,从抽屉缝掏出一张黑白复印的奖状,上面印着“优秀节目奖”,没有正式署名,空白处留下了潦草的铅笔印记,写着他的名字。他拿起来瞧了瞧,说了声“害”,轻轻地扔到桌面一摞过期文件堆上。
见到前上司的第一天,这个一脸胡子、有点痞气的年轻男子,带我在公司水吧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将一杯冰美式推到我面前。简短寒暄后,他很快切入正题,盯看我的眼睛,但却用略带闲散的语调,讲出了在这里生存的关键:理解你在系统中的位置,然后严格遵守每一道流程,就能规避95%的风险。
我把这条建议用红笔抄写下来,再画上三颗五角星,代表“非常重要”。之后我记下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反思、悲欢离合,95%是这句话的注解和延伸。但这又能怎么样?我从稚嫩、生疏、惶恐的新人,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老编辑”,却依旧没法把自己的头脑和屁股,牢牢地按在工位上。

我摇摇晃晃地把自己从床上拔起来,踩着时间点走进办公大楼,碰见了也在等电梯的同事。她随意朝我说了句“嗨”,眼下两坨乌黑,像墨汁似地流过干瘪的苹果肌,滴落在手机屏幕上,她低头埋进一个个小红点,整齐划一地回复“收到!”
我走进办公室,穿过一堆大小各异的电子屏幕,停在工位边。隔壁同事从电脑前抬起头,递过来一个眼色,算是打了招呼,荧光屏把他蜡黄色的脸照白了一个色号。
上午没有什么事,我蹲在电脑前,手指一页又一页地翻阅头条消息,脑袋里却想着下午合作项目的策划会。项目是另一个组主导,我组辅助调研和策划。推进到现在,选题文档都出了好几轮,高屋建瓴的、平实亲民的、未来狂想的,都出个遍,可每回都收到如此回复:不够上升、有点敏感、观众不懂、咱再看看。
私下和搭档吐了不少苦水,我们究竟是做项目,还是服侍渣男海后。费尽心计揣摩对方的心思,你说东,它要西;你给西,它捋了捋额前刘海,甩了甩一头大波浪,揶揄你怎么给了这不上台面的腌臢玩意儿。如此几回,我恍然大悟,原来既要又要,不是一种偏好,是一项命令。
想起立项初期的“年轻态”和“创新”的定位,我踌躇了一下,决定不自我设限,最终写上了看上去有些“冒险”的选题。令人意外的是,我的选题策划居然收到一致好评,一轮投票后,几乎全部被采纳。对面领导反复表示,我的选题让她眼前一亮。
散会后,我立马找到自己的项目领导汇报结果。领导听闻,笑了笑,鼓励了一两句又提了几点建议,末了,没头没脑地来了句:“你可别跑到他们组去了哈哈哈。” 我愣了一秒,随即有些惶恐地说:“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
我沉浸在想法能被落地和传达出去的喜悦中。等待两周走完剩下的上报流程后,编导正式拉了工作对接群。待她宣布新一期的制作安排后,却报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选题。我懵了,私聊编导,她简短地说了一句,我的题被报上去后,领导看了,觉得不安全,还是可以再想想。
设想,你想买双鞋,去太古里的精品店逛了一圈,对橱窗里的现代设计赞不绝口。又去小商品批发市场逛了一圈,对摊位上摞在一起的传统品位赞赏有加。但你最后买下穿上的,左脚是一只优雅小羊皮高跟,右脚是一只老北京布鞋,为了让他们风格统一,干脆喷上死亡芭比粉色漆。
原来既要又要,是这么个要法。我心里憋着一股郁气,咽不下,吐不出。同事凑过来开导我,你看啊,人家主导的项目,怎么能用“外人”的主意呢?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嘛。别气啦,不值得。
我已无从了解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发觉,原来,“傻瓜”竟是我自己。最终,我在对接群里回了个“收到!”,重新穿上“听话”的皮套子,回到了那95%里。

前上司走后,我组一个司龄次于他的“老编辑”,顺理成章地上了位。晚上唠嗑,我妈问我新上司长啥样,我“嗯”了半天,回答说,精瘦,个高,目目鼻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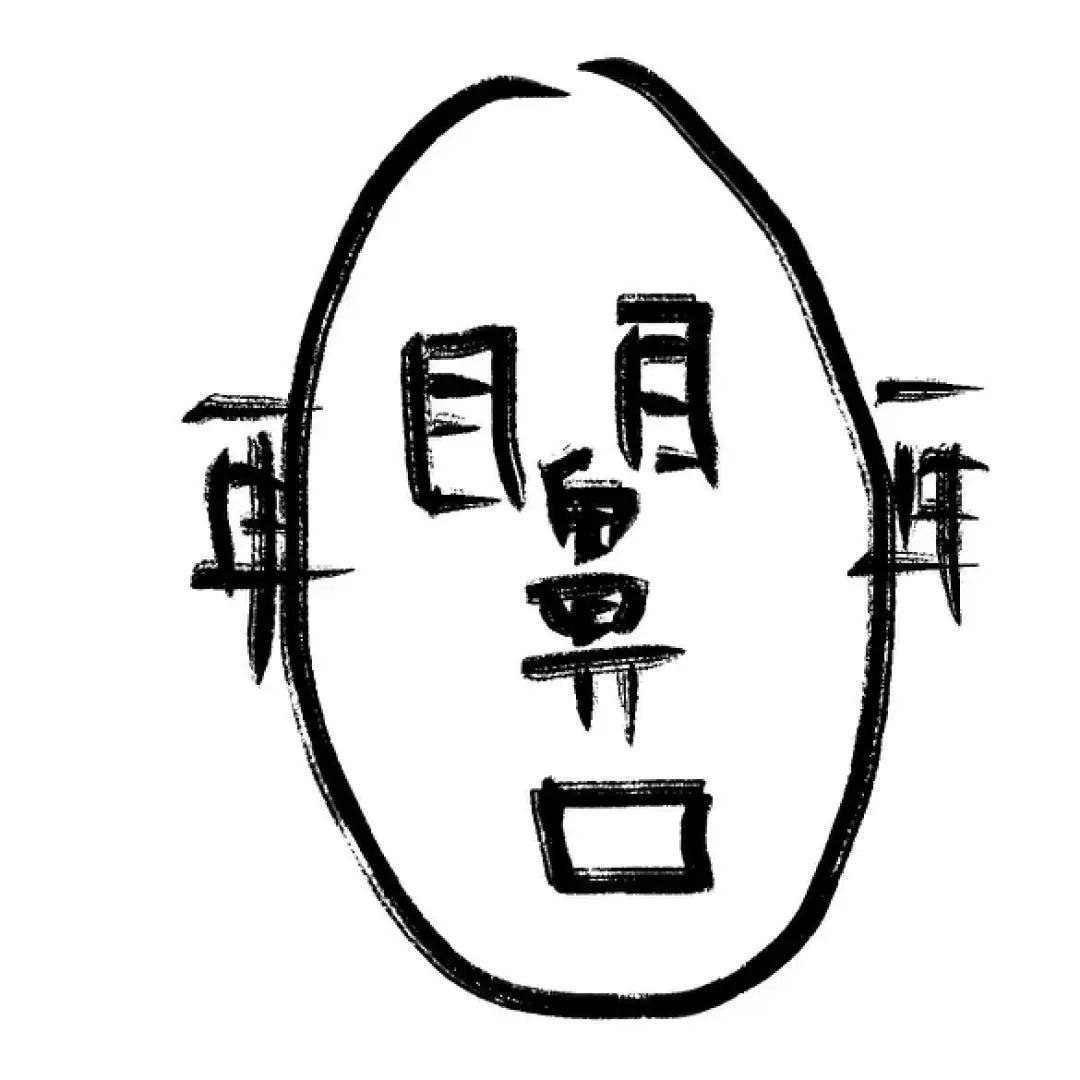
入职都大半年了,我俩的关系一直停留在标准工作交接流程上,私下几乎没交流。他是那种责任心很强的人。因为尽责,所以龟毛,更容易焦虑。他好像不把我当成年人看,有回跟我解释一件事,末了来了句“你还小,可能不懂”,把我震惊了个七荤八素。我心想,咱俩年龄差,顶多你当我哥,怎么听你这意思,却想当我爸。上任后,当他对作为下属的我拥有控制权时,我又发现他好碎嘴子,工作安排,办公室八卦,甚至私事,都能叨逼叨个没完,而且,他真想当我爸。
我跟我爹的关系,不远不近,动态紧张,基本源于他对我的控制欲。上高中时,他命令我报考商学专业,学成归来跟着他闯荡商界,最后在他的精心栽培下,成为商界顶级接班人宗馥莉二世。我虽然是我爹的翻版,又倔又自我,但没有遗传他的控制欲,相反,我只能讲合作,最讨厌被逼迫。自认为不是商业那块料的我,在我爹晓之以理不成遂威胁谩骂之下,我反抗到父女关系近乎决裂,最终他后退一步,我如愿以偿学了传媒。
对这份工作,我也继续不动声色地反抗。我开了个新微信号,专门用来处理工作。头像里的我迎面走来,眼睛却看到别处。我把朋友圈可见设置成三天,即便什么内容都不发。
且从上工第一刻起,我就坚决执行“非工作时间,非重要消息,一律不回”的纪律。虽然有不少不得不妥协的时刻,比如涉及到紧急的对接。但这项纪律弹性执行了一年多后,还是引发了我和新上司之间的矛盾。
做媒体的要义是“快”,我的龟毛上司,深谙其道。他发消息通知,需要马上得到下属回应,并用他认可的方式和方法执行,同时,他会时刻掌握进度,以最大程度把控结果。但我,抓大放小,在统一重要安排上,无条件配合每个环节,其他时候则收着力气。在那95%的安全范围内,我肯定给出合格的结果,但可甭管我怎么操作。
一天上午,新上司突然让我来隔壁的开放办公室找他。他引我去沙发处,这里平时是开会和做节目的地方,正对人来人往的大门,视野开阔。我们面对面坐下,寒暄几句后,他突然猛地提高嗓门,指控我下班不回信息,上班玩儿失踪,被举报态度不端正,行为不规范,整个组,没有一个同事像我这样搞特殊。
连珠似炮的指控把我砸懵了。我握了握拳头,软绵绵的,使不上力,心脏“咚”、“咚”、“咚”强有力地吹响了号角,召唤名叫恶心、挫败、羞耻、愤怒、恐惧、怀疑、委屈的球员同时上场,满场乱传球,争先恐后地要射门。
胡说八道!
我欲解释,他立刻提高音量打断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如此几次,我才反应过来,他就是要嚷嚷着让别人听到。我越解释,他就会说得越欢。
“我看你平时挺辛苦,但凡有奖金,我可都报你的名字呢。”
我心想,我加我的班,我拿我的钱,关你屁事。
“之前你迟到,我还替你上了会儿班,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把奖金分我一半啦?”
不卖冰毒卖蘑菇,警察是不是还得夸你是道德模范?
“你要再这样,我就告诉领导,看看要怎么惩罚你。” 他似笑非笑。
我的这些球员,此时把混乱的比赛推到了最高潮。在这关头,理智这位替补飞奔上场,抢球,扬起它的黄金右脚,一脚射门,堵住了我的嘴。我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嚷嚷了15分钟,“行了,你走吧”,起身叫上其他同事吃午饭去了。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于是我戴上口罩,妈妈总说我藏不住情绪。穿过那扇大门前,一个同事悄悄拉住我,说,刚才她拉着另一个同事去别的地方避嫌了,问我没事儿吧。
我一屁股坐回工位,假装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比起安抚挥着小拳头的球员们,更要紧的是,我要怎么收场呢?到这个地步,下班不回消息还真成我的错了。我失去先发制人、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机会,加上他意在泄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如何,我都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反击时机。
下班前,我拎着外卖送来的奶茶,挨个塞进组里同事的手中。最后,趁着交班时间,人来人往,我来到背对我而坐的新上司身旁,把奶茶放在他手边。
“我刚买了些奶茶,给大家分一分。这杯少糖,您快喝吧,” 我笑意盈盈,把手搭在他肩上,他迅速转过身看着我,没能掩饰一脸惊讶。“我呢确实做得不对,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您管理团队真得很辛苦,给您添麻烦了。”
新上司立刻送给我180度大变脸,我从来没见他笑得这样灿烂。“没事没事,你怎么这么客气啊,这多不好意思呢。下回我请你喝咖啡吧,但以后你可别再这样啦。”
但那位更大的领导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仍然是开放办公室的沙发处,这位真正评绩效的领导,先是跟我交代了别的工作,而后话语一转,问我最近是不是很劳累,嘱咐我多多睡觉,出门散散心,把不愉快留在工作外。
“你在我这里,能力和态度都没有问题。就刚结束的项目,我给你报了评优,” 她顿了一顿。“咱们也要知道,做好了99件事,但只要一件有瑕疵,某种意义上讲,前功尽弃,因为别人眼里只有这一件没做好的。”
我意会。不必解释,我老老实实地表示,自己有行为不当的地方,以后一定会更加注意。
过了几天,新上司递来了咖啡拿铁,我们表面上客客气气地把这一章翻过去了。不回消息的纪律,难得执行这么久才寿终正寝,我先是有些得意,而后叹气。我也明白,新上司大约觉得被我无视、权威受到挑战,哪个男人能忍着被不如自己的人,如此这般伤自尊?
他、我和同事们,边喝咖啡边聊明星八卦,有说有笑,一派和气。我盯着他,心里想,无论我做了什么,任何人,都无权对我进行打压贬损。总有一天,我要把此番受的气,如数还给你,一分不差。

入职不久后的某天饭点,同事们张罗着一起去吃饭,我伸着懒腰转过身,第一次见到了大美女球姐。
办公室里的好看女孩子,就像放牧一样,遍地都是,但球姐的漂亮确实是独一份。即使共事到现在,当我们交谈的时候,我总有那么几秒走神,陷入她水光盈盈的眼神中——这双大圆眼,透着天真、机敏、精明。
刚认识的时候,我是有些抵触她的,只因我们还不怎么了解对方时,她就同我大倒感情的苦水。随随便便对陌生人倾诉个人隐私,我觉得,这并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边界。但是她有一种能力,能让人不由自主地放下防备、产生同情心,即便知道她带着什么目的走近你。通过日常一次又一次约饭、出游、请求我帮她一个小忙,我渐渐允许她半夜11点——我休息的时间打电话,哭诉感情失败,吐槽“故意”为难她的同事,指责原生家庭的种种不是。
我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为了安慰她,我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或是附和她的主观意见,全然忘记她只是我的一个普通同事,而我们的关系不应该带离办公室,交浅言深,就是犯了大忌。
来北京前,我妈找到了一个懂易经的师傅,给我算了一卦。师傅说北京很适合我发展,但同时我会遇到小人。我很担心,问他怎么防,师傅笑说别紧张啊,小人哪儿都有,这很正常。
当时我以为,小人总是躲在暗处构陷,防不慎防;后来我发现,人家也在明处,比如,球姐大约是被派来考验我的撒旦,利用我的同情心,引诱我跳进她的地盘,成为她的血包。
正式宣布岗位调动前,球姐三番五次约我吃饭,每次都把话题往新上司身上引。
“我估计你也知道,他不太欢迎我过来。以前有过一次转岗,他直接说‘你粗心大意,不适合这个岗位,别过来’,所以我才去了别的组,” 球姐的语气平平淡淡,却在转回头夹菜时,顺势翻了个白眼。我没接话,心想,且不说这些,当他见过你多次和其他领导对摔纸笔、吵架告状,他当真希望招来一个会给自己添堵的人吗?
行走办公室,球姐好“主持正义”。她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但凡谁突破了她的认知,她先话里有话地“提点”对方,若再发生一次,就要掐准对方的痛点,狠狠打上一拳。
她盯着盘子里的菜,停顿了几秒,接着说话时像在自言自语:“不过,某某最近也跟他闹不愉快,天天跟我抱怨有的没的。我就安慰,人只是说话直,其实没什么坏心。当领导的总归脾气差点,况且他认真负责,还是别往心里去。”
某某是球姐同组同事,俩人关系一度很好。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你敷衍敷衍得了,别理。”
过了一两周,球姐告诉我,她已经请新上司吃了顿饭。“我跟他保证,我一定收敛着脾气,多多听他指教,” 她眼里荡着得意,呼噜呼噜,一口气喝了两碗汤。这顿饭奏效了。几天后大家一起吃午饭,新上司突然当众夸赞球姐“术业有专攻”,类似的话,我只在工作汇报会议上听他说过。
很快,转岗通知正式下发,球姐来了我组。当天下午,新上司跟我交代完别的事后,突然一改他的强硬命令式语气,放缓语调,甚至夹着一丝商量。“下个月,新同事们要上岗了。你也知道,球姐个性比较强,我就把她交给你,你多带一带,教一教吧。” 随即,他像开玩笑似地补充了一句:“她要出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立刻开始执行,我给球姐发去消息,问她什么时候有空沟通工作流程。她回了句“辛苦你了”,发来一个小兔怀抱爱心鞠躬的表情。
但是如同扎针采血的轻微痛感,挥之不去,提醒着我哪里有些不对劲。第二天,一觉醒来,我顿悟,我们是平级,凭什么让平级教平级,还要我为此承担责任呢?
联想前后发生的事,一个可怕的猜想突然跳出来:原来之前球姐多次找我吃饭,意在确认我的态度吗?她跟新上司吃饭,既让自己顺利接洽新岗位,又照顾新上司怕麻烦的想法,以此来表忠心,而我,则是他两协商出的“解决方案”?
类似的事情已有先例。第一次,她替我“打抱不平”,凭几句一面之词,冲到领导身边质问,为什么不给劳心劳力的我口头表扬;第二次,她绕过我向领导提出,要我配合她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她认为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没理由不接手。
如果论迹不论心,她是明着离间我。如果论心不论迹,我甚至要感谢她的“义气”或是“施舍”。
整个上午,我僵坐在原地,胡思乱想。到底要不要推掉带教?虽然我明确说过不要插手我的工作,但她还会再做一次吗?如果我拒绝,故意推诿责任的人反而变成了我?
球姐似乎没发现我心事重重,又叫上我去吃午饭。她握着筷子,一下又一下地戳青菜叶,突然,她把筷子一扔,抱臂往椅背里一撞,突然转头盯着我,眼神冷冷的,开口道:“之前跟你提到的某某,又来跟我抱怨,还变本加厉。我刚跟咱们上司完整复述了一遍这些话,提醒他要小心点,别被人利用了。”
犹如平地起惊雷,我瞬间回想起新上司指控我搞特殊的那件事。我们虽然表面握手言欢,但我的委屈喷涌而出,球姐两句安慰,轻而易举地勾出我的怨气。她像我对她一样安静地倾听,难得没把话带到自己去。末了,她也像对某某那样安慰我,当领导的总归脾气差点,况且他认真负责,别往心里去。
我的担心升级成恐惧。我这通对新上司的不满,如果和某某一样,成为她换取信任的投名状......不管球姐和新上司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管他们各对我有什么想法,总之,我不能卷入其中。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办公室,直奔领导的工位。
后果远没有我想象的复杂,其实压根没有后果。
关于带教,新上司和球姐谁都没有再提,彷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甚至没有在其他事情上找我麻烦,相反,平日说话,倒是客气了几分。
工作间隙,我从其他同事处听说,新上司吐槽球姐“大错小错不断”。球姐还像以前一样,时不时约我出去玩,向我倾吐情绪。我按耐住每一次怒火飙升,深呼吸,然后拒绝她。
她最后一次找我又是半夜,要求我过几天上门,给她的猫铲屎。“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只要周一二三六七过来,四五休息一下哈,我找了别人。主要是我儿子喜欢你哈。”
“什么强盗逻辑啊,” 我翻了个白眼,一边从善如流地敲下一行拒绝。我们的对话停在了这里。
若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很可能执着于琢磨“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但当我开始练习拒绝后,慢慢地确认,我不是非要同情她的遭遇、理解她的动机,才能学会拒绝,面对吸血鬼,不想被吸血的唯一办法,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地说“不”。

工作的体验,就像边际效用递减的抛物线,只是没想到仅过一年,我就已经越过最高点,向下坠落。慢慢的,我开始经历失眠、腰背疼痛、内分泌失调这些慢性疾病,精神内耗更像是钝刀子割肉,让人一点点变得麻木。持续不断损耗我的,几乎无关业务本身,而是系统里的游戏规则和人际关系,为了让我按部就班地成为螺丝,直到有一天磨损成残次品。
办公室像一面厄里斯魔镜,哈利·波特看见了去世的双亲,我原以为自己会看见名和利,而当镜子里的幻影散去,我看到的是“流动的可能性”和“不受约束的表达”。为了接受这份offer,我找到了很多理由,自以为有世俗层面的说服力。然而在日复一日的体验中,我就是糊弄不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愿当一个只有工具价值的95%。
那当初,我在逃避和恐惧什么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惧怕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于是两眼一闭,把决定权交给了别人。如果结果不错,似乎满足外部规则、符合外部期待,就算做自己;而一旦没有得偿所愿,便可以把不能做自己的痛苦,推向他人。
邓布利多搬走了厄里斯魔镜,告诉哈利,不能沉缅于镜子中的渴望而虚度了现实。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然需要穿着工具人的皮套子,尽力为未来做积累,无论是在此地还是在彼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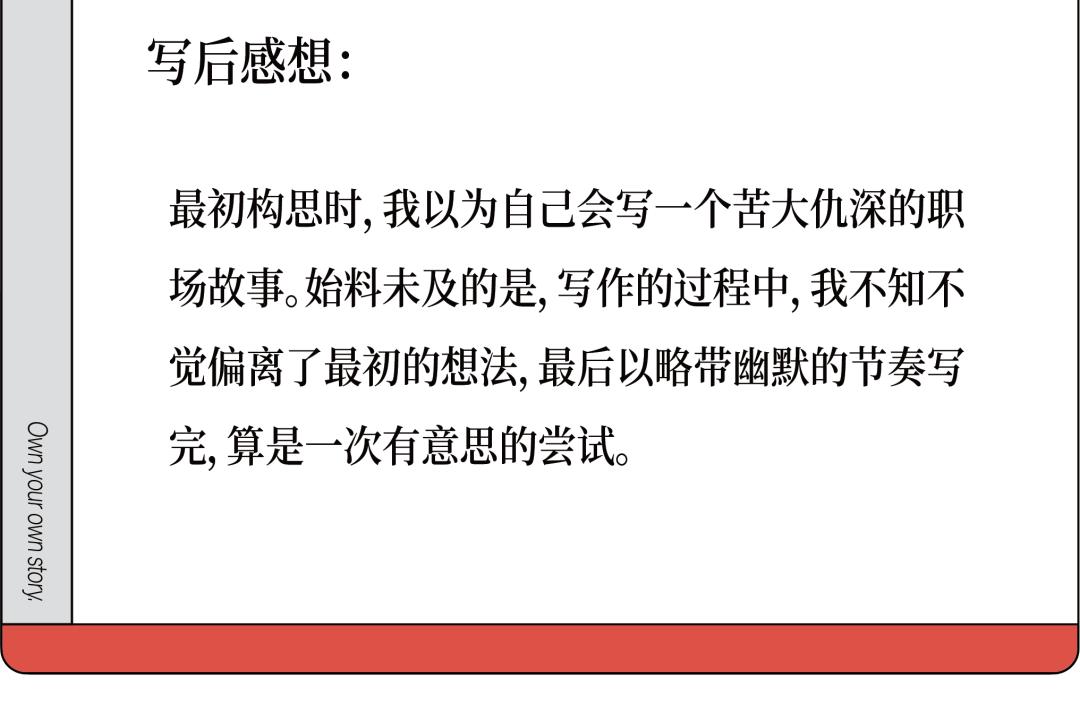
原标题:《工作持续不断损耗我,让我按部就班地成为螺丝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