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德威|从延安文艺到西北民谣:西北文学的历史与政治
7月31日,学者王德威在陕西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名为《现代历史,西北文学》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关中·外缘”的一个部分。讲座上,王德威提出什么是西北,什么是西北文学的问题。以下文字根据王德威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来,略有删改。

西北文学现代性的源起
西北现代文学可以以陕西作为聚焦点,形成一个概念。在西安讨论西北,注意力所及不仅应该包含陕西,还应该延伸至一般容易忽略的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十九世纪以来,西北风起云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与西北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西北”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层次:“西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所在,也是(流动的)人文、政治的物质空间,更是想象、言说、辨证的历史场域。尤其西北文化、民族形式和实践多元杂糅,冲击了汉族文化中心的论述。文学所指不止限于纸上文章,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活动。因此从文学角度而言,“西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文化的“感觉结构”。

西北文学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06年出版的《三原白话报》等活动。1912年,同盟会会友李桐轩等多人成立易俗社,可以视为标志性事件之一。易俗社糅合传统戏剧形式与现代观念,致力移风易俗,启迪民智,也因此赋予传统戏曲新的生命。虽然远离上海北京,易俗社却在西北成为民初的一股维新力量。
易俗社不仅搬演秦腔旧戏,同时也推出新编戏曲。影响所及,连当时中国文化领军人物鲁迅都为秦腔的风采所折服。根据鲁迅日记,1924年7月14日来到西安,在友人的建议下,16日观赏易俗社的演出。作为新文化最强烈的倡导者之一,鲁迅对传统戏曲的批判一向不假辞色,却从秦腔得到新的灵感。他在西安短短一个月,一共观看易俗社演出五次之多,并给予“古调新弹”的美誉。
戏曲这样一个文类和中国的现代历史有着怎样直接的联系?这里也涉及了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是什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竟和秦腔不无关系。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策划西安事变的根据地之一就是西安的秦腔剧场——易俗社。事变发生前的三天里,杨虎城坐镇剧场,以招待蒋介石周遭的亲信看戏为名,实为掩人耳目。场内锣鼓喧天,场外电光石火。彷佛剧场内外,都有了戏中戏的意味。
延安政治与延安文学
1936年,陕西另有大事。在前一年,1935年红军长征主力部队到达延安。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同时也是在文学史的叙述上,不论立场为何,都不能回避的一部分。
红军长征确切人数从八万到十万,有待辩论,到达陕北者十中得一。1930年代的延安是一个蕞尔小城,居民三千,一下来了近万红军,为地方文化带来了彻底改变。到了1943年,延安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三万,与此同时,一则关于革命的传奇兴起。

除了知识分子的文字传播,国际记者友人的报道也成为推波助澜的一部分。他们的叙述是否也应该成为延安文学的一部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让所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最为人津津乐道。这本书记录斯诺1936年7月到9月访问延安的经验,见证战时最为艰苦的一面。《西行漫记》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也是使延安故事成为世界革命话语的重要文本。另外一位是特立独行的女性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她展开和中共绵密的联系,报道许多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情况,其中包括丁玲的故事。
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毛泽东在延安这些年里建立起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文化、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延安时代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页应该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23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影响力到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它不仅成为文艺界的操作指南,也渗入了日常生活的实践。
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延安。是这些人为延安神话带来一道又一道壮丽色彩。比如何其芳,1937年之前他名列京派作家,作品充满唯美感伤的色彩,是一位典型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1938年,何其芳从他的故乡四川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同行的还有沙汀夫妇、卞之琳等人。他们抵达延安,立刻感受到新的气象,为之砰然心动。
何其芳在延安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提议:延安也有一些可以书写的东西吧。在延安观察了多日之后,何其芳决定不回去了,他加入贺龙部队,深入陕甘宁边区体验战地生活。之后他积极参与革命和党务,曾是延安代言人之一。1949年后,他恢复了文学本业,成为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丁玲也是那时的知识分子之一。她此前创作的《莎菲女士日记》曾以颓废的的,波西米亚式女性自白,记述在两个男性之间的徘徊。这部小说于1927年出版,让她一炮而红,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然而她之后选择了左翼路线,并为之献身。1933年,丁玲被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人们一度以为她已被害。丁玲的好友沈从文甚至写了文章悼念她。但到了1936年,她神奇地出现在了延安。丁玲是怎么样逃离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南京到延安,至今也是一桩公案。而她的故事经过史沫特莱的报道后,成为当时革命女性的一个典范。她日后的遭遇我们则是耳熟能详了。
萧军来自东北,是当时从四面八方到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又一个代表。萧军在1938年访问延安,1940年决定加入革命队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文人。因放言高论,他在当时及日后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而萧军的日记至今没有在大陆公开出版。这本日记是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文献。文学、政治、历史之间的互动,由萧军日记可以得见。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延安,怀有共同的抱负理想,那就是藉革命推翻现状。但他们各自的背景习性不同,对什么是延安生活,什么是延安精神,则各有各的看法。放言高论的结果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让统治者日益犹疑。于是有了1942年5月2-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出席座谈的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聆听毛泽东三次讲话。讲话内容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提到文艺工作者的态度、立场、实践方法等诸多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自此确立;文艺必须成为革命整体大型机器的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延安讲话之后,新的文学和文化政策及实践方式得以诞生。那就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展开中国形式、中国作风的文艺实践。这些实践的基础是乡土表演说唱艺术,经过党工及文化工作者加工后,形成独特的左翼文艺传统。其中包含着诉诸“始源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的力量,一种对乡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企图,成效见仁见智,却不失为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文艺。
像是秧歌剧《兄妹开荒》这类演出,或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或者戏曲《白毛女》(“文革”期间被改为芭蕾舞剧)等作品,都是例证。更易引起注意的是《东方红》。1942年冬天,这首歌为陕北农民李有源根据民歌《骑白马》改编,之后多次加工打磨成型,广泛传唱。1949年之后,对《东方红》精益求精的改造一直在进行。1964年《东方红》甚至被制作成大型史诗歌舞剧,动员3000名演员,而且更摄制成彩色银幕奇观。但这部电影1965年首映之后就消失了。“文革”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部分因为作词者田汉的政治问题及其他因素而被消音。《东方红》几乎具有了类国歌似的地位。《东方红》延续了所谓乡土情怀的“始源的激情”,歌词内容又与当时最前卫、最革命的思想结合。这是延安文艺的特殊实验,也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历史与文艺得失时无法规避的课题。
从五四的启蒙精神,即寻求个体自由解放,到延安的革命精神,即寻求群体意志的发扬,中国的20世纪前半段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达到高峰。在此之后,我们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们却要真真实实的面对延安讲话带来的“紧箍咒”。另一方面,讲话所发展的政治动能,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到政策、意识形态的斗争,随处可见。“文学”不仅反映、批判或创造“现实”。“文学”自身又成为另一种隐喻,指向其他社会、政治、权力斗争活动。“陕北”或“西北”在塑造新中国文艺,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命名的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1949后的新中国西北文学
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文艺迅速更新面貌。陕西文学的变化可以以三位小说作家的遭遇综述。第一位是杜鹏程,1954年出版《保卫延安》。杜鹏程来自陕北,也是延安时期的随军记者,他有感于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历史意义,从1950年开始,花费大量心力写出《保卫延安》。杜鹏程的小说多次修改,终于成书。这本小说是左翼军事叙事文学的高峰,在当时广受瞩目。但因为歌颂了彭德怀,这本书在1960年代被禁,杜鹏程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保卫延安》再次证明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交错关系。杜鹏程的遭遇表明了作为作家,并不仅仅只是写作、再现历史;写作本身已经是一个事件,参与到诡谲多变的历史与政治之中。
第二个例子是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小说以1929年陕西旱灾为背景,以主人公梁三老汉和养子梁生宝为线索,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历史背景,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政治正确意味浓厚。这种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柳青对风土民情的亲近,对人物内心转折的同情,仍然颇有客观。他深深影响后来的陕西作家路遥和陈忠实。柳青同样在“文革”中遭遇迫害。柳青的创作哲学也值得注意。他认为作家不能在书斋里写作,必须下放到农村,从最艰苦的第一线学习经验,挖掘写作材料。柳青有所谓“三个学校”的说法: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第三个案例是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刘志丹是早期革命将领,1936年牺牲。他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包括高岗建立陝北根据地、王明左倾路线,导致陝北1935年肃反等。1958年党内认为刘志丹的英雄事迹应该得到肯定,于是由刘志丹的弟妹作家李建彤执笔,屡经修订后由周扬拍板准予出版。未料康生等认为小说里暗含反党野心,尤其涉及“反革命”集团的领导高岗问题,竟然因此引发一场冤案。这些案例一再说明文学不是等闲之事,而是以血水换墨水的行动。
新启蒙时代的西北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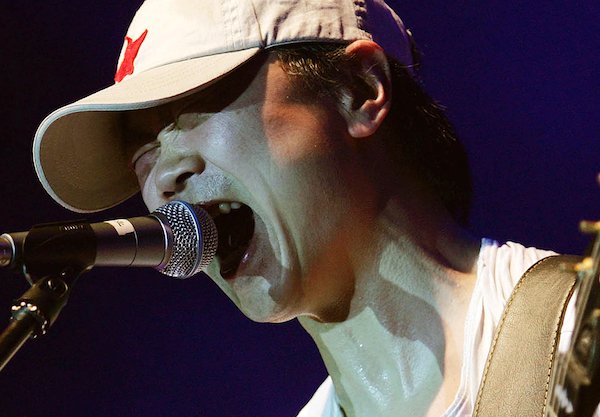
1980年代,“西北风”激起流行音乐的狂潮。崔健的“红色摇滚”尤其引领一代风骚,而西北民谣曲式是这股狂潮的底色。崔健的《一无所有》在1986年推出后立刻风靡一时。在1980年代末的一次集会上,百万人齐唱《一无所有》,堪称一段有声的中国的历史时刻。西北风不仅仅启发音乐创新,也为新一代的导演带来了灵感。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为“第五代”电影首开其端,正是根据柯蓝有关陕北红军采风的文字改编。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当时是重要基地,佳作无数,吴天明的《老井》也是其中之一。
在文学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路遥的作品,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1992年过世。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延续了柳青所代表的那种根植土地的叙事,有社会主义牺牲奉献的向往,却也关注个人生命里参差交错的情感体验,每每透露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特点。尤其《平凡的世界》讲述在圣人不在、诸神告别的时代里,一群来自农村的普通人如何历经城乡考验,重新体会“平凡”这两个字的真谛。这部小说在今天被重新提起,自然有其政治意义。
九十年代初,一群陕西作家引起全中国读者的注意,形成所谓“陕军东征”热潮。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都是当时引起热烈讨论的作品。《废都》以虚构的西京天降异象开始,描写作家庄之蝶在1980年代的情色历险,但更投射了新时期以来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废都”是荒废之都、颓废之都、残废、报废之都;相对社会主义“经济”观,这样的“废”学出现自然有划时代意义。某些桥段“因色情而被删去xx字“等的版式设计更勾引出读者的好奇与欲望。总之,1993年《废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出版文化、阅读伦理。不能忽视的是,作者悲悯和寂寞的情怀自在其中。
西北文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是不可错过的文化奇观。我们需要思考它的尺度、可能性和局限在哪里。
陕西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西北文学的作者和作品。在宁夏,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作品讲述一代知识分子在放逐生活中如何找寻心灵的慰藉,这种慰藉不是别的,而是女人。这当然被女性主义者所诟病,但是在1980年代张贤亮曾是人人必读的“新时期”代表作家之一。又如九十年代末崛起的石舒清,以《清水里的刀子》一系列作品探讨西北质朴的生活和宗教精神面貌。
张承志是另一位描述西北的重量级作家。他的《心灵史》讲述近三百年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在中国开枝散叶的历史,充满血性和血泪。这部作品虽有信仰导向,但是叙述动人,堪称杰作。张承志不但是位作家,也曾经是“文革”时代“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起者之一。1980年起张承志对自己回族身份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之后成为哲合忍耶教派最重要的代言人。《心灵史》一如书名所示,是张承志个人——和他的族裔——心路历程的记录。
在新疆,老作家王蒙曾有许多文字记录在伊犁生活的经历;年轻作者李娟则从在新疆成长的汉族眼光,描写地方风貌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关系。前不久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也曾在新疆居住,有多篇文字记录他的经验。《西去的骑手》讲述回族英雄马仲英对抗盛世才的故事。这些作品不断延伸出以中原或者汉族坐标以外的文学视野,成为新的“想象中国”的动力。
不得不说的还有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这部作品引用西夏王李元昊的典故,但以多重跳接后设方式写出与西夏几乎没有关系的故事,充满幻魅元素。骆以军以西夏神秘灭亡映射了1949年父辈作为外省人流亡台湾的经验,和自身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失落迷茫,也间接投射对台湾当下现况的忧心。
结论:史统散而小说兴

陕西是一个具有“诗史”悠远传统的地方。但是在16、17世纪之后,诗歌未必是唯一文类传达历史现象。冯梦龙曾经说,“史统散而小说兴”,这里断章取义,我们强调叙事文类在近现代中国和历史相互为用的过程。就此,我们再次思考,文学如何记录、形塑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想象?历史和文学的分野何在?
其次,陕西近现代文学再次提醒我们华夏文明的驳杂多元。胡汉华夷分野何在?我们的文学以及历史眼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汉族和中原的文化。我们必须叩问,人种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分野上,什么是被我们有意无意排除在外的,律法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作为丝路起点,西安这座城市面向广大的中国西北,中亚和西亚,本身就已经呈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现代性的丰富场域。
最后,在西安,在西北,我们不仅可以观看历史的文物和古迹,也必须思考什么是人和土地的关系。这里的“土地”指的不只是平面的地方或地区,同时也是纵深的、层层累积的垂直空间。就像我们观看考古遗址,不只是在地上,还有更多的是在地下。当我们行走在这样的土地之上,千百年的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只能体会自己的渺小卑微。当土地上的人在思想、信仰、利益之间你争我夺,土地之下的一切提醒我们生而有涯,苍茫深邃的大地承载看不见的一切。面对这样无限无垠的大地,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西北”。我们对于西北文学、历史的理解和深切反省,从这里开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