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有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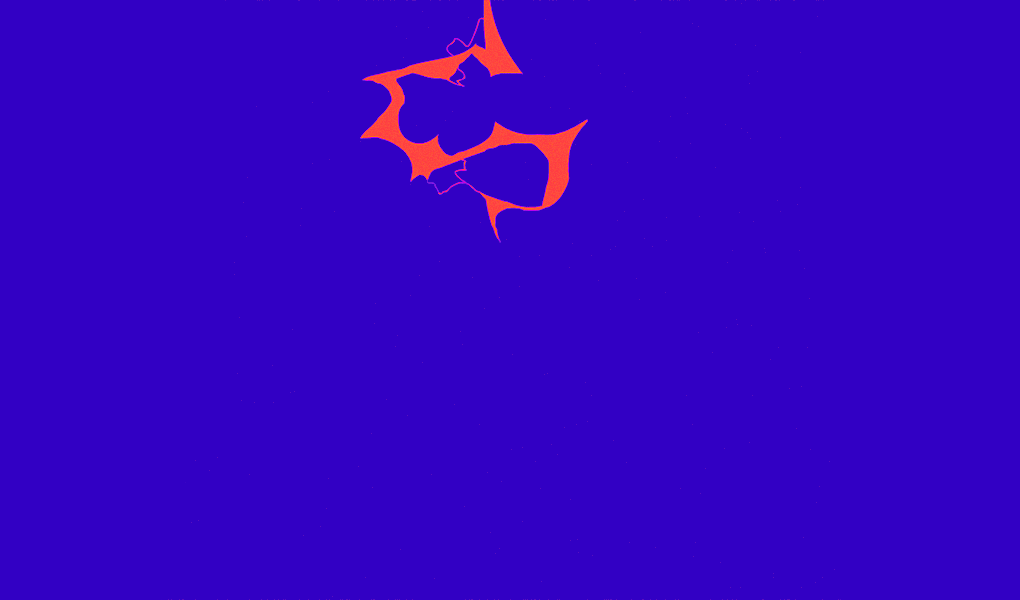
“我告诉身边的每一个大人,他们都对我说,没那么严重。”
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情绪,绝大部分孩子并不是没有求助过——被明显表现出的低落、紧张、焦虑情绪,逃课厌学,甚至出现幻觉与暴力行为,其实都是初次接触负面情绪无所适从的表现。如果成年人能够拥有高于及格线的警觉,很多问题就可能更早被意识到、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是任其发展,产生恶果,直到成为社会事件,才被更多人“看见”。
近几年来,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对于精神类疾病、精神科的偏见、污名化现象有减少;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对这类疾病、还是对生病的人、治病的医生,大家仍然缺乏真正的理解。即使是寻求医学帮助的家庭,往往也是直到孩子出现厌学、成绩下降才认为“孩子出了问题”,并不理解孩子的种种“反常”背后的真正问题,开始也难免陷入“让孩子在医院治好”的误区。青少年的种种情绪表达并不仅是医学问题,与辨认“疾病”和药物治疗同样重要的是对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道德内涵加以重视。
“病”可以完整解释精神苦痛吗?不同个体所承受的苦痛有共性吗?每个时代青少年面对的问题相同吗?今天单读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荣荣的文章,从医生的视角为我们详细介绍儿童精神科医生如何进行临床分析与治疗。
走近精神科医生
撰文:李荣荣
精神苦痛何以是“病”?
上个世纪 70 年代,好莱坞拍摄了经典影片《飞越疯人院》,片中的情节至今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还好,当年自由不羁的麦克所遭受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早已被摒弃。如今代表精神医学出现在公众眼前的是多巴胺、内啡肽等奇妙又高深的概念,以及百优解、速开朗等具有平易近人名称的新药品。
近年来,大众媒体关于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的报道变得日益常见。与此同时,讨论精神医学的非虚构及学术作品也越来越多,而对现代生物精神医学的反思便是其中一个常见主题。可以说,现代精神医学始终是个多义的场域,在它日渐成为人们缓解焦虑、苦痛与无助的一种重要途径时,对它的批评如影随形。

电影《阳光普照》
事实上,自福柯写作《疯癫与文明》、戈夫曼完成《精神病院》以来,西方社会思想对精神医学的拷问就不曾停歇。人们意识到,精神疾病或许与权力对越轨行为的捕获和塑造有关。如今,虽说强调精神疾病乃是社会建构物的“反精神医学”思潮早已落幕,该思潮影响下的不少观点、做法也遭到了批判,但对精神医学的质疑始终存在,只是方向发生了变化。
例如,有声音批评精神医学诊断范畴的扩张。社会学家艾伦·霍维兹和杰洛米·维菲德批评当代精神医学没有考虑症状发生的因果脉络,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外在压力导致的强烈但正常的精神痛苦当成精神疾病。负责编纂《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的精神医学教授罗伯特·史匹泽认为,霍维兹和维菲德的批评不同于全盘否定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的“外部批判”,是一种令人信服且引人注目的“内部批判”。(《我的悲伤不是病——抑郁症的起源、确立与误解》)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编纂者艾伦·法兰西斯批评手册第五版放宽了诊断准则,将日常生活中正常的焦虑、怪癖、遗忘乃至不好的饮食习惯都归结为精神障碍,由此带来了更多依赖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抗焦虑药、安眠药的“病人”。作为业内人士,法兰西斯认为精神医学唯有谨守边界方能实现拯救正常人以及拯救自身的目标。(Saving Normal: An Insider’s Revolt against out-of-control Psychiatric Diagnosis, DSM-5, Big Pharma,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Ordinary Life)
非虚构作家罗伯特•惠特克批评道,大幅扩展的诊断界定将数量上前所未有的成人与儿童纳入精神疾病范畴,作为标准照护方式的药物治疗则增加了他们成为慢性病患的可能,最终人们迎来了精神疾病的大流行。(《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患者》)
还有声音批评美式生物精神医学的全球扩张。非虚构作家伊森•沃特斯批评美国生物医学模式的解释与治疗抹平了不同文化对于心理痛苦的表达差异,原本多样的疗愈形式以及独特的心理保健文化信念在美式标准下变得不断扁平化。(《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面对将精神疾病归因于大脑内某种化学失衡的生物精神医学模式的兴盛,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犀利地捕捉到了某种“神经化学自我”的诞生。也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从大脑及大脑的神经化学(神经元、突触、受体、神经传递素、酶等)角度来理解与认同自我,一度被认为是“心灵”表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如今无非就是大脑内某种化学失衡的后果。(《生命本身的政治——21 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人类学、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更是在沉入个体疾痛叙事、挖掘苦痛根源的基础上丰富、加深了这些反思。戴维·A.卡普强调从主观的、经验的或以人为本的视角来解读抑郁症(《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若昂·比尔对忽略苦痛根源的药疗化倾向所展开的深刻批判(《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等等,无一不在提示我们去关注精神苦痛背后更加复杂的生活世界与社会脉络。

电影《晒后假日》
总之,在精神医学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距离渐渐趋近的当下,这些反思声音从不同角度提醒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精神苦痛何以是“病”?单纯说“病”能否完整解释精神苦痛?
当然,“精神疾病”不仅仅是隐喻,反思并不需要以取消精神医学为目的。在这些反思之外,我们或许还会好奇,精神科门诊究竟是什么样?精神科医生如何将精神医学知识运用于临床场景?我曾在《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的门诊日常》里描述过我的一些观察见闻,现在我继续以曾出现在那篇文章中的王瑜医生为个案,以旁观者及医生的视角来说一说儿童精神科医生怎么看“病”。个体的疾痛叙事与精神苦痛的社会性根源这里暂不讨论。透过王瑜的工作,我们会看到精神医学作为实践技艺的一面,在书本知识的积累之外,精神科医生需要在摸索中积累经验来救助他人。
相似现象背后可能存在不一样的原因
C 市三甲医院精神科门诊的走廊上,塞满了若干一脸焦急的候诊者。每个人不是担心错过叫号,就是发愁医生不给加号。为此,王瑜不得不派名研究生在门外维持秩序,顺带安排首诊者完成一系列的问卷测试,以便为接下来的问诊节约点儿时间。
诊室里除了电脑和打印机外没有任何仪器设备。不到十平米的房间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不大的桌子把屋子分成了两个空间,靠窗方向坐着王瑜和她的助手,靠门方向的椅子则留给了就诊者。比起门外的嘈杂,诊室里显得安静许多,就诊者叙说着自己的身心感受:从焦虑紧张、消极悲观、割手拔头发;到情绪忽高忽低,低的时候顿觉人生不值得,高的时候肆意消费彻夜不眠;再到耳边出现路人议论自己的声音、感到自己被陌生人控制想法等 等......各种各样的痛苦感受似乎在等待医生给出一个明确诊断。

电影《瀑布》
王瑜本科学的是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读的是精神医学专业。工作后,王瑜通过申请评审获得了国家认证的注册心理治疗师资格。此后,为了通过每三年一次的注册再认证,她必须持续接受专业培训,2020-2022 三年间接受培训的课时就达 910 节之多,平均下来几乎一天一节。在生物精神医学占据主流的医学大环境里,她比较愿意接受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心理治疗,也会在特需门诊做心理治疗。不过,王瑜的基本倾向仍是生物精神医学,临床中更多运用的也是来自生物精神医学的知识。我曾问她,精神科医生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技能?她的回答是:精神科医生实际上还要懂其他生物医学知识,熟知病理、神经系统通道,神经系统的化学变化等等,要能从母亲怀孕期的神经发育不足来理解儿童青少年目前的症状等。治疗方面,要根据病变部位、原理来用药,思考推断药物的副反应与正作用,用药同时还要考虑是否会合并癫痫、心血管系统疾病等等。倘若不看书、不背书、不懂药理,用药就会混乱出错。最后,临床思维尤其重要,包括诊断、鉴别诊断、病因推断、治疗方案制定(包括用药)等等。
王瑜举例说起鉴别诊断的重要。几年前看成人门诊时,有一天,诊室来了位产妇自述产后抑郁、情绪低落、浑身无力,王瑜根据抑郁方向进行了问诊和诊断,然而就在她开好药时发现这位产妇往诊室外走时需要家人一左一右地搀扶着,自己完全没办法走路。王瑜立刻觉得不对劲,既往的经验告诉她抑郁症不至于走不了路需要两个人来扶着,于是要求产妇立刻做 MRI 排除脑部疾病,结果证明产妇患的是脑膜炎,她的情绪与无力实际上是身体疾病造成的。相似的现象背后可能存在不一样的原因,医生的观察、思考和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王瑜举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两兄弟:兄弟俩都厌学,从家长的叙述来看两人表现大同小异,但精神科检查之后发现,老大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导致丧失学习兴趣,老二是因为多动症影响学习成绩继而失去学习兴趣。“如果看到看厌学就加抗抑郁药,那就走偏了”,王瑜说。
询问比量表检测更重要
自精神障碍诊断分类中的诊断手册(包括《国际精神障碍诊断手册》《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手册》)问世以来,分类诊断便成为了精神医学的核心诊断思维。这里的分类并非据据生物标记来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或病因讨论,而是依据可观察到的症状或行为来对精神障碍进行描述性分类与诊断。事实上,精神医学至今尚未确定精神障碍的各种生化异常指标,诊断过程中也没有验血、影像或核磁共振之类客观检查指标来加以辅助。如有,一般也是用于排查器质性疾病。因此,医生更多是从症状(包括情感症状和躯体症状)入手,依据病史采集(包括询问疾病表现、诱发因素、既往史等)与精神科检查(包括一般检查、认知检查、情感检查等)等诊断程序来进行综合判断。随后,症状较轻的考虑心理治疗,中度及以上症状则考虑药物治疗或联合治疗。
乍看之下,《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对不同精神障碍做了分类,清单式的检测量表还提供了一目了然的诊断标准,似乎医生根据量表打分就能作出明确诊断。但事实上,量表检测只是诊断过程的一部分,它可以为医生诊断提供线索,也可以提高医生问诊效率,但不能完全决定最后的诊断。在精神科门诊,细致观察与耐心询问就诊者的行为和情绪表现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很多时候,医生的询问方向与量表结构密切相关,但具体询问过程还需要察言观色,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最终,由于缺少明确的生物标记以及不得不依赖观察与询问,精神科医生的诊疗鲜明地体现出医学作为技术或艺术,需要“在做中学”的一面。
谭亚·鲁尔曼在医院做田野调查时发现,精神科医生与患者会谈时就像试图去徒手抓鱼一样困难(《两种心灵——一个人类学家对精神医学的观察》)。在王瑜和她同事的门诊现场也能看到类似情形。有时候,就诊者不一定愿意吐露自己的心事;有时候,就诊者的诉说或回答是片段的、零散的。医生询问就得讲究技巧,尤其是涉及复杂问题时,更是只能像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来,以免对就诊者造成伤害,或是破坏了就诊者的信任感。此外,儿童青少年往往与家长一起来到诊室,什么问题可以大人孩子都在场时问,什么问题需要请其中一方回避,都在考验医生的经验与耐心。
更困难的是,从生物精神医学的角度讲,不同精神障碍的症状之间很有可能存在重叠。并且,与成人问题相比,儿童青少年的症状更加丰富、复杂。有时候,同一位就诊者身上甚至会不同程度地同时涉及与焦虑、抑郁、强迫甚至精神分裂(港台地区现称为“思觉失调”)相关的诸多症状。此外,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症状比成人的症状更加变动不居,这段时间有这样的表现,过段时间又会有那样的表现。于是,对于医生来说,如何抓住重叠、变动的症状 背后的“疾病”就显得迷雾重重。

电影《阳光普照》
不是所有幻觉都与精神分裂有关
在各种症状中辨识真假是儿童精神科医生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按照精神医学的描述,幻觉、妄想是精神分裂的核心症状,存在幻觉、妄想的就诊者有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临床中,有的孩子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幻听、幻视。在不熟悉儿童青少年状态的成人精神科医生那里,这些表现可能会引出比较严重的诊断,但在儿童精神科医生看来,不是所有的幻觉都与精神分裂有关。有时候,这些表现只是孩子缓解自身情绪、自我守护的一种方式而已。
有一天,王瑜的诊室来了一位在重点中学就读的女孩。几个月前,女孩因心情低落、焦虑到精神科就诊,当时没挂到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号,只能在成人精神科医生那里就诊。因为存在幻视和幻听,医生怀疑她的抑郁症伴有精神分裂,建议服用抗精神分裂药物。暑假时,焦急不已的家长挂上了王瑜的号。一番长谈之后,王瑜发现女孩的所谓幻视、幻听多是在她学习疲惫甚至上课时脑海中出的一些轻松场景,不论是耳边响起的美妙歌声,还是从天而降的二次元人物,其实都在起着缓解女孩压力的作用。女孩心情好时,这样的声音和场景很少出现,心情不好时,它们就又跑出来了。女孩很喜欢与她的幻视、幻听共处,“愉快的时候想的少,不愉快的时候想的多,不想不愉快,不想治”。虽然女孩说这些歌声是她真实听到的,二次元人物也是她真实看到的,但王瑜认为这些都不像是精神分裂症中常见的在不同时段持续出现的、与环境无法对应的、对个体具有恶意或威胁的幻视与幻听。在与女孩父亲交流得知她的家庭和学习情况之后,王瑜进一步相信她的幻视和幻听带有自我疗愈的成分,抗精神分裂药物对于她来说并不合适,适当吃点儿氟西汀(百优解)加上心理治疗缓解焦虑和抑郁即可。
当然,王瑜清楚,诊断和治疗不是一锤定音,有的时候它还意味着某种漫长的求证过程。作为临床医生,她往往是在首次就诊时根据当时发现的主要症状给出治疗方案,并且要求就诊者两周后复诊,以便确认或调整之前的方案,随后又再根据情况决定再次复诊的时间与频率,并随时根据实际变化调整治疗方向。
事实上,聚焦儿童青少年门诊多年来,王瑜时常会接触到有幻觉、幻视、幻听的孩子。每次遇到,她都会询问,是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声音?是眼睛看到,耳边听到,还是脑子里出现?接触多了,她日渐意识到很多时候儿少的幻听、幻视中有太多的想象与安慰成分,并不一定就是精神医学所说的幻听、幻觉。前两年,王瑜带研究生在某个留守儿童地区做大规模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时也发现,通过任意幻想或做白日梦来抚慰自己的焦虑与 忧伤的情况并不少见。
无奈的是,也有不少孩子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画面并不让他们感到愉快。有的孩子会听到声音让自己自杀,有的孩子会凭空看见黑影人或是地上汩汩向外冒的鲜血,有的孩子会觉得有人控制自己让自己做不想做的事。这时就得更加耐心、仔细地观察、询问,综合各种病史采集、量表测评与身体检查来综合判断。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在诸多线索中锁定核心症状
症状重叠、变动,以及青少年自身处于发育过程中,叙述不完整、不清晰等因素都会使得医生试图锁定的“疾病”扑朔迷离。此时,经验往往能帮助医生将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的轨道内。
某次到基层医院会诊,王瑜遇到了一位情绪烦躁、容易哭泣、有自杀想法并且反复实施自杀行为的男孩。据男孩的主治医生介绍,男孩患有严重抑郁症,自杀意愿强烈。但是,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后,他的症状不但没有好转还有加重,甚至发展到了看见坚硬小物件儿便要拿了就吞的情形。为此,医院不得不一边为他制定一套抢救方案,一边邀请省城专家来会诊讨论。
会诊时,王瑜观察到男孩在诉说自己的自杀行为时表情既不悲伤、也不沉重,反而是轻松的、开心的。既往的经验告诉王瑜,一般意图自杀的人不会像男孩这般面露开心,他的表情与行为极不协调。于是,王瑜有意识的询问男孩是否觉得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谁知道自己的想法以及具体如何知道。随后,王瑜得知男孩认为自己会被陌生人看透,为了不被看透,男孩甚至会在周围人多时屏住呼吸,因为他担心呼吸会让自己内心的想法变成别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此,王瑜怀疑男孩的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中混合、藏匿着一种泛化的被洞悉感,而这恰好是精神分裂的一级症状。用精神医学的话来说,王瑜认为男孩的抑郁症“共病”精神分裂症,并且精神分裂是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精神分裂的症状压制住,防止其继续恶化。
本来,从诊断程序上讲,医生在对就诊者进行首次精神症状诊查时,需要做全面的精神科检查,其中便涉及询问是否存在幻觉、幻听、幻嗅、内心被洞悉感等等,住院病人更是需要全面询问。但是,症状重叠、变化以及问诊时间有限等诸多因素都可能使得某些重要线索被遗漏。很多时候,就诊的儿童青少年既会说自己情绪低落、烦躁、想自杀,也会说自己的想法被他人看透。事实上,不少前来就诊的孩子都会有一种简单的被洞悉感,即觉得周围人在议论自己,同学、老师会看透自己。不过,这些通常是一种局限在小范围内的被洞悉感,与男孩泛化的被洞悉感不一样。因此,医生必须仔细分辨,既不能漏掉症状线索,对泛化的被洞悉感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儿童的常见想法加以病态化处理。总之,在诸多线索中锁定核心症状是儿童精神科医生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倘若辨识出现误差,药物治疗方向就有可能走偏,由于不同药物作用于不同神经通道,最后就会出现疗效不佳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
最后,针对这位男孩,王瑜建议增加抗精神分裂药物,停用药物机制中涉及增加多巴胺的抗抑郁药物舍曲林(达到一定的量有可能让之前存在的分裂症状加重)。两周后,王瑜了解到男孩的自杀意念及行为以及幻听症状都有明显缓解。当然,最终疗效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知道,至于诱发抑郁、精神分裂的非生物因素更是需要慢慢分析和应对。
不管怎样,诊治不会轻易完成,疗愈更是漫长。
时代的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新问题
诊室里最让人感到无常的一件事,就是不知怎的孩子身上出现了幻听、幻视、敏感多疑等分裂样症状。当医生说出“精神分裂”几个字时,家长的震惊、无助、失声痛哭、不知所措令人唏嘘、伤感。这时,王瑜往往会一边综合症状、药理等因素开出药方,一边安慰家长说:虽然精神分裂在诊断分类中是严重的,但是有很多科学家在做研究,药物也已更新换代,只要按医嘱吃药避免复发,孩子就能好转,不影响以后结婚生孩子,反而是很多孩子的焦虑、抑郁、厌学情绪难治疗。
王瑜到 D 省精神病医院开会,儿少科主任感慨地和她聊到,十多年前该医院刚刚开设儿少科时,整个科只有一个儿童住院,那时根本不想象不到如今儿少科会挤满如此之多在生活和学习中受挫的孩子。王瑜所在的 Y 医院也是类似情形,出现在门诊、住院部的儿少身影越来越多。疫情以来儿少在就诊者中所占比例更是增加,疫情前儿少占就诊人数三成,疫情以来占到五成以上。
我在王瑜的门诊观察了两个暑假,见到了无数身心出问题,厌学、休学在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在住宿制中学上学,离开父母的不适还没缓解又遇到激烈竞争或校园霸凌;有的孩子家庭期待过高,父母一路推动,报了各种提高班,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进入了重点高中,可学着学着忽然没动力了;有的孩子疫情期间上网课,学习不够自律、效果不佳,网课结束回到学校突然发现原本的学霸变成了学渣,情绪顿时崩溃。有的孩子一进学校就紧张、害怕,手脚不听使唤;有的孩子一焦虑就拔头发,摘下帽子便可看到裸露的头皮。有的孩子根本不愿或没法去学校,在精神科医生这里拿到诊断后就去学校办理休学手续,家长也在孩子出现状况后一改往日态度,“学习的事不管了,我们现在也想开了”。也有孩子休学一年半载后情绪稳定下来,拿到诊断证明后打算办理复学手续,家长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才开学不能马上减药、停药”的医嘱仍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失去学习兴趣或者不适应主流教育体系的孩子或许很难靠吃药调整多巴胺、内啡肽之类来恢复动力。王瑜说,最初她开设儿童青少年特需门诊时,每位就诊者每次至少得看一个多小时,一下午看六个人都要九点半才能回到家。在那个时候,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儿童青少年的问题,她觉得非常棘手,必须花很长时间和他们交流。“在我读书期间,没有厌学、冲动、频繁严重自伤等问题,时代的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儿童青少年问题已经不是我们以往学的知识所能解释了”。如今,看多了让人感到忧伤与无奈的个案,再看到有家长不顾一切的催促普通孩子奋力追求一个不是那么可行的目标,或是看到家长不假思索不讲方法地压制青春期孩子臭美打扮谈恋爱时,王瑜会忍不住说“等他厌学不读躺倒了你就真麻烦了”。
青少年情绪不止是医学问题
一位长期带孩子就诊的母亲在孩子出现精神问题后自学了精神科最大部头的教科书,当王瑜和她说“你太负责任了,太不容易了”时,这位一直以来表现得都非常坚强的母亲瞬间泪如雨下。外人或许可以想象孩子的苦痛、母亲的付出,但现实总会超出想象,诊室里呈现出来的永远只是定格在某一时刻的苦痛。
走近门诊不难发现精神苦痛的折磨真实存在。不过,《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列出的数以百计的精神障碍类别虽然可以概括不同个体所承受的精神苦痛的某些共性,但引起每个人精神苦痛的生活脉络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也不一样。这自然意味着如上文那样单纯描写医生如何看“病”将难以完整描摹精神健康、精神医学的复杂世界。反过来讲,缺少医生视角的叙事也不完整。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在列出各种障碍类别后还有一章,描述的是“可能成为临床关注焦点的其他状况”,其中涉及家庭教养、亲子关系、学习成绩不良等生活问题。《诊断手册》没有将该章所列内容视为精神障碍,但指出这些问题可能影响患者的诊断、病程与预后,临床实践应该关注。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诊断手册》所列这些内容无疑具有提醒医生重视引起精神苦痛的生活事件的作用。但站在反思生物精神医学的 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又可从中瞥见一点儿精神医学的知识范畴向日常生活扩张,甚至取代生活逻辑的医学化倾向。不难设想,倘若全社会接受、认为青少年厌学、自伤、违抗对立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情绪表达是且只是医学问题,只要辨识出某种“疾病”然后加以药物治疗就能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原本所具有的社会、文化、道德等复杂内涵就很有可能会被忽视。
当然,《诊断手册》甚至精神医学本身都不可能是推动医学化发生的唯一引擎,诊室里医生对就诊者的关切与救助更是真切、实在。我们在此无法对医学化这一复杂问题展开讨论,而医疗资源有限的社会现实实际上还会让讨论加倍复杂。但无论如何,精神医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值得思考。
原标题:《我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有病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