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斜杠青年高罗佩和宝藏男孩狄仁杰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末尾,大白猿载着法师从天而降,并肩赵又廷与封魔族鏖战正酣,本是生死一线,我却乐出了声,因为无法克制地想起高罗佩与其爱猿的经典合照:它伏在他的肩头,他拽着它的小手。毕竟某次和好友喝了点小酒,高罗佩喃喃自语过“狄公就是我”,《长臂猿考》又恰好是他最后一本汉学著作。若天堂有知,徐老怪安排了这场戏,他大概会直呼过瘾,抚琴一曲又黯然神伤:“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1942年,高罗佩于荷兰驻日本大使馆供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荷交战,他被迫撤离,于是挑选了一些中国小说打发路途时光,其中就有石印本的《武则天四大奇案》。
这是一部六十四回的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可考,现存最早的版本来自19世纪晚期,前三十回是昌平县令狄仁杰破获三起同时发生却毫无瓜葛的命案故事,后半部分则着重武后是如何在狄仁杰压力之下还政李唐的,大致以狄仁杰的政治仕途为主线。
彼时的中国通俗小说,已走过了西方侦探文学的译介浪潮,试图摆脱传统公案的樊篱,呈现出与西方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日本文人却多做我们现在做的事,致力于收集他国,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戏剧和通俗小说,并将它们根据日本读者的口味加以改变、出版。
为了向中日读者表明,“古代中国的犯罪文学”比当时上海和东京书摊上的侦探译作高明许多,在华盛顿安顿下来的高罗佩,着手将《武则天四大奇案》前三十回译成英语。1949年,译本《狄公案:三起狄公解决的杀人事件》(Dee Goong An: Three Murder Cases Solved by Judge Dee)由他于日本自费出版,6个月内抢销一空。
高罗佩得到了鼓舞,于是建议本土侦探小说家们尝试此类作品,传统公案小说也不致于遗忘。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他决心用英语自己写下去。通常情况是,他在休息时间酝酿好故事情节和人物,画出脑海浮现的城市地图,构思初步的地理轮廓。一旦动笔,六周左右就可以完成一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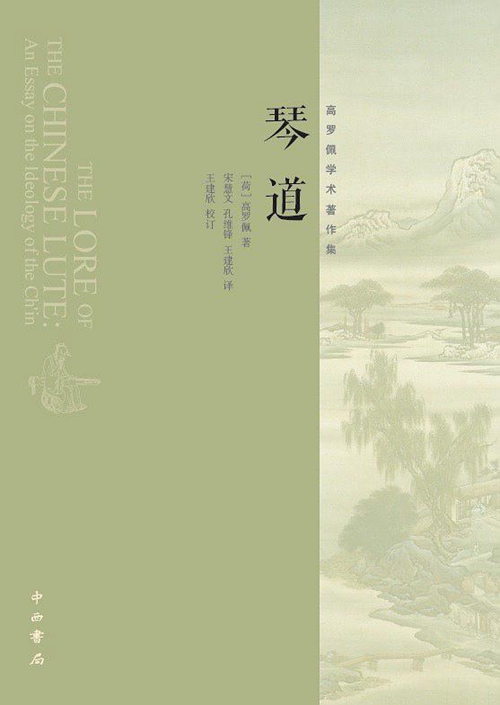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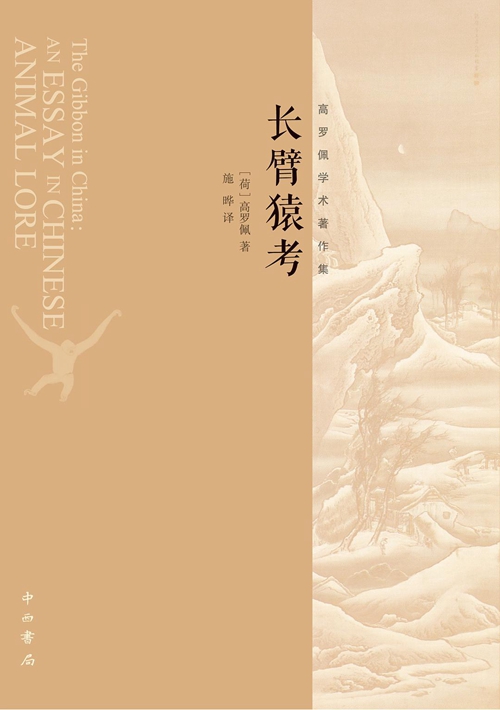
所以才能共生出狄仁杰这般“宝藏男孩”吧:“执法如山却不拘泥古板,睿智机敏却不矫饰,敢冒风险却不蛮干,嫉恶如仇而又心怀恻隐,喜欢女人而不失风度,诙谐幽默而不失威严,精通文墨又谙武功。”
何况,高罗佩还有一种能力,永远热情开放,从不同的物事上攒获养分,编织想象力的罗网,灵感就不会困顿。《湖滨案》中内藏玄机的围棋残局,来自他的学术研究对象;书房里的明代屏风为《四漆屏》提供了母题;《迷宫案》的迷宫本质上,是《香印图考》的一幅插图。“狄公”在这些枝蔓里蓄力生长,大唐便溶在诗里,月里,也在残忍,和高深莫测里。
其实,史料中的狄仁杰不见得无趣。早年明经及第,文采一定是有的;曾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追讨突厥,武功大约也是有的;值大理寺时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且无冤诉,任刺史不夺农时,为生民立命,业绩与情怀他统统不缺。耿直是面子也是里子,但同时,他也有不争气的儿子,看不顺眼的同事,和自以为是的上级。
《朝野佥载》就录过一则逸闻,说某天刑部侍郎狄仁杰和刑部侍郎卢献嘴仗,狄仁杰先开炮:“足下配马乃作驴。”卢献哪能示弱:“中辟明公,乃成二犬。”狄仁杰旋而自喜:“狄字犬傍火也。”卢献折枝为剑:“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说不定还附赠了一个白眼。
这很像后世纪晓岚、和珅间“尚书是狗”的段子了。《朝野佥载》确实多为坊间笑谈,也许不足为信。而同为笔记小说,《大唐新语》的一条记载倒是得到了司马光的盖章认可,收录进了《资治通鉴》。
武则天发现狄仁杰总爱排挤同班宰相娄师德,于是问他:“师德贤明吗?”答:“他做将领时恪尽职守,贤明不贤明臣不知道。”又问:“师德知人善用吗?”答:“臣和他同朝为官,并未听闻他知人善用。”武则天停了很久,慢幽幽地说:“其实当初是娄师德荐你入相,爱卿你说他是知人还是不知呢?”
狄仁杰瞬间石化吧,反正他的尴尬都快溢出书页了。而在《唐语林》记载的另一版本里,武则天问他是否清楚自己为何得以重用,狄仁杰显得更加自负:“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嗯,摔得很惨没错了。
大致宋话本《梁公九谏》以后,狄仁杰便在民间记忆中稳扎稳打下来。先是反武周复李唐的功绩深入人心,明清白话小说时,演变为惩恶扬善的“青天”形象。而狄公与包公的成名之路有区别,一是因为,他先前在大理寺多主持案头工作,复审地方司法案件,实判的机会并不多;二是士人对官员的道德诉求往往高于业务要求,可以有脾气,使手段,但政治立场一定不能站错。
《旧唐书》里说,武卫将军误伤了皇陵的一棵柏树,唐高宗坚持将其问斩,狄仁杰便上奏:“人们都说犯言直谏很难,我却不以为然。桀纣时是很难,但尧舜时就很容易了。”又,武后时政治高压,狄仁杰遭诬下狱,他一面以头触柱,拒绝同流合污,一面撕下小块被面书冤,假意替换棉衣请家人带走。后来,狄仁杰出狱,他自己和他举荐的一批臣子,继续重用,继续在匡扶李唐的道路上浓墨重彩。
“功成身退”是中国士人心里的一抹白月光。因为他们实际像风筝,能走多远,在人主的一念之间。于是,他们偏爱辗转腾挪的机智,以及君臣良性互动的秩序感。
随着狄仁杰脱模为“青天大老爷”,同时出炉的,还有民间的集体寄托。惩恶扬善,意味着秩序即使被打乱也可以恢复,生活或许是简单的,是千头万绪的,但最后一定要是安宁的。
所以,狄仁杰的存在既合乎道德,又合乎实际,君爱臣、臣忠君、官爱民,是士人和民间在其形象上可以截获的能量。只是,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向来密切,历史书写到底是种评价体系,加上中国史传文学传统,文人不自觉地倾向春秋笔法,追求近似实录的写作效果。却往往忽视了,形象历经层累,却仍是当下的产物,即便有个人道德之长,仍无法补救制度建设之短。
再看当年高罗佩只翻译《武则天四大奇案》前三十回的决定,倒不难觉察背后观念的差异。东方语境下,人伦道德秩序最高,政治法律秩序最低,调转到西方正好相反。高罗佩对狄公的忠君形象并不感冒,所以删去了原书中政治斗争的内容。
无论在新德里、海牙还是吉隆坡,高罗佩描摹他的狄公孜孜不倦,至少写了十七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相信善能够战胜恶,公平能够战胜黑暗。他似乎是个老派的人,身居庙堂,也有颗江湖儿女心。
实际,高罗佩只有1950年至1958年间的五部作品,比较接近中国公案小说的原貌。其余大多符合西方侦探小说的标准,除了那条“不准有中国人出现在故事里”。案件常为一些神秘氛围笼罩,但出场人物有限,不相干的细枝末节很少,以狄仁杰的分析推理和实际调查发现真相,罪犯身份最后才会揭晓。
诚然,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文学有很多脉搏互通的地方,《狄公案》中典狱、刑律大多有历史依据,不少司法问题都符合《唐律疏议》,小说内容和插图也在后记中尽可能做了考证,虽然不少物质文化是仿照明代设定的。
但西方侦探重个性,中国判官自带官方背景,对人物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极少。准确说,狄仁杰不能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顶多算“雷垂斯特·狄”吧。古代中国,口供比推理重要,判官更依赖五听和刑讯:先要判断嫌疑人说话是否语无伦次、面红耳赤、理亏气喘,是否紧张到听觉失灵、眼神躲闪,口供验证“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
所以,清官同时也可能是酷吏。往往历史真相,就是不会那么好看。而《太平广记》中,湖州别驾苏无名单凭“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墓无伤也”就破获太平公主的珠宝失窃案,大概是最接近推理断案的一次了。
无论如何,从新旧《唐书》到《武则天四大奇案》,狄公形象完成了由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嬗变,而洋溢着中国情调的《狄公案》,则暗示了小说旨趣由说教偏向娱乐。
西方对这套书有多爱不释手呢?据说当时荷兰外交官人手一本,美国国务院也曾规定,到中国任职的美方工作人员,都要阅读高罗佩的小说,加深对中国人的了解。
好在八十年代初,还是研究生的赵毅衡偶然读到了狄公案系列,便委托同学胡明和其友人陈来元翻译出来。2006年,《大唐狄公案》由海南出版社刊印发行,收录了全部故事,并按狄公的任职时间排列。在尊重高罗佩原文的基础上,尽力模仿宋元白话风格,采用古典小说中的习语;为了将所有故事串联成完整,删去了原先叙述者由明朝穿越到唐朝的入话内容,和部分章节的对仗标题;省略了一些政治敏感话题,过于残忍和色情的描摹;增添了一些人物的道德评价。“译作虽来源于原作,但与其说它来自于原作的生命,倒不如说来自于其来世的生命。”
万岁通天元年(696),狄仁杰为魏州刺史,百姓为感谢他勤政爱民,特设生祠,也是祈祷他百年之后,依然能够庇护地方。时过境迁,大概狄仁杰自己也不曾料到,他会始终以英雄的姿态,留在民间想象中。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